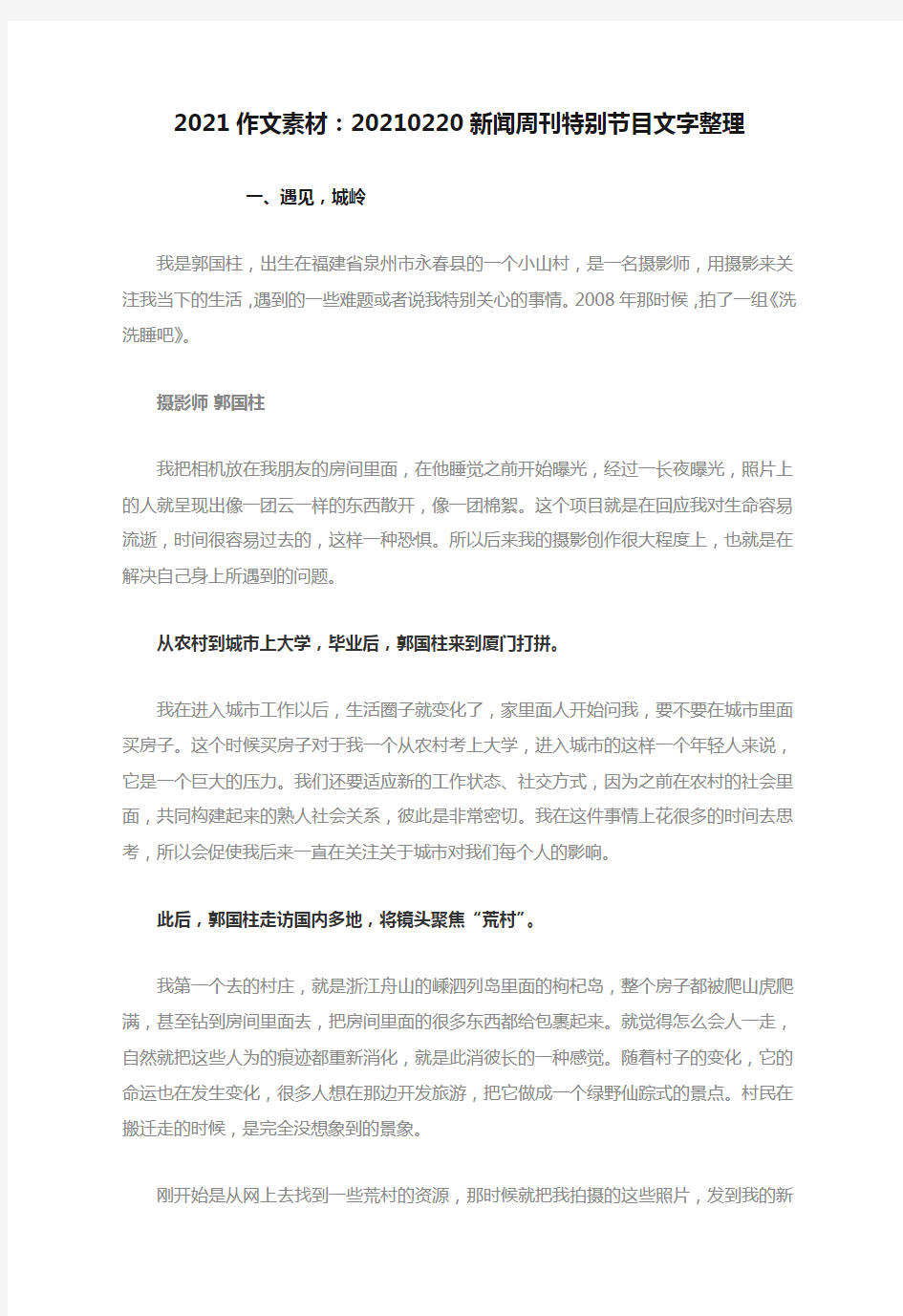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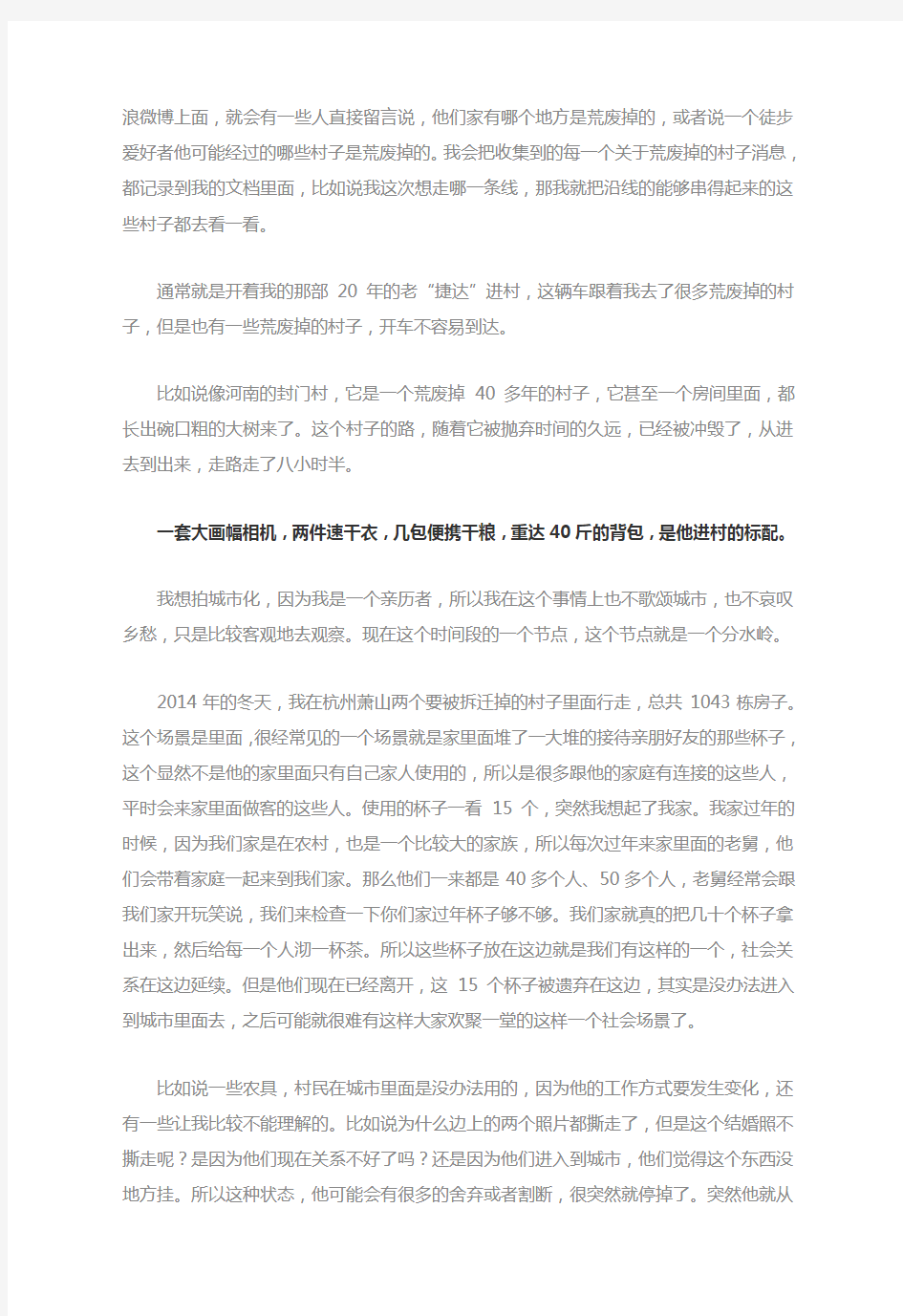
2021作文素材:20210220新闻周刊特别节目文字整理
一、遇见,城岭
我是郭国柱,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的一个小山村,是一名摄影师,用摄影来关注我当下的生活,遇到的一些难题或者说我特别关心的事情。2008年那时候,拍了一组《洗洗睡吧》。
摄影师郭国柱
我把相机放在我朋友的房间里面,在他睡觉之前开始曝光,经过一长夜曝光,照片上的人就呈现出像一团云一样的东西散开,像一团棉絮。这个项目就是在回应我对生命容易流逝,时间很容易过去的,这样一种恐惧。所以后来我的摄影创作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在解决自己身上所遇到的问题。
从农村到城市上大学,毕业后,郭国柱来到厦门打拼。
我在进入城市工作以后,生活圈子就变化了,家里面人开始问我,要不要在城市里面买房子。这个时候买房子对于我一个从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城市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我们还要适应新的工作状态、社交方式,因为之前在农村的社会里面,共同构建起来的熟人社会关系,彼此是非常密切。我在这件事情上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所以会促使我后来一直在关注关于城市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
此后,郭国柱走访国内多地,将镜头聚焦“荒村”。
我第一个去的村庄,就是浙江舟山的嵊泗列岛里面的枸杞岛,整个房子都被爬山虎爬满,甚至钻到房间里面去,把房间里面的很多东西都给包裹起来。就觉得怎么会人一走,自然就把这些人为的痕迹都重新消化,就是此消彼长的一种感觉。随着村子的变化,它的命运也在发生变化,很多人想在那边开发旅游,把它做成一个绿野仙踪式的景点。村民在搬迁走的时候,是完全没想象到的景象。
刚开始是从网上去找到一些荒村的资源,那时候就把我拍摄的这些照片,发到我的新浪微博上面,就会有一些人直接留言说,他们家有哪个地方是荒废掉的,或者说一个徒步爱好者他可能经过的哪些村子是荒废掉的。我会把收集到的每一个关于荒废掉的村子消息,都记
录到我的文档里面,比如说我这次想走哪一条线,那我就把沿线的能够串得起来的这些村子都去看一看。
通常就是开着我的那部20年的老“捷达”进村,这辆车跟着我去了很多荒废掉的村子,但是也有一些荒废掉的村子,开车不容易到达。
比如说像河南的封门村,它是一个荒废掉40多年的村子,它甚至一个房间里面,都长出碗口粗的大树来了。这个村子的路,随着它被抛弃时间的久远,已经被冲毁了,从进去到出来,走路走了八小时半。
一套大画幅相机,两件速干衣,几包便携干粮,重达40斤的背包,是他进村的标配。
我想拍城市化,因为我是一个亲历者,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也不歌颂城市,也不哀叹乡愁,只是比较客观地去观察。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一个分水岭。
2014年的冬天,我在杭州萧山两个要被拆迁掉的村子里面行走,总共1043栋房子。这个场景是里面,很经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家里面堆了一大堆的接待亲朋好友的那些杯子,这个显然不是他的家里面只有自己家人使用的,所以是很多跟他的家庭有连接的这些人,平时会来家里面做客的这些人。使用的杯子一看15个,突然我想起了我家。我家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在农村,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所以每次过年来家里面的老舅,他们会带着家庭一起来到我们家。那么他们一来都是40多个人、50多个人,老舅经常会跟我们家开玩笑说,我们来检查一下你们家过年杯子够不够。我们家就真的把几十个杯子拿出来,然后给每一个人沏一杯茶。所以这些杯子放在这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关系在这边延续。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这15个杯子被遗弃在这边,其实是没办法进入到城市里面去,之后可能就很难有这样大家欢聚一堂的这样一个社会场景了。
比如说一些农具,村民在城市里面是没办法用的,因为他的工作方式要发生变化,还有一些让我比较不能理解的。比如说为什么边上的两个照片都撕走了,但是这个结婚照不撕走呢?是因为他们现在关系不好了吗?还是因为他们进入到城市,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没地方挂。所以这种状态,他可能会有很多的舍弃或者割断,很突然就停掉了。突然他就从一个农村人,变成一个城市人了,所以那种割断感可能跟我们情感是不太一样的。
在农村的建筑里面,都有这么一个空间,有些地方叫前厅,有些叫堂前间,它是农村的一个很广泛的会客厅,它除了维持熟人社会关系,还承担生活礼仪、对外关系。主人会把这
个家庭想对外展示的一些东西都放在这个空间,这个在农村的熟人社会关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2014年底的时候,当时我被这个空间吸引,就是因为墙上贴了满满一墙奖状,数了一下有24张。看她是从2004年开始,到2014年,有三好学生,有她文体竞赛的那些相关的奖状,见证了一个女孩她的成长史。在拍摄的时候,正好他们家的主人进来了,他眉飞色舞地跟我说,这个是他的孙女,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因为她的这个孙女,他觉得他在这个村子里面的社会地位都觉得高了一等。所以正好也是这个空间所承载的乡村里面的,这种人情往来、宗族伦理。这个空间在城市的建筑里面是不会有的,因为城市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卧室也好,我们的客厅也好,都是相对私密的。
2020年11月1日,根据网友线索,郭国柱寻找福建湖坪自然村。
是一个特别小的自然村,因为被遗弃的时间比较久了以后,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地名,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知道这个村子是因为这个村子里面移出来的一个年轻人告诉我的,这个村子原先住着一个家族的人,他们现在整个家族都往外搬迁了。当到那个村子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让我惊讶的景象,这个荒废掉的村子里面,居然建了一栋大大的别墅。这栋大别墅住着一个大约六十多岁的人,他的孩子回来,为他建了这样一个房子,就是让他方便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他不太适应城市的生活,但是住在这个村子里面其实他也是很孤单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搬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住在里面。
在郭国柱的镜头里,因不适应城镇生活而返回乡村的面孔并不少见。
2020年6月份的时候,我进入到陕西榆林的一个小乡村。是一个很贫瘠的一个乡村。它这个乡村里面的人以前就是放羊,他现在搬到城镇住的时候,他发现他没办法在城镇里面放羊。他现在的生活就是,白天从城镇里面雇一辆农用车,把羊运到他原先住的那个村子里面去放羊,然后到了晚上又雇一辆农用车把羊给拉回来。
2020年11月22日,郭国柱跟随提供线索的陈家人,来到广东普宁白马村。
线索提供人陈锡明
现在退休了,准备过一两年也要回家里来住,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想回来。因为我们感觉这里山清水秀,还有那个空气特别好,还有很安静,没有城市那么喧哗,叫叶落归根
吧。子女都长大了,他们在外面工作,我们老人一般都是想回到家乡来住,感觉就是想让晚年清静一点。
线索提供人陈爽
我这次其实有在想,就是为什么我爷爷从他那一辈,他就要从这个村子走出去,但是到我爸爸这一辈到我们这一辈,为什么我们还回来。我就想,感觉还是就是寻根,因为我觉得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好像是没有根的,他跟土地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但是我每次回到村里面会有一种情感上,就是好像一条线冥冥中牵引着你跟这个村落。开始我可能是一个很被动的状态,就是大人们说每一年,今年我们要去拜一拜,要去祭祀了,那我就跟着回来了,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要回去看一下。就好像是一定要去找到一些自己跟这片土地的关系,太陌生了。
摄影师郭国柱
在2014年的时候,我农村的这个家,因为时间太久了太破了,变成了一个危房,那时候在城市里面,我是买不起房的,那只能决定把这个危房重新修缮一下。我的女儿当时大约是3岁我就说,筱瑾,你会不会喜欢回到农村来呢?她说,爸爸我是厦门人,因为我是在厦门出生的,山里面太破了,我不想回去。然后我那时候想,我如果把这个农村的房子建好了,她又不想回来,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房子建设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些互动,我们在海边捡贝壳,踩到我们家的地板里面。我的小孩看到她在海边捡的贝壳,在这个家里面出现了,这个就勾起了她很大的兴趣。所以她现在就非常愿意回来,倒不是我非得强迫她一定要喜欢上乡村,但是我觉得在她的身上有这个方面的血液在流淌的话,我觉得她的选择会更加开阔,她会更加客观去观察和思考这件事情。
一路上见到的人拍过的村庄,让郭国柱对城乡生活的选择,有了更多思考。
摄影师郭国柱
每个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他可能有不同的困境,他的困境可能是他的一个社会关系的转变,有可能是房价,有可能是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或者就业的方式。比如说他在城市里面
务工,但是经过了一代人、两代人他也没有生活得很好,他乡下的这个房子也凋零了,然后他的技能又是城市里面务工的那套技能,所以他就更加难以回到乡村去了。再回到乡村的时候他可能又丧失了在乡村里面谋生的能力,所以对于他来说又是更加困惑了。可能并没办法让他对城市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他们有的人能够解决,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需要逾越的一个“岭”,或者说也是现在大时代背景下面的一个“分水岭”。
拍摄荒村至今,郭国柱的足迹遍布国内18个省(区市)142个村。
我把经纬度写在这个底片上,因为时间久了以后,这个村子的名字可能会被大家所遗忘,村子的名字可能会在地图上消失,只有经纬度它是没有变化的。
二、遇见,菜市场
何志森
2018年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我来到扉美术馆做馆长。这个美术馆的旁边是一个菜市场,就这样的一个契机,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有这样的一个菜市场改造课程。我就想把这个目光锁定在,我们美术馆旁边的农林菜市场。
何志森担任馆长的扉美术馆,是一座位于广州闹市区里的小型美术馆,美术馆拥有一排亮眼的艺术墙,而墙的另一面是一座存在了近四十年的菜市场。何志森和学生们一直希望为一墙之隔的菜市场做点什么。
刚进菜市场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一件事情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没想到特别特别难,因为摊贩根本不接受我们。摊主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奇怪的群体,他们是从来没有交流的一些人,非常熟悉的陌生人,这个是我非常吃惊的,在一个地方工作30多年的同事,竟然不知道彼此的名字。
东山口农林肉菜市场不大不小,四排摊档,为周边的街坊们保障着一日三餐。何志森的出现,给互相之间鲜有交流的摊贩带来了改变。
我不希望说一进来就开始改造他的空间。所以我是想让学生跟摊主工作一个月,才能知道摊贩真正需要是什么。
摊主开始跟学生去聊他们很多的故事,我们把所有的故事搜集起来,我们特别惊讶的发现,他们聊所有的故事几乎跟他们的手都有关系。每一个摊主都通过诉说他的手来去诉说他们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比如说有一个摊主他其实不识字,所以他每一次把数字写在手上,每一次照一个相发给他的小孩儿,说这是500块,你帮我加一下今天的营业额是多少。所以他通过手这个媒介,通过跟他小孩的交流去打理这个生意。
我记得有一个是卖鸡蛋的人手全是茧,如果你摸鸡蛋摸30年,你的手上都会是茧。这些东西我们从来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平滑的鸡蛋,会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难以抹掉的一些伤疤。
其实我们来到菜市场永远不会关心他们的手,我们只关心手上的菜,它们的价格,新鲜不新鲜,其实我们是忽略了他们的手,也就是说他们的手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以手为生。
44双手的照片在美术馆展出后,便有档主提出,要把自己的照片挂到菜市场的档口,出乎何志森的意料,因为手,菜市场悄然发生着改变。
豆腐档主祁红艳
顾客就会问我,这么好看谁给你做的啊,我说是一个老师给做的,会发现很微妙的,会跟我聊话题,我们跟顾客之前沟通也就越来越多。
了解了档主的不同诉求,2019年,何志森决定带领学生,对菜市场进行微改造,这一次,他想让档主能工作得更为便利。
何志森
一个卖蔬菜的西安人叫阿正。我们跟阿正聊天的时候,其实阿正的需求特别简单,他特别容易出汗,他说能不能有一个窗可以把他的衣服晾干。其实这一扇窗打开的时候特别魔幻,就是你从美术馆这么一个干净、漂亮的一个空间,突然把混凝土打开的时候,你看到是一个完全,非常有不一样冲突的场景。一阵猪肉的味道,就是菜市场的味道迎面扑过来。
一扇窗,不仅打开了实用的通风口,更打破了美术馆和菜市场之间心理间隔。
再见,菜市场
2020年9月,一则拆迁通告让摊主们始料未及。
何志森
应该先是菜市场的管理方先发出一个通告,菜市场在一个月之后无条件拆除。因为本来这个菜市场其实它是一个违建的菜市场,所有人都知道,它违建了39年,它是占道经营。刚好它是在一个河涌的上面,所以这次拆迁,其实它也是以要把河涌复原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拆,一个理由来拆菜市场。
阿正,选择离开奋斗多年的广州,回到老家西安,其他摊主也不得不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农林菜市场。按照规划,这座在地下河道上建起来的农林菜市场,将要永久性拆除。
何志森
毕竟菜市场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像一个家。虽然这个家在过去的三年,过去的两三年,其实他们经历了一次改变。应该就是他们刚刚有了一个归属感,他们刚刚有了一个家的感觉,我觉得就30多年来,因为这三年大家开始相互认识了,这个时候突然说要解散了。
东山口老居民陈国明
好像现在这么一拆,居民也挺舍不得的,加上之后我们买菜也很不方便。我在这里买排骨,我说我要一条她就砍一条给我,但是去超市,它都扎得好好的,你就没办法啦,你就只好拿一包,再一个方面,超市始终没有这种气氛,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气氛。
豆腐档主祁红艳
2006年那一年到这里开档,刚进来的时候生意也很好的,生计也舍不得,还舍不得在这里生活就是说跟这里的人的情感吧,对这个市场的留念吧。
蔬菜档主吴玉珠
因为我在这里这么多年,散伙了以后都碰不到了,发两个橘子,大家都吉利,大家去外面也吉利。
何志森
当他们面临一个菜市场要拆掉的时候,他们是没得选择的。要不就去另外一个菜市场,但是去另外一个菜市场面临一个困难,就是他们的顾客群。二三十年这些顾客、街坊没有了,他们迎来了新的客户群,其实对他们打击是蛮大的。他们是靠熟人去维系他们的生意,这个很重要。
“重见”,菜市场
豆腐档主祁红艳
我是安徽的,我16岁就来广州打工,我在广州,反反复复,辗转很多地方帮人家卖豆腐。1992年吧。那个时候90块钱一个月的时候,一年才挣1000多。当时对我家庭来说,真的是可以说很大的帮助。
来广州打拼了24年的祁红艳,靠着一个豆腐档在这座城市立足,先后把女儿和儿子抚养长大。当市场拆除后,再度怀孕的她,选择在离农林市场不远的店铺门口,租下了一个拐角,继续经营。
豆腐档主祁红艳
我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要很早起来,我是5点钟起床,然后来到这市场这里,先把就是说早上很多来赶早集的人要买的东西,我知道他们习惯买哪一个东西,要早嘛,所以我会把那些东西先摆出来。大概摆到,我看时间差不多,大概6点半的时候我就会回去做早餐,做早餐叫我儿子起床。
豆腐档主祁红艳
叫他起了床我才又要赶着回去,什么东西给他一切都做好,然后把车子给他开好,放在那里,衣服晚上我都给他找好,放在那里的。然后把他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之后,我就会又继续出来开我的档。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从小经过那种很艰苦的环境,我知道生活不易,我就想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会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优越的环境,让他们在那种好的环境中去成长。
在这条小小的街道上,一头是已经被拆除的菜市场废墟,另一头则散落着不愿离去的档主们,他们仍然选择在最靠近菜市场原址的地方,等候老主顾。但并不是每个档主都像祁红
艳一样,能够再租一个摊位,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选择送货上门,通过线上下单,再逐一亲自配送,继续维系着熟客。
临近中午,奔走在东山口街巷间的档主们基本送完了货,这时候,卖鸡肉的郑爱萍来到了祁红艳的豆腐档口,为了让怀孕的祁红艳能回家睡个午觉,市场拆除后,便有档主主动来给祁红艳换班,替她照看中午的生意。
豆腐档主祁红艳
我觉得有这次身孕,压力很大的,但是就是他们这些摊主,各个都帮我,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关怀着我,他们对我太好了,真的,他们对我太好了。
何志森
在菜市场拆迁之后他们没有离开,反而抱团取暖,相互照顾对方。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菜市场到底有没有“死”,到底有没有消失?它的实体空间是消失了,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其实没有因为菜市场的消失而消失,它反而延续到城市的不同角落。
何志森
2020年的冬至,其实这个冬至,应该是美术馆应该发起一个百家宴,因为旁边是他们的菜市场已经变成了废墟,他们觉得很难受,不想过去了,说可不可以转移到家里来做一次聚会,这是第一次聚会,菜市场拆迁之后的第一次聚会。
何志森
很多摊主过来,你可以看得到大家其实还是心事重重的,因为大家都没有工作,没有着落,很多人还在街头工作,所以都还是跟之前的状态还是不一样,都很累。大家很安静,所以我觉得这种能量也是我一直想去消化的。这种能量,这种普通人,平凡人的能量,去消化的。
何志森
我觉得他们都很难离开东山口,30多年,其实他们跟东山口的关系非常强了,他们离不开那里,离不开那里的人,所以很多人舍不得离开。
豆腐档主祁红艳
我就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场所,大家都有生存,大家都经过这次,更珍惜。
何志森
菜市场这个项目,其实我是把这些特别普通的,从来不被建筑师关注,不被城市管理者关注的,这群人的故事呈现出来,让所有人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都有故事,当你在做城市改造的时候,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其实能不能从人的出发点开始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