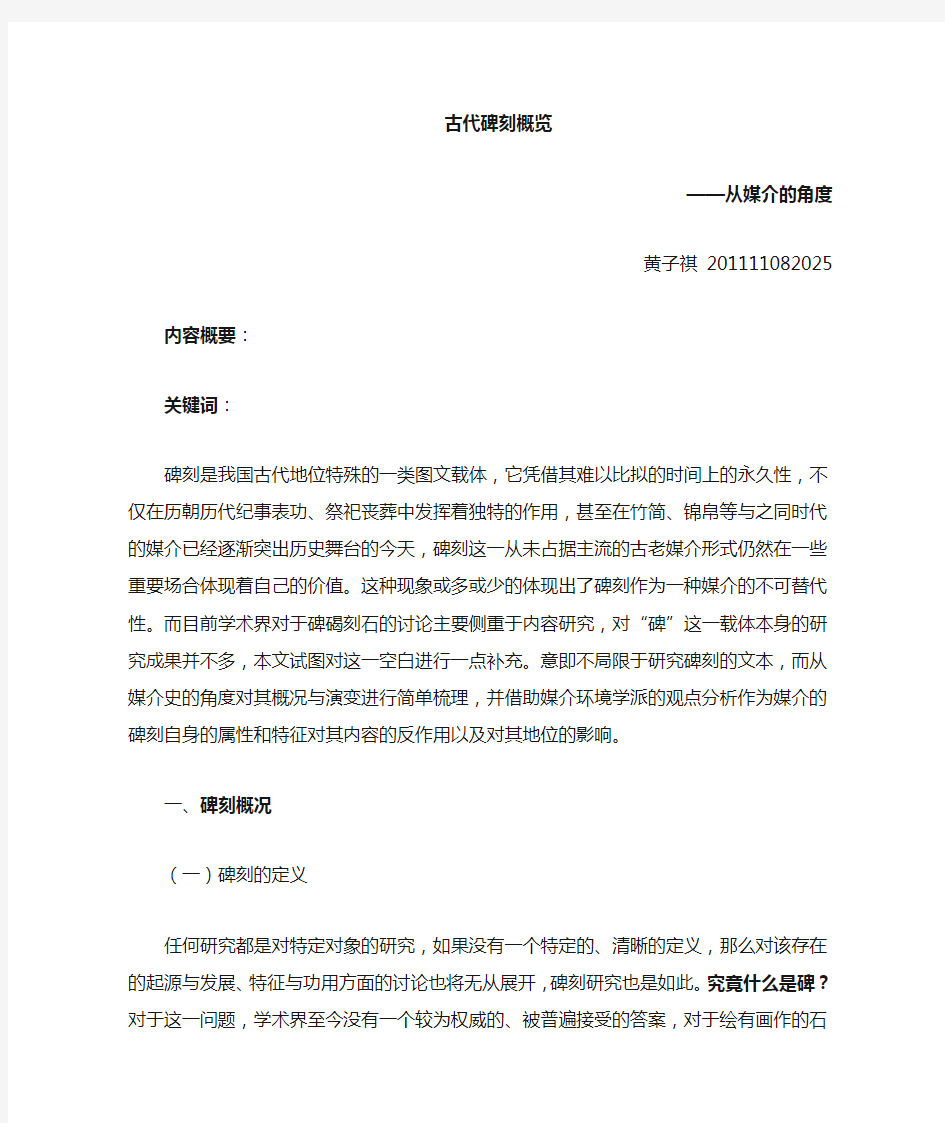

古代碑刻概览
——从媒介的角度
黄子祺201111082025 内容概要:
关键词:
碑刻是我国古代地位特殊的一类图文载体,它凭借其难以比拟的时间上的永久性,不仅在历朝历代纪事表功、祭祀丧葬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甚至在竹简、锦帛等与之同时代的媒介已经逐渐突出历史舞台的今天,碑刻这一从未占据主流的古老媒介形式仍然在一些重要场合体现着自己的价值。这种现象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了碑刻作为一种媒介的不可替代性。而目前学术界对于碑碣刻石的讨论主要侧重于内容研究,对“碑”这一载体本身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试图对这一空白进行一点补充。意即不局限于研究碑刻的文本,而从媒介史的角度对其概况与演变进行简单梳理,并借助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分析作为媒介的碑刻自身的属性和特征对其内容的反作用以及对其地位的影响。
一、碑刻概况
(一)碑刻的定义
任何研究都是对特定对象的研究,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清晰的定义,那么对该存在的起源与发展、特征与功用方面的讨论也将无从展开,碑刻研究也是如此。究竟什么是碑?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较为权威的、被普遍接受的答案,对于绘有画作的石头、摩崖、不规则刻石等是否属于碑的范畴也存在见仁见智的意见。在这里我们首先梳理几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碑”,按《说文解字》的解释,“碑,竖石也”,段玉裁的注文就此补充说“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后此凡刻石皆曰碑矣……凡刻石必先立石,故知竖石者,碑之本义”,《辞源》的解释也与此类似,其“石刻”条区中“碑”的说法是“长方形立石”,由此可见古代对这一概念大多采取了从形制上加以定义的方式;而《新华字典》(第十版)将其解释为“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这一释义则更多的是从内容和功用的角度出发的。“碣”是与之类似的概念,《新华字典》解释为“圆顶的石碑”、在《辞源》中则为“刻字的圆首、上小下大的石头”,由此可见碣是碑的一类。“摩崖”是又一经常与之相提并论的事物,指“在山崖上刻的文字、佛像等”(《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由此,可以作这样的总结,学术视野中,狭义的碑是“刻有文字的、经过精心磨制加工、有一定规格尺寸的长方形立石”,广义的碑是刻以文字的石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叶昌炽《语石》)。
如前文所言,本文试图从媒介的角度对碑刻进行研究,因此,恰切的定义应最大限度的将对象与其它媒介区分开来,以便讨论它独有的属性及其影响。基于这一出发点,笔者试图这样定义本文中所要使用的“碑”的范畴:就材质而言,它应当是石头(或其他具有坚固性、耐久性的材质,如金属);就手法而言,采用雕刻的方式表现内容;就功能而言,被用于表达、传承某种特定的信息和意义(这种定义包括了“无字碑”等特殊的碑刻),至于其形状、大小、位置等次要方面不影响到作为媒介的碑刻的传播效果,因此在此不作为定义的一部分。(二)碑刻起源
将石头作为记录信息的载体的历史不可谓不悠久。石头是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物质,又加之其具有坚固、耐久的特征,是最早被人类利用的自然物之一。早在四万年前,史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在岩壁上作画,其历史远远早于文字的产生。岩画与碑刻虽然形式与内容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是本质上都是以具有时间上永久性的石质材料作为内容载体的创作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岩画是碑刻的起源之一。
随着人类搬出洞穴、建造城市,石头作为媒介出现了相当长的消沉期,取而代之的是甲骨和青铜器。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一步发展,值得记载并流传后世之事逐渐增多,新兴贵族对彰显功勋的热衷也越发旺盛,这两种载体因为数量有限而较为贵重不在适应记录的需要,石头因具有同样的时间上的长久保存性而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记事与颂德的新一代载体,人们开始“以石代金,同乎不朽也”。发现于1974年的东周中山国河光刻石便是一例,其篆字书法古拙具有铭文的特点,体现了从青铜载体到石质载体的迁移;著名的石鼓也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记录了东周时期秦国国君出行游猎之事,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帝王记事刻石。
作为一个词语的“碑”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存在,只不过其性质和功能迥异于后世。其一,时间的测度工具。《仪礼·聘礼》记载“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对此郑玄的注文中解释道“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也就是说,碑竖立在宫廷院落之内,作为投射太阳的影子来推算时间的工具。其二,系牲畜的固定物。《礼记·祭义》记载“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也就是说碑也被用作祭祀场合用来系绑牺牲用品的桩子。其三,墓穴四角牵引绳索的工具。《礼记·檀弓下》记载“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的注释解释道“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竖之,穿中,于间为鹿卢(辘轳)也”,也就是说碑被用来牵引绳索,将棺椁下放到墓穴中。这种较大的最终被不易腐坏的石头所取代并刻上死者生平,成为墓碑的雏形。
在战国末期及秦朝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碑”开始形成。一方面,被称为碑的竖石开始出现文字,具有了记事的效用;另一方面刻石的形制发生变化和发展,如泰山刻石“高三丈一尺,广三尺(《晋太康地记》)”,琅邪台刻石“高一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顶宽二尺三寸,厚二尺五寸(《山左金石志》)”,这表明秦石的刻石已经不同于直接在山崖石壁上雕刻,而是出现了人工雕磨的一定形制,是正在进化的碑。到了西汉,语用上的“碑”最终形成,这个词汇开始被用于描述刻石,原本的意义逐渐失落了。
(三)碑刻发展概况
碑刻,像其他任意一种媒介一样,其发展演进的历程都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政治局面的清明与统一与否、文化的繁荣程度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影响着碑刻的数量与规模、性质与内容,其中不同朝代的碑刻发展状况既有特殊性与偶然性也有着共性和规律。
西汉作为我国第一个历史较长的大一统朝代,经济与文化空前繁荣,又上承秦朝以刻石纪功之遗风,本该有大量碑刻留存,但事实上存世总量只与秦朝相当,丰碑巨制几乎没有发现,早在明代这一现象就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赵崡在《石墨镌华》中特别指出“西汉石刻传者极少”。这种反常主要是由于王莽篡汉之后,对社会制度、礼仪德行等诸方面进行全面颠覆,大量汉朝碑刻被毁,加之年代久远、磨损严重,故而传世极少。到东汉,碑刻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正如祝嘉《书学史》所说“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事亦隆,书家辈出,百世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后代常见的碑刻的形制、内容与功能基本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如墓
碑的勃兴。如前文所言,碑原本是用作牵引绳索放入棺椁的,在使用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标记墓穴地点方位的效果,渐渐开始出现将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刻在碑上的现象,进而发展为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其他种类的碑刻也逐渐繁盛,广泛用于记表功德、刊载经书、宗庙祭祀等领域。随后的三国两晋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长期征战消耗了社会大部分资源,从客观上限制了碑刻的繁荣和发展;此外,统治者出于减少奢靡、维护统治、镇压世家大族势力的考虑(详见下文“碑刻与话语权”),多次出台抑制碑刻的条文政策,禁碑运动从曹魏一直绵延下来,南朝也依旧承袭东晋遗风,碑刻未能产生新的发展。此时反观由少数民族控制的北方,碑刻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状态。北朝,尤其是北魏时期,既无禁碑政策,又方便就地取材,石刻艺术空前发展,设立墓志、镌刻摩崖等承袭前朝已有的成果并蔚然成风,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广泛传播,南朝主要表现为兴建寺庙,北朝则表现为兴建大量石窟、佛像,伴生的石刻造像题记也极大地丰富起来,如《辅国大将军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等,是对石刻像的有力补充,魏碑的书法价值在后世格外引人关注。其后的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期,碑刻文化也相当繁荣,大量涌现制作精良、文辞华美的御碑称谓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碑刻因其不易损坏、流传久远成为帝王记功记事以图流芳百世的最佳媒介,唐太宗的《圣教序》、《晋祠铭》,唐高宗的《大唐纪功颂》、《万年宫铭》,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唐太宗的《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均是唐代帝王亲自撰写碑文的代表作。此外,汇集众多碑刻于一处,统一加以存放和保护的碑林肇始,在唐后期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已经成为保存《开成石经》等重要碑刻的荟萃之地。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萧条期之后,宋代的碑刻艺术略有复苏,但是由于大多数时间偏安一隅,国家始终处于北方少数民族侵略的压力之下,赵宋一朝的碑刻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始终无法和唐朝媲美,只是传承和沿袭了以有的传统。碑刻艺术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而成熟的体系,从客观角度而言,已经难有什么飞跃和突破,这是由碑刻的生长周期阶段决定的;加之元朝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且存续时间较短,而明朝历代帝王又崇尚帖学而轻视碑学,故而元明两朝碑刻艺术处于总体停滞、局部创新的状态,如元代白话碑以及明朝经济类碑刻的萌芽于兴起。清代出现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完成了两千多年古来帝制的回光返照,这一时期的碑刻艺术亦然。这种复兴主要是由三种原因导致的,其一,作为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清统治者尤其是康熙大帝吸取了元朝短命的经验,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学习,碑刻作为具有权威性和传承性的媒介自然被纳入利用和控制的范围重新受到重视;其二,帖学盛极而衰,由于技术等原因多次翻刻之后的帖本与书法家真迹出现较大的误差,学书者转而钟情于误差小的古碑拓本,推动了碑学的繁荣;其三,满清统治者出于思想集控的考虑实行严厉的文化钳制政策,文人士大夫不敢轻易谈论国事政治而转向故纸堆从事训诂考据,在乾隆和嘉庆朝达到顶峰,金石学再度兴起,理论著作大量出现,古碑碣频繁出土,佳拓广泛流传。这种热潮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覆灭而消退,碑刻的再度复兴亦是现当代。建国以后,一方面古碑的发掘与保护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果,如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大唐故骠骑大将军卢国公程使君墓志》、从明至清有关天文类碑刻十七块等;另一方面,新建的碑刻在各大城市、旅游景区、革命老区大量涌现,起着纪念事项、教育群众、美化环境的作用,其中纪念碑数目最大,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唐山抗震纪念碑、南昌起义纪念塔碑等。在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的支持下,现当代碑刻在形式与材质更加多样化,巨字摩崖的纪录反复刷新,新式
碑林的规模与数量也显著增长,碑刻艺术换发新的生机。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适逢政治修明、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的时代,碑刻也会呈现出蓬勃繁荣的局面,重大事件或社会思潮也会引起碑刻建造的高潮。此外,碑刻作为一种媒介,无论是其形制设计还是内容偏向亦或是功能用途已经基本定型,会作为纸质媒体与电子媒体的补充持续存在下去。(四)碑刻的形制
(由于摩崖是在山崖石壁上直接雕刻,不存在形制的问题,因此本部分所谓之碑刻不包括此类)
前文已经提到过,最早的碑是立在墓穴的四角上用以系绑绳索之物,后来才演化为镌刻墓志的载体,虽然下葬悬棺的使用价值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系绳用的“碑穿”却保留下来,典型的如现藏于西安碑林的《仓颉庙碑》,碑额上就有一直径十厘米左右的圆孔。碑穿的高低大小并不统一,一般在碑额的碑题与碑身的正文之间,以免孔洞妨碍碑文,但也有少数穿在碑身正中的,如汉和帝时期的《原安碑》。这种先秦碑的遗留还体现在碑晕上,即碑首上刻出的状如绳索勒痕的印记,如汉代《仙人唐公房碑》及西晋的《菅氏夫人墓碑》的碑首上就刻有三条弧形沟槽。这种形制是两汉到魏晋时期的碑所独有的,清代王芑孙在《碑版文广例》中指出“汉碑穿外由晕,其晕缭绕,或即自穿中出,或从穿外起”,这种对古制的保留没有实际意义而影响碑文篆刻和排布,在魏晋之后逐渐消失。
后代具有固定样式的碑一般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这种形制被广泛采用并延续至今。碑座又叫碑趺,早期的碑趺一般都是长方形巨石,较为朴素,仅仅起到固定碑身的作用,汉代开始在碑趺上雕刻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图案,到南北朝时期“龟趺”开始出现,发展到了唐代,龟趺数量激增,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碑刻,尤其是涉及到宗教方面内容的碑刻普遍使用龟的形态作为碑座如唐玄宗时期的《大智禅师碑》、唐德宗时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北宋宋徽宗亲自撰写的《大观圣作碑》等。驮碑的龟正式名称为赑屃,俗称霸下,民间传说中是龙生九子之一,好负重,这种具有稳定、郑重之感的碑趺寄寓了雕刻者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的希望。碑身,也就是镌刻碑文的主体部分,多为扁长体,正面成为碑阳,反面成为碑阴,左右两面被称为碑侧。汉碑的碑阴鲜少有内容丰富的,正所谓“汉碑阴,类多题名,或补前碑所未及,无大论著”;到了魏晋时期立碑者开始在碑阴和碑侧雕刻精致反复的花纹和图案,使其具有装饰性和艺术价值,如北魏神龟年间的《魏故使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领雍州刺史文宪公墓志》的碑侧上就刻有四神兽及与它们风格保持一致的云纹;这种形制到了唐代更加普遍,雕刻的技术与美学价值也显著提升,如唐开元时期的《兴福寺残碑》,左右碑侧以双波纹为干线,分别勾勒出凤凰、舞人、狮子背上的骑士等异域风情浓厚的形象,唐显庆年间的《道德寺碑》、唐武宗时期的《玄秘塔碑》、元仁宗时期的《大开元寺兴致碑》等碑上也刻有与碑刻正文互相呼应和补充的图画。随着时代的发展,除了碑身的雕刻成现出不断追求艺术性的趋向之外,其形状也不再仅是单一的长方形,如北魏太和年间的《宕昌公晖福寺碑》的碑身下部呈弧形向内部收缩,颇为别致;又如《魏故处士元显俊墓志》和唐贞观时期的《李寿墓志》的碑身更是呈现出完整、逼真的龟形,体现了我国古人丰沛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碑首,也就是碑的最上端不刻文字的部分,又叫碑额,历朝历代有各自流行的形状和样式。汉代作为碑刻发展的初级阶段,碑首形状较为简单,大多有尖形(又称圭首)、半圆形(又称晕首)和方形,按照这种不同碑被细分为不同的种类,方首的叫做碑,其余的叫做碣(又分为圆首的普通碣和尖首的笏头碣);随
着对碑刻艺术性要求的不断提高,模仿勒痕的碑晕逐渐被其他龙、虎、雀等其他纹样取代,晕首转变为直接在碑首上雕刻纹饰,而圭首的则是将尖状突起包含于半圆形纹饰之内,这样螭首逐渐形成,并盛行于唐代,螭作为龙的一种,代表着封建皇权的神圣地位,用在碑刻中显得格外郑重,如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孔子庙堂碑》、《皇甫诞碑》等较为著名的碑刻都采用这种形制。宋代以后多用螭首碑和无首碑的格局基本确定下来。
碑刻的材质大多以石头为主,方便取得、价格低廉、结实耐磨,具有长久保存的价值和可能,为历代立碑者多青睐。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出现了一些其他材质的碑刻,因起少有而格外引人注目。如瓷制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发现的古回鹘文的瓷制墓碑就属此列;再如铜制碑,明神宗时期的《泰山天仙金阙》、明熹宗时期的《泰山灵佑宫》等铜碑至今光可鉴人。
二、碑刻研究的现有方向与价值
碑刻作为我国古老而独特的艺术形式,一直以来受到多个领域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从南朝梁元帝萧绎敕儒臣编纂的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部碑文化专著《碑英》以来,无数关于碑刻研究之作至今已经汗牛充栋。笔者以为,这些研究几乎可以分为三个大类,文字学的、美学的以及历史学的,即大多是由文字与内容两个角度对碑刻展开探讨,将其作为媒介加以研究的资料较少。
(一)文字学视野中的碑刻。
目前出土的刻石上迄周朝,忠实的记录了两千多年以来文字的发展历程,一方面,研究不同时代的碑刻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文字和语用演变轨迹,另一方面,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域文字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可以借此推断判定碑刻的年代和国别。有一些古碑因为磨损严重或是所记之事普通琐碎等原因在内容研究上意义不大,但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却具有重要价值。碑刻对于文字学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三:其一,研究某一时期的文字。从先秦到西汉近千年的时间纸质媒介尚未产生,通过简牍、锦帛保存下来的文字较少,年代越是悠久碑刻这一载体便越是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福建仙字潭摩崖石刻和浙江天姥山蝌蚪文摩崖石刻的成书年代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对研究少数民族原始文字具有重要意义;又如在中山国墓葬发现的《公承得守丘刻石》寥寥二十个字书法古拙,气息近于东周青铜器铭文,成为研究金文演化的凭据之一;如又如石鼓历经千年流传虽已严重磨灭残损,但却保留了存世少有的籀文(大篆);再如始皇帝时期的《泰山刻石》对研究秦代小篆的作用等,不胜枚举,东汉蔡伦以后碑文仍和纸媒起着互相印证、补充的作用。其二,研究字体的演变。西汉是文字隶变的关键时期,由篆书到隶书的转型也清楚地体现在碑刻中,在汉文帝后元年间的《群臣上寿刻石》(亦称《娄山石刻》,是现存汉碑最早者)中的字体虽为篆书但已由长形转为方形,某些笔画已由圆转改为方折,初显隶意,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的《三老讳字忌日碑》已经篆意尽褪,只是还未现汉隶的明显波磔,再到汉末的桓帝永兴年间的《乙瑛碑》的字体已经显示出波磔分明、蚕头燕尾、扁方整齐的成熟期汉隶气象。由隶书到楷书的演变同样可以在碑刻中找到证据,如东晋安帝义熙年间的《爨宝子碑》到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的《刘怀民墓志》最终到《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碑铭》;楷书到行书的变化亦然,不做赘述。其三,研究语用方面的现象,如古代白话文的起兴、简化字俗字的演变历程、复音词叠音词的使用、不同年代丧葬词语的变化。在知网上以“碑刻”为关键词的检索中多可见这三类研究,如《汉魏六朝碑刻古文字研究》(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博士论
文)、《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专著)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加以介绍。(二)美学视野中的碑刻。
由于碑刻可以忠实记载和保存书碑者真迹,模仿碑刻的碑学成为与推崇书帖的帖学双峰并峙的两大流派,在书法领域具有极高的价值。一方面,名家撰写的碑刻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描摹的机会,历朝历代之间、擅长不同字体的书法大家几乎都有以碑刻形式传世的名作,如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等。尤其是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有纸质版本作品存世的名作来说,碑刻更是学习研究的唯一途径,如被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赞为“古今妙绝”的李斯的真迹几乎只保存在《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会稽刻石》等刻石之中;又如书圣的真迹,由于唐太宗痴迷王羲之书法不仅生前动用一切手段收集其作品,死后也一并带入坟墓陪葬,至今流传的除了集碑与模仿之外就只余《独笔“鹅”字碑》和《“振衣濯足”摩崖石刻》,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对美学价值的追求也催生出一批书撰精良的碑刻。在碑刻诞生的初期,除谕制碑之外书碑者大多只在意内容层面,随着碑刻艺术的发展,书写是否美观、雕刻是否精良也成为制碑的目标,唐宋以降的历代各朝涌现出集撰文、书法与镌刻三种卓越技能于一体的“三绝碑”,如《大唐中兴颂摩崖》、《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等。此外,集碑的出现也与对碑刻美学与艺术价值的追求有关。集碑指将不同书者的字拼合在一个碑面上,也指将同一书法家在不同作品中使用的字按照内容的需要抽出排列组合成一篇碑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宏福寺怀仁为唐太宗制作的《三藏圣教序》碑文,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中他广集王羲之真迹,找出需要的字(实在没有的就用偏旁点画加以拼接)重新缩放、编排、布局,最终拼合为两千五百余字的碑文,虽则如此但全篇宛如一气呵成、不露斧凿痕迹,被后人评价为“与右军遗贴所有者纤微克肖”(宋黄伯思《东观余论》)、“钩心斗角、天衣无缝”(清叶昌炽《语石》),在书法界地位极高。自清代的学者兼书法家阮元提出“南北书派”和“北碑南帖论”后,邓石如、包世臣、康有为等竞相发挥,遂形成同崇帖对峙的尊碑学派。
(三)历史学视野中的碑刻。
碑刻与书籍一样都是图画与文字的书写、留存载体,但前者的当下性更为明显,意即碑文大多记录当下发生的近景,鲜少有关于上百年之前的事情的碑文,这种内容上的偏向性使得碑刻作为史料的可信性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存在更多以讹传讹可能性的书籍。碑刻在政治经济、天文地理、风俗信仰、科学技术、对外交流等诸多领域都有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有的忠实的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如《施琅记功碑》;有的对史籍记载有着校正和补充的作用,如《武德皇后墓志》、《独孤浑贞墓志》等碑刻有利弥补了北周历史的空白;有的有助于开解历史疑难问题,如陕西省凤县出土的南宋残碑使考古学家找到了众说纷纭的古代军事要冲大散关的确切位置;有的记载了中央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会盟情况,如唐朝的《唐蕃会盟碑》、《南诏德化碑》、宋代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等,当年为表承诺之郑重而刻的碑而今成为研究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以上三个方面殊途同归,无一不是对将碑刻作为一种文本来对待的。因此,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将落脚点放在了碑刻的内容上。不同于简帛与纸张,碑刻这种承载文字和图画的媒介在空间中占地较大,高度从一米到十几米不等,除了碑林之外几乎没有其它途径对碑刻的实体进行集中和收藏,为了方便研究,拓片成为普遍采用的最接近原物的再现碑刻的方式。捶拓,又称拓印,是把石碑或器物表
面上刻的文字或图形复印到纸张上的一种方法。捶拓的基本操作将洇湿的宣纸
铺在石上,用软刷将纸刷匀,经轻轻捶打使纸紧贴于石面;然后,用细布包裹棉花而做成拓包,蘸上墨汁,在纸面上轻轻拓刷。石上的字是凹进石面的,所以有文字的部分受不着墨,把纸揭下来,便成为一件黑底白字的复制品,这就是拓本,也称拓片。这样的拓片被单独保存或是装订成书,成为碑刻研究的对象,如《中国碑刻全集》、《历代碑刻辑录》等专著都属于此类,更有大量将文字内容单独剥离出来的碑刻文献学著作,如《经典碑帖释文译注》等。这种意义上的碑刻研究实际上是对碑上所刻之物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中,碑学是指“崇尚碑刻之书派,与帖学相對称”或“研考碑刻之源流、時代、体制、拓本真伪及碑文内容之学问1”。换言之,现有的研究主要是脱离了碑刻这一载体的内容研究。
三、作为媒介的碑刻所具有的特征及其对内容的反作用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受传统的文化研究的习惯性视角的影响,现有的对碑刻的研究中绝大部分属于内容研究,而忽视了作为载体的石碑本身。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媒介环境学派在北美萌芽以来,“媒介即讯息”、“媒介即隐喻”等爆炸性的观点接连提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媒介本身所固有的特征以及传播技术的演进出发,探讨这些因素对媒介内容选择的偏向作用,以及在一定历史阶段占主要地位的媒介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如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偏向论,即根据媒介自身固有的特征将其分为两类,有利于在时间的纬度上长久传承的媒介和有利于在空间的纬度上延展和传播的媒介,前者如石板、泥板等,后者如纸张等。按照这一观点,他论证了沙草纸对埃及文字、宗教和政治统治所起的作用、泥板对古巴比伦文明和楔形文字的产生的影响、羊皮纸在西欧封建社会形成的教育垄断以及印刷术引起的民主革命,这种论述开创了媒介研究的新角度。然而,中国古代的碑碣又不同于英尼斯笔下的任何一个例子,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碑碣从来没有成为某一历史阶段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从青铜时代到简牍时代在到纸本时代,碑碣始终作为主流媒介的补充活跃在文化视野中。这种地位决定了碑刻文字范围的有限性和选择性大于主流媒介,而这种偏向性恰恰是由碑碣本身属性决定的,即所谓的形式和载体影响内容。
(一)雕刻技术与图文比例
在目前遗存的数以千计的古代碑刻中,绝大部分是以文字为主要内容的碑刻。相较于文字而言,图画要求笔触更灵巧、细腻和圆润,而刻刀的走势粗重、转角刚折,这种冲突限制了碑碣队图画的表现能力,因此,历史上图碑的比例远远小于文字碑刻。然则,也有一些精品之作被雕刻并保留下来,如吴越国王钱元瓘墓后室出土的后晋天福年间星相刻石、根据北宋黄裳元丰星图摹刻的《天文图碑》、描绘王致远描刻的宋代版图和地形图碑、产生于西汉中期于明清两代又分几次翻刻的《五岳真形图碑》等。如果对现存的图碑进行内容分类就会发现,其中主要是地理、水文和星象类,以人物、风景、鸟兽等艺术创作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图碑数量极少,这种倾向性也与科学类碑刻对笔触的要求较低有关。此外,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还提到的“石头对文字演化的阻碍作用”,并引用了“沙草纸这种书写流畅的媒介在埃及出现之后,象形文字逐渐衰落,拼音文字兴起”
作为案例。在古代中国,由于碑碣并不是文字的主要载体,不至于影响整个字体演变的发展脉络,但这种偏向性依旧得到了体现,即就碑刻采用的字体而言,书写规范、横平竖直的楷书最多,行书次之,草书最少。一方面是由于草书产生时
1李光德编译.中华书学大辞典.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第771页
间较晚,艺术性强头而记录的功能较差,另一方面,草书灵活率性的笔触与碑碣雕刻的不兼容性也是原因之一。
(二)“倚重时间的媒介”与碑刻内容
由于石头本身稳固、致密、坚硬耐磨、不易损坏的固有特性,碑刻具有其它媒介难以比拟的某种永恒性,可以百年、千年的传承下去,就像英尼斯指出的那样“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人们在使用这一类媒介的时候,看中的不是可以使内容在多大范围内传播和让多少受众知道,而是重视由此获得在时间长河中永久地传承下去的可能,所谓“刻石立铭,以示后昆,忆载万年,子子孙孙”,这种希求永垂不朽的立碑意图体现在内容偏向上就是记功碑和墓志碑的繁荣。
记功碑,顾名思义,是记录、歌颂以至于吹捧碑刻主人公功绩成就的碑刻,在我国古代碑刻中数量较大、成就较高,其中帝王御制的记功碑更是其中的精品,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产生至日起便绵延不绝。据碑学家金其桢根据历代史学家研究得出的结论,始皇帝纪功所立之石共有九块,如《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芝罘刻石》等,“讨伐乱逆”、“威动四极”、“大义修明”等记录和歌颂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封建专制国家的丰功伟绩,而立碑的目的便是“垂于后世”、“永承重戒”;唐代是清以前御碑最兴盛的朝代,不少帝王都亲撰亲书、勒石立碑,如唐太宗万年亲自撰文的《晋祠铭》,抒发了自己实行周道、以德治国的政治观念以及匡扶天下、开创盛世的历史功绩;再如由宋真宗亲撰碑文,为宋太宗、宋太宗歌颂功德的《汾阴二圣配飧铭》;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御制的《平定准噶尔丹纪功碑》两块,四面环刻,用满、藏、蒙、汉四种语言记录和歌颂了他平叛的经过、功绩和意义。考察历代御制纪功碑的作者与内容,不难得出这样的规律:在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拥有至高的地位,因此越是雄才大略、自命不凡的君主越是不满足于此世的权力和享受,而是追求更高远的目标,比如长生久视,退而求其次便是永垂不朽、彪炳千秋,在死后仍然荣享世人的崇敬,盛世立碑成为规律,碑刻成为帝王追求流芳万世的一种手段。反观那些黑暗动荡的年代和昏聩无能的帝王,则无心立碑,如明嘉靖以后的各代皇帝自觉愧对帝位竟然连皇陵中的碑碣都懒于编造而空置无字。除了帝王之外,历朝历代的名将、功臣和大儒也是纪功碑经常歌颂的人物,如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的《韩世忠万字碑》,记录了他英勇无畏的抗金事迹,歌颂了他正直忠愤的高尚品德;又如东汉桓帝建和年间的《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记录了杨孟文再三奏请多方努力重开石门水利工程的功绩;再如康熙年间的《御制孟子庙碑》,对孟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歌颂了他“以承先圣、以正人心”的历史作用。甚至可以说,碑刻有记载的大多都是历史名人,而历史名人也大多以碑刻主人公或撰写者的形象出现过,碑刻与功德在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由此及彼的伴生关系和联想机制。
如果说纪功碑几乎为帝王霸主、功臣名将、学者大儒等小部分社会顶层人所垄断的话,那么以墓志碑的形式将自己的姓名、生平和业绩长久的保存下去就属于全体士大夫阶层甚至普通文人、富商都可以承受和拥有的保持不朽的方式。碑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墓葬有这着不解之缘,早在春秋时期就被当作系绑绳索、引吊棺椁之物,在战国时期(按照情理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有的人怕日久没有特征的墓穴难以辨认和祭祀,便将死者的名字姓氏刻在碑上作为标记。进而出现了对于死者生平的记载和功德的赞颂,“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留之不忍去”(唐陆龟蒙《野庙碑》)“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碑
碣》),墓碑的作用发生重大转变。到了大约西汉时期开始初具后代墓碑性质的雏形,如《麃孝禹碑》。到了东汉时,用墓碑歌颂死者功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世家大族和地主富豪更希求用这种形式把生前的覆盖权势带入冥界,并期望自己能永垂不朽。如同皇帝和贵族的谥号一样,墓碑碑文是对一个人生平功绩的最终判定和描绘,具有某种盖棺定论的性质,历来为人所重视,请名家作志成为一种惯例,以至于东汉大文豪蔡邕的文集中有近一半都是帮人写的碑文,甚至青少年早夭的死者也有歌功颂德之作。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西晋末年和南北朝初年,墓志碑的形制最终成型,如《南阳王妃墓志》,具有齐全的首题、志文、颂文并且明言“墓志铭”,这种体例沿用至今。历朝历代,墓碑始终是碑碣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所收的7853块碑刻中墓碑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古人没有将墓志写在纸张或简牍上而是刻于碑石之上,无疑体现了媒介与内容互相选择和适应的关系,碑刻作为倚重时间的媒介所提供耐久性、永恒性为死者及其家属提供了一种寻常百姓也可享有的垂之不朽的心理安慰。(三)“不刊之论”与碑刻内容
除了上文提到的时间上的永久性之外,碑刻作为一种内容的载体还具有一经刻成不易更改的特质。民间谚语有言“白纸黑字、板上钉钉”,形容话语一旦从口头语言付诸书面文字就变得更加郑重,由此推知,刻于石上的文字其严肃性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换言之,石质和金属类载体赋予其内容某种不可变更的权威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如历史上最早的法典——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刻在一根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无独有偶,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也是刻在青铜板上的。法律以及经典等郑重而严肃的不刊之论需要笨重的、不易移动和坍倒的、耐磨损的材料作为传承和公示的载体,碑刻正式其中之一。
在我国古代碑刻丰富的内容题材中,有一个分类不可不提——刊刻各学派经典之作碑刻——石经。其中,又以儒家经典数量最大、复刊次数最多、雕刻最为精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刻石是汉灵帝时期议郎蔡邕等人核定并刊刻的《熹平石经》,包括《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儒家经典共四十六石(一说四十八石),立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的太学外,供学子抄录;三国时期魏齐王曹芳在位时又组织刊刻了包括《尚书》以及《春秋三传》在内的《正始石经》,每个字先刻古文,再刻篆书和隶书予以释文,具有规范经籍字体的作用;唐代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文宗时期又组织将贾公彦、孔颖达等人校订的儒经正义刊刻于碑石上,史称《开成石经》,除上文所述之经书外又添加了《孝经》、《尔雅》、《周礼》、《礼记》共十二部儒家经典,双面刻一百一十四石、总字数达到六十五万两千余字,现存于西安碑林。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家思想始终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儒家经典更是书生士子们考试入宦所必学必会之物。然而在印刷术普及推广以前,书籍的复制与传播主要以手抄本为主,多有讹谬和疏漏之处,皇室官方承担着考证经典、颁布定本的职责。一方面,公示儒家经典需要承载量大、耐久耐磨、一目了然的媒介来承载,碑石成为首选;另一方面碑石带来的郑重感与严肃性为儒家经典更增添了神圣性和权威性。除了儒学之外,其他宗教经典也经常见于碑碣刻石中:如刊刻佛教经文的山东台山东南麓刻石面积达两千多平方米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从隋大业年间到明末天启年间由智泉寺里代僧人刊刻的共一千一百二十二部经书
共计一万余块经板,又如刊刻道教经文的山东泰礴顶《太上老子道德经摩崖》、王常月祠堂由赵孟頫题写的《阴符经碑》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也都有经
文以碑刻的方式流传于世,有代表性的主要经文更是被反复刊刻。在英尼斯的分类体系中,以石板泥板为媒介、以倾向于使用书面文字为特征的、倚重时间传承性的帝国又被称为宗教性帝国,这种归类是有原因的,郑重而严肃的使用体验和耐久耐磨的媒介特性使得碑刻与宗教一直存在一种互相增益的联系和互动,越是经典的不刊之论越是倾向于选择碑刻作为载体。
四、碑刻的媒介权力
在一定区域范围与一定历史时期之内,往往有多种媒介共同存在,在不同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能否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媒介,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权力。一方面,媒介有层级之分,有的媒介因其获取和使用成本较高的客观条件以及需要使用者有较高的素养的主观条件使其处于较为高端的位置,(举例而言,如在中国古代的话语体系中,文言文相较于白话文就属于高层级的媒介),这类媒介为其使用者和内容都注入了一种重要性和严肃性,使该媒介的运用具有某种地位与权力上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媒介是信息在空间上以及时间上传播的载体,能够运用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反之,统治者通过赋予或剥夺某一群体的媒介使用权可以达到对该群体的鼓励或抑制作用。
碑刻是一种高层级的媒介。正如上文所言,高层极的媒介所需的主客观条件都较为严格,使用范围有限、频度较低,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媒介拥有不同于
一般媒介的话语权力,碑刻正是处于这样的地位。虽然相较于青铜等材质,石质材料获取方便,但与纸张等更廉价易得的媒介还是无法相比,加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碑刻总体上呈现出体积越来越巨大、雕工越来越精美的趋势,以碑刻作为记载文字的媒介成本居高不下。此外,碑刻往往较为笨重,存放、运输、查检都并非易事,不会随意或草率使用。这些因素使得作为一种媒介的碑刻在我国古代的地位较高,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作为高层级的媒介,碑刻象征着权力与地位。在碑刻产生和发展初期,碑的形状、大小、题什么字、有什么样的碑首和碑趺、雕什么样的花纹都是根据立碑者自己的喜好和经济实力决定的,到了唐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碑的形制开始成为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如《通典·唐会要》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墓碑可以使用“龟趺螭首”,而六品、七品官员只能“方趺圭首”;明代亦有这样的规定,一品用螭首、二品麒麟首、三品天禄辟邪首(《明会典·职官坟茔》)等等,详细而具体。能够立碑、能立高规格的碑变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此外,古代帝王经常采用立碑尤其是立大碑的方式来彰显宏伟磅礴的皇家气度,如明成祖为歌颂其父功德下令雕制的巨碑重达三万吨、石料累计高度八十二点七米,让前去检视的官员“心悸目眩……惊叹所未见”,虽然最终因为运输条件的限制而无疾而终,但足以见得帝王谕制巨碑在激起臣下和百姓仰慕与折服之意方面的作用。由此观之,碑刻在我国古代不仅是一种记载文字的工具,更是权力的象征,远远超过了一般媒介的意义和价值。
“无字碑”是碑刻强烈象征意味的又一有力佐证。对一般的媒介来说,没有内容就没有意义,所以不会有“无图电视”这样的说法,但是碑刻由于本身具有超越载体功能本身的象征意义,因此使其成为一种可以脱离文本独自存在的媒介,在没有内容的情况下甚至表现出了更深刻的言外之意。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无字碑,如汉武帝泰山玉皇顶无字碑,唐中宗为其母女皇武则天树立的无字碑,连臭名昭著的秦桧的墓碑也是无字碑,明皇陵的无字碑甚至达到了二十二块之多。碑刻无言,下自成蹊,对于这些无字碑,尤其是武则天等有争议人物的无字碑,
为什么立、究竟想要说明什么等问题引起了历朝历代学者们的探讨,被解读出的含义远远超过了碑文(如果有的话)可能承载的范围。言不尽意,媒介可以替它开口,因为碑刻本身就是功勋卓著、永垂不朽的代名词。
由于碑刻特殊的象征意义,只有重要的人和事才有权得到这种媒介的记录,那么反其道而推之,从碑刻的有无和多少的角度可以窥探某一历史阶段内某一群体或领域的社会地位及其变化。这里略举两例。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妇女长期处于夫权、男权的压制下,地位卑微,缺乏媒介使用权和话语表达权。然而,在唐朝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妇女书碑,如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接连有一
些唐朝妇女效而仿之,操笔书碑,如唐睿宗之女玉真公主所书的《金仙公主墓志》、唐玄宗时参军房嶙之妻所书的《石壁寺铁弥勒像颂》等。书碑体现了唐朝女性拥有相对其他时期而言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与其平等宽松、开明奔放的文化大环境和女主天下的特殊背景息息相关。同理,某一社会现象如果在碑刻这种高层级媒介上出现,也暗示着该领域的重要性。古代记事类碑刻历来多政治类题材,然而在明清时期却大量出现经济类碑刻,如清雍正年间记录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能够成为碑刻的内容暗示着雇佣关系与手工作坊已经不
是偶然现象。碑刻,作为一种有权力隐喻的媒介可以佐证其客体的重要性或普遍性。
正因为碑刻具有象征性意义和刊载、传递信息的实际性作用,历代统治者往往有意的运用对立碑的御赐或允许、毁弃与禁止来表示自己的亲疏与褒贬,因
为正如福柯所言“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着权力”。碑刻首先是一种
媒介,是话语和文本的载体,通过对这一媒介进行控制可以达到抹除、消灭某种特定信息并阻止其进一步传播的作用。王莽篡汉以后的毁碑行径就是其试图颠覆毁灭西汉文化系列行动的一部分,由郑明、黄简编的《中国书法史年表》中对此作过清晰地说明“王莽代汉,建新,甄鄷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又新莽恶称汉德,凡所在有石刻者,皆令仆而磨之,不容略留”,这种大规模的毁碑使得西汉
碑碣鲜有流传。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这种“破旧才立新”的传统,如烧毁前王朝的宫殿等,值得庆幸的是,磨除前王朝的碑刻只此一家。再者,由于碑刻具有使内容流芳千古、永垂不朽的功能以及对地位与身份的象征性功能,深谙此道的古代帝王会通过媒介钳制来打击其主要使用者的势力,如曹魏统治者发起的禁碑运动。据《宋书·礼志二》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壁、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名义上禁碑是为了
防止浪费,而在政治意义上则有效钳制了立碑颂德成风的世家大族的气焰和势力。到了两晋时期,这种意图更加清晰,晋武帝在诏书中明确表示“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换言之,禁碑可以达到保持立碑作为一种权力的“含金量”的效果。对于古代统治者而言,禁止或允许立碑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不仅应用于对某一群体的打击或器重,也用于对个人的惩罚或奖励。前者如明朝著名学者方孝孺因为斥责承租篡位被灭十族,其碑刻也被铲毁;后者如唐高宗李治嘉奖开国勋臣李勣而御赐《赠太尉英贞武公李勣碑》,宋哲宗为司马光的《司马温公碑》题写碑额等。碑刻既是永垂不朽的机会又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这种媒介的使用被纳入权力的体系和事业。
碑是一种刻石以记事的形式,其石质材料本身具有耐久耐磨、难以搬运、雕刻困难等特点,这些特征赋予了其内容庄重严肃、永垂不朽的属性,从而使得作为媒介的碑刻不仅具有记录、传播信息的基础功能,还具有对权力、身份、地位、
荣誉、尊严等社会概念的象征作用。碑刻的这种特殊的文化意义使其历尽两千余年时光而没有被历史所淘汰,至今仍然凭借其在时间传承方面的优势在纪念表功等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i
i《中国碑文化》.金其桢.重庆出版社.2002.
《秦汉刻石选择》.李樯.文物出版社.2009 序言部分
《中国的石刻与石窟》.徐自强吴梦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石刻史语》.赵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古代石刻》赵超.文物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