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技术效率的测算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应用
- 格式:pdf
- 大小:87.71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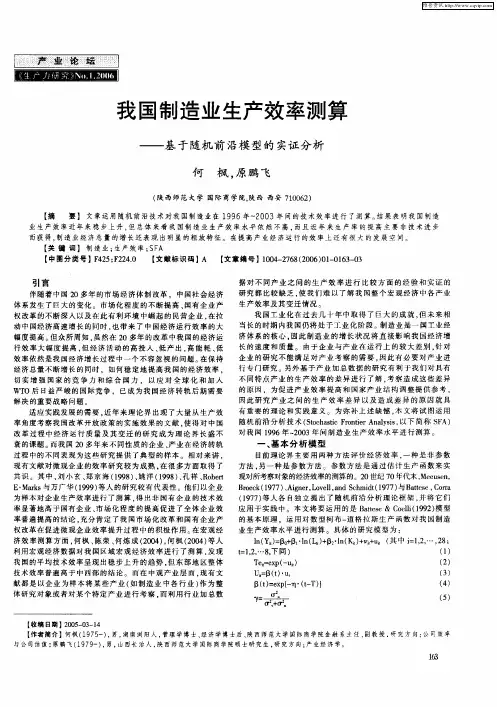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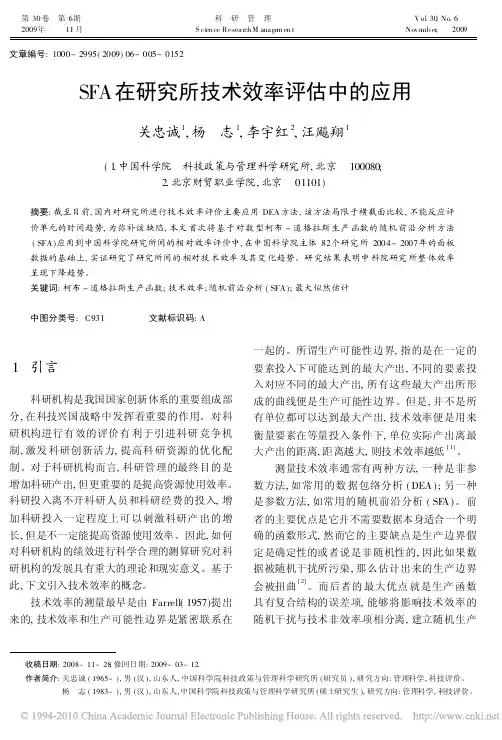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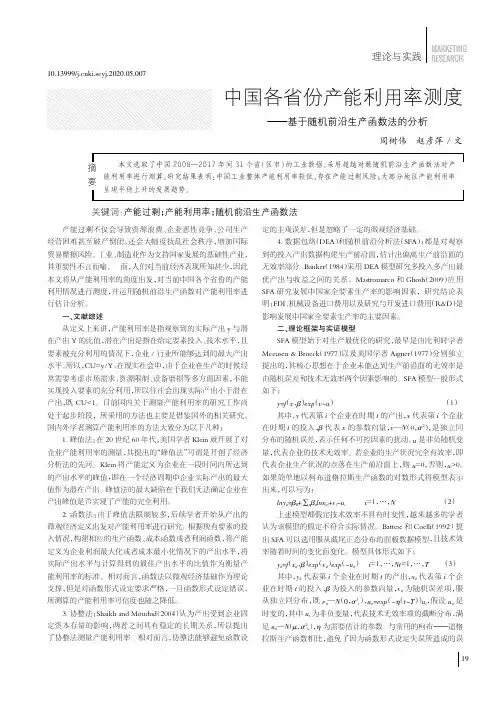
产能过剩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企业恶性竞争、公司生产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倒闭,还会大幅度扰乱社会秩序,增加国际贸易摩擦风险。
工业、制造业作为支持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人们对当前经济表现所知甚少,因此本文将从产能利用率的角度出发,对当前中国各个省份的产能利用情况进行测度,并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产能利用率进行估计分析。
一、文献综述从定义上来讲,产能利用率是指观察到的实际产出y 与潜在产出Y 的比值,潜在产出是指在给定要素投入、技术水平,且要素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企业/行业所能够达到的最大产出水平。
所以,CU=y/Y。
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企业在生产的时候经常需要考虑市场需求、资源限制、设备磨损等多方面因素,不能实现投入要素的充分利用,所以往往会出现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既CU<1。
目前国内关于测量产能利用率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所采用的方法也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测算产能利用率的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种:1.峰值法: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Klein 就开展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量,其提出的“峰值法”可谓是开创了经济分析法的先河。
Klein 将产能定义为企业在一段时间内所达到的产出水平的峰值,即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企业实际产出的最大值作为潜在产出。
峰值法的最大缺陷在于我们无法确定企业在产出峰值是否实现了产能的完全利用。
2.函数法:由于峰值法限制较多,后续学者开始从产出的微观经济定义出发对产能利用率进行研究。
根据现有要素的投入情况,构建相应的生产函数、成本函数或者利润函数,将产能定义为企业利润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情况下的产出水平,将实际产出水平与计算得到的最佳产出水平的比值作为衡量产能利用率的标准。
相对而言,函数法以微观经济基础作为理论支撑,但是对函数形式设定要求严格,一旦函数形式设定错误,所测算的产能利用率可信度也随之降低。
3.协整法:Shaikh and Moudud (2004)认为产出受到企业固定资本存量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稳定的长期关系,所以提出了协整法测量产能利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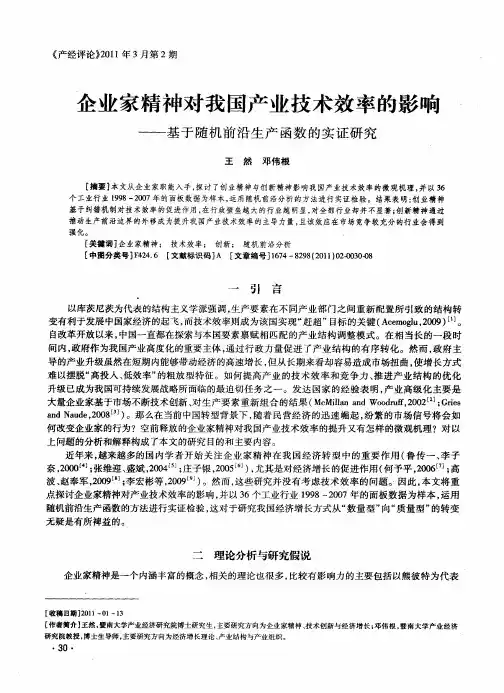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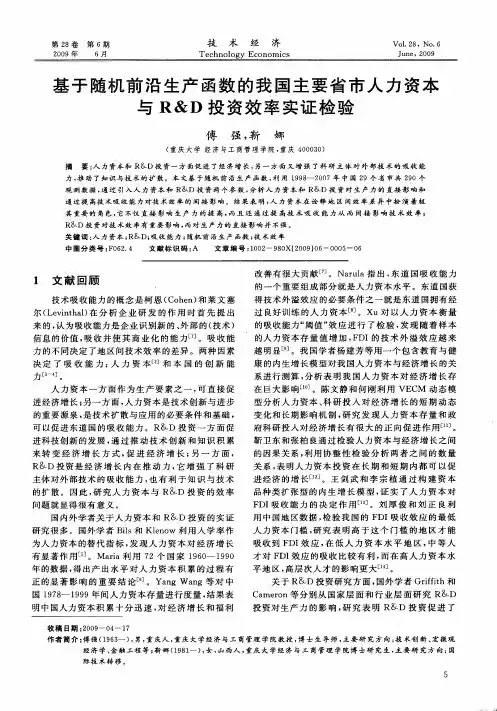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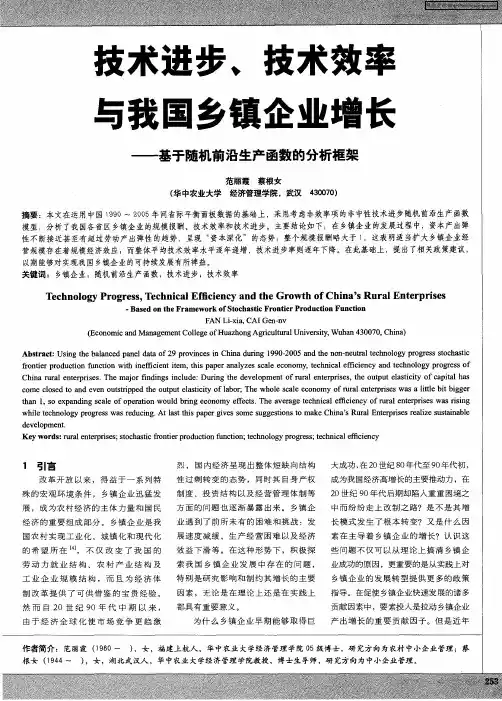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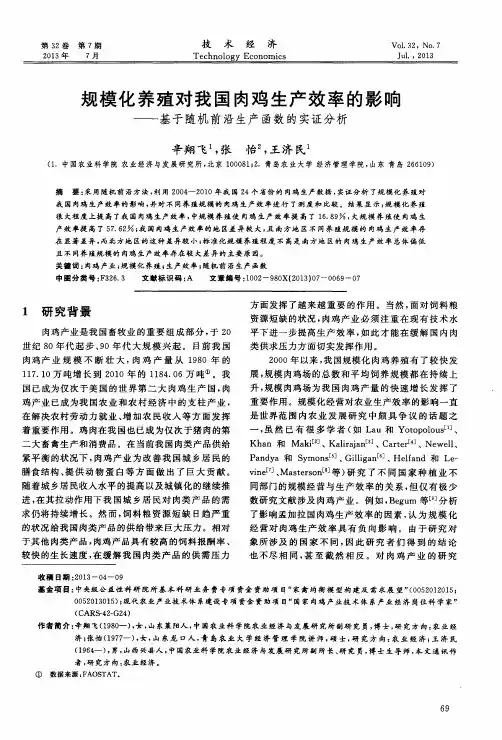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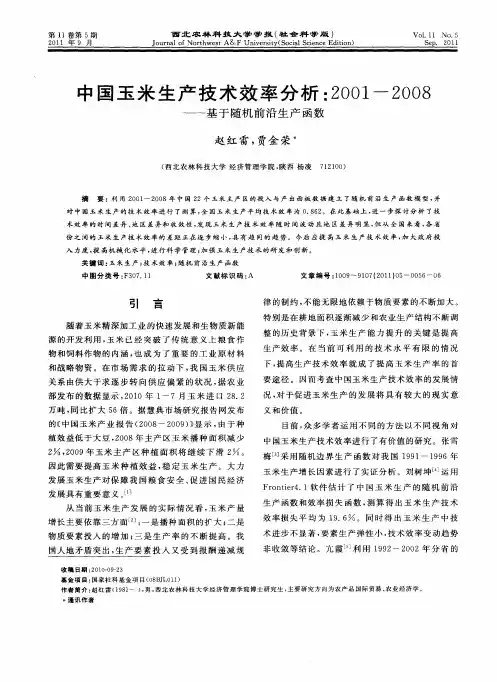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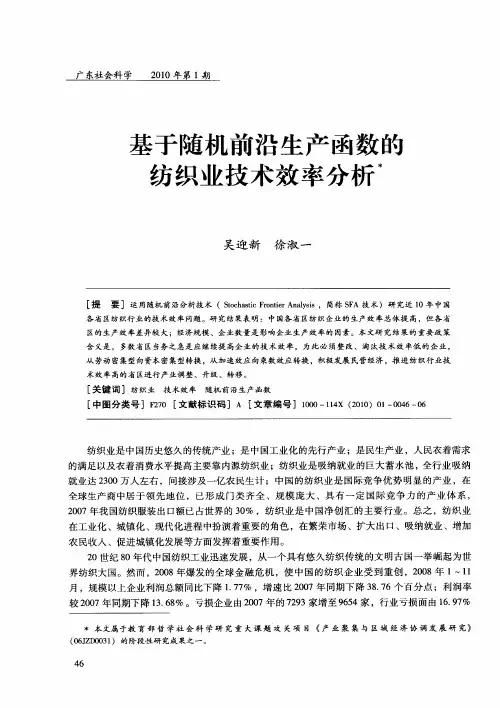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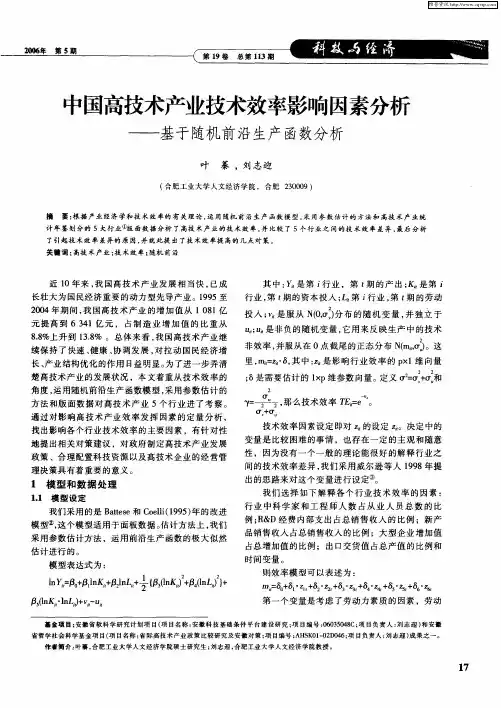
基于SFA模型的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SFA)模型,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
因此,全面、准确地评估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对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简要介绍SFA模型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技术创新效率研究中的应用。
随后,通过对我国各区域技术创新活动的数据收集与整理,运用SFA模型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进行量化分析。
研究将涵盖技术创新投入、产出以及环境因素等多个方面,以全面反映我国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实际状况。
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将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总体水平及差异;二是影响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三是如何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效率。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旨在为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将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通过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效率,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贡献力量。
二、理论框架与模型构建技术创新效率是衡量一个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源利用效果的重要指标。
在当前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我国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
SFA模型起源于经济学中的生产前沿理论,它假设每个生产单位都存在一个潜在的最大产出,而实际产出则受到各种非效率因素的影响,如技术无效、管理不善等。
通过估计生产单位的随机误差项和技术无效项,SFA模型能够准确地量化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
本研究采用SFA模型对我国各区域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南 开 经 济 研 究NANKA I ECO NOM I C STUD I ES2006年 第2期 No.2 2006 随机生产前沿方法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傅晓霞 吴利学3 摘 要:本文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生产率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了评述。
文章首先介绍随机前沿方法的基本原理、估计方法和在面板数据下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随后评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最新进展和在经验分析中的优势与作用,最后总结了在中国行业和地区经济增长研究中随机前沿方法的成果和不足,并探讨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随机前沿方法;生产函数;技术效率;最大似然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 生产率分析是研究经济增长源泉和确定增长质量的主要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重点从单一要素(如劳动)生产率(Partial fact or p r oductivity)转向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 or p r oductivity),分析方法主要有四种:索洛余值法、指数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前沿法①。
随着数据的丰富和估计方法的发展,随机前沿法(St ochastic fr ontier app r oach)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都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它作为工具箱中的必备组件,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近来,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分析中,基于随机前沿法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和较多成果。
本文将对随机前沿模型的特点、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Deco mpositi on of TFP gr owth)及对中国生产率分析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文章各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随机前沿方法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讨论生产函数方程估计的困难和方法;第三部分评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最新发展;第四部分描述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第五部分是对在中国生产率分析中随机前沿方法的研究成果的讨论;最后是总结性评述。
第25卷 第5期2004年 9月 科 研 管 理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Vol.25,No.5Sep , 2004收稿日期:2003-06-04.作者简介:何 枫(1975-),男(汉),湖南浏阳人,博士,现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后及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陈 荣(1976-),女(汉),辽宁海城人,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郑江绥(1974-),男(汉),陕西绥德人,经济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
文章编号:1000-2995(2004)05-004-0100对我国技术效率的测算: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应用何 枫1,陈 荣2,郑江绥3(1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西安 710069;2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香港,新界沙田;3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中国西安 710062)摘要:本文在1981—2000年间我国29个省市数据的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tochastic Frontier Pro 2duction Function )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的技术效率变迁进行了测算。
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整体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是相对较低的,但其在20年中却一直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
关键词:随机前沿分析;技术效率;生产函数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1 引言技术效率的测量最早是由Farrel (1957)和Afriat (1972)提出来的。
技术效率和生产性可能性边界是联系在一起的。
测量技术效率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非参数方法,另一种是参数方法。
非参数方法首先根据样本中所有个体的投入和产出构造一个能够包容所有个体生产方式的最小的生产性可能性集合:即所有要素和产出的有效组合。
所谓“有效”,即是以一定的投入生产出最大产出,或以最小的投入生产出一定的产出。
但是,在实践中,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参数方法来测算技术效率。
本研究将在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Stochas 2tic Frontier Analysis ,以下简称SFA 技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的技术效率进行测量。
2 SFA 模型的基本原理根据S.C.Kumbhakar & C.A.K.Lovell (2000,p8-10)的总结,研究者们一致认为Meeusen &Broeck (1977)、Aigner ,Lovell ,and Schmidt (1977)与Battese &Corra (1977)这三篇论文是标志着SFA 技术诞生的开创性文献。
他们的模型基本上可以表达为y =f (x ;β)・ex p(v -u ),其中,y 代表产出、x 表示一组矢量投入、β为一组待定的矢量参数。
误差项ε为复合结构,第一部分v 服从N (0,σ2v )分布,v ∈iid (独立一致分布)。
第二部分u ≥0,用以表示那些仅仅对某个个体所具有的冲击;因此,该个体的技术效率状态则用T E =exp (-u )来表示。
这样的话,当u =0时,厂商就恰好处于生产前沿上(即y=f (x ;β)・ex p (v ));若u >0,厂商就处于生产前沿下方,也就是处于非技术效率状态。
图1直观地显示了技术效率的定义。
根据对u 所服从分布的假设不同,SFA 技术在具体估计上也有着不同的方法。
本文拟在Bat 2tese &Coelli (1992)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981~2000年间的省际数据测算我国的平均技术效率状态。
Battese &Coelli (1992)模型的基本原理是,考虑一组涉及N 个个体且时期数为T 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 ),有:ln (y it )=β0+∑nβln nit +v it -u it(1)T E it =ex p (-u it )(2)u it =β(t )・u i(3)β(t )=ex p{-η・(t -T )}(4)γ=σ2uσ2v +σ2u(5)图1 技术效率示意图在式(1)中,i 为个体的序号,i =1,…,N ;t 为时期序号,t =1,…,T ;y 为因变量,x 为一组解释变量;β0为截距项;βn 则为一组待估计的矢量参数。
式(1)的误差项εit 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v it ∈iid 并服从N (0,σ2v )分布;第二部分为u it 非负数,它反映那些在第t 时期仅仅作用于第i 个个体的随机冲击变量。
u it ∈iid 并服从正态截断分布(Trucnciton at zero of the N (u ,σ2v )),v it 与u it 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在式(2)中,T E =ex p(-u it )表示样本中第i 个个体在第t 时期内的技术效率水平。
显然,如果u it =0,则T E it =1,即处于技术效率状态,此时该个体的生产点规模位于生产前沿上;相反,如果u it >0,则0<T E it <1,我们称这种状态为技术非效率,此时该个体的生产点位于生产前沿之下。
η是待估计的参数,Battese &Coelli (1992)模型构造了式(3)和(4)以定量描述时间因素对U it 的影响。
其中,易知B (t )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β(t )≥0。
第二,当η>0,β(t )将以递增的速率下降;当η<0,β(t )将以递增的速率增加;当η=0时,β(t )将维持不变。
在式(5)中,γ也是为待估计的参数。
显然,γ=0]σ2u →0,进一步可推理得到误差项εit =v it 。
在统计检验中,如果γ=0这一原假设被接受,即说明样本中所有个体的生产点都位于生产前沿曲线上;此时,则无须使用SFA 技术,而直接运用OL S 方法即可。
在对模型中的参数估计上,Battese &Coelli (1992)认为应使用最大似然法;其中,关键步骤是对γ=0这一原假设使用似然比检验。
根据Battese &Coelli (1992)模型的基本原理,我们运用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在我国1981—2000年间的省际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各省市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测定。
这样,式(1)就可以具体演变成式(6),式(2)—(5)保持不变。
ln (y it )=β0tt +β1・ln (L it )+β2・ln (K it )+v it -u it (6)在式(6)中,y 表示各省市的G DP (单位:亿元人民币),L 表示年均从业人员数量(单位:万人),K 表示年均固定资本存量(单位:亿元人民币),β1实际上就是劳动力产出弹性,β2实际上就是资本产出弹性。
3 数据与实证分析结果3.1 数据采集本文选择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29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作为样本。
在时期跨度上,我们截取了1981~2000年间的有关数据,并将其平均分为四段时间(即1981~1985年,1986~1990年,1991~1995年,1996~2000年)。
通过求算术平均值的方法,每个省市可在G DP 、年均从业人员、年均固定资本存量这三个方面分别提供四个观测值。
有关的基础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
具体如下:①y 为各省市的G DP 。
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将各省市历年的G DP 全部按照1990年的价格基・101・第5期何 枫等:对我国技术效率的测算: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应用 准进行了折算。
②L 为各省市的年均从业人员。
本年年均从业人员=(上年年末数+本年年末数)÷2。
③K 为各省市的年均固定资本存量。
由于我国现行的统计资料中只有历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而并没有固定资本存量的数据。
因此,本文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给出的各省市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运用何枫等人(2003)提出的方法,对我国这29个省市的年均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估计。
各省市历年的年均固定资本存量也都按照1990年的价格基准进行了折算。
3.2 实证分析结果根据上述数据,本文对式(2)~(6)进行了估计。
表1中给出了最终估计结果;表2给出了对我国29个省市平均技术效率的数值及其描述性统计。
表1 对我国生产函数的估计:跨省随机前沿分析(1981—2000)系数标准差t 统计值β0-2.52820.2245-11.2594333β10.33390.04257.8581333β20.88280.024735.7587333γ0.84960.049917.0357333u0.33850.0695 4.873333η0.10190.0251 4.0575333Log likelihood function 92.7380333L R test of the one -sided error121.6454333注:3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33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333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L R 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此处它符合混合卡方分布(Mixed Chi -squared Distribution )。
表2 对我国29省市技术效率状态的描述性分析(1981—2000)项目1981—1985年1986—1990年1991—1995年1996—2000年平均技术效率0.63590.66310.68900.7134标准差0.13200.12470.11730.1099相对变异度0.20770.18800.17020.1541东部地区平均技术效率0.73190.75330.77340.7921中部地区平均技术效率0.61350.64270.67040.6964西部地区平均技术效率0.54660.57850.60910.6383注:(1)平均技术效率为全国29省份的算术平均值;标准差为全国29省份技术效率的标准差;相对变异度=标准差÷平均技术效率。
(2)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0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共11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8个省份。
4 结论我们认为,在20年来我国跨省数据的基础上,运用SFA 技术我国的生产函数并测算平均技术效率,比单纯的时间序列研究或截面研究更加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