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心先生: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研究(2015)
- 格式:docx
- 大小:42.47 KB
- 文档页数: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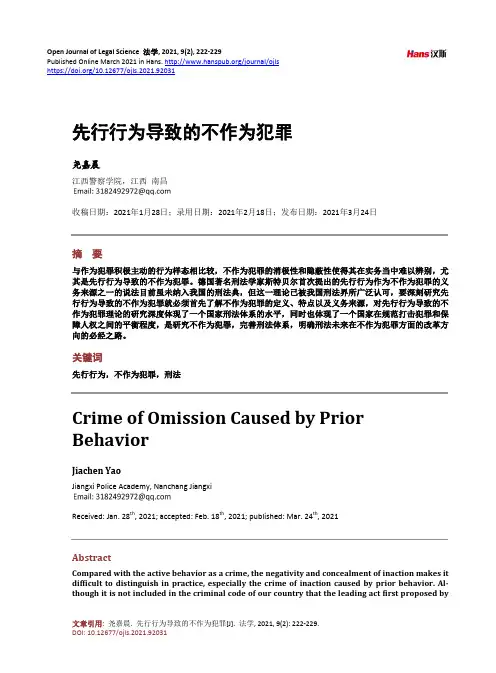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1, 9(2), 222-229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1 in Hans. /journal/ojlshttps:///10.12677/ojls.2021.92031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尧嘉晨江西警察学院,江西南昌收稿日期:2021年1月28日;录用日期:2021年2月18日;发布日期:2021年3月24日摘要与作为犯罪积极主动的行为样态相比较,不作为犯罪的消极性和隐蔽性使得其在实务当中难以辨别,尤其是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斯特贝尔首次提出的先行行为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之一的说法目前虽未纳入我国的刑法典,但这一理论已被我国刑法界所广泛认可,要深刻研究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就必须首先了解不作为犯罪的定义、特点以及义务来源,对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理论的研究深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刑法体系的水平,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在规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程度,是研究不作为犯罪,完善刑法体系,明确刑法未来在不作为犯罪方面的改革方向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先行行为,不作为犯罪,刑法Crime of Omission Caused by PriorBehaviorJiachen YaoJiangxi Police Academy, Nanchang JiangxiReceived: Jan. 28th, 2021; accepted: Feb. 18th, 2021; published: Mar. 24th, 2021AbstractCompared with the active behavior as a crime, the negativity and concealment of inaction makes it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in practice, especially the crime of inaction caused by prior behavior. Al-though it is not included in the criminal code of our country that the leading act first proposed by尧嘉晨the famous German criminal law scientist Stebel as one of the sources of the obligation of non-criminal, this theory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criminal law community in our coun-try, and we must deeply study the first For the crime of omission caused by behavior,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 of obligation of the crime of omission. The depth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omission caused by prior behavior reflects the level of a coun-try’s criminal law system and also reflects a country’s regulation. The degree of balance between fighting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the only way to study the crime of inaction, improve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and clarify the direction of criminal law reform in terms of inaction in the future.KeywordsAntecedent Behavior, Crime of Omission, Criminal Law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licenses/by/4.0/1. 引言目前,在整个的犯罪体系中,犯罪的行为方式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型犯罪,以积极的行为样态为表现形式,而另一种是不作为型犯罪,以消极的行为样态为表现形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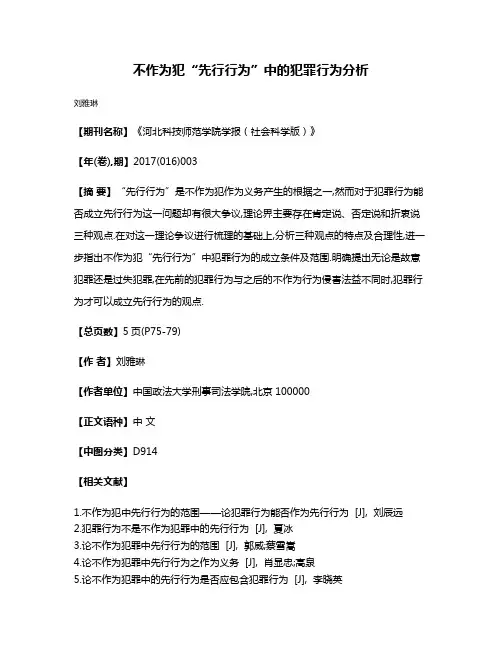
不作为犯“先行行为”中的犯罪行为分析
刘雅琳
【期刊名称】《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16)003
【摘要】“先行行为”是不作为犯作为义务产生的根据之一,然而对于犯罪行为能否成立先行行为这一问题却有很大争议,理论界主要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在对这一理论争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三种观点的特点及合理性,进一步指出不作为犯“先行行为”中犯罪行为的成立条件及范围.明确提出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在先前的犯罪行为与之后的不作为行为侵害法益不同时,犯罪行为才可以成立先行行为的观点.
【总页数】5页(P75-79)
【作者】刘雅琳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4
【相关文献】
1.不作为犯中先行行为的范围——论犯罪行为能否作为先行行为 [J], 刘辰远
2.犯罪行为不是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J], 夏冰
3.论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的范围 [J], 郭威;蔡雪嵩
4.论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 [J], 肖显忠;高泉
5.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是否应包含犯罪行为 [J], 李晓英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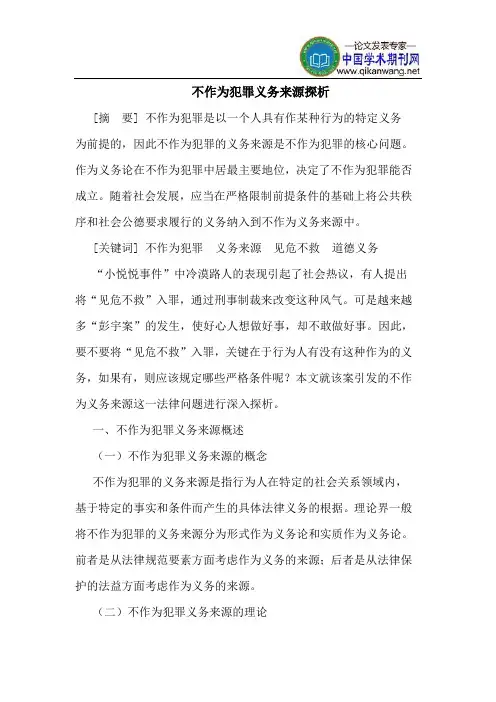
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探析[摘要] 不作为犯罪是以一个人具有作某种行为的特定义务为前提的,因此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
作为义务论在不作为犯罪中居最主要地位,决定了不作为犯罪能否成立。
随着社会发展,应当在严格限制前提条件的基础上将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义务纳入到不作为义务来源中。
[关键词] 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见危不救道德义务“小悦悦事件”中冷漠路人的表现引起了社会热议,有人提出将“见危不救”入罪,通过刑事制裁来改变这种风气。
可是越来越多“彭宇案”的发生,使好心人想做好事,却不敢做好事。
因此,要不要将“见危不救”入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有没有这种作为的义务,如果有,则应该规定哪些严格条件呢?本文就该案引发的不作为义务来源这一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析。
一、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概述(一)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概念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指行为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领域内,基于特定的事实和条件而产生的具体法律义务的根据。
理论界一般将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分为形式作为义务论和实质作为义务论。
前者是从法律规范要素方面考虑作为义务的来源;后者是从法律保护的法益方面考虑作为义务的来源。
(二)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理论我国有关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理论集中在形式作为义务论,主要理论如下:“三来源说”○1、“四来源说”○2和“五来源说”○3。
形式作为义务论本意是把作为义务的根据限定在法律根据上,同时列举出来,一目了然。
但是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形式作为义务说已经不能涵盖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于是,我国刑法理论界中也出现了研究实质义务说的学者。
笔者认为马克昌教授提倡的把特殊场合下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归结为来源之一,就已经考虑了实质义务说的本质特点。
正是该特定义务不同于前面的四种形式义务,正好将形式与实质的义务来源综合到了一起。
但是笔者认为自愿承担行为是与合同行为并列属于法律行为的,而不能说“自愿承担的义务包括合同签定的义务,行政委托的义务和公民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托付义务。

社科文化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王明戌(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000)摘 要:“无行为则无犯罪”是中外刑法学界的基本理念,且绝大多数法学家都赞同“行为”中包含作为与不作为两种行为方式。
尽管学说纷纭,但目前通说认为,不作为的行为性应根植于刑法规范,来源于对刑法命令性规范的违反,自此作为与不作为终于统一于违反刑法规范的概念之下。
但我国目前在不真正不作为犯义务领域只进行了形式上的规范,在程度、范围等实质性来源上并无详细的解释。
笔者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存在形式与实质的区分,应双管齐下,齐头并进。
形式作为义务来源回答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律依据 ,实质作为义务来源回答在形式的框架中行为人负有特殊义务的具体原因。
关键词:作为义务;形式义务论;实质义务论目前我国法学界绝大数学者的共识是,在逻辑思维层面上,作义务为于不作为犯而言,应当作为一种先决条件,这种认知对不作为犯的发展作用斐然。
我国刑法学理论界经历了因果关系说、违法性说和构成要件相当性说等学说之后,保证人说成为了目前的主流观点,也奠定了作为义务在不作为犯理论中的体系性地位。
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义务体现于命令性规范的规定,命令性规范,是指规定人们的积极义务,即人们必须或应当作出某种行为的规范,其在立法中的用语表达式为:“有……义务”“须得……”“应……”“必须……”等。
因此,当违反命令规范的积极义务时,便实施了不作为的实行行为。
这里所谓违反命令规范,主要就是指违反作为义务,因而违反作为义务就成为不作为的显性存在的标志。
正是通过违反作为义务这一规范要素,使不作为从物理上的“无”转变为法律上的“有”。
①由于法是一种复合性规范,同时包含禁止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一体两面。
因此,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从“无”到“有”就可以解释为,不纯正不作为犯因违反了法规范中的命令性规范,致其依照以作为形式规定的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被予以定罪量刑;进一步来讲,不纯正的不作为犯若违反命令性规范,则必然导致法规范的另一侧面-禁止性规范的被违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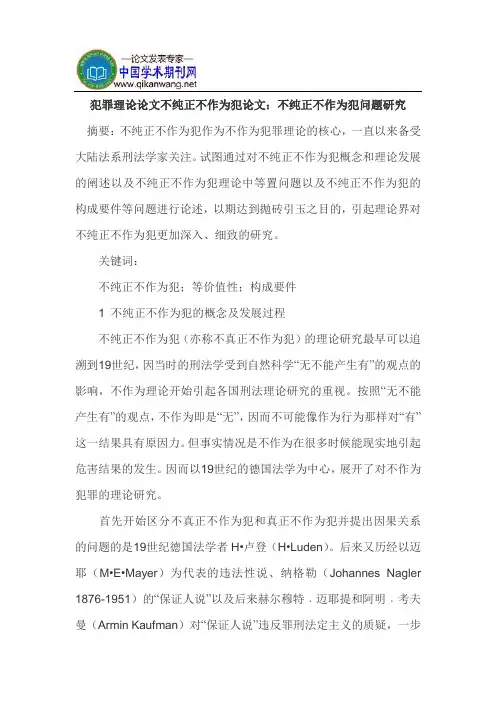
犯罪理论论文不纯正不作为犯论文:不纯正不作为犯问题研究摘要: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不作为犯罪理论的核心,一直以来备受大陆法系刑法学家关注。
试图通过对不纯正不作为犯概念和理论发展的阐述以及不纯正不作为犯理论中等置问题以及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论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引起理论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键词:不纯正不作为犯;等价值性;构成要件1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概念及发展过程不纯正不作为犯(亦称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因当时的刑法学受到自然科学“无不能产生有”的观点的影响,不作为理论开始引起各国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视。
按照“无不能产生有”的观点,不作为即是“无”,因而不可能像作为行为那样对“有”这一结果具有原因力。
但事实情况是不作为在很多时候能现实地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
因而以19世纪的德国法学为中心,展开了对不作为犯罪的理论研究。
首先开始区分不真正不作为犯和真正不作为犯并提出因果关系的问题的是19世纪德国法学者H•卢登(H•Luden)。
后来又历经以迈耶(M•E•Mayer)为代表的违法性说、纳格勒(Johannes Nagler 1876-1951)的“保证人说”以及后来赫尔穆特﹒迈耶提和阿明﹒考夫曼(Armin Kaufman)对“保证人说”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质疑,一步一步地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研究推向深入。
由此看来,不作为犯的理论研究比作为犯要复杂的多,而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不作为犯理论的核心,其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在不作为犯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个层次。
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不作为的一般概念。
刑法理论认为,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具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
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刑法亦没有作出规定,历来争论也比较大,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见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是“不为法律所期待的一定行为因而惹起一定结果发生的场合”,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在结果犯中才能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作为该当要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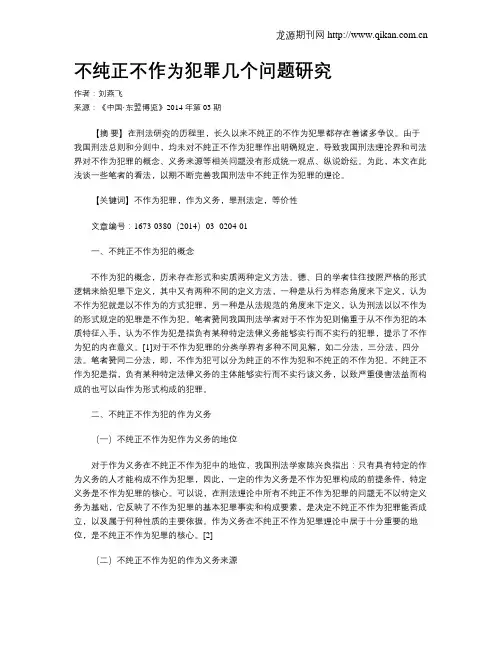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几个问题研究作者:刘燕飞来源:《中国·东盟博览》2014年第03期【摘要】在刑法研究的历程里,长久以来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罪都存在着诸多争议。
由于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中,均未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界对不作为犯罪的概念、义务来源等相关问题没有形成统一观点、纵说纷纭。
为此,本文在此浅谈一些笔者的看法,以期不断完善我国刑法中不纯正作为犯罪的理论。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罪刑法定,等价性文章编号:1673-0380(2014)03 -0204-01一、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概念不作为犯的概念,历来存在形式和实质两种定义方法。
德、日的学者往往按照严格的形式逻辑来给犯罪下定义,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一种是从行为样态角度来下定义,认为不作为犯就是以不作为的方式犯罪,另一种是从法规范的角度来下定义,认为刑法以以不作为的形式规定的犯罪是不作为犯。
笔者赞同我国刑法学者对于不作为犯则偏重于从不作为犯的本质特征入手,认为不作为犯是指负有某种特定法律义务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犯罪,提示了不作为犯的内在意义。
[1]对于不作为犯罪的分类学界有多种不同见解,如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
笔者赞同二分法,即,不作为犯可以分为纯正的不作为犯和不纯正的不作为犯。
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负有某种特定法律义务的主体能够实行而不实行该义务,以致严重侵害法益而构成的也可以由作为形式构成的犯罪。
二、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一)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地位对于作为义务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的地位,我国刑法学家陈兴良指出:只有具有特定的作为义务的人才能构成不作为犯罪,因此,一定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构成的前提条件,特定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
可以说,在刑法理论中所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问题无不以特定义务为基础,它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实和构成要素,是决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能否成立,以及属于何种性质的主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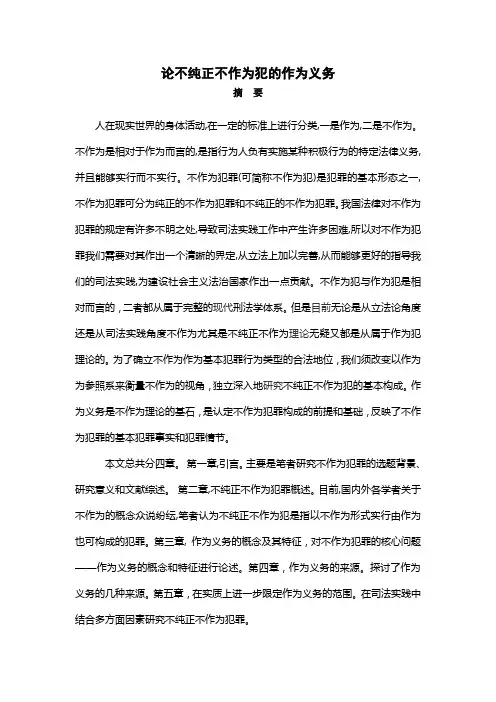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摘要人在现实世界的身体活动,在一定的标准上进行分类,一是作为,二是不作为。
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的,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
不作为犯罪(可简称不作为犯)是犯罪的基本形态之一, 不作为犯罪可分为纯正的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罪。
我国法律对不作为犯罪的规定有许多不明之处,导致司法实践工作中产生许多困难,所以对不作为犯罪我们需要对其作出一个清晰的界定,从立法上加以完善,从而能够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贡献。
不作为犯与作为犯是相对而言的,二者都从属于完整的现代刑法学体系。
但是目前无论是从立法论角度还是从司法实践角度不作为尤其是不纯正不作为理论无疑又都是从属于作为犯理论的。
为了确立不作为作为基本犯罪行为类型的合法地位,我们须改变以作为为参照系来衡量不作为的视角,独立深入地研究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基本构成。
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理论的基石,是认定不作为犯罪构成的前提和基础,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
本文总共分四章。
第一章,引言。
主要是笔者研究不作为犯罪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和文献综述。
第二章,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概述。
目前,国内外各学者关于不作为的概念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行由作为也可构成的犯罪。
第三章, 作为义务的概念及其特征,对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作为义务的概念和特征进行论述。
第四章,作为义务的来源。
探讨了作为义务的几种来源。
第五章,在实质上进一步限定作为义务的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结合多方面因素研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
[关键词]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义务特征义务来源The obligation of Impure OmissionAbstractPeople in the real world of physical activity, at a certain standard on the classification, first act, as the two are not. Are compared with the omission of an act, people are referring to acts of affirmative conduct has specific legal obligations, and be able to implement rather than a. Not as a crime (which can be referred to not as committed) is one of the basic form of crime, not as a crime can be divided into pure and not as a crime not as a pure crime. Our country as the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do not have much of the unknown, leading to judicial practice have a lot of difficult work, so do not as a crime we need to make a clear definition, be improved on from the legislation, which can better guide U.S.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build a socialist country 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rule of law. Not as guilty as guilty are relative, both subordinate to the complete study of modern criminal law system. However, whether it is from the legislative point of view or theory of judici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mission are not pure in particular omission is no doubt they are subordinate to the theory as a theory committed. No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s criminal acts as the basic types of legal status, we have to change as a frame of reference to measure the omission perspective, independent and in-depth study of non-pure omission committed a basic component. As the obligations are not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theory, are found not to constitute a crime as a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reflecting the omission of basic crime crim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crime.In this paper, a total of four chapters. Chapter I, Introduction. The author are not the main research topics as crime,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and literature review. Chapter II, non-pure omissions outlined crime. At present, various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bout the concept not as diverse, I do not think pure omission refers to the omission by the way, taking into account as may also constitute crimes. Chapter III, as the concept of obliga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the core problem as a crime - as an obligation on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Chapter IV, as a source of obligations. Of several sources as an obligation. Chapter V, in essence, as a furtherlimit the scope of the obligation. At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ombin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is not pure research is not considered a crime.Key words:Impure Omission obligation Obligatio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urce of obligations目录导言 (1)(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1)(二)现有文献综述 (1)一、不纯正不作为犯概述 (3)二、作为义务的概念及其特征 (4)1. 概念 (4)2.特征:(一)具有会发生危害结果的迫切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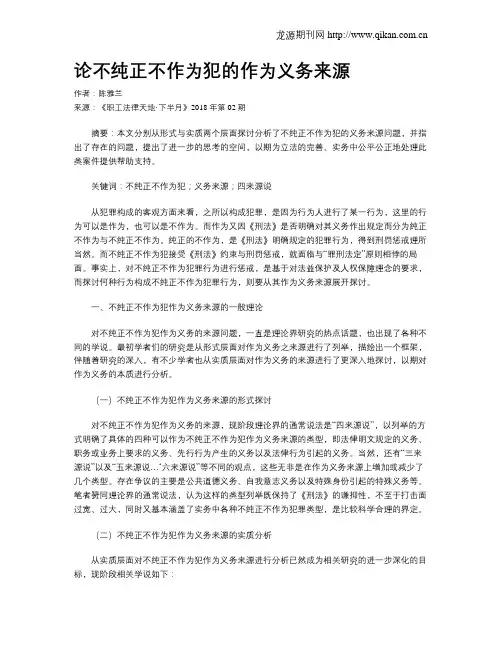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作者:陈雅兰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8年第02期摘要:本文分别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探讨分析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问题,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的空间,以期为立法的完善、实务中公平公正地处理此类案件提供帮助支持。
关键词: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四来源说从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来看,之所以构成犯罪,是因为行为人进行了某一行为,这里的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而作为又因《刑法》是否明确对其义务作出规定而分为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
纯正的不作为,是《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得到刑罚惩戒理所当然。
而不纯正不作为犯接受《刑法》约束与刑罚惩戒,就面临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的局面。
事实上,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行为进行惩戒,是基于对法益保护及人权保障理念的要求,而探讨何种行为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行为,则要从其作为义务来源展开探讨。
一、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一般理论对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来源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学说。
最初学者们的研究是从形式层面对作为义务之来源进行了列举,描绘出一个框架,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不少学者也从实质层面对作为义务的来源进行了更深入地探讨,以期对作为义务的本质进行分析。
(一)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形式探讨对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来源,现阶段理论界的通常说法是“四来源说”,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具体的四种可以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类型,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
当然,还有“三来源说”以及“五来源说…‘六来源说”等不同的观点,这些无非是在作为义务来源上增加或减少了几个类型。
存在争议的主要是公共道德义务、自我意志义务以及特殊身份引起的特殊义务等。
笔者赞同理论界的通常说法,认为这样的类型列举既保持了《刑法》的谦抑性,不至于打击面过宽、过大,同时又基本涵盖了实务中各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类型,是比较科学合理的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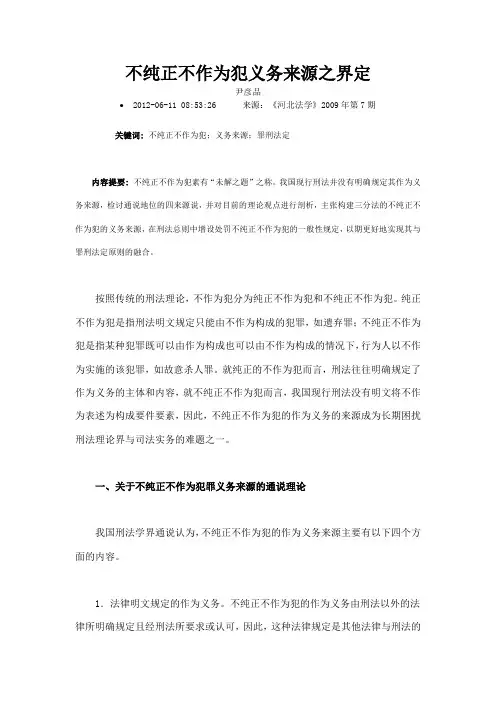
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之界定尹彦品2012-06-11 08:53:26 来源:《河北法学》2009年第7期关键词: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罪刑法定内容提要:不纯正不作为犯素有“未解之题”之称。
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作为义务来源,检讨通说地位的四来源说,并对目前的理论观点进行剖析,主张构建三分法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在刑法总则中增设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一般性规定,以期更好地实现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融合。
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不作为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
纯正不作为犯是指刑法明文规定只能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如遗弃罪;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某种犯罪既可以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的情况下,行为人以不作为实施的该犯罪,如故意杀人罪。
就纯正的不作为犯而言,刑法往往明确规定了作为义务的主体和内容,就不纯正不作为犯而言,我国现行刑法没有明文将不作为表述为构成要件要素,因此,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来源成为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的难题之一。
一、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通说理论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由刑法以外的法律所明确规定且经刑法所要求或认可,因此,这种法律规定是其他法律与刑法的双重性规定。
如果仅有其他法律规定而无刑法的要求或认可,则不得成为刑法上的作为义务{1}。
2.职务上或业务上所要求的义务。
所谓职务上或业务上所要求的义务是指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因其职务或业务本身要求其负有某种作为的义务。
例如:医生有救治病人的义务,工人有按规定安全生产的义务,消防队员有灭火的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人只有在担任此职务或从事此行业的工作期间才负有相应的义务,但也有例外。
如:我国《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对警察义务的履行不分工作与非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只要从事警察这一职业就应该履行警察义务,并无时间、地点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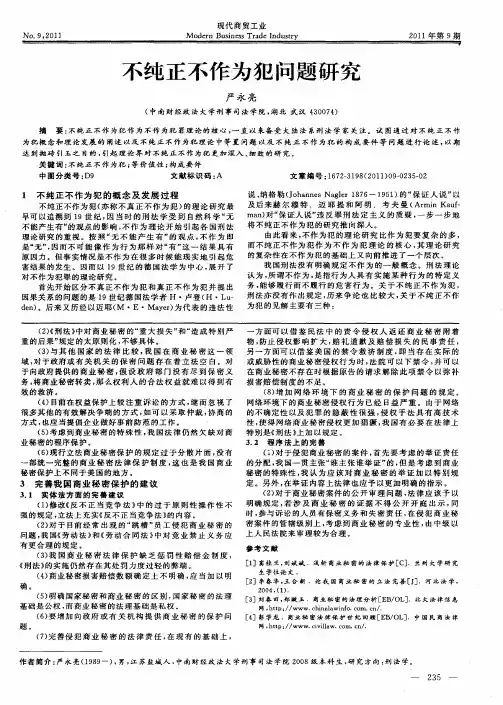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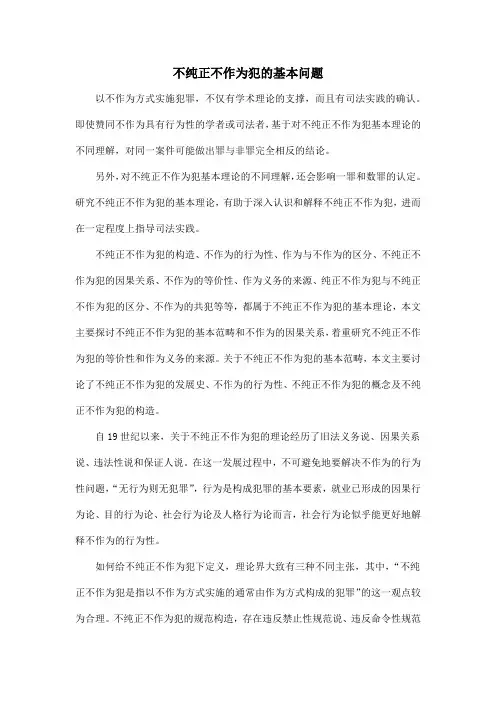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基本问题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犯罪,不仅有学术理论的支撑,而且有司法实践的确认。
即使赞同不作为具有行为性的学者或司法者,基于对不纯正不作为犯基本理论的不同理解,对同一案件可能做出罪与非罪完全相反的结论。
另外,对不纯正不作为犯基本理论的不同理解,还会影响一罪和数罪的认定。
研究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基本理论,有助于深入认识和解释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司法实践。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造、不作为的行为性、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不作为的等价性、作为义务的来源、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区分、不作为的共犯等等,都属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基本理论,本文主要探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基本范畴和不作为的因果关系,着重研究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和作为义务的来源。
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基本范畴,本文主要讨论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发展史、不作为的行为性、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概念及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造。
自19世纪以来,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理论经历了旧法义务说、因果关系说、违法性说和保证人说。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解决不作为的行为性问题,“无行为则无犯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基本要素,就业已形成的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及人格行为论而言,社会行为论似乎能更好地解释不作为的行为性。
如何给不纯正不作为犯下定义,理论界大致有三种不同主张,其中,“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通常由作为方式构成的犯罪”的这一观点较为合理。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规范构造,存在违反禁止性规范说、违反命令性规范说、既违反禁止性规范又违反命令性规范说之争。
命令性规范属于义务规范,从另一角度看,禁止性规范也当属于义务规范。
可以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违反了义务规范。
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学说,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有否定说、准因果关系说和肯定说,我国刑法理论存在消极说和积极说之争。
因果关系一直被认为犯罪成立的必要要素,尽管部分学者主张以客观归责代替因果关系,但应当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定罪必不可少的环节。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作者:史梅梅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4年第06期【典型案例】2008年12月24日下午,被告人陈某约涂某到其家中卖淫。
晚六时许,涂某称身体不太舒服,但两人仍然进行卖淫嫖娼行为。
后涂某称身体更不舒服,且其脸色开始变黄。
其间,陈某帮涂某揉了太阳穴约二、三分钟。
陈某意识到涂某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怕嫖娼的事情败露,并未采取送涂某上医院或拨打“120”求助电话等积极措施予以施救。
晚九时许,涂某已无法开口说话,眼睛翻白,嘴巴微微张开,手脚不能动弹。
晚十点半左右,涂某眼睛上翻、嘴巴张开并留出泡沫状的液体,但身体还有温度。
陈某见状即找来绳子和木梯,将涂某转移到山上丢弃。
在移动过程中,涂某两边肋部被擦伤,头顶部被碰伤。
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涂某系左心功能不全、并发室性心律失常死亡。
同时,经某医院检验病理科病理诊断,涂某头部及腋下的伤均系生前伤,但并非主要致死原因,应视为加速死亡的原因。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与涂某在自己家实施卖淫嫖娼行为,在涂某有生命危险之际,陈某有实施救助的作为义务,但其因为害怕事情败露,并未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反倒将其转移到山上丢弃,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被告人服判,未上诉。
一、形式来源论下的作为义务分析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存在形式来源论和实质来源论的区分。
就形式来源论而言,我国大陆地区代表性的观点有:三来源说,即法律明文规定;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先前的行为。
[1]四来源说,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
[2]五来源说,即法律的明文规定;职务和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的先行行为;自愿承担的某种特定义务;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
[3]而实质来源论,德、日等国在该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如德国的功能说、依赖关系和信赖关系学说,日本的危险前行为说、开放和闭锁的关系说等。
不作为犯罪中“法律义务”内涵探究作者:曹小青张国伟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1年第04期【摘要】特定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要素,不作为犯罪必须以行为人负有某种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为前提。
在当今各国刑法理论中,对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都普遍强调只能限于法律义务,而不包括道德义务,在此对法律义务的内涵进行了层层递进的深入探究。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法律义务作为义务内涵作为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必须以行为人负有某种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为前提,作为义务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实和构成要素,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要素。
可以说,在不作为犯罪的研究领域,所有的问题无不以特定义务为基础。
因此,作为义务在不作为犯罪中居最重要的地位。
作为义务的来源指的是作为义务产生的根据,纯正不作为犯罪中,其作为义务可以由分则条文的规定中明确推知,因此,理论界不存在争论。
刑法学界关于作为义务来源的争论大都是围绕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而展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经过刑法理论学界与实务界判例的确认,法律义务、契约义务、先行行为义务并称为作为义务的三大来源。
这种作为义务形式的三来源说成为形式的作为义务理论的基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德日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对后来的德国刑法学界以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以三来源说为基础,学说与判例又扩大了作为义务的来源范围,将交易上的诚信义务、自愿承担的义务、场所及危险物的持有等也作为作为义务的来源,但是在学说上仍然存在着争议。
人们对法律义务的理解并不一致,持严格的形式作为义务来源说的学者往往将作为义务只限定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范围甚至只能是刑法规定的义务;而有的则对法律义务作了扩大化的理解,将超法规的基于道德或者习惯产生的义务都视为法律义务。
这势必引发了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法律义务是否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根据德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必须依法负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但是一般认为,在解释上不以明文的法规为限,还包括一般的法律原则在内,只是纯粹的道德义务不在其列。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理论考察作者:杨燮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04期摘要刑法理论中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其构成要件由于缺乏规范的明示,使得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一直是刑法理论的一个困惑。
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构成要件特殊性的分析,以揭示对作为义务的限定是完成其构成要件补充的核心要素,并提出从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和实质根据两方面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进行充分的限定。
关键词不纯正不作为犯构成要件理论考察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2-020-03刑法理论从危害行为的客观形态出发,将犯罪划分为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不作为犯中又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
纯正不作为犯是指只能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如遗弃罪等,而不纯正不作为犯乃以不作为形式而犯通常以作为形式实施的犯罪,如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故意杀人罪、放火罪等。
对于纯正不作为犯的认定,由于刑法明文规定了其构成要件,故争议不大。
但就不纯正不作为犯而言,由于“刑法对各种罪多依作为而规定,至于与其相当之不作为则不设明文,而有待于审判者个别认定”,正因缺乏规范的明示,而各国刑法学界相关的理论和判例又各见仁智,使得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一直是刑法理论的一个困惑。
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构成要件特殊性的分析,以揭示对作为义务的限定是完成其构成要件补充的核心要素,并提出从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和实质根据两方面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进行充分的限定。
一、作为义务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核心要素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有以下要素:(1)行为人有作为义务;(2)行为人没有履行义务;(3)发生了危害结果;(4)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作为义务的界定,即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何种主体在何种情况下负有防止的义务。
如何理解这一核心要素,须从不纯正不作为犯构成要件的特殊性进行分析。
通常认为,以作为形式实施的绝大多数犯罪,同时也可以由不阻止结果发生的不作为实施,只要行为人具有阻止这一结果发生的法律、义务。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研究【摘要】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应当是对法益安全造成了现实、具体、紧迫危险的行为,先行行为具有直接性、高概然性、临近性三个特征。
原则上,先行行为应当以违反法律规范为前提。
但是,在对行为人施加作为义务不与刑法的其他更高价值追求相违背的前提下,合法的先行行为也能够引起作为义务。
在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前提下,应当肯定犯罪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
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自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既可以是故意或者过失行为,也可以是无责任行为。
【关键词】不纯正不作为犯;先行行为;作为义务;范围一、先行行为义务的含义在大陆法系不作为犯罪的学说史中,先行行为(Ingerenz)是继法律、合同之后提出的第三种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
19世纪的前30年,先行行为保证人义务只是出现在个别案件中,很长时间是为了填补法律义务和合同义务的不足,堵塞不纯正不作为犯处罚的漏洞而发挥作用,后来成为一条基本的原则,即实施危险行为者,有义务消除自己造成的危险。
[1]英美刑法也肯定先行行为的义务来源,称其为“Crea-tion of danger”或“Danger caused by defendant”(引起危险),即如果被告人造成了危险状态而没有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法庭认定被告人有作为义务。
英国刑法中曾有过这样的判例:一个流浪者在一所空房子里睡觉。
他在睡觉时抽烟,烟引着了床垫子。
流浪者警醒后发现着火,没有采取任何扑救措施就挪到另一个房间。
结果房子被烧着,造成了重大损失,流浪者被判构成放火罪。
[2]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将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表述为:“由于本人的行为而使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处于危险状态,行为人就负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排除这种危险的义务。
”[3]为了肯定先前行为人的作为义务,先行行为造成的法益危险状态应当是现实而紧迫的危险,即如果不实施一定的作为,危害结果很快就会发生。
在德国,“危险的迫近现在一般被判例作为一个前提条件”。
[4]我国台湾学者洪福增也主张,先行行为的危险应当限定为“迫切”及“具体危险”的情形,理由是:“如以抽象的危险为以足者,则其范围似嫌过广,且有与将不纯正不作为犯同等(同价值性),应以具有一定的条件为限,以避免有过分的扩张处罚范围之旨趣相违背。
”[5]笔者赞同这种见解。
实际中,行为人实施一定行为之后发生法益危险的情况相当复杂,并不是任何情况下的不作为都可能产生类似作为犯的社会危害内容。
由于犯罪实行行为的实质属性是“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6]不作为是实行行为的表现形态,因此,对法益的侵害也应当具有“现实的危险”。
所以,只有先行行为对法益安全造成了现实、具体、紧迫的危险,行为人才能处于保证人地位,其不作为才能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罪。
笔者认为,在司法中,对先行行为危险的限定,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1)直接性。
即先行行为直接导致了法益损害的危险,而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如果先行行为只是对危险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或提供了契机,而由其他因素直接导致危险发生,行为人不负作为义务。
例如,甲过失引起乙的自杀意图,甲即便在乙自杀时故意不救助,也不构成杀人罪的不作为犯,因为乙的生命危险是由其自杀行为直接引起的,而非甲的行为直接造成的。
(2)高概然性。
即先行行为在自然属性上,客观地具有引起危险状态的高度可能性,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偶然引起了法益的危险,一般应当排除作为义务的存在。
比如,甲因琐事争执而辱骂乙,乙碰巧是严重心脏病患者,乙被辱骂后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产生生命危险,甲并没有救助乙生命的义务。
(3)临近性。
即法益危险与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具有时间、空间上的密接联系,而非“遥远”的联系。
比如,甲在旅游中不慎将乙撞落山沟,乙在山沟内生存10天后,因为得不到救助死亡,甲即便有救助能力,也不构成杀人罪的不作为犯。
据此,那种认为丈夫与妻子吵架后,妻子自杀,丈夫不予制止,丈夫便构成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的不作为杀人罪的观点,显然过分地扩大了先行行为的范围。
二、先行行为义务的学理根据与限制关于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外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务中有三种处理模式:第一,不纯正不作为犯模式。
即将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来源,对违反先行行为义务的,按照不纯正不作为犯处罚。
其中,有的国家或地区在刑法典总则中对先行行为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如西班牙刑法、韩国刑法、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等;[7]有的虽然没有进行立法规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将其作为一种法律义务,对违反义务者按照杀人罪、伤害罪等的不作为犯处罚,如德国刑法、日本刑法等。
第二,纯正不作为犯模式。
即将违反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的情形在刑法分则条文中作出独立规定,按照纯正不作为犯处罚。
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25条规定:“明知他人处于有生命或健康危险的状况而且因为年幼、衰老或孤立无援不能采取措施自救而不给予救助,如果犯罪人有可能对该人给予救助并对他负有照顾义务,或者是犯罪人自己使之处于有生命或健康危险的状态之中的”构成见危不救罪,最高处一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财产刑。
[8]其中“犯罪人自己使之处于有生命或健康危险的状态之中的”就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第三,不处罚。
即既不将先行行为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也不以纯正不作为犯的形式处罚违背先行行为义务的行为。
如意大利刑法中,除了分则条文的个别规定外,原则上行为人本身的先行行为不能成为阻止危险义务的渊源,法律制度不承认这种渊源。
[9]理论上,关于先行行为能否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来源,目前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也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意见的对立:第一,肯定说。
即认为先行行为是引起作为义务的根据,如果行为人违反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应当以不纯正不作为犯处罚。
如德国学者Hruschka认为,如果有义务不造成某种不被期待的现象,那么自己违反不作为义务而造成那种现象有发生的危险时,也有义务阻止任何不被期待的现象发生。
而前行为的保证人类型是所有安全义务类型中最典型的类型,安全义务正是源于前行违反义务的行为,其他安全义务类型都是从前行为保证人这种基本类型类推出来的。
[10]日本学者日高义博甚至主张只有先行行为才能引起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而否认其他的义务来源。
他认为,只有不作为人在其不作为之前,自己就设定了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才可以与作为行为在法律上“等置”,假如不作为人并没有设定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就不能以作为犯的构成要件处罚不作为人,非要处罚不可的,应采取立法措施以纯正不作为犯处罚。
[11] 第二,否定说。
即认为先行行为不能成为不纯正不作为犯中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对违反“先行行为义务”的行为,不能以“作为犯”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形态处罚。
持否定说的学者提出的理由不尽相同。
德国学者阿敏·考夫曼(Armin Kaufmann)的理由是两点:(1)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法理结构误植于因果作用上,变成了一种习惯法上的法义务;(2)前行为的义务类型可以经由立法成为一种法定的,而不是习惯法的法义务,但违背此种义务只能成立纯正的不作为犯,因为前行为后的不作为不可能和作为等价,光是因为前行为可能造成结果发生的危险,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保证人类型,除非再加上其他能满足等价性要求的条件类型。
[12]日本学者西田典之将先行行为从作为义务根据中排除的理由是:首先,先行行为在多数场合,是作为过失犯、结果加重犯被处理了。
再以此为根据而追究行为人更重的罪责,是不当的二重处罚。
其次,在此种情况中,作为作为义务事实前提的支配领域性,是随具体情况而变化的,即与交通肇事后逃走、失火等现场的具体情况相应而左右犯罪的成立。
因此,一时的或偶然的情况下,不作为者的立场是极不安定的,有害于法的稳定性。
[13]我国台湾学者许玉秀也竭力反对将先行行为义务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义务类型。
她认为,依据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法理所拟制出来的不作为,在规则流程中不是毫无意义,就是和结果加重犯相重叠,因此这种保证人类型没有实用价值,台湾地区刑法典应当取消第15条第2项先行行为义务的规定。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和司法实务对先行行为义务都采取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理模式,肯定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是一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类型。
在我国刑法中,“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使某种合法权益处在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状态,该行为人产生采取积极行动阻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
[14]但是,近年也有学者提出否定先行行为义务观点,论者所持的理由与上述否定说大同小异。
[15]笔者认为,在理论上一概肯定先行行为义务,认为只要由于自己的行为使法益处于危险状态而不救助就一定在司法中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或者完全否定先行行为义务,在司法中对先行行为的情形一律以作为犯、过失犯或者结果加重犯处罚的观点都是片面的。
在笔者看来,如果行为人以自己的行为制造导致危害结果的自然原因力,而后在能够阻止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基于故意或过失心理不阻止结果发生,虽然故意或过失产生于制造自然原因力的行为(先行行为)之后,行为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与主观可责程度都与一般的作为犯相差无几,不论从法律公正的角度考察,还是从防止危害发生的刑事政策立场出发,都应当予以处罚。
但是,这时由于罪过心理产生于自然的危险行为(先行行为)之后,不能以先行行为的作为犯处罚,于是只能取道事后不作为的途径以不纯正不作为犯处罚。
因此,原则上应当肯定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认为先行行为义务不是法律义务,违背先行行为义务产生不了与作为犯等价的危害性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否定说反对先行行为义务有两个基本理由:一是在先行行为义务的情形里,先行行为是造成最终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先行行为之后,行为人只是针对结果增加了犯意,并没有透过客观的积极力量促成其追加意志的实现,案件中的因果流程只有一个,如果既成立先行行为自身的犯罪,又成立其后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是将一个因果关系截成两段,进行了重复评价,因此,一般应当以先行行为自身处罚;二是对先行行为和事后不作为侵害不同法益的犯罪,由于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先行行为犯罪的结果加重犯,应当径直以结果加重犯处罚,无需借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理论。
笔者认为,这两种理由均值得商榷。
首先,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与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具有不同的实质意义和内容。
作为犯中的因果关系是自然意义的,具有事实的和客观的内容,而不作为犯中的因果关系表现为对既存因果进程的不中断,是社会和规范意义的,没有客观实在内容。
不作为行为原因力的产生和存在,不需要行为人制造物质性的力量。
在先行行为的案件中,不能因为事后不阻止结果发生的行为没有产生“客观的积极力量”就否认社会意义的因果关系的存在,进而认为全案中只有先行行为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力,只存在一个“因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