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身份焦虑——读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
- 格式:pdf
- 大小:249.8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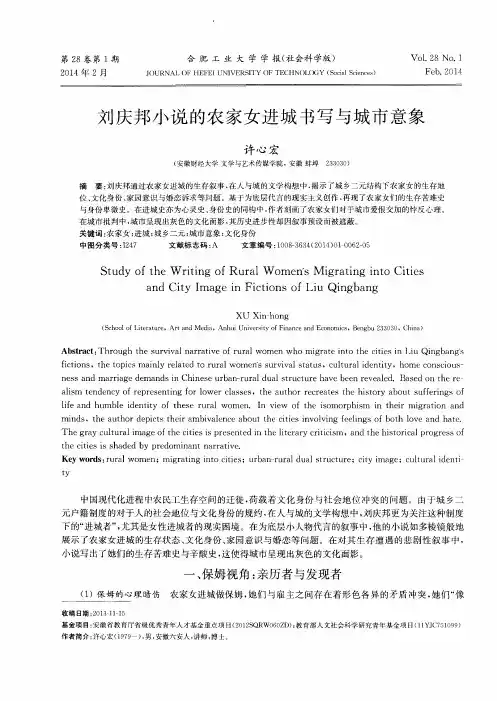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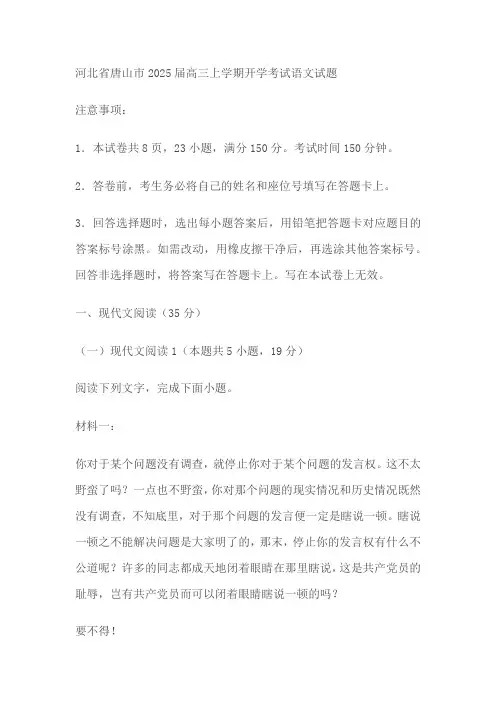
河北省唐山市2025届高三上学期开学考试语文试题注意事项:1.本试卷共8页,23小题,满分150分。
考试时间150分钟。
2.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3.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1(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列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
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
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
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
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
这是懦夫讲的话。
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
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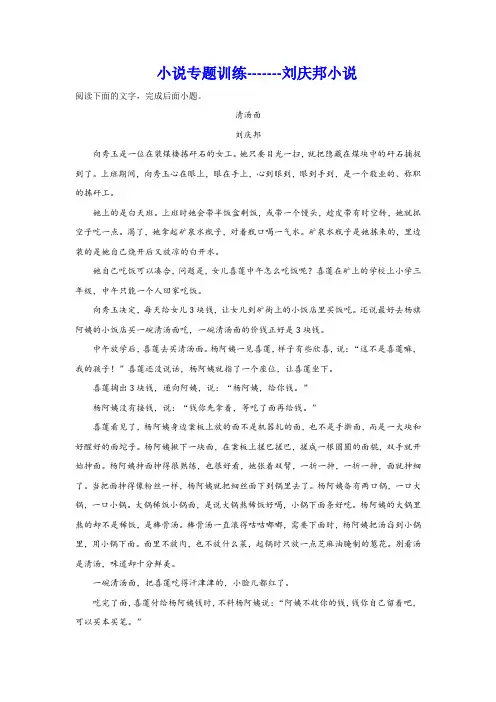
小说专题训练-------刘庆邦小说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清汤面刘庆邦向秀玉是一位在装煤楼拣矸石的女工。
她只要目光一扫,就把隐藏在煤块中的矸石捕捉到了。
上班期间,向秀玉心在眼上,眼在手上,心到眼到,眼到手到,是一个敬业的、称职的拣矸工。
她上的是白天班。
上班时她会带半饭盒剩饭,或带一个馒头,趁皮带有时空转,她就抓空子吃一点。
渴了,她拿起矿泉水瓶子,对着瓶口喝一气水。
矿泉水瓶子是她拣来的,里边装的是她自己烧开后又放凉的白开水。
她自己吃饭可以凑合,问题是,女儿喜莲中午怎么吃饭呢?喜莲在矿上的学校上小学三年级,中午只能一个人回家吃饭。
向秀玉决定,每天给女儿3块钱,让女儿到矿街上的小饭店里买饭吃。
还说最好去杨旗阿姨的小饭店买一碗清汤面吃,一碗清汤面的价钱正好是3块钱。
中午放学后,喜莲去买清汤面。
杨阿姨一见喜莲,样子有些欣喜,说:“这不是喜莲嘛,我的孩子!”喜莲还没说话,杨阿姨就指了一个座位,让喜莲坐下。
喜莲掏出3块钱,递向阿姨,说:“杨阿姨,给你钱。
”杨阿姨没有接钱,说:“钱你先拿着,等吃了面再给钱。
”喜莲看见了,杨阿姨身边案板上放的面不是机器轧的面,也不是手擀面,而是一大块和好醒好的面坨子。
杨阿姨揪下一块面,在案板上搓巴搓巴,搓成一根圆圆的面棍,双手就开始抻面。
杨阿姨抻面抻得很熟练,也很好看,她张着双臂,一折一抻,一折一抻,面就抻细了。
当把面抻得像粉丝一样,杨阿姨就把细丝面下到锅里去了。
杨阿姨备有两口锅,一口大锅,一口小锅。
大锅稀饭小锅面,是说大锅熬稀饭好喝,小锅下面条好吃。
杨阿姨的大锅里熬的却不是稀饭,是棒骨汤。
棒骨汤一直滚得咕咕嘟嘟,需要下面时,杨阿姨把汤舀到小锅里,用小锅下面。
面里不放肉,也不放什么菜,起锅时只放一点芝麻油腌制的葱花。
别看汤是清汤,味道却十分鲜美。
一碗清汤面,把喜莲吃得汗津津的,小脸儿都红了。
吃完了面,喜莲付给杨阿姨钱时,不料杨阿姨说:“阿姨不收你的钱,钱你自己留着吧,可以买本买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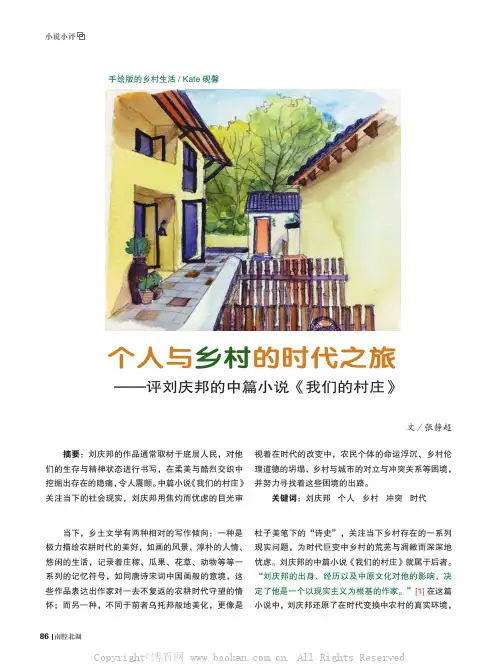
86南腔北调手绘版的乡村生活/ Kate砚馨——评刘庆邦的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文/张静超个人与乡村的时代之旅摘要:刘庆邦的作品通常取材于底层人民,对他们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进行书写,在柔美与酷烈交织中挖掘出存在的隐痛,令人震颤。
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刘庆邦用焦灼而忧虑的目光审视着在时代的改变中,农民个体的命运浮沉、乡村伦理道德的坍塌、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与冲突关系等困境,并努力寻找着这些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刘庆邦 个人 乡村 冲突 时代当下,乡土文学有两种相对的写作倾向:一种是极力描绘农耕时代的美好,如画的风景、淳朴的人情、悠闲的生活,记录着庄稼、瓜果、花草、动物等等一系列的记忆符号,如同唐诗宋词中国画般的意境,这些作品表达出作家对一去不复返的农耕时代守望的情怀;而另一种,不同于前者乌托邦般地美化,更像是杜子美笔下的“诗史”,关注当下乡村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为时代巨变中乡村的荒芜与凋敝而深深地忧虑。
刘庆邦的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就属于后者。
“刘庆邦的出身、经历以及中原文化对他的影响,决定了他是一个以现实主义为根基的作家。
”[1]在这篇小说中,刘庆邦还原了在时代变换中农村的真实环境,87南腔北调小说《我们的村庄》中的主人公叶海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恶棍,敲诈勒索、盗取财物、殴打老婆、不孝顺父母、不尊敬长辈……这种蛮横无理、盛气凌人的背后,掩藏的是一个农民堕落的痛苦与无奈。
从这一点上讲,叶海阳是可恶的,也是可怜的。
很多时候,作家的写作动机在于制造一个悬念,这个悬念必须是可以解释的,否则作家自己便走入了一个自己设计的陷阱。
小说一开始的悬念是叶海阳为什么会堕落?而后刘庆邦在徐徐展开的文本中告诉了读者答案。
叶海阳小时候家境优越,父亲叶挺坚是公社粮店的会计,靠着手头的权力成为村中的小康之家,叶海阳也是村中孩子之中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因为父亲的财富与威望,叶海阳娶了妻,在生产队担任要职。
然而父亲退休之后,叶家走向了下坡路,二亩薄田难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冻馁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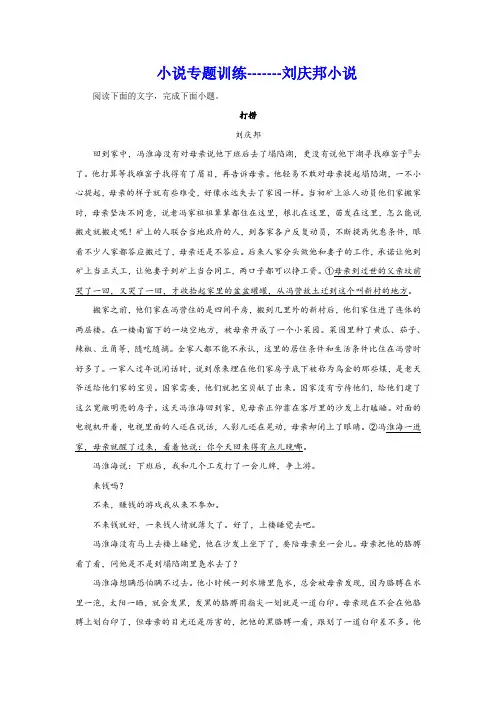
小说专题训练-------刘庆邦小说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打捞刘庆邦回到家中,冯淮海没有对母亲说他下班后去了塌陷湖,更没有说他下湖寻找碓窑子①去了。
他打算等找碓窑子找得有了眉目,再告诉母亲。
他轻易不敢对母亲提起塌陷湖,一不小心提起,母亲的样子就有些难受,好像永远失去了家园一样。
当初矿上派人动员他们家搬家时,母亲坚决不同意,说老冯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根扎在这里,苗发在这里,怎么能说搬走就搬走呢!矿上的人联合当地政府的人,到各家各户反复动员,不断提高优惠条件,眼看不少人家都答应搬迁了,母亲还是不答应。
后来人家分头做他和妻子的工作,承诺让他到矿上当正式工,让他妻子到矿上当合同工,两口子都可以挣工资。
①母亲到过世的父亲坟前哭了一回,又哭了一回,才收拾起家里的盆盆罐罐,从冯营故土迁到这个叫新村的地方。
搬家之前,他们家在冯营住的是四间平房,搬到几里外的新村后,他们家住进了连体的两层楼。
在一楼南窗下的一块空地方,被母亲开成了一个小菜园。
菜园里种了黄瓜、茄子、辣椒、豆角等,随吃随摘。
全家人都不能不承认,这里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比住在冯营时好多了。
一家人过年说闲话时,说到原来埋在他们家房子底下被称为乌金的那些煤,是老天爷送给他们家的宝贝。
国家需要,他们就把宝贝献了出来。
国家没有亏待他们,给他们建了这么宽敞明亮的房子。
这天冯淮海回到家,见母亲正仰靠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打瞌睡。
对面的电视机开着,电视里面的人还在说话,人影儿还在晃动,母亲却闭上了眼睛。
②冯淮海一进家,母亲就醒了过来,看着他说:你今天回来得有点儿晚哪。
冯淮海说:下班后,我和几个工友打了一会儿牌,争上游。
来钱吗?不来,赚钱的游戏我从来不参加。
不来钱就好,一来钱人情就薄欠了。
好了,上楼睡觉去吧。
冯淮海没有马上去楼上睡觉,他在沙发上坐下了,要陪母亲坐一会儿。
母亲把他的胳膊看了看,问他是不是到塌陷湖里凫水去了?冯淮海想瞒恐怕瞒不过去。
他小时候一到水塘里凫水,总会被母亲发现,因为胳膊在水里一泡,太阳一晒,就会发黑,发黑的胳膊用指尖一划就是一道白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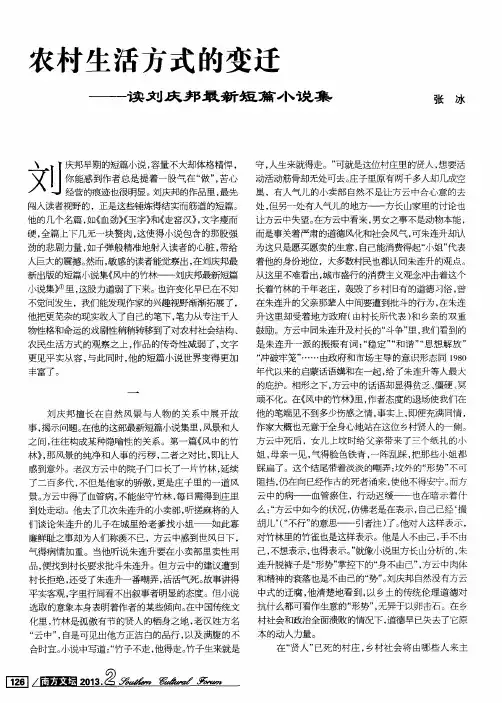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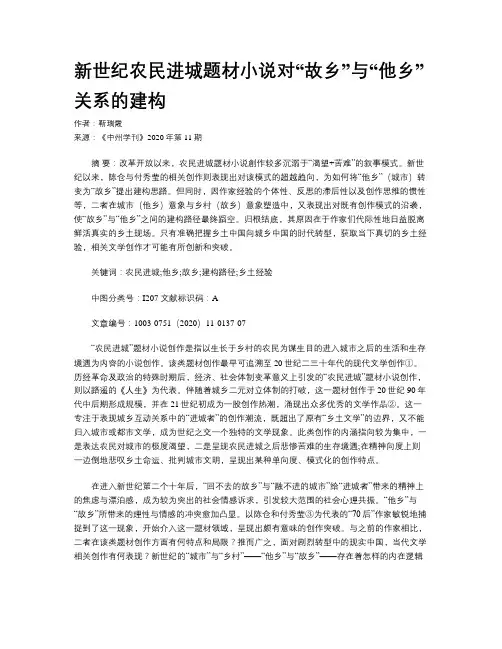
新世纪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对“故乡”与“他乡”关系的建构作者:靳瑞霞来源:《中州学刊》2020年第11期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創作较多沉溺于“渴望+苦难”的叙事模式。
新世纪以来,陈仓与付秀莹的相关创作则表现出对该模式的超越趋向,为如何将“他乡”(城市)转变为“故乡”提出建构思路。
但同时,因作家经验的个体性、反思的滞后性以及创作思维的惯性等,二者在城市(他乡)意象与乡村(故乡)意象塑造中,又表现出对既有创作模式的沿袭,使“故乡”与“他乡”之间的建构路径最终蹈空。
归根结底,其原因在于作家们代际性地日益脱离鲜活真实的乡土现场。
只有准确把握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时代转型,获取当下真切的乡土经验,相关文学创作才可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关键词:农民进城;他乡;故乡;建构路径;乡土经验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1-0137-07“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是指以生长于乡村的农民为谋生目的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和生存境遇为内容的小说创作。
该类题材创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创作①。
历经革命及政治的特殊时期后,经济、社会体制变革意义上引发的“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则以路遥的《人生》为代表。
伴随着城乡二元对立体制的打破,这一题材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规模,并在21世纪初成为一股创作热潮,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②。
这一专注于表现城乡互动关系中的“进城者”的创作潮流,既超出了原有“乡土文学”的边界,又不能归入城市或都市文学,成为世纪之交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
此类创作的内涵指向较为集中,一是表达农民对城市的极度渴望,二是呈现农民进城之后悲惨苦难的生存境遇;在精神向度上则一边倒地悲叹乡土命运、批判城市文明,呈现出某种单向度、模式化的创作特点。
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回不去的故乡”与“融不进的城市”给“进城者”带来的精神上的焦虑与漂泊感,成为较为突出的社会情感诉求,引发较大范围的社会心理共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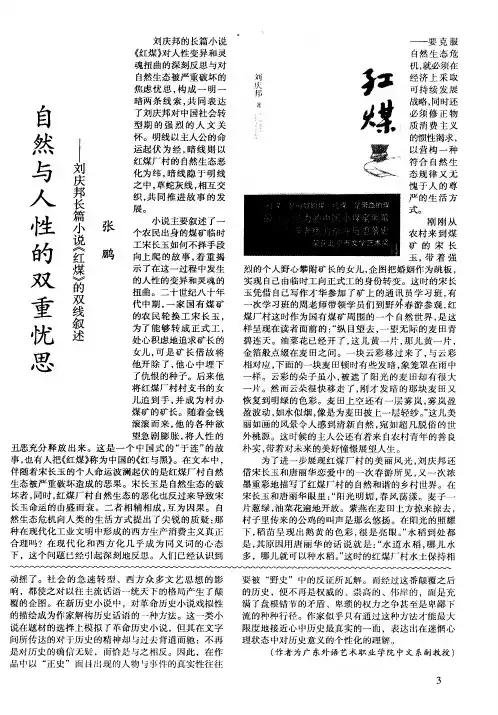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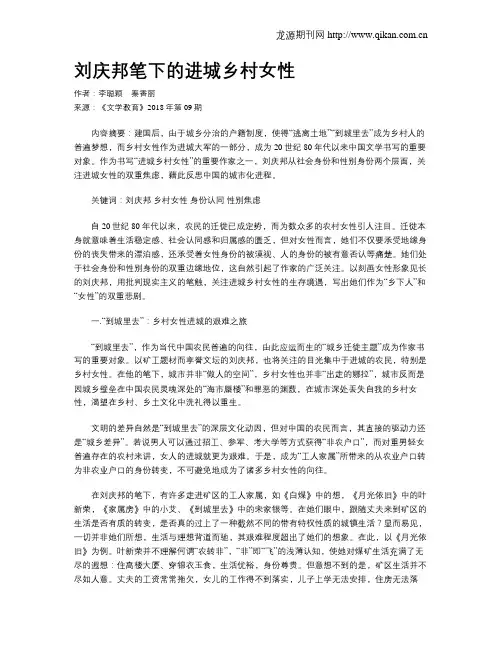
刘庆邦笔下的进城乡村女性作者:李聪颖秦香丽来源:《文学教育》2018年第09期内容摘要:建国后,由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使得“逃离土地”“到城里去”成为乡村人的普遍梦想,而乡村女性作为进城大军的一部分,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
作为书写“进城乡村女性”的重要作家之一,刘庆邦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两个层面,关注进城女性的双重焦虑,藉此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刘庆邦乡村女性身份认同性别焦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的迁徙已成定势,而为数众多的农村女性引人注目。
迁徙本身就意味着生活稳定感、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匮乏,但对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承受地缘身份的丧失带来的漂泊感,还承受着女性身份的被漠视、人的身份的被有意否认等痛楚。
她们处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双重边缘地位,这自然引起了作家的广泛关注。
以刻画女性形象见长的刘庆邦,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关注进城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写出她们作为“乡下人”和“女性”的双重悲剧。
一.“到城里去”:乡村女性进城的艰难之旅“到城里去”,作为当代中国农民普遍的向往,由此应运而生的“城乡迁徙主题”成为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
以矿工题材而享誉文坛的刘庆邦,也将关注的目光集中于进城的农民,特别是乡村女性。
在他的笔下,城市并非“做人的空间”,乡村女性也并非“出走的娜拉”,城市反而是因城乡壁垒在中国农民灵魂深处的“海市蜃楼”和罪恶的渊薮,在城市深处丢失自我的乡村女性,渴望在乡村、乡土文化中洗礼得以重生。
文明的差异自然是“到城里去”的深层文化动因,但对中国的农民而言,其直接的驱动力还是“城乡差异”。
若说男人可以通过招工、参军、考大学等方式获得“非农户口”,而对重男轻女普遍存在的农村来讲,女人的进城就更为艰难。
于是,成为“工人家属”所带来的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身份转变,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诸多乡村女性的向往。
在刘庆邦的笔下,有许多走进矿区的工人家属,如《白煤》中的想,《月光依旧》中的叶新荣,《家属房》中的小艾、《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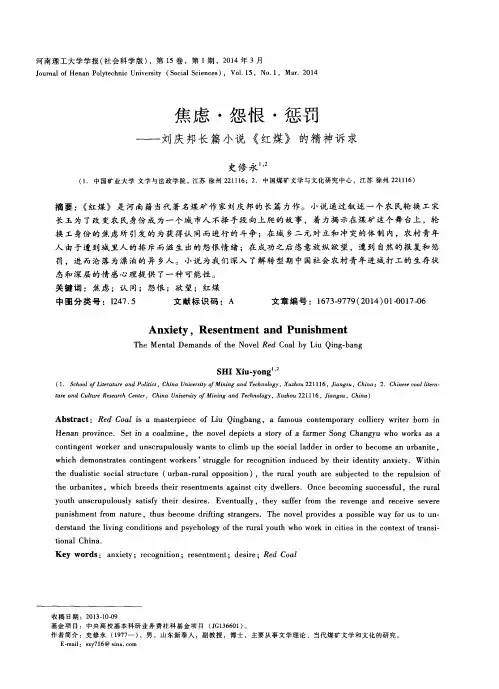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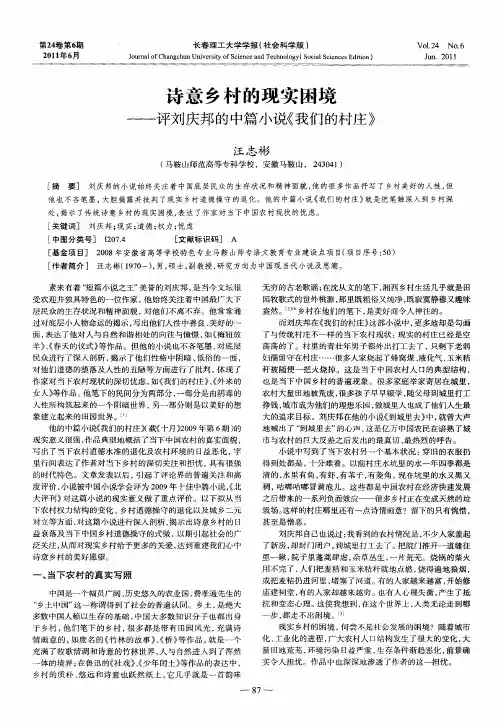
从《到城里去》看刘庆邦笔下的城乡关系作者:严媛媛来源:《文学教育》2020年第02期内容摘要:在中篇小说《到城里去》中,刘庆邦对主人公宋家银进城的渴望进行了详细描述,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辛酸和无奈。
在刘庆邦笔下,进城成为了梦想,城市殖民了乡村,乡村面临的是转型期的尴尬与阵痛。
关键词:《到城里去》城市乡村回家从晚清开始,城市对乡下人来说,就构成了一种向往,一种诱惑。
《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这类小说,无不展现了上海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乡下人的吸引,以及人们在现代物质文明中的堕落。
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发表于2003年,此时,“到城里去”已经成为了一个在乡下流行开来的口号和宣言。
农家妇女宋家银把进城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而在这巨大的进城洪流之中,城市究竟能给进城的人带来什么?1.为何进城在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危机,为了尽快把我国就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国家,农村成为了城市的补给,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农村像一个哺乳期的妇女,向城市日益输送着乳汁。
而当乡村发展日趋停滞,城市茁壮成长的时候,城市却摇身一变,关上了进城的大门。
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的断裂,让城市成为了先进、文明、整洁、体面的代表,而乡村则成为了落后、愚昧、不觉悟、不得体的典型。
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兴起,城市把“进步”的观念带入了乡村,摆脱贫穷,寻求进步,永不满足,也成为了乡下人的生存格言。
为了摆脱农民身份,宋家银先是把身体献给了一个要去新疆当工人的年轻人,发现被骗之后,她又选择了长相平庸但拥有临时工身份的杨成方。
择偶条件不再是两情相悦,这是宋家银面对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做出的妥协。
对宋家银来说,婚姻也不是让她享有甜蜜生活的依靠,她需要杨成方的工人身份带来的虚荣。
杨成方失业之后,她让杨成方继续去郑州、去北京,多年漂泊在外,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婚姻的胜利,虽然她暂时进城,但她丈夫一直在城里。
北乔在《刘庆邦的女儿国》一书中分析了宋家银的性格:你要问宋家银过的好不好,她肯定觉得日子还不错,她的满足,都来自向上的攀比之中……一个人的活法,有时靠自己做主,但更多的时候,则是由生养的文化土壤所决定。
84美学2020/05刘庆邦出身河南沈丘农村,虽然他早已离开乡村并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相比较来说,他的城市生活经验比乡村要丰富得多,时间也更长,可在他心里却始终与乡村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
他曾说过:“我在农村长到19岁,对那儿非常熟悉。
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野菜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流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家乡我每年都要回去,回去也不刻意去体验什么,一回去心就激活了,那里的山水、草木、人,看什么都有感觉,乡村有让我心动的东西。
”[1]少年刘庆邦曾想尽力逃离乡村,想“甩掉脚上的泥巴,到别的地方去”。
时过境迁,他早已不是那个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当不成兵,为无法离开灰扑扑的乡村而茶饭不思的少年。
后来,刘庆邦到北京工作,也去过很多地方,到过很多的国家,可他却始终没有放下生养他的故乡,始终保持着对乡土的书写欲望。
可以说,他长大的那片土地不仅仅是他生命之根,也是他文学之根,他始终以一种温情的姿态守望着乡村这片土地。
刘庆邦始终将关切的目光投向现实乡村,兴衰浮沉在他的笔下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传统乡村的静美和谐,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下乡村的种种问题和病象在他笔下得到充分的展示。
从《鞋》《少男》《梅妞放羊》等和谐自然的乡村图景,到《黄胶泥》《八月十五月儿月儿圆》《金色小调》等乡村伦理道德的急剧衰败,再到《天凉好个秋》《回家》《到城里去》等农民群体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异乡者”,刘庆邦对乡村进行全景式的观照和整体性的扫描。
《到城里去》是最能体现刘庆邦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下对农民工进城的生命体验。
刘庆邦曾坦言:“我对乡土的确有一种矛盾的情感,正如我对家乡怀有感恩之心,却要千方百计从家乡走出来。
好不容易从家乡走出来了,又和家乡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
我看到了乡村的美,也看到了乡村的丑;我看到了乡人的善,也看到了乡人的恶。
我在家乡感到了痛之深,也对家乡爱之切。
树德中学高2024级高一上学期11月半期测试语文试题(时间:150分钟总分:150分)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进城”与“返乡”贯穿了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史。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剧,农民进城谋生已成为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
他们困窘的城市生活境遇和坎坷的心路历程逐渐引起作家的关注,表现“返乡”的作品由此频繁出现。
在刘庆邦2005年发表的小说《回家》里,农民工梁建明的儿子回乡后发现,乡村早已无法接纳他,在孤独的煎熬下;他只能再次离去。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乡土小说中塑造的返乡者形象,大多是城市的漂泊者、逃离者。
这些旧式返乡者因为现实的困窘和精神的苦闷选择返乡,但故乡却再难成为他们的归宿。
新时代以来也涌现出了一批乡土小说,虽然也会书写乡村的衰弱以及农民在“进城”与“返乡”间的徘徊,但总体基调不再耽于对乡村前景无路的沮丧或对乡村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尝试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捕捉时代脉动,为乡村振兴寻求可行的方法。
作家关仁山曾经说过,乡土小说仅有批判是不够的,还需要建设,比如对乡村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给予启示。
长篇小说《暖夏》将“返乡”作为主人公二泉故事的起点,讲述他从进城打工者转变为返乡创业者的成长之路,极具建设意义。
承载着人的记忆和乡村历史的乡愁,成为促使以《暖夏》中的二泉、《金谷银山》中以范少山为代表的新时代返乡者投身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这些新式返乡者纷纷尽己所能将城市的资金、技术、人脉等资源注入乡村。
他们既有增加收入、创造更好生活的务实精神,更有着造福乡邻乡亲、反哺故土的理想憧憬。
这些新型返乡者,经历了“离乡——返乡——留乡”的动态过程,与其形成明显差异的坚守者们则始终扎根于乡土社会。
新世纪乡土小说也塑造了许多乡村坚守者形象,但他们往往被作者大肆批判,以图引发人们的反思。
如在阎连科于2007年发表的小说《黑猪毛白猪毛》中,李屠户、刘根宝仍延续着“五四”以来被反复抨击的“国民劣根性”。
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农民告状故事r——张继小说《去城里受
苦吧!》解读
卢军
【期刊名称】《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33)005
【摘要】新锐作家张继的长篇小说《去城里受苦吧!》通过讲述村民牛贵祥因征地纠纷被迫状告村长李木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下鲁南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权大于法"的观念仍在根深蒂固地左右着许多农民的思想;个体权利意识淡薄的农民习惯于服从行政指令;农民文化素质相对偏低,直接影响了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因此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小说还表现了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深刻变化的关注和思考.
【总页数】5页(P72-76)
【作者】卢军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城里人的故事--论沈从文的都市题材小说 [J], 尹变英
2.回不去的乡村--张继《去城里受苦吧》的寓意分析 [J], 孙书文
3.论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 [J], 王志尧
4.无尽的挽歌:底层趋城意识的批判——论刘庆邦中篇小说《到城里去》的心理内涵 [J], 李杰;何希凡
5.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身份焦虑——读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 [J], 陈旭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作者: 董之林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出版物刊名: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页码: 1-2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1期
主题词: 乡下人进城;身份焦虑;底层写作;人性意志
摘要:在世纪交替的变革时期,"乡下人进城"的小说或其他文学体裁,是对当下生活的迅即反映。
但文学艺术的普适性,又使其意义不局限于此。
作品中"乡关何处"的焦虑,如果不是寄寓着一种社会焦虑,就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与共鸣。
身份认同问题正凸现于变革时期的日常生活,使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农民工或城里的"乡下人",他们戏剧性的命运也倒映着其他人的现实处境。
那些细节描写越是具体生动,所构成的意象空间,连同对人性发掘的力度就越强。
这种文学状态,有可能摆脱以往对作品题材的类型定位,形成一种更富于活力的艺术表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