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罪恶的母亲谈起_浅析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
- 格式:pdf
- 大小:43.35 KB
- 文档页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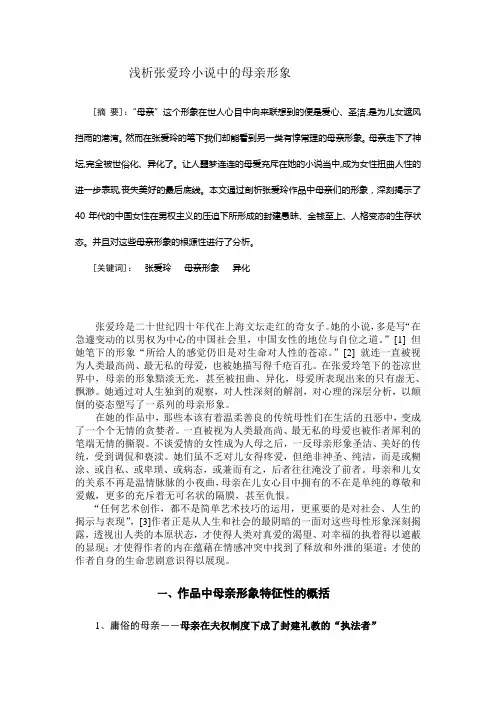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摘要]:“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
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类有悖常理的母亲形象。
母亲走下了神坛,完全被世俗化、异化了。
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充斥在她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扭曲人性的进一步表现,丧失美好的最后底线。
本文通过剖析张爱玲作品中母亲们的形象,深刻揭示了4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所形成的封建愚昧、金钱至上、人格变态的生存状态。
并且对这些母亲形象的根源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异化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走红的奇女子。
她的小说,多是写“在急遽变动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位之道。
”[1] 但她笔下的形象“所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对生命对人性的苍凉。
”[2] 就连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描写得千疮百孔。
在张爱玲笔下的苍凉世界中,母亲的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母爱所表现出来的只有虚无、飘渺。
她通过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人性深刻的解剖,对心理的深层分析,以颠倒的姿态塑写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
在她的作品中,那些本该有着温柔善良的传统母性们在生活的丑恶中,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贪婪者。
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作者犀利的笔端无情的撕裂。
不谈爱情的女性成为人母之后,一反母亲形象圣洁、美好的传统,受到调侃和亵渎。
她们虽不乏对儿女得疼爱,但绝非神圣、纯洁,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琐、或病态,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没了前者。
母亲和儿女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小夜曲,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拥有的不在是单纯的尊敬和爱戴,更多的充斥着无可名状的隔膜,甚至仇恨。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是简单艺术技巧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表现”,[3]作者正是从人生和社会的最阴暗的一面对这些母性形象深刻揭露,透视出人类的本原状态,才使得人类对真爱的渴望、对幸福的执着得以遮蔽的显现;才使得作者的内在蕴藉在情感冲突中找到了释放和外泄的渠道;才使的作者自身的生命悲剧意识得以展现。

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一、绝望和苍凉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绝望与苍凉充斥其中,很少有大团圆的结局。
这是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书写者,她以老辣犀利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以独有的绝望和苍凉的人生意识揭示了她们的生存困境,表现了她们面对这种困境时的异化以及抗争。
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探索,张爱玲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挖掘女性不能脱离困境的原因,揭示女性在经济、精神上的难以自立,展现女性个性解放的艰难。
女儿,阴影下的生存与毁灭张爱玲自小生活在一个充满遗少气氛和现代文明相交杂的环境中。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加大家族浪荡子式的人物,而母亲和姑姑则是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新代人物。
面对这样一种新旧文明“犯冲”的状况,她深深体味到自我在家庭中,她所属的那个没落阶层在社会中,人类在荒凉的时空背景中等诸种失落:这种失落感构成作者的情绪基调,笼罩在作品中,使人物的内心体验都呈现出宿命的虚无感,形成了她作品主题的总特色:悲观、虚无。
我们知道,作家童年的性经验缺失对于作家以后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爱玲自小在豪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凉的生活。
旧式豪门巨族的腐朽生活在她面前上演了一幅幅鸦片烟、姨太太、争遗产、狎妓的丑剧,同时她又经历了父母离异的痛苦,16岁时在“继母”的统治下讨生活。
其间曾被父亲幽禁,“他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
”逃离之后,进入母亲的家。
虽然精神上比以前要充实一些,但每每陷入物质困境。
有着彻骨经验的作者,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内容也是极为深刻的。
作为一个爸爸不疼妈妈不爱的女儿,张爱玲笔下的女儿几乎都是不幸的。
川嫦死去的原因绝望和苍凉是张爱玲作品的底色,也是其笔下女性形象表现出的共同的生存状态。
她们一直笼罩在绝望的挣扎和苍凉的人生况味之中。
自私,是人性的魔障,也是血缘亲情的天敌。
张爱玲尖刻地挑剔着人的生存世相后面隐藏的人性真相,她总是能够发现种种装饰性表象后面隐藏的空虚、自私、盲目。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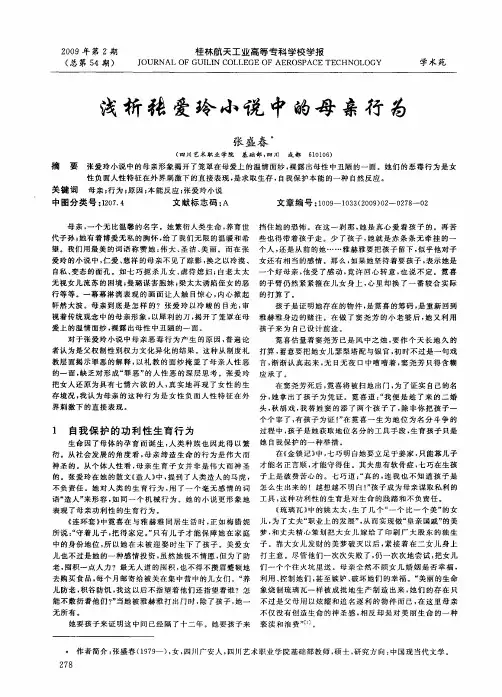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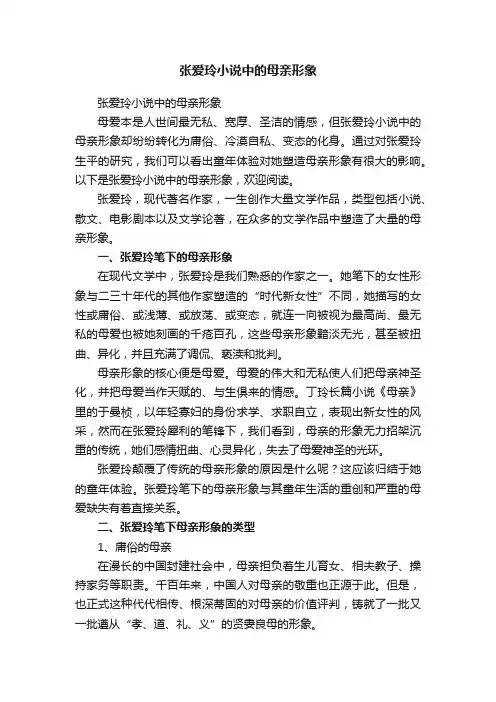
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母爱本是人世间最无私、宽厚、圣洁的情感,但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却纷纷转化为庸俗、冷漠自私、变态的化身。
通过对张爱玲生平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童年体验对她塑造母亲形象有很大的影响。
以下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欢迎阅读。
张爱玲,现代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母亲形象。
一、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在现代文学中,张爱玲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之一。
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描写的女性或庸俗、或浅薄、或放荡、或变态,就连一向被视为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刻画的千疮百孔,这些母亲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并且充满了调侃、亵渎和批判。
母亲形象的核心便是母爱。
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使人们把母亲神圣化,并把母爱当作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情感。
丁玲长篇小说《母亲》里的于曼桢,以年轻寡妇的身份求学、求职自立,表现出新女性的风采,然而在张爱玲犀利的笔锋下,我们看到,母亲的形象无力招架沉重的传统,她们感情扭曲、心灵异化,失去了母爱神圣的光环。
张爱玲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应该归结于她的童年体验。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童年生活的重创和严重的母爱缺失有着直接关系。
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1、庸俗的母亲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担负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职责。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正源于此。
但是,也正式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对母亲的价值评判,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最多的,她们都是“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
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女儿暗恋丈夫,而丈夫又与女儿的同学同居这样一个**的事实,也只是忍气吞声。
这个母亲在自己受尽伤害后,还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寻找退路,虽然令人唏嘘,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母亲的确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层,她不去想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状况的发展,而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捍卫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的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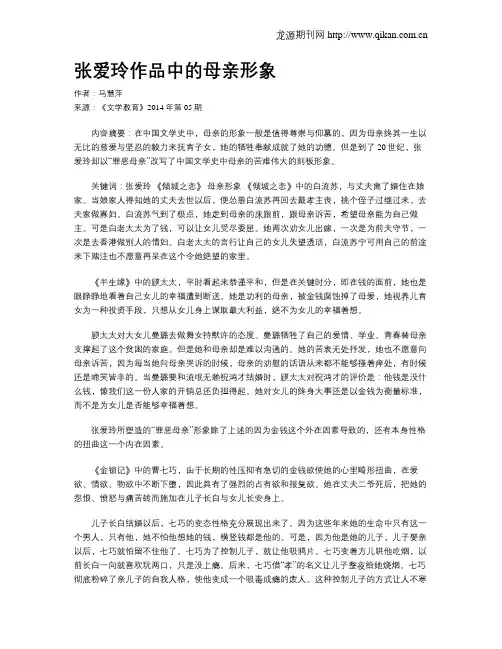
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作者:马慧萍来源:《文学教育》2014年第05期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中,母亲的形象一般是值得尊崇与仰慕的,因为母亲终其一生以无比的慈爱与坚忍的毅力来抚育子女,她的牺牲奉献成就了她的功德。
但是到了20世纪,张爱玲却以“罪恶母亲”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中母亲的苦难伟大的刻板形象。
关键词:张爱玲《倾城之恋》母亲形象《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丈夫离了婚住在娘家。
当娘家人得知她的丈夫去世以后,便怂恿白流苏再回去戴孝主丧,挑个侄子过继过来,去夫家做寡妇。
白流苏气到了极点,她走到母亲的床跟前,跟母亲诉苦,希望母亲能为自己做主。
可是白老太太为了钱,可以让女儿受尽委屈。
她两次劝女儿出嫁,一次是为前夫守节,一次是去香港做别人的情妇。
白老太太的言行让自己的女儿失望透顶,白流苏宁可用自己的前途来下赌注也不愿意再呆在这个令她绝望的家里。
《半生缘》中的顾太太,平时看起来恭谨平和,但是在关键时分,即在钱的面前,她也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女儿的幸福遭到断送。
她是功利的母亲,被金钱腐蚀掉了母爱,她视养儿育女为一种投资手段,只想从女儿身上谋取最大利益,绝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
顾太太对大女儿曼璐去做舞女持默许的态度。
曼璐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学业、青春替母亲支撑起了这个贫困的家庭。
但是她和母亲却是难以沟通的。
她的苦衷无处抒发,她也不愿意向母亲诉苦,因为每当她向母亲哭诉的时候,母亲的劝慰的话语从来都不能够搔着痒处,有时候还是啼笑皆非的。
当曼璐要和流氓无赖祝鸿才结婚时,顾太太对祝鸿才的评价是:他钱是没什么钱,像我们这一份人家的开销总还负担得起。
她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为女儿是否能够幸福着想。
张爱玲所塑造的“罪恶母亲”形象除了上述的因为金钱这个外在因素导致的,还有本身性格的扭曲这一个内在因素。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长期的性压抑有急切的金钱欲使她的心里畸形扭曲,在爱欲、情欲、物欲中不断下堕,因此具有了强烈的占有欲和报复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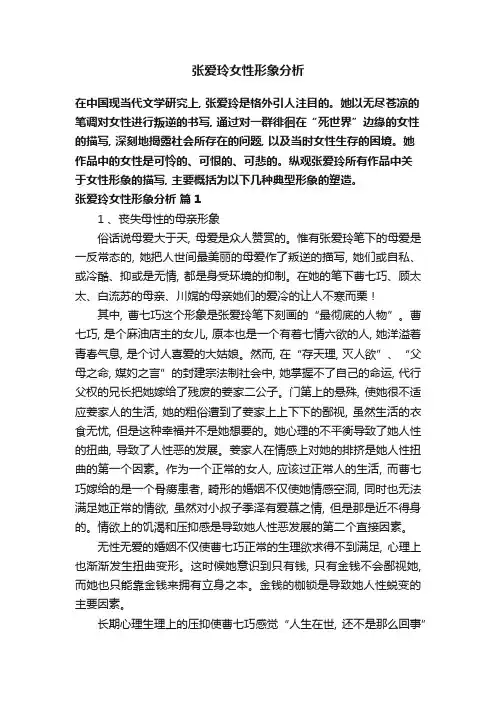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 张爱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 通过对一群徘徊在“死世界”边缘的女性的描写, 深刻地揭露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以及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
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
纵观张爱玲所有作品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描写, 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典型形象的塑造。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篇11 、丧失母性的母亲形象俗话说母爱大于天, 母爱是众人赞赏的。
惟有张爱玲笔下的母爱是一反常态的, 她把人世间最美丽的母爱作了叛逆的描写, 她们或自私、或冷酷、抑或是无情, 都是身受环境的抑制。
在她的笔下曹七巧、顾太太、白流苏的母亲、川嫦的母亲她们的爱冷的让人不寒而栗!其中, 曹七巧这个形象是张爱玲笔下刻画的“最彻底的人物”。
曹七巧, 是个麻油店主的女儿, 原本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 她洋溢着青春气息, 是个讨人喜爱的大姑娘。
然而, 在“存天理, 灭人欲”、“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 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了残废的姜家二公子。
门第上的悬殊, 使她很不适应姜家人的生活, 她的粗俗遭到了姜家上上下下的鄙视, 虽然生活的衣食无忧, 但是这种幸福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心理的不平衡导致了她人性的扭曲, 导致了人性恶的发展。
姜家人在情感上对她的排挤是她人性扭曲的第一个因素。
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 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曹七巧嫁给的是一个骨痨患者, 畸形的婚姻不仅使她情感空洞, 同时也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情欲, 虽然对小叔子季泽有爱慕之情, 但是那是近不得身的。
情欲上的饥渴和压抑感是导致她人性恶发展的第二个直接因素。
无性无爱的婚姻不仅使曹七巧正常的生理欲求得不到满足, 心理上也渐渐发生扭曲变形。
这时候她意识到只有钱, 只有金钱不会鄙视她, 而她也只能靠金钱来拥有立身之本。
金钱的枷锁是导致她人性蜕变的主要因素。
长期心理生理上的压抑使曹七巧感觉“人生在世, 还不是那么回事”而后, 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地所剩无几的时候, 便到她面前倾诉起爱情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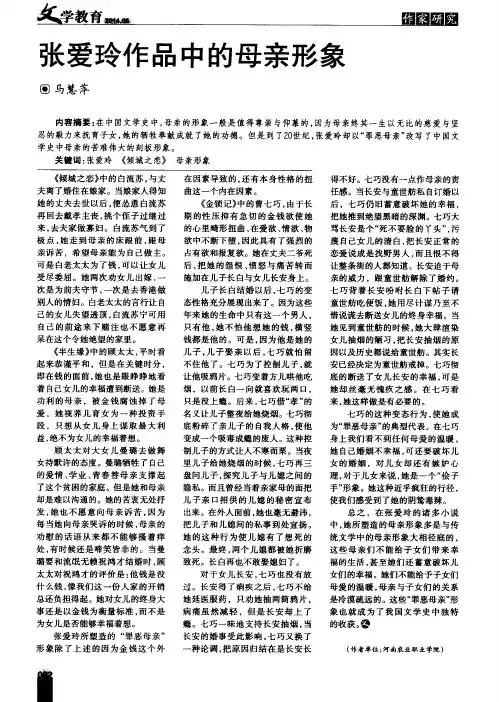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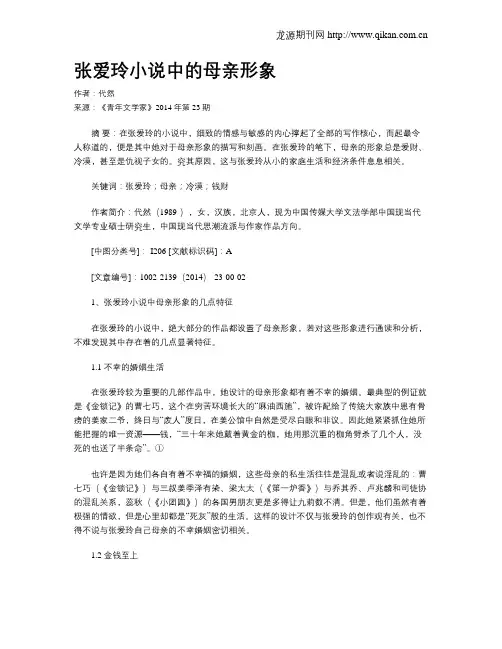
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作者:代然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3期摘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细致的情感与敏感的内心撑起了全部的写作核心,而起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其中她对于母亲形象的描写和刻画。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的形象总是爱财、冷漠,甚至是仇视子女的。
究其原因,这与张爱玲从小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条件息息相关。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冷漠;钱财作者简介:代然(1989-),女,汉族,北京人,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3-00-021、张爱玲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几点特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绝大部分的作品都设置了母亲形象,若对这些形象进行通读和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的几点显著特征。
1.1 不幸的婚姻生活在张爱玲较为重要的几部作品中,她设计的母亲形象都有着不幸的婚姻。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金锁记》的曹七巧,这个在穷苦环境长大的“麻油西施”,被许配给了传统大家族中患有骨痨的姜家二爷,终日与“废人”度日,在姜公馆中自然是受尽白眼和非议。
因此她紧紧抓住她所能把握的唯一资源——钱,“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①也许是因为她们各自有着不幸福的婚姻,这些母亲的私生活往往是混乱或者说淫乱的:曹七巧(《金锁记》)与三叔姜季泽有染、梁太太(《第一炉香》)与乔其乔、卢兆麟和司徒协的混乱关系,蕊秋(《小团圆》)的各国男朋友更是多得让九莉数不清。
但是,他们虽然有着极强的情欲,但是心里却都是“死灰”般的生活。
这样的设计不仅与张爱玲的创作观有关,也不得不说与张爱玲自己母亲的不幸婚姻密切相关。
1.2 金钱至上张爱玲小说母亲形象的第二点特征,是他们都将金钱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为了钱,母亲可以舍弃一切,甚至是女儿。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半生缘》,顾曼祯的姐姐以其做诱饵,致使祝鸿才逼奸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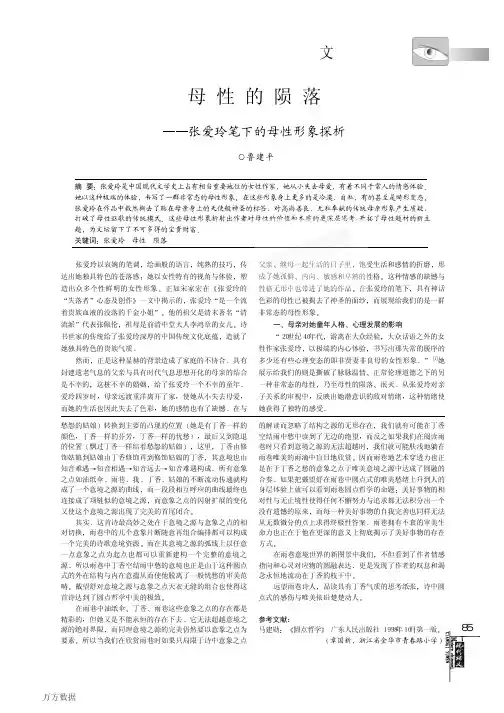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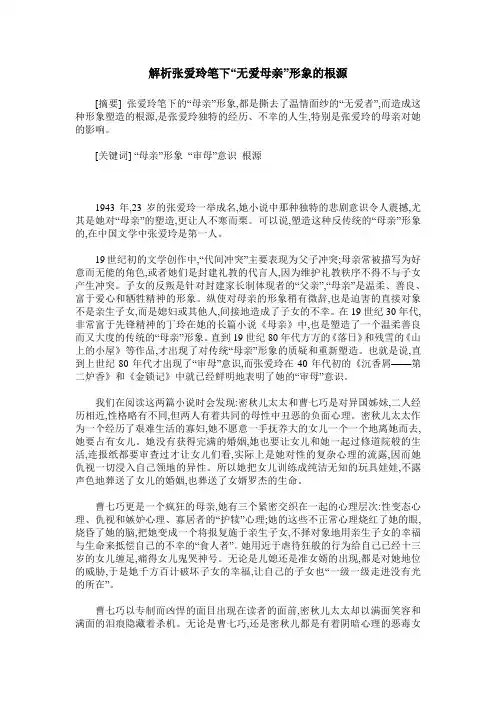
解析张爱玲笔下“无爱母亲”形象的根源[摘要]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都是撕去了温情面纱的“无爱者”,而造成这种形象塑造的根源,是张爱玲独特的经历、不幸的人生,特别是张爱玲的母亲对她的影响。
[关键词] “母亲”形象“审母”意识根源1943年,23岁的张爱玲一举成名,她小说中那种独特的悲剧意识令人震撼,尤其是她对“母亲”的塑造,更让人不寒而栗。
可以说,塑造这种反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在中国文学中张爱玲是第一人。
19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代间冲突”主要表现为父子冲突;母亲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或者她们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因为维护礼教秩序不得不与子女产生冲突。
子女的反叛是针对封建家长制体现者的“父亲”,“母亲”是温柔、善良、富于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
纵使对母亲的形象稍有微辞,也是迫害的直接对象不是亲生子女,而是媳妇或其他人,间接地造成了子女的不幸。
在19世纪30年代,非常富于先锋精神的丁玲在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中,也是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又大度的传统的“母亲”形象。
直到19世纪80年代方方的《落日》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作品,才出现了对传统“母亲”形象的质疑和重新塑造。
也就是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审母”意识,而张爱玲在40年代初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中就已经鲜明地表明了她的“审母”意识。
我们在阅读这两篇小说时会发现:密秋儿太太和曹七巧是对异国姊妹,二人经历相近,性格略有不同,但两人有着共同的母性中丑恶的负面心理。
密秋儿太太作为一个经历了艰难生活的寡妇,她不愿意一手抚养大的女儿一个一个地离她而去,她要占有女儿。
她没有获得完满的婚姻,她也要让女儿和她一起过修道院般的生活,连报纸都要审查过才让女儿们看,实际上是她对性的复杂心理的流露,因而她仇视一切浸入自己领地的异性。
所以她把女儿训练成纯洁无知的玩具娃娃,不露声色地葬送了女儿的婚姻,也葬送了女婿罗杰的生命。
曹七巧更是一个疯狂的母亲,她有三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心理层次:性变态心理、仇视和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她的这些不正常心理烧红了她的眼,烧昏了她的脑,把她变成一个将报复施于亲生子女,不择对象地用亲生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的“食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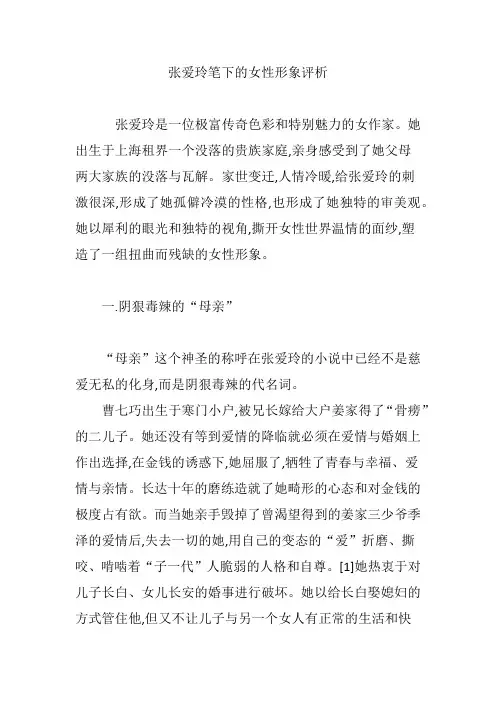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评析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和特别魅力的女作家。
她出生于上海租界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亲身感受到了她父母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
家世变迁,人情冷暖,给张爱玲的刺激很深,形成了她孤僻冷漠的性格,也形成了她独特的审美观。
她以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撕开女性世界温情的面纱,塑造了一组扭曲而残缺的女性形象。
一.阴狠毒辣的“母亲”“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呼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已经不是慈爱无私的化身,而是阴狠毒辣的代名词。
曹七巧出生于寒门小户,被兄长嫁给大户姜家得了“骨痨”的二儿子。
她还没有等到爱情的降临就必须在爱情与婚姻上作出选择,在金钱的诱惑下,她屈服了,牺牲了青春与幸福、爱情与亲情。
长达十年的磨练造就了她畸形的心态和对金钱的极度占有欲。
而当她亲手毁掉了曾渴望得到的姜家三少爷季泽的爱情后,失去一切的她,用自己的变态的“爱”折磨、撕咬、啃啮着“子一代”人脆弱的人格和自尊。
[1]她热衷于对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婚事进行破坏。
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另一个女人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
她整夜不睡地盘问儿子的私生活,并且在亲家母在场的麻将桌上将儿子与儿媳的隐私公之于众,并百般羞辱儿媳,使亲家母都不忍听下去而离开,直至把儿媳妇活活逼死。
因为在儿媳身上她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
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对于女儿迟来的爱情,曹七巧不但没有祝福,反而处心积虑的加以破坏,看到女儿与童世舫和谐交往,并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与童世舫谈婚论嫁,便大骂童世舫是看上了她家的钱财,后来又无端地辱骂女儿长安不守妇道,品行不端,并对女婿童世舫散布阴森的谎言,说女儿是一个断不了瘾的烟鬼,从而断送了女儿的婚事。
如此母亲,如此婆婆!正是她对儿子变态的占有,对女儿变态的嫉妒使她迸发出了无穷的复仇欲,最终驱使她失掉了与生俱来的母性。
密秋儿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川娥的母亲(《花凋》)、顾太太(《十八春》)等人物跟曹七巧一样都是狠毒异常、残害人命的暴君“母亲”。
母爱的异化与反思———以萧红张爱玲笔下的恶母形象为例周宇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作者简介】周宇纯(1997-),女,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母性光辉是闪耀在华夏大地上的神圣之光,是千百年来缔结的民族情结。
孟母三迁煞费苦心,岳母刺字大义凛然,这些高尚的母亲形象在文化中构建起了经典的母爱主题。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母亲形象在一些作品中被重新定义,母爱给人的温暖逐渐被消解,恶母形象取代了原本神圣的母亲形象,她们作为善的对立者,以母爱的名义给子女或者他人带来伤害。
与和善、温柔的母亲不同,恶母形象中的母亲刻薄、疯狂甚至变态的人物性格,使她们面对人生抉择时会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常常由此造成个人家庭悲剧的同时,也会反射出社会上某种值得探究的原因,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萧红、张爱玲两人的作品为例,从恶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恶母形象类型以及恶母形象产生的根源三方面着手,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恶母形象,进而拓展现代文学中母性话题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恶母形象;人性;母爱【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36(2020)02-0050-04《诗经》有云:“凯风自南,吹彼棘薪。
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1]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对母亲的书写无疑都是正面的,主要书写母爱之伟大、母亲品德之高尚诸如此类。
试观古今中外,时至今日,提到母亲这个话题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依旧是母爱,书写母爱的作品更是不一而足。
“母亲”也同样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话题,成为了众多作家争先书写的对象。
冰心所创“爱的哲学”里,母爱是她眼中亘古不变的存在,它与童真、自然一起,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满着温暖与真情的爱的世界。
这一观点为现代大众所认同,故而在实际创作中便会增加对于母亲这一话题的正面形象的创作,学者在面对此类形象的研读中也就更偏重于对于母亲正面形象的解读,我们姑且将这一类的形象称之为“慈母”形象,这样一来实则不难看出,现代学者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忽略了“慈母”的对立面———“恶母”的解读与研究。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引言:简要概括张爱玲以及她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她成长、生活的背景和其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个性。
“母亲”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歌颂性形象,但张爱玲小说中母亲的形象有多种面貌并且大多是冷漠的负面形象。
对其作品中塑造的母亲人物形象进行分类概括,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种对母亲形象的颠覆,源于张爱玲独特的成长经历,反映了她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思考。
一、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在张爱玲笔下所呈现的女性是悲剧的,是无主张的,异化的。
苍凉而复苍白,安命而又怨命的女性悲剧,在张爱玲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
然而,在这些作为悲剧的女性中,母亲这一形象奴化变态且面目皆非似乎更让人感到凉入骨髓。
现把她们分为三大类型:1、金钱扭曲灵魂而泯灭亲情的母亲2、病态的母亲。
3、传统世俗的母亲(一)被金钱扭曲灵魂而泯灭亲情的母亲1、《十八春》中的顾太太眼睁睁地看着二女儿近乎完美的爱情和婚姻将要被无情地断送,却在金钱的诱惑下心安理得地走开了,独自留下曼桢在那呼天抢地。
2、《花凋》里的郑夫人为了守住自己的私房钱而不肯给女儿治病,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寸一寸地死去”而无动于衷。
3、《琉璃瓦》中欲借女儿攀上豪门的姚太太、《封锁》中为获富贵姻亲而培育女儿的吴翠远之母都是在亲情与金钱之中选择了金钱。
4、小结(二)病态的母亲1、《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长期在婆家遭受人格上的侮辱、情感上的挫折和情欲上的压抑,人性严重扭曲,变得乖戾、暴躁、刻毒、歇斯底里。
当一双儿女长大成人后,她的变态心理,愈发不可收拾。
2、《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养母性质的梁太太真的不在乎葛薇龙的遭遇感受。
她不把薇龙当成亲人,反而视之为手中的一名棋子、一项财产、一副工具,好让她能不断吸引更多有钱有权势的男人,以维持她纸醉金迷的生活。
3、《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畸形家教导致女儿靡丽笙、素西斯视正常的性行为为兽行,结果逼死了两个女儿的丈夫。
她不但毁了子女的人性,也毁了子女的幸福生活。
读·闻·观38论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车文利摘要:无论古今,提到母亲,皆是圣洁、无私的化身,张爱玲作品的出现让人们逐渐发现了伟大母爱的另一面,如同恶魔一般的母性被写在了张爱玲的文字中。
这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另类,这是开始重新审视母亲形象的重大一笔,母亲的形象一反传统的圣洁与美好,冷漠、自私的形象隐藏在传统母亲形象的面纱之下。
关键词:张爱玲;母爱;颠覆作家张爱玲从不追随主流,她开启了母亲形象的另类书写,将母亲与“神圣”“无私”“含辛茹苦”的形象剥离开来,用“冷漠”“自私”“物质”等特质所取代。
一、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一)被金钱扭曲灵魂而泯灭亲情的母亲不论是《花凋》中的郑夫人、《琉璃瓦》中的姚太太、还是《十八春》中顾曼桢之母,她们都是自私、贪婪的化身,在亲情和金钱之间她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金钱。
儿女对他们而言,只是用来炫耀和追名逐利的工具,为了利益,她们可以牺牲儿女的婚姻、幸福甚至生命。
这些母亲的形象无疑是自私庸俗、让人厌恶的,她们泯灭了一个母亲应有的爱和责任。
(二)冷漠、自私的母亲形象《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和《倾城之恋》白流苏之母看似是爱孩子的,但其实她们的爱是冷漠的、自私的。
蜜秋儿婚姻生活的不幸使她产生了畸形的心理,只想把女儿永远地留在身边,不想让女儿拥有美满的婚姻;而白夫人为了逢迎儿子,对白流苏的哭诉“一味地避重就轻”,排斥女儿,两位母亲的自私和冷漠都直接造成了女儿的悲剧。
(三)庸俗的母亲形象在张爱玲的作品里,除了冷漠自私、被金钱控制的母亲外,还有一些传统的母亲形象,她们平凡、普通,愚昧无知。
如《心经》中的许太太,丈夫屡屡出轨,甚至与女儿越过了父女之情的界限。
但许太太选择了忍气吞声,甚至还在为家人寻找退路。
许太太在传统世俗的面前,不仅对伤害已无动于衷,甚至可以将自己的自尊踩在脚下。
(四)变态疯狂的母亲《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
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被贪财的哥哥嫂子嫁给了姜家从小就瘫痪在床的二少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