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第7装甲旅浴血戈兰高地
- 格式:doc
- 大小:34.00 KB
- 文档页数:6

以色列的最高军衔是中将,总参谋长是以色列国防军唯一的中将,军区司令、海空军司令是少将军衔。
以色列是一个血与火里滚过来的国家,总参谋长自然只有军人中的军人才能压得住,但以军少将也都不是等闲之辈。
除了前面提到的以色列·塔尔外,摩西·佩利德也在美国装甲协会名人榜上,和塔尔齐名。
戈兰高地上的第7旅旅长本-加尔和营长卡哈拉尼最后也升任少将,先后担任北方司令部司令。
十月战争期间的北方司令部司令霍菲少将则在战后转任摩萨德首脑,曾负责恩德培机场营救和追杀慕尼黑惨案凶手行动的摩萨德行动。
以军另一个很有特点的少将是摩西·卡普林斯基,他是精锐的戈兰尼旅出身的,曾任中央司令部司令和副总参谋长,但现在是Better Place公司的总裁。
这个公司正在领导世界新潮流,在以色列、丹麦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建造用绿色能源供电的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网络,并建立快速更换电池的体系,可能成为电动汽车实用化的转折点,正在广受各国政府、汽车、能源和环保界的密切注意。
但没有当上总参谋长的少将中最出名的莫过于阿里尔·沙龙。
沙龙出身于英国托管时期的巴勒斯坦,在14岁时参加加德纳(哈格纳的儿童团),后加入哈格纳。
在独立战争中,沙龙在打通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拉特伦战斗中负重伤。
以色列建国后,沙龙到希伯来大学学习中东史,但在学业半途中被召回,担任新组建的第101部队指挥官。
这是以色列第一支特种部队,专用于对巴勒斯坦游击队作报复性袭击。
但沙龙手下滥杀无辜的行径终于激起强烈反弹,尤其是1953年秋天的魁比亚村惨案,包括儿童在内的69名巴勒斯坦村民丧生。
1966年时的沙龙,那时他已经是少将师长十月战争时,他抢先打过运河,这是他军事生涯的顶峰第101部队在组建才几个月后就被迫解散,余部和第890伞兵营合并,组成伞兵旅。
在西奈战争期间,沙龙担任伞兵旅长,任务是夺取米特拉山口,为此将埃坦的伞兵营空降在山口以东,伺机夺占。
但战事发展超出意料,夺取米特拉山口已经不再必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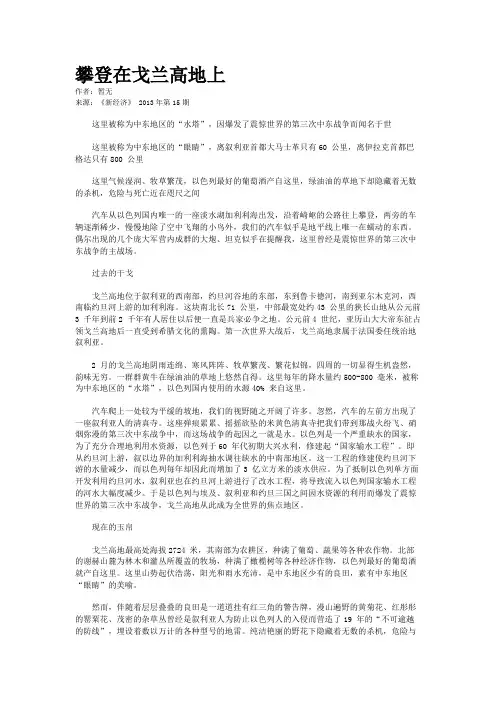
攀登在戈兰高地上作者:暂无来源:《新经济》 2013年第15期这里被称为中东地区的“水塔”,因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而闻名于世这里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眼睛”,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只有60 公里,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只有800 公里这里气候湿润、牧草繁茂,以色列最好的葡萄酒产自这里,绿油油的草地下却隐藏着无数的杀机,危险与死亡近在咫尺之间汽车从以色列国内唯一的一座淡水湖加利利海出发,沿着崎岖的公路往上攀登,两旁的车辆逐渐稀少,慢慢地除了空中飞翔的小鸟外,我们的汽车似乎是地平线上唯一在蠕动的东西。
偶尔出现的几个庞大军营内成群的大炮、坦克似乎在提醒我,这里曾经是震惊世界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主战场。
过去的干戈戈兰高地位于叙利亚的西南部,约旦河谷地的东部,东到鲁卡德河,南到亚尔木克河,西南临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
这块南北长71 公里,中部最宽处约43 公里的狭长山地从公元前3 千年到前2 千年有人居住以后便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前4 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占领戈兰高地后一直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戈兰高地隶属于法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
2 月的戈兰高地阴雨连绵、寒风阵阵、牧草繁茂、繁花似锦,四周的一切显得生机盎然,韵味无穷。
一群群黄牛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悠然自得。
这里每年的降水量约500-800 毫米,被称为中东地区的“水塔”,以色列国内使用的水源40% 来自这里。
汽车爬上一处较为平缓的坡地,我们的视野随之开阔了许多。
忽然,汽车的左前方出现了一座叙利亚人的清真寺。
这座弹痕累累、摇摇欲坠的米黄色清真寺把我们带到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而这场战争的起因之一就是水。
以色列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为了充分合理地利用水资源,以色列于60 年代初期大兴水利,修建起“国家输水工程”。
即从约旦河上游,叙以边界的加利利海抽水调往缺水的中南部地区。
这一工程的修建使约旦河下游的水量减少,而以色列每年却因此而增加了3 亿立方米的淡水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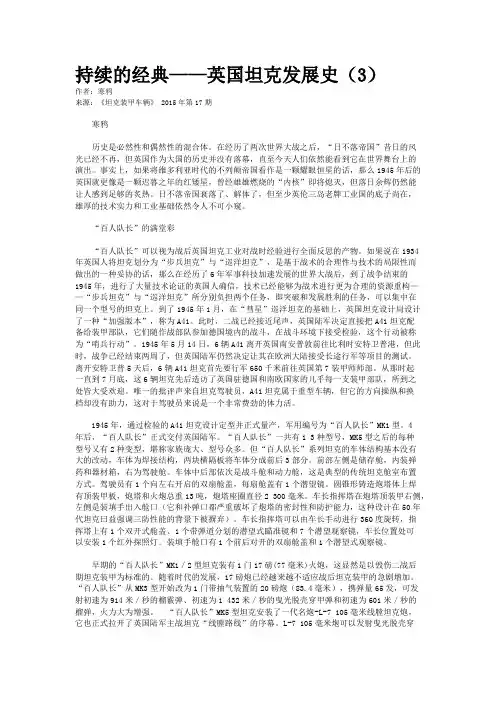
持续的经典——英国坦克发展史(3)作者:寒鸦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5年第17期寒鸦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混合体。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日不落帝国”昔日的风光已经不再,但英国作为大国的历史并没有落幕,直至今天人们依然能看到它在世界舞台上的演出。
事实上,如果将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帝国看作是一颗耀眼恒星的话,那么1945年后的英国就更像是一颗迟暮之年的红矮星,曾经雄雄燃烧的“内核”即将熄灭,但落日余辉仍然能让人感到足够的炙热。
日不落帝国衰落了、解体了,但至少英伦三岛老牌工业国的底子尚在,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工业基础依然令人不可小窥。
“百人队长”的满堂彩“百人队长”可以视为战后英国坦克工业对战时经验进行全面反思的产物。
如果说在1934年英国人将坦克划分为“步兵坦克”与“巡洋坦克”,是基于战术的合理性与技术的局限性而做出的一种妥协的话,那么在经历了6年军事科技加速发展的世界大战后,到了战争结束的1945年,进行了大量技术论证的英国人确信,技术已经能够为战术进行更为合理的资源重构——“步兵坦克”与“巡洋坦克”所分别负担两个任务,即突破和发展胜利的任务,可以集中在同一个型号的坦克上。
到了1945年1月,在“彗星”巡洋坦克的基础上,英国坦克设计局设计了一种“加强版本”,称为A41。
此时,二战已经接近尾声,英国陆军决定直接把A41坦克配备给装甲部队,它们随作战部队参加德国境内的战斗,在战斗环境下接受检验,这个行动被称为“哨兵行动”。
1945年5月14日,6辆A41离开英国南安普敦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但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两周了,但英国陆军仍然决定让其在欧洲大陆接受长途行军等项目的测试。
离开安特卫普5天后,6辆A41坦克首先要行军650千米前往英国第7装甲师师部。
从那时起一直到7月底,这6辆坦克先后造访了英国驻德国和南欧国家的几乎每一支装甲部队,所到之处皆大受欢迎。
唯一的批评声来自坦克驾驶员,A41坦克属于重型车辆,但它的方向操纵和换档却没有助力,这对于驾驶员来说是一个非常费劲的体力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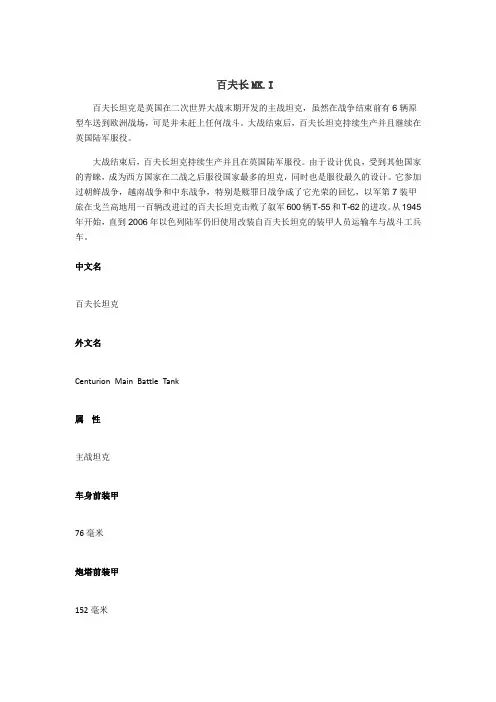
百夫长MK.I百夫长坦克是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发的主战坦克,虽然在战争结束前有6辆原型车送到欧洲战场,可是并未赶上任何战斗。
大战结束后,百夫长坦克持续生产并且继续在英国陆军服役。
大战结束后,百夫长坦克持续生产并且在英国陆军服役。
由于设计优良,受到其他国家的青睐,成为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服役国家最多的坦克,同时也是服役最久的设计。
它参加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特别是赎罪日战争成了它光荣的回忆,以军第7装甲旅在戈兰高地用一百辆改进过的百夫长坦克击败了叙军600辆T-55和T-62的进攻。
从1945年开始,直到2006年以色列陆军仍旧使用改装自百夫长坦克的装甲人员运输车与战斗工兵车。
中文名百夫长坦克外文名Centurion Main Battle Tank属性主战坦克车身前装甲76毫米炮塔前装甲152毫米生产国英国介绍英国陆军第一次使用逊邱伦坦克作战是在朝鲜战争期间。
此后,埃及、以色列、伊拉克和约旦等国在中东战争和黎巴嫩战争中,印度在印巴战争中,澳大利亚在越南战场上均使用过。
1945~1962年英国总共生产逊邱各型主战坦克4423辆,其中MK1型100辆、MK2型250辆、MK3型2833辆、MK5型221辆、MK7型755辆、MK8型108辆、MK9型1辆和MK10型155辆,总共出口逊邱伦坦克2500辆以上。
在英国陆军吸取役的百夫长坦克从60年代末开始逐渐被酋长(Chieftain)坦克所取代。
百夫长坦克的使用实践证明,它具有装甲防护性可以提高,火炮口径可以继续加大的潜力。
该坦克最初安装1门76.2mm火炮,第一次提高火力时被83.4mm火炮取代,后来又被105mm L7式火炮取代。
该火炮为其他一些国家所采用,目前仍是豹1(Leopard 1)、梅卡瓦1型(Merkava MK.I)、M48A5、M60A1/A3、Pz61/68、74式和S坦克、维克斯(Vickers)坦克和M1坦克的主要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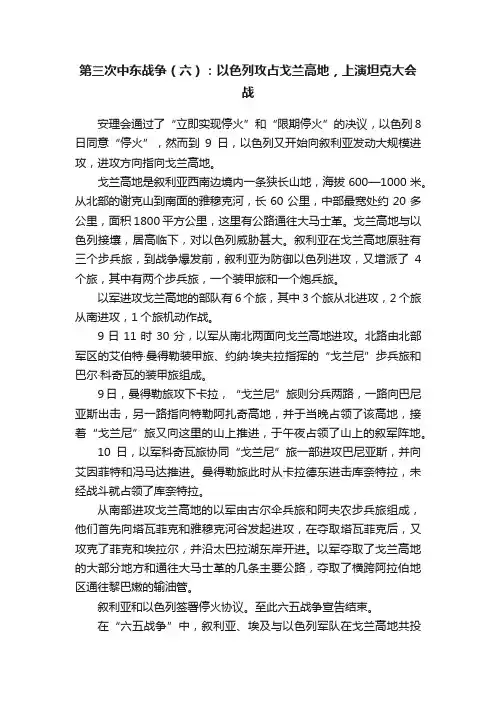
第三次中东战争(六):以色列攻占戈兰高地,上演坦克大会战安理会通过了“立即实现停火”和“限期停火”的决议,以色列8日同意“停火”,然而到9日,以色列又开始向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进攻,进攻方向指向戈兰高地。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边境内一条狭长山地,海拔600—1000米。
从北部的谢克山到南面的雅穆克河,长60公里,中部最宽处约20多公里,面积1800平方公里,这里有公路通往大马士革。
戈兰高地与以色列接壤,居高临下,对以色列威胁甚大。
叙利亚在戈兰高地原驻有三个步兵旅,到战争爆发前,叙利亚为防御以色列进攻,又增派了4个旅,其中有两个步兵旅,一个装甲旅和一个炮兵旅。
以军进攻戈兰高地的部队有6个旅,其中3个旅从北进攻,2个旅从南进攻,1个旅机动作战。
9日11时30分,以军从南北两面向戈兰高地进攻。
北路由北部军区的艾伯特·曼得勒装甲旅、约纳·埃夫拉指挥的“戈兰尼”步兵旅和巴尔·科奇瓦的装甲旅组成。
9日,曼得勒旅攻下卡拉,“戈兰尼”旅则分兵两路,一路向巴尼亚斯出击,另一路指向特勒阿扎奇高地,并于当晚占领了该高地,接着“戈兰尼”旅又向这里的山上推进,于午夜占领了山上的叙军阵地。
10日,以军科奇瓦旅协同“戈兰尼”旅一部进攻巴尼亚斯,并向艾因菲特和冯马达推进。
曼得勒旅此时从卡拉德东进击库奈特拉,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库奈特拉。
从南部进攻戈兰高地的以军由古尔伞兵旅和阿夫农步兵旅组成,他们首先向塔瓦菲克和雅穆克河谷发起进攻,在夺取塔瓦菲克后,又攻克了菲克和埃拉尔,并沿太巴拉湖东岸开进。
以军夺取了戈兰高地的大部分地方和通往大马士革的几条主要公路,夺取了横跨阿拉伯地区通往黎巴嫩的输油管。
叙利亚和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
至此六五战争宣告结束。
在“六五战争”中,叙利亚、埃及与以色列军队在戈兰高地共投入2000辆坦克进行交战,在每千米战线上布置有坦克30辆之多,其中大多数是主战坦克。
戈兰高地的坦克战共进行了18天,双方的主战坦克进行了厮杀,双方共损失一千多辆,这场坦克大战实际上是主战坦克的大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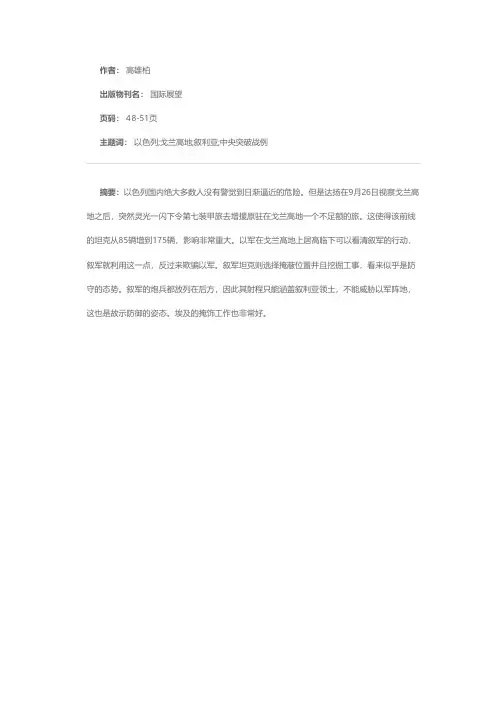
作者: 高雄柏
出版物刊名: 国际展望
页码: 48-51页
主题词: 以色列;戈兰高地;叙利亚;中央突破战例
摘要: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没有警觉到日渐逼近的危险。
但是达扬在9月26日视察戈兰高地之后,突然灵光一闪下令第七装甲旅去增援原驻在戈兰高地一个不足额的旅。
这使得该前线的坦克从85辆增到175辆,影响非常重大。
以军在戈兰高地上居高临下可以看清叙军的行动,叙军就利用这一点,反过来欺骗以军。
叙军坦克则选择掩蔽位置并且挖掘工事,看来似乎是防守的态势。
叙军的炮兵都放列在后方,因此其射程只能涵盖叙利亚领土,不能威胁以军阵地,这也是故示防御的姿态。
埃及的掩饰工作也非常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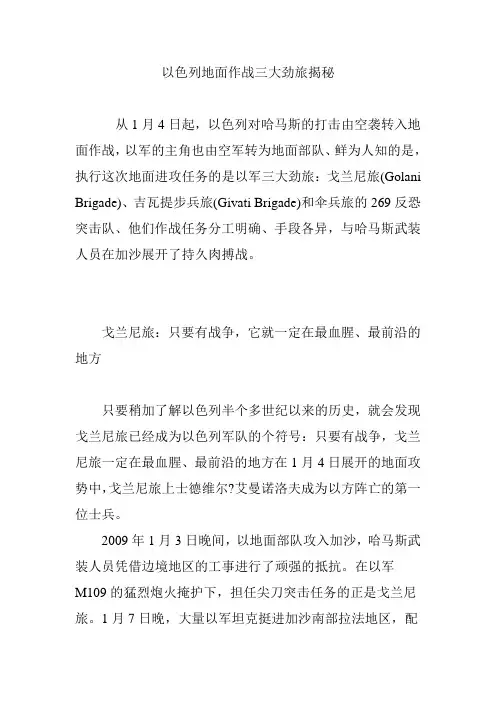
以色列地面作战三大劲旅揭秘从1月4日起,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由空袭转入地面作战,以军的主角也由空军转为地面部队、鲜为人知的是,执行这次地面进攻任务的是以军三大劲旅:戈兰尼旅(Golani Brigade)、吉瓦提步兵旅(Givati Brigade)和伞兵旅的269反恐突击队、他们作战任务分工明确、手段各异,与哈马斯武装人员在加沙展开了持久肉搏战。
戈兰尼旅:只要有战争,它就一定在最血腥、最前沿的地方只要稍加了解以色列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戈兰尼旅已经成为以色列军队的个符号:只要有战争,戈兰尼旅一定在最血腥、最前沿的地方在1月4日展开的地面攻势中,戈兰尼旅上士德维尔?艾曼诺洛夫成为以方阵亡的第一位士兵。
2009年1月3日晚间,以地面部队攻入加沙,哈马斯武装人员凭借边境地区的工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在以军M109的猛烈炮火掩护下,担任尖刀突击任务的正是戈兰尼旅。
1月7日晚,大量以军坦克挺进加沙南部拉法地区,配合以色列空军和海军对拉法地区的地道进行的猛烈轰炸,攻击行动一直持续到8日凌晨,这是以军首次出动坦克攻击哈马斯的走私地道,而此次担任攻击地道任务的同样是来自戈兰尼旅的作战力量。
此前的地道攻击任务主要由空军和海军承担。
加沙南部边境地区有大约300条走私地道,此次攻击以军摧毁了其中的100条。
戈兰尼旅下属四个营,包括2个步兵营、1个轻步兵营和1个城市特种作战侦察营,主要装备是适应城市巷战的短管步枪和装甲人员输送车。
装备有368毫米枪管的标准CAR15、微型“乌兹”冲锋枪和“毛瑟”SR86、“毛瑟”SP66SWS 和Sirkis M36(M14的一种独特改型)狙击枪。
组建于1948年2月的戈兰尼旅是以色列历史最悠久的部队之一,甚至早于同年5月才组建的以色列国防军它的前身是驻扎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Levanoni旅中的一支,Levanoni旅当时被分成了两部分,戈兰尼旅驻扎在加利利南部的村庄和山区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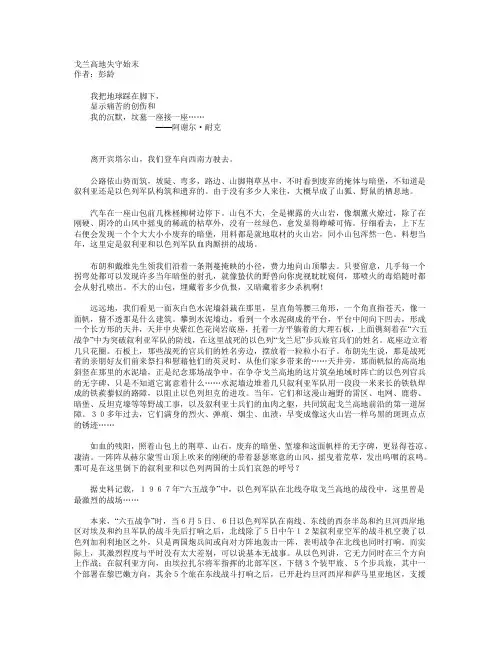
戈兰高地失守始末作者:彭龄我把地球踩在脚下,显示痛苦的创伤和我的沉默,坟墓一座接一座……——阿谢尔·耐克离开宾塔尔山,我们登车向西南方驶去。
公路依山势而筑,坡陡、弯多,路边、山脚荆草丛中,不时看到废弃的掩体与暗堡,不知道是叙利亚还是以色列军队构筑和遗弃的。
由于没有多少人来往,大概早成了山狐、野鼠的栖息地。
汽车在一座山包前几株柽柳树边停下。
山包不大,全是裸露的火山岩,像烟薰火燎过,除了在刚硬、阴冷的山风中摇曳的稀疏的枯草外,没有一丝绿色,愈发显得峥嵘可怖。
仔细看去,上下左右便会发现一个个大大小小废弃的暗堡,用料都是就地取材的火山岩,同小山包浑然一色。
料想当年,这里定是叙利亚和以色列军队血肉厮拼的战场。
布朗和戴维先生领我们沿着一条荆蔓掩映的小径,费力地向山顶攀去。
只要留意,几乎每一个拐弯处都可以发现许多当年暗堡的射孔,就像蛰伏的野兽向你虎视眈眈窥伺,那喷火的毒焰随时都会从射孔喷出。
不大的山包,埋藏着多少仇恨,又暗藏着多少杀机啊!远远地,我们看见一面灰白色水泥墙斜栽在那里,呈直角等腰三角形,一个角直指苍天,像一面帆,猜不透那是什么建筑。
攀到水泥墙边,看到一个水泥砌成的平台,平台中间向下凹去,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天井,天井中央紫红色花岗岩底座,托着一方平躺着的大理石板,上面镌刻着在“六五战争”中为突破叙利亚军队的防线,在这里战死的以色列“戈兰尼”步兵旅官兵们的姓名。
底座边立着几只花圈。
石板上,那些战死的官兵们的姓名旁边,摆放着一粒粒小石子。
布朗先生说,那是战死者的亲朋好友们前来祭扫和慰藉他们的英灵时,从他们家乡带来的……天井旁,那面帆似的高高地斜竖在那里的水泥墙,正是纪念那场战争中,在争夺戈兰高地的这片筑垒地域时阵亡的以色列官兵的无字碑,只是不知道它寓意着什么……水泥墙边堆着几只叙利亚军队用一段段一米来长的铁轨焊成的铁蒺藜似的路障,以阻止以色列坦克的进攻。
当年,它们和这漫山遍野的雷区、电网、鹿砦、暗堡、反坦克壕等等野战工事,以及叙利亚士兵们的血肉之躯,共同筑起戈兰高地前沿的第一道屏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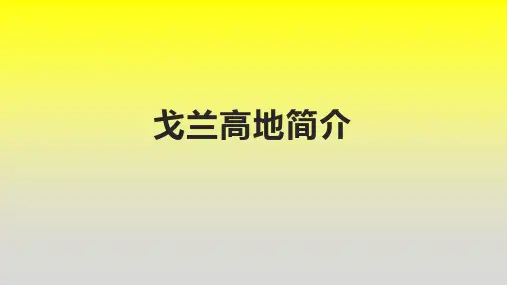
以色列国防军第7装甲旅——阿尔蒙尼特山的“守护神”“以色列国防军可以有许多次伟大的战斗引以为自豪,然而却很少有像第7装甲旅进行的战斗这么出色和伟大!”——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部长恰伊姆·赫尔佐格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数小时后,5个阿拉伯国家的4万军队就高呼着“消灭犹太国”的口号从四面八方越过边界,向以色列发动了全面进攻。
以色列不得不从其降生的第一天起,就投入到捍卫生存权、拓展生存空间的血腥搏杀之中。
此后数十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周边地区,没有一天不是在战火中浸泡,没有一个人不是在战火中熏陶。
为了生存而战的犹太人,向所有阿拉伯人展现了其坚韧的战斗力和巨大的向心力,向整个世界诠释了这个民族游荡两千多年仍然生生不息的原因。
在这六十年的战争中,以色列不仅在战略层面远胜于阿拉伯国家;就是在战术层面、在历次的战役和冲突中,天才的犹太人每每有神来之笔,打出了诸如独占巴勒斯坦的“霍雷夫战役”,侵占西奈半岛的前奏的“阿布奥格拉”战役,哈特米亚、吉迪和米特拉山口坦克战等。
然而就是这些次战役,也全都难以望及第7装甲旅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阿尔蒙尼特山保卫战。
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哈加纳创始人什洛莫·沙米和海姆·拉斯克夫奉命组建第7机械化旅——这是第7装甲旅的雏形,包括一个装甲步兵营(实际上仅有十几辆购自捷克的装甲车而已),一个步兵营,一个由国外移民组成的营。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不被人看好的“乌合之众”,成立三天后就匆匆投入到严酷激烈的恶战之中。
就是这支“乌合之众”,在攻占拿撒利战斗中重创叙利亚第5机械化旅;在哈雷姆战役中快速穿插,杀得阿拉伯联军大败而逃。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第7装甲旅为代表的以色列国防军也在战火中经受住了考验,开始成长壮大。
第二次中东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第7装甲旅都作为以色列国防军在南线的闪击先锋,是横扫阿拉伯国家大军的领路人,使阿拉伯军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带头人。
第三次中东战争央视国际(2003-01-13 18:33:26)1967年6月5日早晨7时45分,以色列出动了几乎全部空军,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一切机场进行了闪电式的袭击。
空袭半小时后,以色列地面部队也发动了进攻,阿拉伯国家进行抵抗。
至十日战争结束,阿拉伯国家失败。
这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称“六.五战争”或“六天战争”。
战争爆发的背景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美苏在中东的对抗更加激烈,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苏联则大力资助阿拉伯国家。
苏联向埃及、叙利亚等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以色列也从美国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
1958年2月,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9月又取消联合),使以色列感到了来自南北夹击的威胁。
1964年,阿拉伯国家出现了团结合作的局面,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利用约旦河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并得到埃及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阿方计划改变约旦河上游的流向,使之不被以色列利用。
1964年11月,以色列出动空军对约旦河上游的阿方工程进行轰炸,迫使阿方取消此次计划。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后,成为以色列的心腹之患。
1964年5月28日至6月4日,巴勒斯坦各界代表在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下,在耶路撒冷东城区举行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国民大会,确定组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建立了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法塔赫”。
从此,法塔赫为了把以色列赶出巴勒斯坦,可是不断的袭击以色列,这支力量在六.五战争前已初具规模,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
所以,削弱阿拉伯联盟的力量,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重要原因。
战争经过1、空中偷袭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出动了全部空军,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这是一个星期一早晨,当开罗时钟的指针指向8点45分的时候(以色列时间7点45分),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上空云雾刚刚消失。
埃及空军基地里,一切象往常一样,军官们正在上班途中,许多雷达值班室正在进行交接班。
拉宾对埃坦的评价是:“哪里有枪声和火光,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拉夫尔”。
拉夫尔·埃坦出生于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的一个摩谢夫,这是和基布茨有点类似的另一种犹太人集体农庄。
和基布茨不一样的是,摩谢夫里的犹太人依然拥有自己的房产和土地,只有在集体购置、集体经销等大方面通过摩谢夫。
埃坦很小就懂得了互相威慑的道理。
十几岁参加了帕尔马克之后,有一天被派到厨房帮厨削洋葱。
一起干活的女孩比他大一岁,闷头削土豆,削完就往他身边的大锅里“噗通”地一扔,水都溅到他身上。
几个“噗通”以后,埃坦也琢磨出怎么回事了,就把削洋葱的手往女孩眼前凑。
三来两去,埃坦身上湿漉漉了,女孩两眼也被洋葱辣的眼泪汪汪。
两人不说话的冷战持续了没多久就休战了,女孩把锅挪开,埃坦也把洋葱挪开,两人继续做无声的战友。
拉夫尔·埃坦也是伞兵出生,还有飞行员鹰徽在独立战争中,埃拉扎尔是埃坦的顶头上司,他们所在部队参加了耶路撒冷南线的战斗,在卡塔蒙的修道院阻击战中,埃坦头部中弹,负了重伤。
伤愈后,埃坦奉命到军官速成班受训,入学考试是早上开始跑步,中午一顿简单午餐后,下午继续跑,直到日落。
跑不下来的就淘汰。
军官速成班毕业后,埃坦获得少尉军衔,回在埃拉扎尔手下当排长。
但他们的部队和达杨的第89突击营是邻居,新兵们都渴望到大名鼎鼎的达杨部队去干。
那个年代,以军士兵换连队没有太多手续,打个背包自己过去就是了。
但是埃拉扎尔不乐意了,把这些新兵作为逃兵关起来。
埃坦求情无用后,自说自话带几个人把这些倒霉的新兵放了,然后自己也到另一个部队去干,到内格夫沙漠方向中继续战斗,参加了“霍雷夫”战役。
不过两人的别扭没有持续多久,在拉法的沙漠里,埃拉扎尔的营和埃坦的侦察队配合作战,战前侦察时,埃拉扎尔主动坐上埃坦的吉普,一起深入埃军阵线侦察,从沙暴中突然钻出来时,对着埃军营地一顿机枪猛扫,然后在沙暴中扬长而去,两人也言归于好了。
独立战争结束后,埃坦退入预备役,回到农场去,手把手地教新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移民种地,但1951年重新加入常备军两年,1953年再次退入预备役。
小国以色列强敌环伺下的生存之道在以色列,有句话家喻户晓:“我们没有石油,只有太阳、死海和脑袋。
”有这样一个国家:领土仅2.5万平方公里,不如海南省陆地面积大,全国人口仅为上海的1/3,资源方面除了沙漠,就是死海。
但这个国家成了“小国中的超级强国”,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灭国千年后还能复国,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会倍加爱惜自己的生命。
但仅仅珍视远远不夠,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屡战屡胜还有更多“秘诀”。
以色列没有前线与前方之分,只要一打仗,炮弹可能落到任何人的家门口。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独眼将军达扬说:“整个国家就是一条边境线。
以色列的平安有着罕见的地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由于阿拉伯邻国的严重敌对性而大大加深了。
”以色列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射程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挺好,如同打不死的“小强”。
全民皆兵,发动能力令大国咂舌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似乎只有草原游牧民族才搞全民皆兵,而这种军民一体制在现代国家已经不合时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而以色列却“逆流而动”搞全民皆兵,成为国家生存和开展的关键因素。
以色列常备军只有约20万,但预备役有40多万,这对一个总人口才800多万的国家来说,已经够多了。
也许其他国家的发动能力不比以色列差,但在这一点上怕是没法儿和以色列比——他们把国防发动做到了全世界。
早在2001年,以色列就在全球设置了兵站。
战事一旦扩大,这些兵站便负责把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组织回国参加卫国战争。
现在,以色列的国防发动令今非昔比,效率高得令人惊叹。
一般战事发生后,18小时,全体预备役领取武器;24小时,机动到位;36小时,投入战斗。
这是理论上的数据,也是最低效率,真正打起仗来效率更高。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利用“赎罪日”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以军一个预备役装甲旅从接到发动令到投入战斗仅仅用了8个小时,比标准时间提前了整整一天。
这个装甲旅尽管是“预备”性质,但到位速度极快,而且战斗力也很强:上去戈兰高地后,顶住了叙利亚4个精锐装甲师的凌厉攻势。
五次中东战争人们总乐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判断一场大事件的是是非非,因此,既有人因为反感恐怖主义而支持以色列,也有人因为同情弱者而支持哈马斯,最后纠结起来,也不过是开口骂这一方还是骂那一方的结果罢了。
然而,在开口之前,人们却很少思考过,为什么中东地区总是不安稳,总是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事实上,很多人看待巴以冲突仍是从情感出发,抱着一方以大欺小、一方反帝反霸的态度,这是我们一贯被灌输的理解,但遗憾的是,传播最广的未必就是事实,至少在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形象并非我们所熟知的那几副脸谱……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49:生存巴勒斯坦战争:建国第二天就面临亡国威胁的以色列1947年11月30日清晨,在耶路撒冷和一些阿犹混合的城镇,爆发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激烈武装冲突,这被称为是巴勒斯坦“非正式战争”的开始。
之后,在1948年1月—3月,双方不断发生冲突。
15日,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战争正式开始。
在英国支持下,阿拉伯联盟的正规军拥有大炮、坦克、飞机和英国教官,而新生的以色列只有相比之下少得可怜的游击队和在纳粹屠刀下逃生并得以建立自己国家的兴奋。
1948年6月11日:美苏联手为以色列送来4周休战期战争一开始,阿拉伯国家军队对比以色列优势明显,势如破竹。
5月17日,开战的第三天,美国代表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一份议案,建议安理会命令战争双方在36小时内停火。
苏联代表也要求安理会立即表决,并指责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要求它们停止行动。
英国最初反对美国的建议,并声称继续给予阿拉伯国家援助。
但不久,英国又同意了美国的建议,并撤走了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军官,停止向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提供武器。
6月11日,阿以双方同意停火四周。
1949年7月20日: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停战协定巴勒斯坦战争从阿拉伯出兵开始到以色列与叙利亚签订停战协定为止,共历时15个月,战争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以色列获胜而告终。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是现代以色列国家建国以来离崩溃最近的一次,西奈半岛到戈兰高地之间的土地在埃叙联军的南北夹攻下颤抖,以色列危如累卵。
但是,仅仅一周之后,涂着大卫星徽的坦克就开上了通往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公路,在这一周里,英雄的以色列装甲兵挽救了整个国家和民族。
上一期,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第188装甲旅在戈兰高地的奋战,在10月6日-7日北以色列最危急的时刻里和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第7装甲旅。
仓促迎战的第7旅顶住了叙利亚第7机步师和第3装甲师的进攻,打赢了“眼泪山谷”战役。
戈兰战役过去三十年了,“眼泪山谷”之战已经被收入各国装甲兵的教范,成为装甲防御作战的经典战例。
百战雄师第7装甲旅诞生在硝烟弥漫的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
战争爆发时,“哈贾纳”创始人什洛莫.沙米和海姆.拉斯克夫奉命组建第7机械化旅。
他们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编成了3个作战营:1个为装甲步兵营;2个是步兵营。
创建之初的第7旅缺少装备,名为机械化部队,实际上仅有10余辆刚刚从欧洲买进的美军在二战期间使用的M-3半履带装甲车,步兵甚至连沙漠地区作战必备的水壶也配不齐。
官兵几乎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大多数人都是在开战前两三天才领到武器。
1948年5月23日,以军向耶路撒冷西部要地拉图恩(现在以色列装甲兵博物馆所在地)发动进攻。
第7旅奉命担任助攻任务,掀开了自己近半个世纪中东征战史的第一页。
战斗中,右翼担任主攻的吉瓦提旅受阻,第7旅变助攻为主攻,从左翼进逼拉图恩,装甲步兵营一路冲进拉图恩镇警察局的大院。
但由于后续步兵分队没能及时跟进,最后被迫撤出阵地。
6月11日,阿以双方第一次停火。
利用这3周的时间,第7旅补充了人员和弹药,并对部队进行了强化训练。
7月9日,战火重燃,第7旅被调往北部参加肃清中加利利地区阿军的作战。
7月15日黄昏,第7机械化旅攻占中加利利重镇拿撒勒,重创叙利亚第5旅。
以色列第七装甲旅是较早换装M-48坦克的部队之一。
1967年六日战争中,第七旅在西奈前线作战,立下赫赫战功,也是以色列国防高层充分认识到装甲兵集群作战的威力。
10月下旬,在2个多月的第二次停火后,以军实施“哈雷姆”作战计划,准备将阿拉伯联军彻底逐出北加利利。
当时,叙军在这一地区约有23000人,20多辆坦克,而以军仅有3个旅9500人,23辆坦克和装甲车。
第7旅在这场速战速决的战役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他们奉命从西路对阿军防线纵深实施穿插,直取以叙边境重镇萨沙,达成战役合围的态势。
10月28日夜,第7旅从萨弗德的前进基地出发,装甲步兵营打头阵,步兵营乘坐搜罗来的五花八门的汽车沿着一条逶迤狭窄的公路向北疾进。
6小时后,提前到达指定位置,展开了对萨沙的攻击。
萨沙地区部署有叙军20辆坦克中的15辆,在攻击过程中,以空军有力地支援了第7旅的战斗。
第7旅攻陷萨沙的消息传到后,叙军整条战线迅速土崩瓦解。
赎罪日战争前,第七装甲旅全部换装了从英国进口的百人队长MK-3/5坦克,以色列根据本国国情对百人长队长坦克进行了多次改进。
第七旅在战争期间装备的应该是百人队长坦克在以色列的第二种改进型-肖特.卡尔型建国后,以色列国防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尤其加强了装甲机械化部队的建设。
第7机械化旅被改编为装甲旅,是当时以军唯一一个拥有2个坦克营的全建制装甲旅。
1956年10月29日,西奈战争爆发,以色列第202空降旅在阿里尔.沙龙上校的指挥下突袭米特拉山隘。
由于对装甲部队缺乏信心,第7装甲旅被搁置在次要地域。
在旅长尤利.本.阿里上校的强烈要求下,参谋部才勉强同意该旅加人支援步兵的战斗。
第82装甲营首先协同第4步兵旅攻占了库赛马,而后调头北上,直扑阿布奥格拉。
阿布奥格拉是一座坚固的要塞,在其东面通往以色列的道路上还建有鲁瓦法炮台和乌姆.卡泰夫、乌姆-希汉两个筑垒阵地,构成完整的多层次防御体系。
30日上午,第82装甲营到达乌姆.卡泰夫前沿,在多次冲击未果后,该营绕开乌姆.卡泰夫外围阵地,连夜转向达伊卡山隘,由那里迂回穿插直捣阿布奥格拉。
天将破晓之时,第82装甲营突然出现在阿布奥格拉南侧开阔地上,经过1小时激战,控制了阿布奥格拉道路交叉口。
埃军对阿布奥格拉的失陷非常恐慌,中午,从阿里什派出1个营南下,从乌姆.卡泰夫派出1个营西进,两面夹击第82装甲营。
第82装甲营依托阵地顽强抵抗,同时召唤空军对北线埃军实施猛烈的空中打击,迫使其北撤。
至10月31日,阿布奥格拉完全被以军占领,动摇了埃军西奈全线的防御。
之后,一直未得到补充和休整的第82装甲营又马不停蹄地进攻仍威胁东线以军的鲁瓦法炮台(这是他们开展2天来的第4次攻坚战)。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82装甲营的许多坦克在将炮弹和重机枪子弹打光的情况下,仍不顾一切地闯入埃军阵地。
埃守军完全丧失了斗志,全线溃败。
10月31日,埃军西撤,收缩至运河区,以军趁势展开追击,第7装甲旅一马当先,一路追击直到埃及重镇伊什梅利亚的对岸。
西奈给以色列军队的建设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第7装甲旅的出色表现使以军高层看清了坦克集群的巨大作用。
以色列的装甲兵建设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装甲部队扩充到9个旅。
1967年6月5日,六日战争爆发。
第7装甲旅作为南部军区的主力,再次踏上了西奈半岛土地。
第7装甲旅所在的塔尔装甲师负责进攻半岛最北端的腊法、阿里什地区。
腊法是半岛北部交通枢纽,而阿里什不仅是控制海岸公路的要地,而且还是西奈行政中心和埃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
因此,埃军在这一带构筑了多个坚固的要塞和据点,部署了约5个旅的重兵设防。
该地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战斗打响后,第7装甲旅(旅长什穆耶.戈南上校,此君在1973年曾担任以南部军区总司令)在腊法东北的外围据点汉尼尤斯歼灭埃守军1个坦克营,然后掉头南进至腊法外围。
根据师部的命令,第7旅抽调1个机械化步兵营协同友邻部队攻击腊法,主力部队则绕过腊法,向西直扑阿里什。
下午3时许,第7装甲旅的先头坦克营首先到达阿里什前方约8公里处的吉拉迪的据点(埃军1个营守卫),不待埃军判明情况,以军坦克群便不与守军纠缠,继续全速开进。
埃军官兵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以军坦克一辆接着一辆从他们工事前疾驶而过,未作出任何反应。
下午4时,第7旅先头营抵达阿里什近郊,比原定计划整整提前了16个小时!但是第7旅的后续部队在吉拉迪却遇到了顽强阻击。
吉拉迪守军在以军先头部队通过后,立即重整工事,堵塞了防线缺口。
在1个小时的激战中,第7装甲旅有10余辆坦克被击毁。
稍后,第7旅的装步营和友邻部队赶到,双方激烈拚杀,阵地几度易手,以军最后经过白刃战才肃清了守军,占领了吉拉迪。
6日凌晨,第7旅会同塔尔师其他部队,对阿里什发起总攻,并一举将其攻占,歼灭埃军1个旅。
至6日早上,以军攻占了西奈北部的所有预定目标,如期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计划。
至此,埃军西奈防线土崩瓦解。
黄昏时分,第7旅的部队已经挺进到阿里什西南的利卜尼山,正待休整之机,又接到追击命令。
第7旅官兵立刻登上战车攻击了埃军第3步兵师的后卫部队,占领了哈马。
随后突破哈特米亚山隘,进抵距运河60公里处的季夫加法,沿途又攻击了埃军最精锐的第4装甲师一部,毁伤坦克数十辆。
8日,挺进到了伊斯梅利亚附近的运河东岸。
临危受命在六日战争结束后,第7装甲旅转隶北部军区,阿维多尔.本.吉尔上校接任旅长之职,全旅在七十年代初换装了肖特-卡尔主战坦克(英国百人队长MK-3/5坦克的以色列改进型,加装了L-7 105毫米线膛炮和泰莱达因.大陆公司的AVDS-1790风冷柴油发动机)。
下辖第77坦克营(营长阿维多尔.卡哈汉尼少校,装备33辆肖特-卡尔坦克)、第82坦克营(装备33辆肖特-卡尔坦克)和第79坦克营。
赎罪日战争爆发的1973年正是第7装甲旅成立25周年,就在战争爆发前五周,第7旅的老兵在拉图恩集会,纪念以色列建国和第7旅成立25周年。
在拉图恩圆形剧场的那个晚上,身材瘦高、一付贵族气派的阿维多尔上校面对着总理和数千名老兵时,并不知道他的旅将在1个月后,为了保卫北加利利而全军覆没。
戈兰高地北起赫尔蒙山南坡,南到雅穆克河河谷,直线距离62公里。
整个高地呈南北窄,,各约12公里,,、中间宽,,约25公里,,形状,地势由北向南缓慢下降,落差约900米,,从1220米到300米,,。
高地北部的赫尔蒙山蜿蜒于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南部,最高山峰海拔2814米,是叙以黎三国交界处的制高点。
高地西坡和南坡陡峭,由高地分水岭到西侧胡拉谷地的落差在1000米左右;由高地到西南侧的加利利湖的落差更大,从高点的1220米一直降到海平面以下209米,其中400—500米的高程完全是峭壁。
正是这种地形使得从西侧、南侧登山的公路必须沿“之”字形攀援而上,行程需10—15公里,只有从高地东坡、即从大马士革方向向上困难相对较小。
高地属玄武岩地质构造,易于渗漏赫尔蒙山的积雪和雨季降水,由此形成了约旦河上游巴尼亚斯河等支流的重要水源。
约旦河的另一条支流雅穆克河虽发源于叙利亚,但也流经戈兰高地脚下。
自六日战争后,以色列的国防战略依赖于少量正规部队在紧密的空军支援下扼守住边境防线,赢得时间动员预备队。
边境防线是以支撑点为核心的预警防御系统。
戈兰高地共有11个沿“紫线”(1967年6月10日停战线)构筑的支撑点,平均每个有15名士兵,每个支撑点后方均部署有1个坦克排。
守备部队来自著名的哥兰尼旅,总兵力约1个加强连。
在他们后方提供支援的就是第188装甲旅。
在10月4日前,由于以色列高层的战略误判,整个戈兰高地仅有这1个装甲旅,不足百辆坦克。
国防部显然也意识到戈兰前线兵力薄弱的危险形势,因此实施了军内的局部总动员,并于10月4日下令第7装甲旅进驻戈兰高地北部。
这支百战雄师在时隔6年后再一次登上中东战争的舞台。
第7装甲旅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多次参加了戈兰高地和黎巴嫩边境的冲突,大多数军官对地形都很熟悉。
在全旅开拔前线之前,第7旅已经奉命将第77营派到戈兰高地加强给第188旅,阿维多尔则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对过去几年同时期的情况的比较,得出结论——赎罪日那天一定会出事。
他的经验告诉他,一旦战争爆发,他的旅都不会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
因此他命令旅属炮兵对戈兰高地地形进行了先期侦察,准备目标和射表,并召集各营营长,温习曾在北部军区先后实施过的作战计划。
10月5日星期五中午,第7装甲旅正式接到了要求他们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的命令。
阿维多尔感到宽慰,因为他已先期将前进指挥所的一部分迁到了戈兰高地。
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和时间赛跑。
由于仓促动员,相当部分的人员尚未归队,大量装备也还在仓库里。
坦克、装甲车和步兵从各个驻地向集结地域开进,由于动员仅限于国防军内部,地方交通系统并未接到动员令,不断的交通拥堵严重影响了集结速度。
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和严格的训练帮助了第7装甲旅,经过了最初的混乱,整个旅的指挥控制体系开始有条不紊的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