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边缘》中的疯女人形象解析
- 格式:pdf
- 大小:273.46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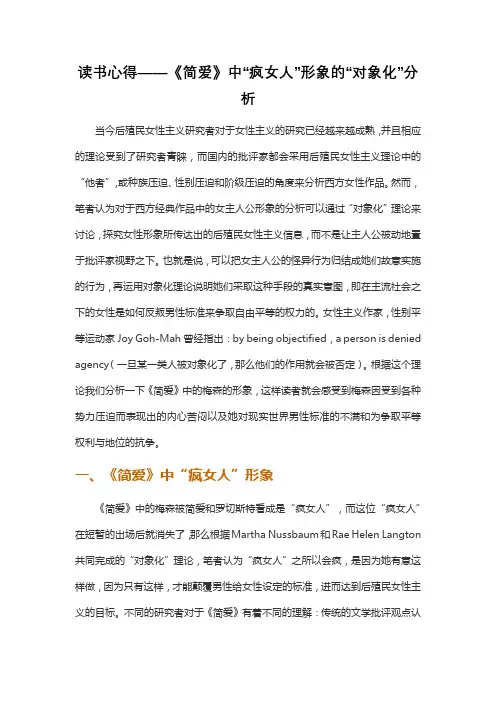
读书心得——《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对象化”分析当今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者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熟,并且相应的理论受到了研究者青睐,而国内的批评家都会采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他者”,或种族压迫、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角度来分析西方女性作品。
然而,笔者认为对于西方经典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可以通过“对象化”理论来讨论,探究女性形象所传达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信息,而不是让主人公被动地置于批评家视野之下。
也就是说,可以把女主人公的怪异行为归结成她们故意实施的行为,再运用对象化理论说明她们采取这种手段的真实意图,即在主流社会之下的女性是如何反叛男性标准来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力的。
女性主义作家,性别平等运动家Joy Goh-Mah曾经指出:by being objectified,a person is denied agency(一旦某一类人被对象化了,那么他们的作用就会被否定)。
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分析一下《简爱》中的梅森的形象,这样读者就会感受到梅森因受到各种势力压迫而表现出的内心苦闷以及她对现实世界男性标准的不满和为争取平等权利与地位的抗争。
一、《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简爱》中的梅森被简爱和罗切斯特看成是“疯女人”,而这位“疯女人”在短暂的出场后就消失了,那么根据Martha Nussbaum和Rae Helen Langton 共同完成的“对象化”理论,笔者认为“疯女人”之所以会疯,是因为她有意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颠覆男性给女性设定的标准,进而达到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目标。
不同的研究者对于《简爱》有着不同的理解:传统的文学批评观点认为,这部小说主要表达了一种理想的爱情,一种超越一切等级、美貌、财富等外在因素的爱情,也是一种追求灵魂与肉体一致的精神之爱,而另一种的观点则是由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芭所提出的,即简爱和梅森分别代表着女性的两面,而梅森就代表了女性的创造力和无穷的破坏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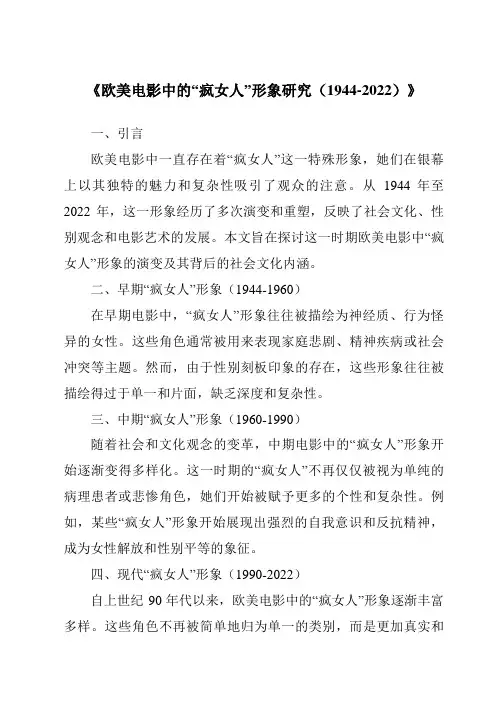
《欧美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研究(1944-2022)》一、引言欧美电影中一直存在着“疯女人”这一特殊形象,她们在银幕上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复杂性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从1944年至2022年,这一形象经历了多次演变和重塑,反映了社会文化、性别观念和电影艺术的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这一时期欧美电影中“疯女人”形象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二、早期“疯女人”形象(1944-1960)在早期电影中,“疯女人”形象往往被描绘为神经质、行为怪异的女性。
这些角色通常被用来表现家庭悲剧、精神疾病或社会冲突等主题。
然而,由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这些形象往往被描绘得过于单一和片面,缺乏深度和复杂性。
三、中期“疯女人”形象(1960-1990)随着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变革,中期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开始逐渐变得多样化。
这一时期的“疯女人”不再仅仅被视为单纯的病理患者或悲惨角色,她们开始被赋予更多的个性和复杂性。
例如,某些“疯女人”形象开始展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成为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的象征。
四、现代“疯女人”形象(1990-2022)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逐渐丰富多样。
这些角色不再被简单地归为单一的类别,而是更加真实和立体地反映了当代女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她们可能具有强烈的情感波动、复杂的心理世界和独特的个性魅力。
同时,这些角色也经常涉及到性别、权力、家庭、爱情等多元主题,为观众提供了更丰富的思考空间。
五、影响“疯女人”形象的因素1. 社会文化因素:欧美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受到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
随着社会进步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逐渐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
2. 电影艺术发展:电影技术的发展和艺术观念的更新也为“疯女人”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导演和演员们通过精湛的表演技巧和创新的拍摄手法,将这一特殊形象塑造得更加生动和立体。
3. 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为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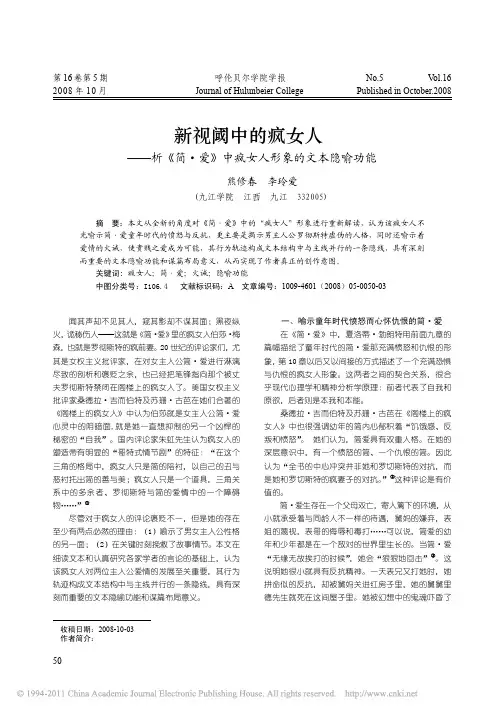
第16卷第5期呼伦贝尔学院学报No.5 V ol.16 2008年10月 Journal of Hulunbeier College Published in October.2008新视阈中的疯女人——析《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文本隐喻功能熊修春 李玲爱(九江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摘 要:本文从全新的角度对《简·爱》中的“疯女人”形象进行重新解读,认为该疯女人不光喻示简·爱童年时代的愤怒与反抗,更主要是揭示男主人公罗彻斯特虚伪的人格,同时还喻示着爱情的火诫,使贵贱之爱成为可能,其行为轨迹构成文本结构中与主线并行的一条隐线,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文本隐喻功能和谋篇布局意义,从而实现了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
关键词: 疯女人;简·爱;火诫;隐喻功能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601(2008)05-0050-03闻其声却不见其人,窥其影却不谋其面;黑夜纵火,诡秘伤人——这就是《简·爱》里的疯女人伯莎·梅森,也就是罗彻斯特的疯前妻。
20世纪的评论家们,尤其是女权主义批评家,在对女主人公简·爱进行淋漓尽致的剖析和褒贬之余,也已经把笔锋指向那个被丈夫罗彻斯特禁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了。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而伯特及苏珊·古芭在她们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认为伯莎就是女主人公简·爱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
国内评论家朱虹先生认为疯女人的塑造带有明显的“哥特式情节剧”的特征:“在这个三角的格局中,疯女人只是简的陪衬,以自己的丑与恶衬托出简的善与美;疯女人只是一个道具,三角关系中的多余者、罗彻斯特与简的爱情中的一个障碍物……”①尽管对于疯女人的评论褒贬不一,但是她的存在至少有两点必然的理由:(1)喻示了男女主人公性格的另一面;(2)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故事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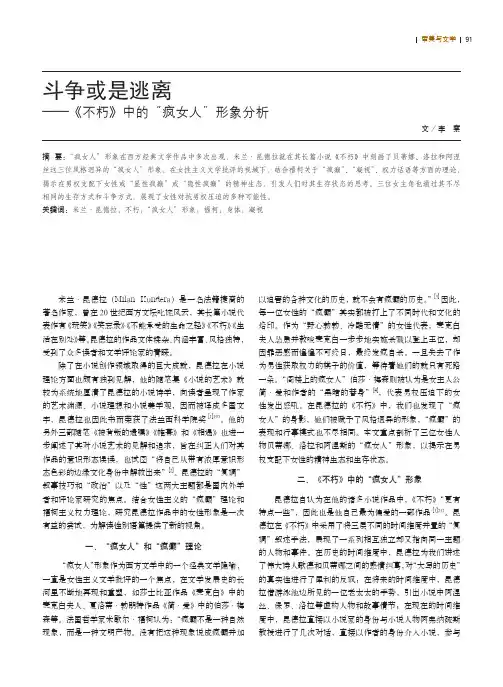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一名法籍捷裔的著名作家,曾在20世纪西方文坛叱诧风云,其长篇小说代表作有《玩笑》《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生活在别处》等。
昆德拉的作品文体糅杂、内涵丰富、风格独特,受到了众多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青睐。
除了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昆德拉在小说理论方面也颇有独到见解,他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就较为系统地厘清了昆德拉的小说诗学,向读者呈现了作家的艺术渊源、小说理想和小说美学观,因而被译成多国文字,昆德拉也因此书而荣获了法兰西科学院奖[1]193。
他的另外三部随笔《被背叛的遗嘱》《帷幕》和《相遇》也进一步阐述了其对小说艺术的见解和追求,旨在纠正人们对其作品的意识形态误读,也试图“将自己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边缘文化身份中解救出来”[2]。
昆德拉的“复调”叙事技巧和“政治”以及“性”这两大主题都是国内外学者和评论家研究的焦点。
结合女性主义的“疯癫”理论和福柯主义权力理论,研究昆德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为解读性别语篇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疯女人”和“疯癫”理论“疯女人”形象作为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文学隐喻,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焦点,在文学发展史的长河里不断地再现和重塑,如莎士比亚作品《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简·爱》中的伯莎·梅森等。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3]因此,每一位女性的“疯癫”其实都被打上了不同时代和文化的烙印。
作为“野心勃勃、冷酷无情”的女性代表,麦克白夫人怂恿并教唆麦克白一步步地实施杀戮以登上王位,却因罪恶感而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发疯自杀。
一旦失去了作为男性获取权力的棋子的价值,等待着她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则被认为是女主人公简·爱和作者的“黑暗的替身”[4],代表男权压迫下的女性发出怒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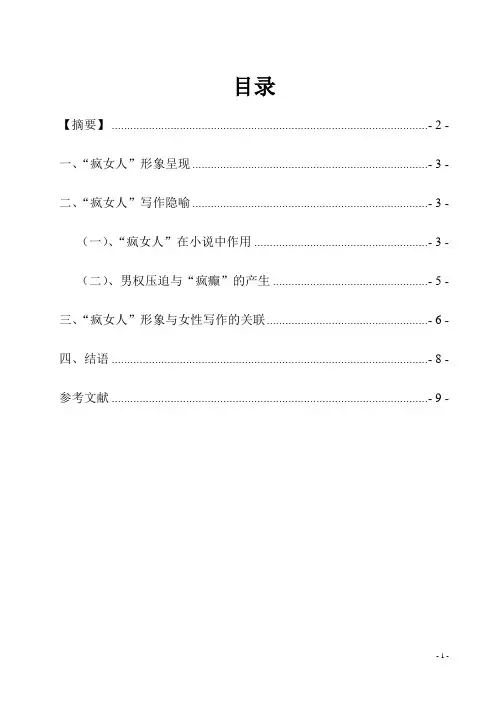
目录【摘要】 ...................................................................................................... - 2 -一、“疯女人”形象呈现 ............................................................................ - 3 -二、“疯女人”写作隐喻 ............................................................................ - 3 -(一)、“疯女人”在小说中作用 ........................................................ - 3 - (二)、男权压迫与“疯癫”的产生 .................................................. - 5 -三、“疯女人”形象与女性写作的关联.................................................... - 6 -四、结语 ...................................................................................................... - 8 - 参考文献 ...................................................................................................... - 9 -【摘要】伯莎.梅森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性人物,是潜藏在桑菲尔德庄园的一座阁楼上的带有精神病史的一朵罂粟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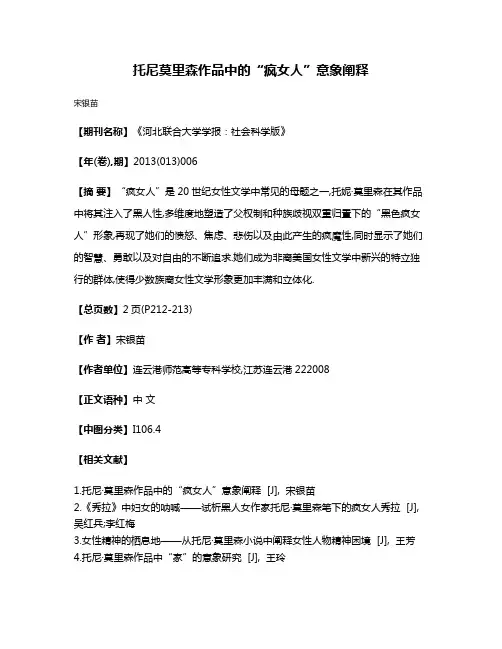
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疯女人”意象阐释
宋银苗
【期刊名称】《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13)006
【摘要】“疯女人”是20世纪女性文学中常见的母题之一,托妮·莫里森在其作品中将其注入了黑人性,多维度地塑造了父权制和种族歧视双重归置下的“黑色疯女人”形象,再现了她们的愤怒、焦虑、悲伤以及由此产生的疯魔性,同时显示了她们的智慧、勇敢以及对自由的不断追求.她们成为非裔美国女性文学中新兴的特立独行的群体,使得少数族裔女性文学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化.
【总页数】2页(P212-213)
【作者】宋银苗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连云港22200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4
【相关文献】
1.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疯女人”意象阐释 [J], 宋银苗
2.《秀拉》中妇女的呐喊——试析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笔下的疯女人秀拉 [J], 吴红兵;李红梅
3.女性精神的栖息地——从托尼·莫里森小说中阐释女性人物精神困境 [J], 王芳
4.托尼·莫里森作品中“家”的意象研究 [J], 王玲
5.在路上:荒诞的存在与个体的反抗——对托尼·莫里森《仁慈》中“反抗哲学”的文化阐释 [J], 王丽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英美文学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解析奚丹芸一、引言英美文学作品中对于疯女人形象的构建很早便已经出现,像莎翁创作于17世纪开端的名作《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和《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都堪称其中的代表人物。
同时,随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莎士比亚之后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对于疯女人形象的描述与运用以更高的频率不断出现。
她们形象各异,在作品中的职能不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与价值也都不一样。
有趣的是,学界对于疯女人形象群体的关注却远远滞后于她们产生的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疯女人形象群体中的成员都是以边缘人物的身份出现在读者的视线中。
同时,从成因上来说,英美文学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群体的设置原因很复杂,疯女人形象的出现与刻画既有可能是时代运动和社会思潮大背景渲染之下的结果,也很有可能跟作家们的自身经历、个人观念或者想要表达的文学含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本文则主要专注于一点,着重从女性意识的角度对英美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若干“疯女人”形象及这些形象所表示的文化意义的变迁展开探讨。
二、“疯女人”群体在英美文学中的出现与形象价值变迁如上文中所言及的,英美文学中的“疯女人”形象虽然很早就已经产生,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队伍不断壮大,具有代表性与研究价值的个例也不断丰富,但在非常长的一段时期里,学界对于英美文学作品中疯癫女性人物形象的关注度一直不够高。
较早的典型疯癫女性形象如前文中略有提及的奥菲利娅和麦克白夫人,她们全都产生于17世纪,但真正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对疯癫女性群体进行专门价值研究的学术著作,如女学者S·M·吉尔伯特和苏珊·格芭所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却迟迟地出现在了遥远的200余年之后。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的价值,特别是疯癫女性这一特殊群体潜在艺术价值的可挖掘性、可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
在女性意识蒙昧且受到压制的时代里,文学作品中的疯癫女性形象往往较少,即便出现,其意味也相对单纯得多,要么是作者无意为之的结果,要么是简单的结构上的需要。

《简·爱》和《藻海无边》中的“疯女人”形象分析○吴明靖(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 101101)[摘 要] 《简·爱》中的伯莎·梅森是一个带有野蛮属性的疯子,《藻海无边》中的安托万内特是一曲殖民主义的悲歌。
本文通过形象学和后殖民理论,分析“阁楼上的疯女人”在两部作品中不同形象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 《简·爱》; 《藻海无边》; 形象; 殖民[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5)10-0067-02 《简·爱》是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自1847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和评论界的关注。
时至今日,人们已不只感动于男女主人公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和简·爱独立不羁地追求平等、幸福的可贵精神,而是转移视角,将目光投向作品里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形象———疯女人伯莎·梅森。
琼·里斯(Jean Rhys,1894-1979)1966年写出《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被公认为是《简·爱》的前传。
《藻海无边》虽然保持了《简·爱》基本的故事表象,但决非简单地模仿或改写,而是一种再创造。
一、两个不同的伯莎·梅森《简·爱》中伯莎·梅森的故事是由罗切斯特一面之词叙述的。
罗切斯特年轻时落入了父兄和梅森家共同设立的圈套,跟伯莎·梅森结了婚,婚后才知道她有一个疯子母亲,她本人粗野下流,26岁就已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和疯子。
他出于人道主义,才把她带回英国。
伯莎·梅森的形象是通过简·爱看到的,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和野兽、魔鬼差不多的疯子,一个可怕的怪物。
在作品中我们听不到伯莎的语言,她只是被言说、被塑造、被控诉的失去任何申辩权利的女人。
《藻海无边》中伯莎·梅森原名叫安托万内特,是英国殖民者在牙买加的混血后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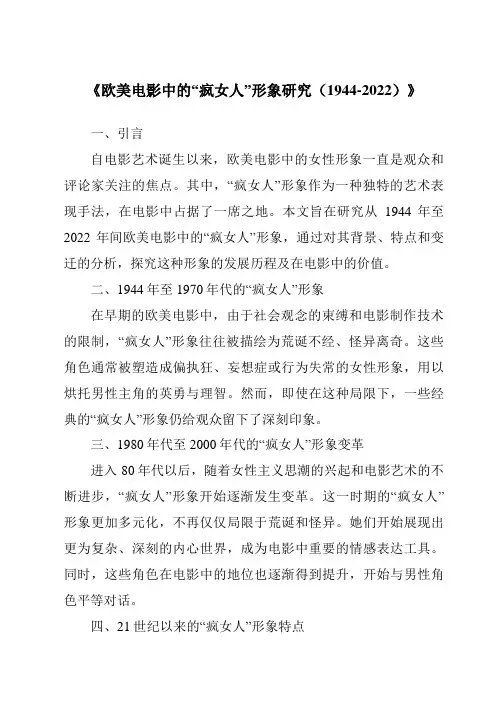
《欧美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研究(1944-2022)》一、引言自电影艺术诞生以来,欧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观众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
其中,“疯女人”形象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电影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本文旨在研究从1944年至2022年间欧美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通过对其背景、特点和变迁的分析,探究这种形象的发展历程及在电影中的价值。
二、1944年至1970年代的“疯女人”形象在早期的欧美电影中,由于社会观念的束缚和电影制作技术的限制,“疯女人”形象往往被描绘为荒诞不经、怪异离奇。
这些角色通常被塑造成偏执狂、妄想症或行为失常的女性形象,用以烘托男性主角的英勇与理智。
然而,即使在这种局限下,一些经典的“疯女人”形象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疯女人”形象变革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电影艺术的不断进步,“疯女人”形象开始逐渐发生变革。
这一时期的“疯女人”形象更加多元化,不再仅仅局限于荒诞和怪异。
她们开始展现出更为复杂、深刻的内心世界,成为电影中重要的情感表达工具。
同时,这些角色在电影中的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开始与男性角色平等对话。
四、21世纪以来的“疯女人”形象特点进入21世纪,欧美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呈现出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特点。
这些角色在性格、背景、经历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使得她们在电影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此外,随着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疯女人”形象开始具有国际化的特点,吸引了全球观众的关注。
五、对“疯女人”形象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疯女人”形象在欧美电影中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首先,她们作为女性主义的重要表现手段,挑战了传统社会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和歧视。
其次,“疯女人”形象在电影中扮演了重要的情感表达工具,使得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此外,“疯女人”形象还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为观众提供了了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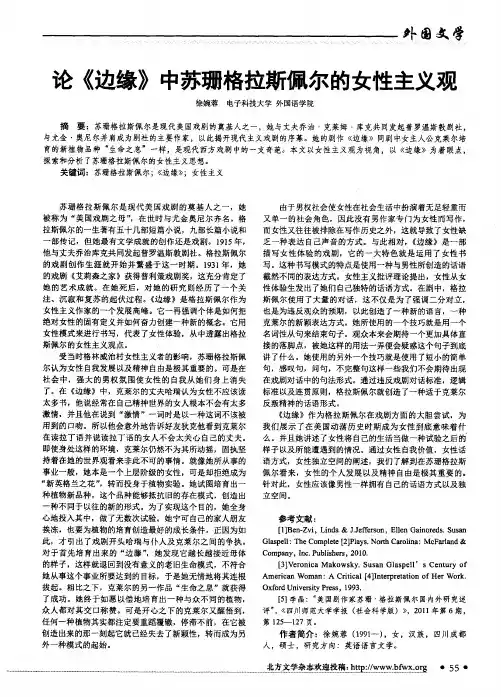
英美文学文化通识课程论文(2011年春季学期)重现“疯女人”—伯莎·梅森胡婉玲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TQLQA111100006“疯女人”这一形象群体在西方文学世界中历史由来已久,当文学被男权社会所垄断的时候,“疯女人”是作为配角的配角存在的。
“疯女人”处于边缘地位,相对于男性故事的存在而存在。
没有男性的故事,“疯女人”的故事便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如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奥菲利亚的《哈姆雷特》,但如果没有哈姆雷特,奥菲利亚将毫无故事可言”1。
那些非天使即魔鬼的女性形象也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们被扭曲变形,涂脂抹粉,披上了虚假的面纱。
男作家们总是全知全能,居高临下地肆意操纵着疯女人们的命运,从让男人们着迷的天使型疯女人“奥菲利亚”(16世纪)到用魔鬼型疯女人“郝维香小姐”,无不受着父权和夫权的压迫至死。
只有当女性拿到了文学的笔,她们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疯女人”形象终于得以真实地呈现,自主地表达。
恩格斯说过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妇女运动便无从谈起,而19世纪以前的妇女是没有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女性财产婚后全归男方所有。
19世纪,随着妇女走向社会,她们逐渐意识到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而妇女与男性社会的对立也在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
西方女性进入了累积了几个世纪的压迫最为深重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
这时一种新型的疯女人形象出现了。
她们跳出了男性文学的偏执,对统治了几个世纪的传统的“疯女人”形象群体进行反驳和颠覆。
《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翻检19世纪女性作品,人们会发现:疯女人的形象一再出现。
即便是外表最为保守的妇女作家,也会着迷似地创造出强悍有力的、独立的女性角色来,竭力要摧毁被作家和女主人公视为理所当然的父权制社会结构。
这种反叛的冲动不是投射到主人公身上的,而是通过疯女人体现出来的,表现出女作家既要接受父权社会的评判,又有意想抵制和拒绝它的双重心态。
”21伊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30到1980)》陈晓兰杨剑锋译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43页2 Gilbert Sandra and Gubar Susan: A Madwoman in the Attic(M)Yale University Press而这一颠覆的代言人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原型—伯莎梅森。
读书心得——《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形象解读《哈姆雷特》是一部关于复仇和伦理的文学作品,颇具人文主义色彩。
戏剧写于1601年,讲述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报仇,最终与弑兄娶嫂篡夺王位的叔叔同归于尽的故事。
《哈姆雷特》历来为众多文学批评家关注,但围绕这部作品展开的文学批评往往由男性主导,女性相对较少,研究的焦点常常投射到哈姆雷特身上,而针对剧中女性形象的研究相对匮乏。
雅克·拉康指出,男性批评家对奥菲利亚这一人物本身不感兴趣,除非是将其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充分揭示了女性被视为性工具的被动地位。
但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疯女人”被视为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形象,奥菲利亚开始进入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视野,1980年,肖瓦尔特在《再现奥菲利亚:女人、疯狂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职责》中分析了奥菲利亚的“疯女人”形象;1986年,怀特在《无辜的牺牲品:莎士比亚悲剧中诗意的不公平》中强调,奥菲利亚是《哈姆雷特》中最无辜、最值得同情的角色。
奥菲利亚的角色虽常被隐形化处理,但事实上不容忽视。
国内有部分学者尝试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奥菲利亚的形象,叶倩对奥菲利亚经历的“常态—疯癔—死亡”三个阶段进行分析,认为后两阶段是奥菲利亚对男权制社会反抗的体现,延续了“疯女人”研究的热潮。
宋声泉认为从男性中心视域分析奥菲利亚形象的塑造是一个误区,并分析产生误区背后的原因,强调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奥菲利亚形象塑造的必要性,但仅关注作者的行文立场,未能从故事中不同人物视角展开分析。
李艳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奥菲利亚的“自我”意识进行分析,并探索奥菲利亚悲剧的现代启示,只分析了奥的形象本身,而未对形象形成过程及原因展开深入讨论。
基于此,本文结合波伏瓦对女性地位的认识,尝试解读男性凝视下奥菲利亚的形象构建过程,揭示奥菲利亚在沉默和疯癫两种状态下被“她者化”的真相。
一、作为“她者”的第二性法国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认为,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
电影《疯狂边缘》中的伦理人情艾丽丝?门罗( Alice Munro )是加拿大女作家,2013 年10 月10 日,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给她的颁奖词是“当代短篇文学小说大师”。
门罗迄今为止出版了13 部短篇小说集和1 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可谓是“短篇女王”。
《疯狂边缘》这部影片就是根据门罗1994 年的一个短篇A Wilderness Station 改编而来,由安妮?维伦担任导演和编剧,主要刻画了三个主人公情感的纠葛,亲情与爱情的较量,在沉重而寂静的野外荒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情感大戏,电影的结局又恰恰说明了人在当时社会伦理之下的悲剧收场,而女孩却似乎收获了新的爱情。
笔者从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伦理人情入手,阐述其中两个男主人公的情感纠葛,再探讨佐治与安妮的这段乱伦之爱,以及佐治与安妮的结局,最后研究作者所要表达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影片《疯狂边缘》的创作风格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创作特色通常是以荒郊野外的溪流之地为故事主要发生的背景地点,以城郊小镇的平凡人的生活为写作题材,以沉重严肃的笔调来刻画一些令人难忘的角色。
《疯狂边缘》也不例外。
安妮、西蒙、佐治、赛德、牧伦先生,这些角色无不有着悲剧色彩。
影片中大篇幅的场景都是发生在荒郊野外,与大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包括兄弟俩砍树盖房子、无情的火灾等,有些事人们是无力与自然抗争的。
成长、婚姻、爱情、死亡,这些熟悉不过的字眼都被作者以生态自然的方式显露出来,然在自气息浓厚的景色之外,意蕴令人震撼。
影片是以时空转换的手法进行的,这也是艾丽丝?门罗创作的常用手法,现实生活与回忆打乱,重新组合起来,这在小说与电影之中是可以表现得很精湛的。
影片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世界,打开了另一个认识世界的视角。
二、《疯狂边缘》中的西蒙与佐治西蒙与佐治的矛盾与争斗是影片中的最重要部分,也是把剧情引向高潮的转折点。
西蒙与佐治是亲兄弟,同时也是情敌。
西蒙野蛮而粗鲁,佐治正直而温柔,西蒙与佐治因为安妮而陷入了争斗,最后佐治为了要与安妮在一起,把亲哥哥亲手杀掉。
赏析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
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心地纯洁、善于思考的女性,她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磨难。
她的生活遭遇令人同情,但她那倔强的性格和勇于追求平等幸福的精神更为人们所赞赏。
在里德太太家,10岁的简面对舅母、表兄妹的歧视和虐待,己经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
当她的表兄殴打她时,她勇于回击;当舅母嚷着叫自己的孩子远离她时,她高喊“他们不配和我在一起”;当她被囚禁在空房中时,想到自己所受到的虐待,从内心发出了“不公正”的呐喊。
在孤儿院,简的反抗性格更为鲜明,这和她的朋友海伦·彭斯忍耐顺从的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海伦·彭斯虽遭迫害却信奉“爱你的仇人”,在宗教的麻痹下没有仇恨,只有逆来顺受。
而简对冷酷的校长和摧残她们的教师深恶痛绝。
她对海伦说:“假如她用那根条子打我,我要从她手里把它夺过来,并且当面折断它。
”充分表露了她不甘屈辱和不向命运妥协的倔强性格。
小说主要描写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
简·爱的爱情观更加深化了她的个性。
她认为爱情应该建立在精神平等的基础上,而不应取决于社会地位、财富和外貌,只有男女双方彼此真正相爱,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在追求个人幸福时,简·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纯真、朴实的思想感情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仆人地位而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她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她对罗切斯特的财富不屑一顾,她之所以钟情于他,就是因为他能平等待人,把她视作朋友,与她坦诚相见。
对罗切斯特说来,简·爱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他精神为之一振。
罗切斯特过去看惯了上层社会的冷酷虚伪,简·爱的纯朴、善良和独立的个性重新唤起他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因而他能真诚地在简面前表达他善良的愿望和改过的决心。
简·爱同情罗切斯特的不幸命运,认为他的错误是客观环境造成的。
尽管他其貌不扬,后来又破产成了残废,但她看到的是他内心的美和令人同情的不幸命运,所以最终与他结婚。
2013年11月November ,2013University Education[摘要]夏洛蒂·勃朗特作为19世纪女权运动的先驱,摈弃了传统的“才子佳人”式的小说创作。
她以现实的笔触,在作品中刻画了一位其貌不扬但敢于反抗、敢于追求自由爱情的新型妇女形象。
小说中疯女人伯莎这一艺术形象具有其生活来源与心理基础。
文学作品作为作家主体意识的反映,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心态。
作品给我们的启示: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形象,她的产生和存在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
[关键词]疯女人艺术形象生活经历心路历程[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21-0048-02[收稿时间]2013-06-21[作者简介]周蒲芳(1954-),男,上海金融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汉翻译理论暨实践研究。
作为19世纪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爱情之作,《简·爱》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人们对《简·爱》的关注和喜爱已经超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
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品读它、赏析它。
《简·爱》带给人们的是强烈的精神震撼,作为读者我们不仅要为夏洛蒂·勃朗特那洞察事态人心的细腻笔触所折服,也深深地对她笔下塑造的人物的不幸命运给予同情。
历来人们谈及这部作品,更多的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男女主人公身上,而将文中的疯女人———伯莎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
这一欣赏角度不免偏颇,文中的伯莎并非可有可无,也并不是男女主人公曲折爱情故事的陪衬,而是推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一个有力道具。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才使得小说的情节多了许多惊心动魄。
小说中疯女人的每次出场都会产生一种紧张的气氛,其中以她在婚礼上的出现尤为精彩:一边是热闹的婚礼现场,一边是疯女人的出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如果不是这个插曲,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爱情可以完美收官,而这个小插曲,使读者对小说的结尾充满了期待和无限的遐想。
“疯女人”的抗争作者:杨荣珍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12期从作者与主人公审美关系的角度看,疯癫形象大致可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作为丧失理智与精神失常的病人形象进人艺术世界,其主要特征是在正常人的理性的语境中,成为情节发展的一个环节。
作者仅仅把疯癫看作是理性的文明社会中的边缘现象,而不从这种边缘现象反过来看主流社会;另一类则具有文学狂欢化的功效。
疯癫不只是正常人眼中的一种患病事实、社会生活中的边缘现象,更主要的是正常人的理性的世界、主流社会的世界可以在疯癫的语境中被颠倒过来。
作者通过对疯癫现象的戏仿,可以使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非常规逻辑得到突显,并与读者意识中的常规逻辑发生激烈的冲突。
本文要讨论的是第二类疯癫形象,笔者选取了《打出幽灵塔》、《阿珍》和《雷雨》中的三个“疯女人”形象进行讨论,探究她们的处境、性格、抗争及发疯的原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光明的中国又成了黑暗的中国。
广大的剧作者们目睹了中国人民遭受的种种压迫,紧握手中的笔,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去。
左剧作家于伶曾坦言:“到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即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可说是中国话剧运动的青年时期。
这时期话剧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大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
”在国内外环境和思潮的影响下“抗争”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关键词。
在这些“抗争”的儿女们当中有一类人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活跃在文本中“疯女人”。
由于她们自身的特殊性,注定“抗争”具有独到之处。
本文选取了《打出幽灵塔》、《阿珍》和《雷雨》中的三个“疯女人”形象进行讨论来分析其蕴涵着和折射着的不合理的社会和其抗争的特殊性。
一、《打出幽灵塔》中的月林1928年6月,鲁迅主编的《奔流》创刊,在第一卷第一、二、四期上,刊登了被白薇标注为“社会悲剧”的三幕剧《打出幽灵塔》。
月林,一个私生女,一个养女,她的处境在那个以荣生为首的幽灵塔中必定是最糟糕的她。
她既想要效仿当时新文学作品中所创造出的新女性人物,想跳出家庭的藩蓠与父权社会的束缚,但由于受旧的伦理道德的浸染,使她的行动显得迟疑而犹豫,散发着奇异的悲观情绪和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