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伯莎·梅森的“疯癫”形象
- 格式:doc
- 大小:64.00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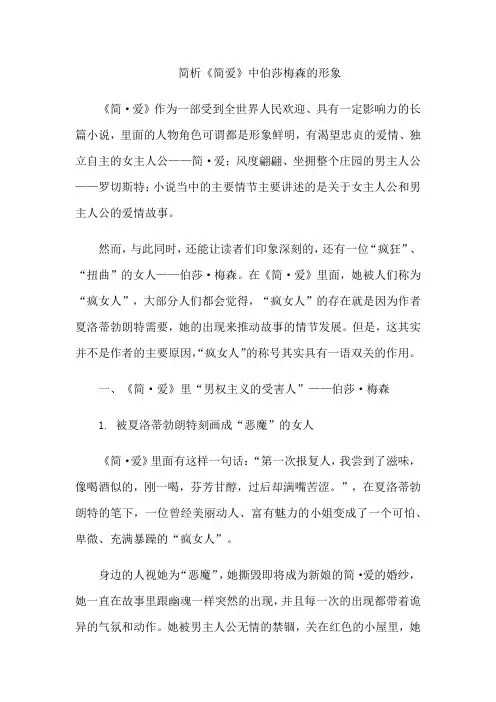
简析《简爱》中伯莎梅森的形象《简·爱》作为一部受到全世界人民欢迎、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长篇小说,里面的人物角色可谓都是形象鲜明,有渴望忠贞的爱情、独立自主的女主人公——简·爱;风度翩翩、坐拥整个庄园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小说当中的主要情节主要讲述的是关于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的爱情故事。
然而,与此同时,还能让读者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疯狂”、“扭曲”的女人——伯莎·梅森。
在《简·爱》里面,她被人们称为“疯女人”,大部分人们都会觉得,“疯女人”的存在就是因为作者夏洛蒂勃朗特需要,她的出现来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
但是,这其实并不是作者的主要原因,“疯女人”的称号其实具有一语双关的作用。
一、《简·爱》里“男权主义的受害人”——伯莎·梅森1. 被夏洛蒂勃朗特刻画成“恶魔”的女人《简·爱》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第一次报复人,我尝到了滋味,像喝酒似的,刚一喝,芬芳甘醇,过后却满嘴苦涩。
”,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笔下,一位曾经美丽动人、富有魅力的小姐变成了一个可怕、卑微、充满暴躁的“疯女人”。
身边的人视她为“恶魔”,她撕毁即将成为新娘的简·爱的婚纱,她一直在故事里跟幽魂一样突然的出现,并且每一次的出现都带着诡异的气氛和动作。
她被男主人公无情的禁锢,关在红色的小屋里,她受尽了压迫,她之前高贵的地位,美丽的梦想都化为灰烬。
所以,她的内心充满了对她身边一切的“憎恨”。
2.男主人公的冷漠和歧视造就了伯莎·梅森的“疯狂”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没有男权主义,没有身份、种族的歧视,这位美丽的夫人的生活是美好的,自由的。
在《世界文学评价》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冷漠无礼的天性和过分自尊的疾病而言,你简直是无与伦比。
”在书本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位“疯女人”她是有自己的名字——伯莎·梅森,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黑洞”,男主公对她的态度除了对她身份的厌恶,没有任何情感,所以,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是十分痛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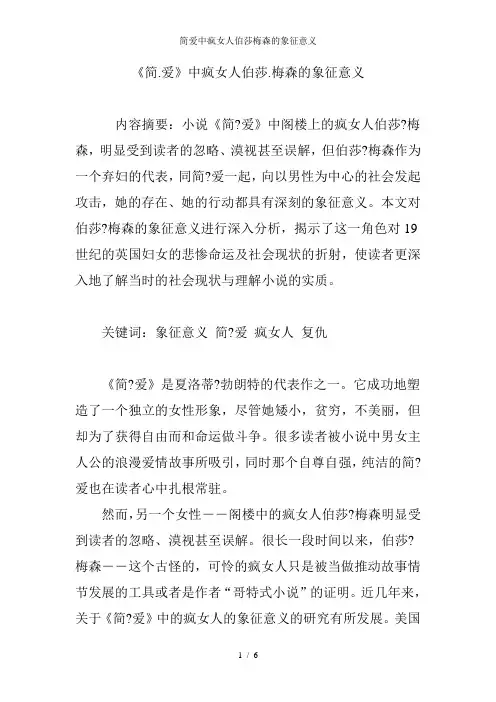
《简.爱》中疯女人伯莎.梅森的象征意义内容摘要:小说《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明显受到读者的忽略、漠视甚至误解,但伯莎?梅森作为一个弃妇的代表,同简?爱一起,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发起攻击,她的存在、她的行动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本文对伯莎?梅森的象征意义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一角色对19世纪的英国妇女的悲惨命运及社会现状的折射,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与理解小说的实质。
关键词:象征意义简?爱疯女人复仇《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之一。
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尽管她矮小,贫穷,不美丽,但却为了获得自由而和命运做斗争。
很多读者被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浪漫爱情故事所吸引,同时那个自尊自强,纯洁的简?爱也在读者心中扎根常驻。
然而,另一个女性――阁楼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明显受到读者的忽略、漠视甚至误解。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伯莎?梅森――这个古怪的,可怜的疯女人只是被当做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工具或者是作者“哥特式小说”的证明。
近几年来,关于《简?爱》中的疯女人的象征意义的研究有所发展。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以及苏桑?古芭在他们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认为伯莎?梅森就是女主人公简?爱的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
本文中,我将尽力呈现那个时代女性的命运以及社会条件,从个人角度来阐释疯女人的象征意义。
一.我眼中的《简?爱》和疯女人伯莎?梅森《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于1847年创作的,是19世纪英国文坛的最著名的小说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女主人公形象,简?爱虽然相貌平平,却自信机警,正直且富有同情心,摈弃了以往女主角的千篇一律的形象。
《简?爱》成功的克服了以往小说的弊端,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成为19世纪英国文坛的经典之作。
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出现使得整个故事都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她的出现难道仅仅是为了增加小说的神秘色彩以及趣味性吗?我们究竟该怎么定位这个疯女人呢?接下来我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挖掘和剖析疯女人这一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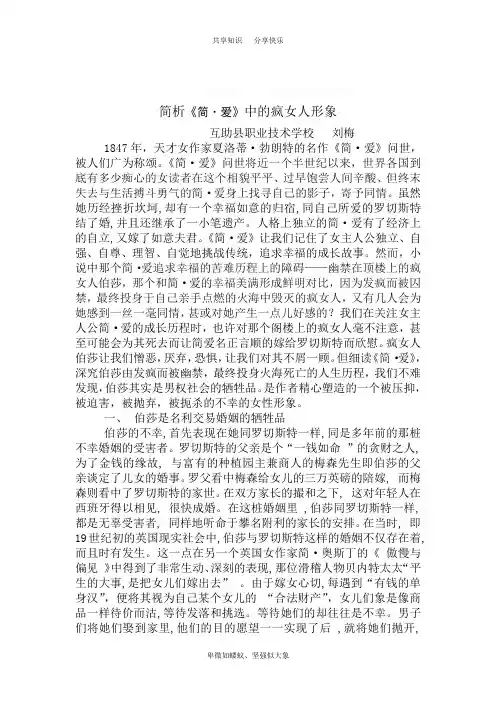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简析《简·爱》中的疯女人形象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刘梅1847年,天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名作《简·爱》问世,被人们广为称颂。
《简·爱》问世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到底有多少痴心的女读者在这个相貌平平、过早饱尝人间辛酸、但终末失去与生活搏斗勇气的简·爱身上找寻自己的影子,寄予同情。
虽然她历经挫折坎坷,却有一个幸福如意的归宿,同自己所爱的罗切斯特结了婚,并且还继承了一小笔遗产。
人格上独立的简·爱有了经济上的自立,又嫁了如意夫君。
《简·爱》让我们记住了女主人公独立、自强、自尊、理智、自觉地挑战传统,追求幸福的成长故事。
然而,小说中那个简·爱追求幸福的苦难历程上的障碍——幽禁在顶楼上的疯女人伯莎,那个和简·爱的幸福美满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发疯而被囚禁,最终投身于自己亲手点燃的火海中毁灭的疯女人,又有几人会为她感到一丝一毫同情,甚或对她产生一点儿好感的?我们在关注女主人公简·爱的成长历程时,也许对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毫不注意,甚至可能会为其死去而让简爱名正言顺的嫁给罗切斯特而欣慰。
疯女人伯莎让我们憎恶,厌弃,恐惧,让我们对其不屑一顾。
但细读《简·爱》,深究伯莎由发疯而被幽禁,最终投身火海死亡的人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伯莎其实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被压抑,被迫害,被抛弃,被扼杀的不幸的女性形象。
一、伯莎是名利交易婚姻的牺牲品伯莎的不幸,首先表现在她同罗切斯特一样,同是多年前的那桩不幸婚姻的受害者。
罗切斯特的父亲是个“一钱如命”的贪财之人,为了金钱的缘故, 与富有的种植园主兼商人的梅森先生即伯莎的父亲谈定了儿女的婚事。
罗父看中梅森给女儿的三万英磅的陪嫁, 而梅森则看中了罗切斯特的家世。
在双方家长的撮和之下, 这对年轻人在西班牙得以相见, 很快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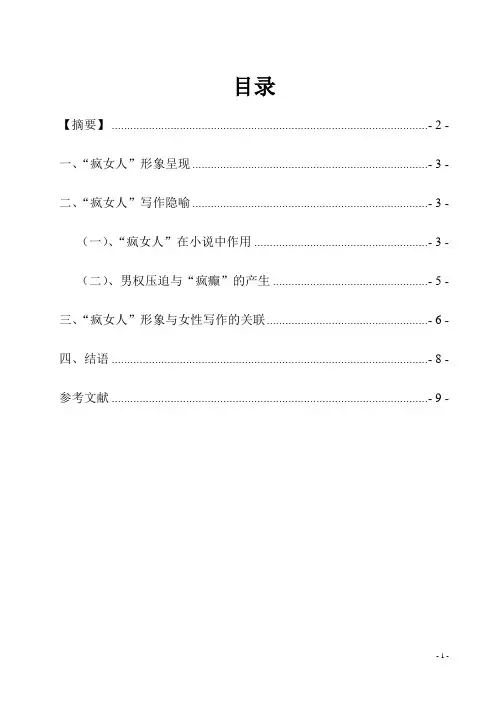
目录【摘要】 ...................................................................................................... - 2 -一、“疯女人”形象呈现 ............................................................................ - 3 -二、“疯女人”写作隐喻 ............................................................................ - 3 -(一)、“疯女人”在小说中作用 ........................................................ - 3 - (二)、男权压迫与“疯癫”的产生 .................................................. - 5 -三、“疯女人”形象与女性写作的关联.................................................... - 6 -四、结语 ...................................................................................................... - 8 - 参考文献 ...................................................................................................... - 9 -【摘要】伯莎.梅森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性人物,是潜藏在桑菲尔德庄园的一座阁楼上的带有精神病史的一朵罂粟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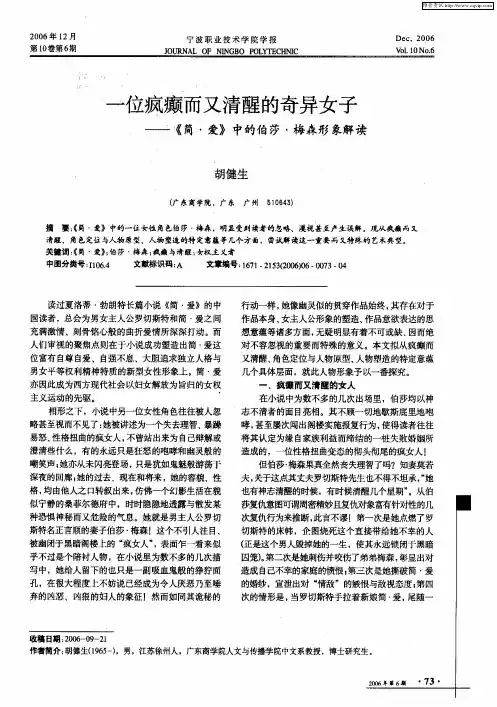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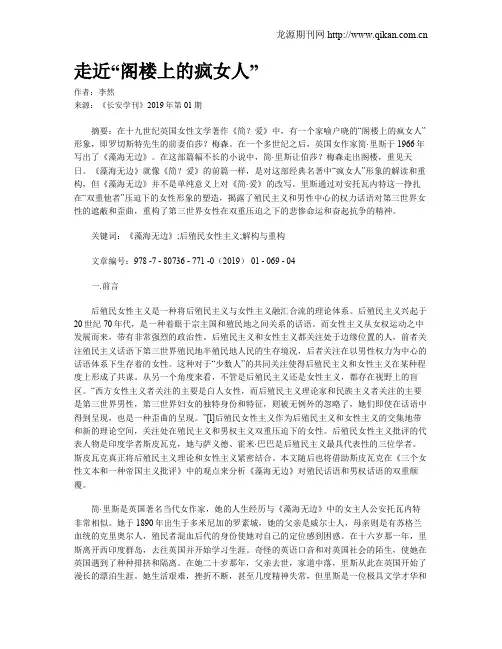
走近“阁楼上的疯女人”作者:李然来源:《长安学刊》2019年第01期摘要:在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著作《简?爱》中,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形象,即罗切斯特先生的前妻伯莎?梅森。
在一个多世纪之后,英国女作家简·里斯于1966年写出了《藻海无边》。
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简·里斯让伯莎?梅森走出阁楼,重见天日。
《藻海无边》就像《简?爱》的前篇一样,是对这部经典名著中“疯女人”形象的解读和重构,但《藻海无边》并不是单纯意义上对《简·爱》的改写。
里斯通过对安托瓦内特这一挣扎在“双重他者”压迫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揭露了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第三世界女性的遮蔽和歪曲,重构了第三世界女性在双重压迫之下的悲惨命运和奋起抗争的精神。
关键词:《藻海无边》;后殖民女性主义;解构与重构文章编号:978 -7 - 80736 - 771 -0(2019) 01 - 069 - 04一.前言后殖民女性主义是一种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融汇合流的理论体系。
后殖民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
而女性主义从女权运动之中发展而来,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性。
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关注处于边缘位置的人,前者关注殖民主义话语下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生存境况,后者关注在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下生存着的女性。
这种对于“少数人”的共同关注使得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共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管是后殖民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都存在视野上的盲区。
“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白人女性,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男性,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特征,则被无例外的忽略了,她们即使在话语中得到呈现,也是一种歪曲的呈现。
”[l]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交集地带和新的理论空间,关注处在殖民主义和男权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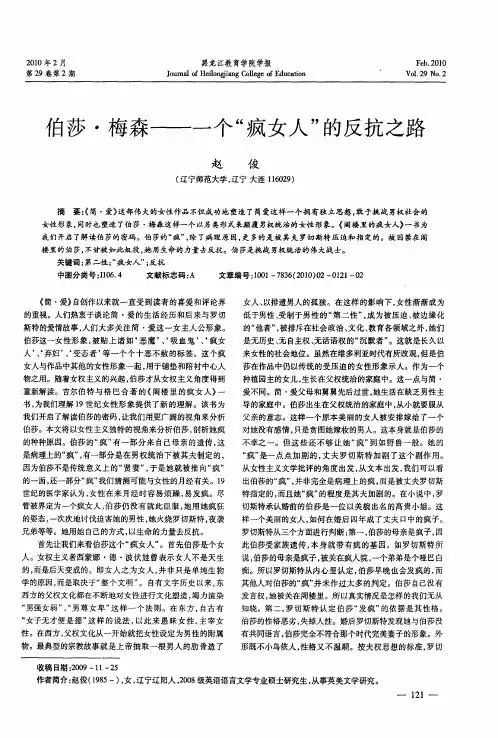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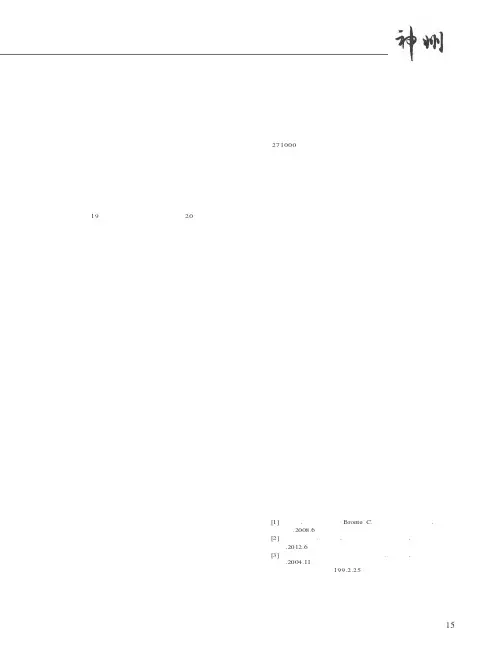
夫权体制下困兽的斗——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伯莎梅森和曹七巧李笑妍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71000摘要: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伯莎梅森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虽然处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从女权主义视角看却都有着困兽的斗一般强烈的复仇和悲剧命运。
本文旨在通过二者的比较,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刻地理解女权主义,从而对追求平等的两性关系做出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夫权困兽的斗女性主义伯莎梅森曹七巧不管是19世纪英国的伯莎梅森还是20世纪中国的曹七巧,都是男性话语体制下备受压抑走向疯癫的复仇之路而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
她们有着惊人相似的悲剧命运——都从美丽单纯的少女变成了邪火燃烧的恶妇。
下面让我们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剖析造成她们各自悲剧相似或不尽相同的原因。
一、同:(一)无爱的婚姻牢笼——与交易有关夫权社会下的女性作为一种商品是男人利益交换的工具。
她们一切作为人的的思想、情感和需求都被男性置之度外,有的只是被理所当然地作为商品来衡量的交换价值。
伯莎梅森是来自西班牙城的美丽姑娘,气质高雅、衣着华丽,曾经有众多的追求者。
然而罗切斯特却说从来没爱过她,没敬重过她,甚至没了解过她,对这段婚姻的评价就是认为自己当时“又蠢、又贱、又瞎”。
可见这是一桩被操纵的、有预谋的婚姻,自始至终毫无爱情可言。
可以说这场婚姻交易中男女双方地位和精神的双重不平等一开始就预示了后来的悲剧。
而跨越了一个世纪的东方,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也演绎着相似的故事。
“七巧被趋炎附势、贪图钱财的哥哥嫂嫂用“三媒六聘”抬进了姜公馆,嫁给了姜家患“骨痨”的二少爷做姨奶奶,后来成为了与自己寒门出身不符的姜家二奶奶。
纵观二者的悲剧命运,男权社会下无爱的婚姻交易无疑是其日后癫狂质变的深层根因。
(二)相似的反抗复仇——疯子的理智因了这无爱的婚姻与濒死的幽囚,不得不进行牢笼中困兽的斗。
在无边苦海里飞蛾扑火的死搏,看似癫狂荒谬、不可理喻,实则审慎机智又充满预谋。
《简爱》中的伯莎梅森,她的悲剧就在于她是人们眼里的“疯子”,是癫狂且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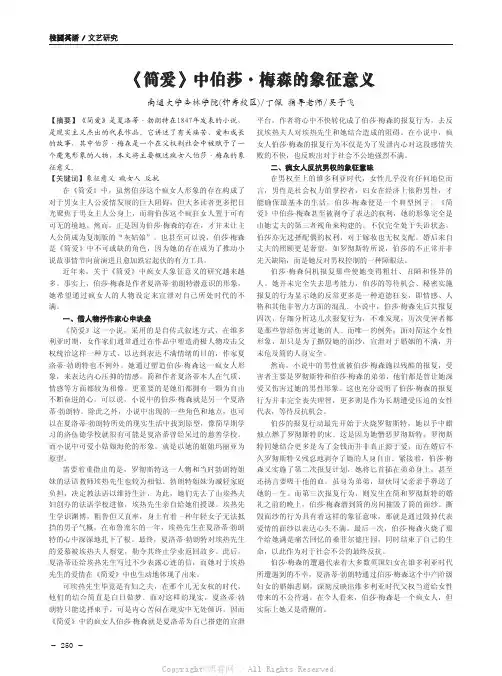
- 250-校园英语 / 文艺研究《简爱》中伯莎·梅森的象征意义南通大学杏林学院(钟秀校区)/丁佩 指导老师/吴子飞【摘要】《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在1847年发表的小说,是现实主义杰出的代表作品。
它讲述了有关痛苦、爱和成长的故事,其中伯莎·梅森是一个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赋予了一个魔鬼形象的人物,本文将主要概述疯女人伯莎·梅森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象征意义 疯女人 反抗在《简爱》中,虽然伯莎这个疯女人形象的存在构成了对于男女主人公爱情发展的巨大阻碍,但大多读者更多把目光聚焦于男女主人公身上,而将伯莎这个疯狂女人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
然而,正是因为伯莎·梅森的存在,才并未让主人公简成为复制版的“灰姑娘”。
也甚至可以说,伯莎·梅森是《简爱》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她的存在成为了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向前演进且愈加跌宕起伏的有力工具。
近年来,关于《简爱》中疯女人象征意义的研究越来越多。
事实上,伯莎·梅森是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潜意识的形象,她希望通过疯女人的人物设定来宣泄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满。
一、借人物抒作家心中块垒《简爱》这一小说,采用的是自传式叙述方式,在维多利亚时期,女作家们通常通过在作品中塑造消极人物攻击父权统治这样一种方式,以达到表达不满情绪的目的,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也不例外。
她通过塑造伯莎·梅森这一疯女人形象,来表达内心压抑的情感。
简和作者夏洛蒂本人在气质、情感等方面都较为相像,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拥有一颗为自由不断奋进的心,可以说,小说中的伯莎·梅森就是另一个夏洛蒂·勃朗特。
除此之外,小说中出现的一些角色和地点,也可以在夏洛蒂·勃朗特所处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像简早期学习的洛伍德学校就很有可能是夏洛蒂曾经呆过的慈善学校。
而小说中可爱小姑娘海伦的形象,就是以她的姐姐玛丽亚为原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罗彻斯特这一人物和当时勃朗特姐妹的法语教师埃热先生也较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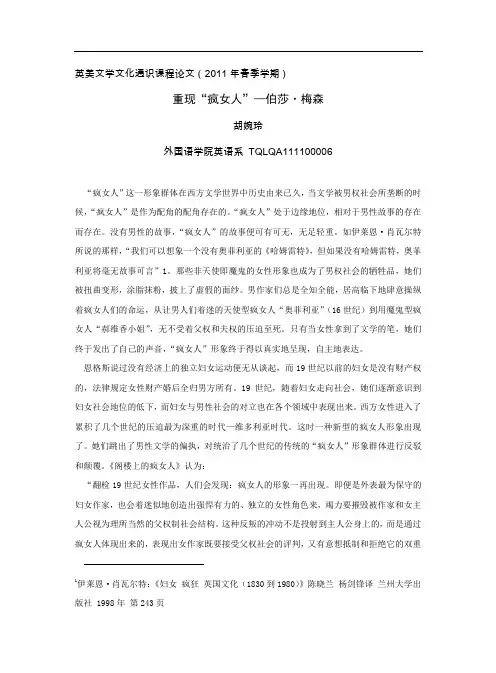
英美文学文化通识课程论文(2011年春季学期)重现“疯女人”—伯莎·梅森胡婉玲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TQLQA111100006“疯女人”这一形象群体在西方文学世界中历史由来已久,当文学被男权社会所垄断的时候,“疯女人”是作为配角的配角存在的。
“疯女人”处于边缘地位,相对于男性故事的存在而存在。
没有男性的故事,“疯女人”的故事便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如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奥菲利亚的《哈姆雷特》,但如果没有哈姆雷特,奥菲利亚将毫无故事可言”1。
那些非天使即魔鬼的女性形象也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们被扭曲变形,涂脂抹粉,披上了虚假的面纱。
男作家们总是全知全能,居高临下地肆意操纵着疯女人们的命运,从让男人们着迷的天使型疯女人“奥菲利亚”(16世纪)到用魔鬼型疯女人“郝维香小姐”,无不受着父权和夫权的压迫至死。
只有当女性拿到了文学的笔,她们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疯女人”形象终于得以真实地呈现,自主地表达。
恩格斯说过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妇女运动便无从谈起,而19世纪以前的妇女是没有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女性财产婚后全归男方所有。
19世纪,随着妇女走向社会,她们逐渐意识到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而妇女与男性社会的对立也在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
西方女性进入了累积了几个世纪的压迫最为深重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
这时一种新型的疯女人形象出现了。
她们跳出了男性文学的偏执,对统治了几个世纪的传统的“疯女人”形象群体进行反驳和颠覆。
《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翻检19世纪女性作品,人们会发现:疯女人的形象一再出现。
即便是外表最为保守的妇女作家,也会着迷似地创造出强悍有力的、独立的女性角色来,竭力要摧毁被作家和女主人公视为理所当然的父权制社会结构。
这种反叛的冲动不是投射到主人公身上的,而是通过疯女人体现出来的,表现出女作家既要接受父权社会的评判,又有意想抵制和拒绝它的双重心态。
”21伊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30到1980)》陈晓兰杨剑锋译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43页2 Gilbert Sandra and Gubar Susan: A Madwoman in the Attic(M)Yale University Press而这一颠覆的代言人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原型—伯莎梅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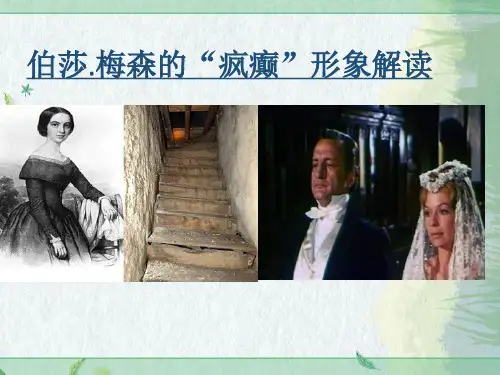
浅谈《简爱》中的边缘人物——伯莎梅森洪晓睿【摘要】《简·爱》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的价值=尊严十爱.然而,其中与女主人公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女性角色伯莎·梅森,明显受到读者的忽略甚至产生误解.本文将对这个悲剧人物进行介绍,并从女权主义分析这个边缘人物伯莎·梅森,从而证明她的存在对于《简·爱》具有重要意义.【期刊名称】《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卷),期】2014(034)005【总页数】2页(P67-68)【关键词】边缘人物;疯癫与清醒;命运;女权主义【作者】洪晓睿【作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以前人们读《简·爱》往往并不注意伯莎这个形象,毕竟她在小说中的出现机会很少。
因此,多数人把伯莎视为可有可无的陪衬,实际上,她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契机,她的行动总是选择“关键”时刻。
当简与主人神话般相遇,对桑菲尔德的环境感到高兴时,伯莎以她可怕的笑声向这宁静的生活之湖投入一颗石子,激起简的疑惧之波。
当简习惯了家庭教师的角色,一切释然,伯莎就深夜纵火,这把火促进了罗切斯特对简的了解,为他们爱情种子萌发提供了温床。
此后罗切斯特不冷不热,以及英格拉姆小姐的出现,使爱情故事趋于平淡,于是伯莎再次行动,用刀刺伤了神秘来访者梅森,这才引出了简的那段不卑不亢的求爱宣言。
一、疯癫而又清醒的女人伯莎·梅森果真全然丧失理智了吗?知妻莫若夫,关于这点其丈夫罗切斯特先生也不得不坦承:“她也有神志清醒的时候,有时候清醒几个星期”。
换言之,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由于两人毫无感情基础与交流,婚后生活颇不如意。
伯莎的性情变得更加暴躁,而罗切斯特亦深感失望,对妻子不闻不问而远游寻欢的做法,彻底打破伯莎对幸福生活的幻想。
从此她只能困守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棺木”——桑菲尔德府中那间幽暗的阁楼里,压抑之久必然会形成暴躁易怒的性格。
从佛洛伊德的精神角度分析《简爱》中的伯莎·梅森[摘要]从女权主义角度出发,《简爱》中伯莎?梅森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疯女人,她是隐藏在作品中的巨大密码,通过多这个密码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她与简实际上是同一人格的不同部分,伯莎以简的“本我”面目出现,隐藏在简的背后,通过她的行动,理性世界里的“自我”——简潜意识里要做的事情都由伯莎来完成。
[关键词]佛洛伊德、简爱、伯莎1979年,女权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库巴合著的《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简爱》中伯莎以一个女性控诉者的形象由阴暗的阁楼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之内。
她也被解读成女作家女权主义思想的表现:“疯女人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女作家的复本,是作家的自身的焦虑和疯狂、精神上的压迫感和分裂感的投射,女作家既要实现自己逃离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望,又难以摆脱其过程中的自卑情结,所以她们不是通过塑造浪漫主义的女强人而是塑造一位巫婆加恶魔般的疯女人来进行情感宣泄。
”方平先生曾直截了当的指出;“疯女人的形象成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她储存的信息是有多层次含义构成的:既有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又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
”伯莎的形象密码中的确隐藏了大量的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信息,在此,我仅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切入,通过对伯莎的再讨论,论证伯莎在作品中的地位。
一在大量的女权主义作品中都把伯莎看成简灵魂的化身或她的另外一个自我。
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伯莎被诠释成了简的灵魂。
“就字面上看,夜间出没于桑菲尔德庄园的幽灵是伯莎?梅森?罗切斯特,然而从寓意和心理学的层面上讲,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就是简灵魂的化身。
弗洛伊德曾经明确的指出;“以症候的形成来解读精神矛盾也是一种很便利的办法,最符合唯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候可以免去病人精神上的痛苦。
”而精神上的疾病是症候的典型表现,所以,以精神病人、疯子面目出现的伯莎就变成了唯乐原则即“本我”的理想代言人。
《简爱》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摘要:经典的具有女性独立反抗意识的文本《简·爱》,主人公简爱形象被认为是一个要求平等独立的新型女性。
而作品中的疯女人这一角色常常被忽略视为简的陪衬物,甚至被视为“贵族社会的一种象征”。
而疯女人伯莎是一个进行复仇的大胆的抗争女子;同时伯莎是男权社会中另一个被压抑的简爱,是简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她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关键词:简爱;疯女人伯莎;男权社会;复仇形象在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群当中,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简爱》可谓是真正在文字中确立妇女主体意识的一部发轫之作。
简爱因其刚毅的个性、自尊自爱的品格、要求人格独立和平等的美德等,为广大读者所喜欢。
然而,作品中仍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女性——疯女人伯莎-梅森,她常被世人冷落忽略,被视为“简爱的陪衬,以自己的丑与恶衬托出简的善与美;疯女人只是一个道具,三角关系中的多余者,罗切斯特与简的爱情的一个障碍物” ,更有甚者,认为“疯女人,可以说是贵族社会的一种象征”笔者认为这是对疯女人这一形象的误解。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权主义批评方法也应运而生。
批评家们从社会、文化、生理等各个方面对女性问题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系统研究,特别是从以往著名的女作家创作的经典作品人手,运用最新颖的批评话语重新解读女性作家创作的文本,并从中挖掘出许多新意,由此形成了许多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
其代表人物桑德拉·吉而伯特和苏珊·格巴合著了《阁楼上的疯女人》,在这部论著中他们仔细地考察了十九世纪妇女文学的文本,明确指出从夏洛蒂·勃朗特和简·奥斯丁,到爱米莉·狄金森,弗吉尼亚·伍尔夫,尽管这些作家属于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时代,然而她们的作品在主题和意象上都有某种同一性。
通过对这种贯穿于女性文学传统之中同一主题和意象进行研究,她们清晰地发现“历代的女性文学中都反复出现?锁闭和逃跑?的意象,小说中往往有精神失常者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现出,这些疯癫人物充当了那些安分守己的自我的社会替身,这些作品中还反复出现被禁闭在冰冷的或滚烫的环境中痛苦煎熬的种种隐喻。
失语的女人——伯莎.梅森之印象《简·爱》是世界文学作品中一部著名的小说。
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常常会被女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所折服,于是就自然而然的忽视甚至讨厌伯莎·梅森这个藏在阁楼中的疯女人。
从女性意识角度来看,伯莎与简·爱是同受男性社会压迫的姐妹。
相对于简·爱而言,由于丧失语言功能,伯莎的反抗隐蔽迂回,但却更彻底。
最终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在她们自己的反抗和小说的主题中实现了统一。
标签:简·爱;伯莎·梅森;失语的女人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大国,但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妇女的地位。
英国妇女仍然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
“嫁人”几乎是唯一向他们敞开的“职业”,而集谦卑、柔顺、牺牲、忘我等品德于一身的“家庭天使”或“高尚淑女”则成为当时理想的女性角色。
简·爱针对当时认为妇女只要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就可以了的观点,大声疾呼:“妇女可以做更多的事,学更多的东西,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
”“我不是天使,我就是我自己。
”这句话也成了女权主义者经久不衰的口号。
纵观《简·爱》,到处都渗透着女作家对爱情、自由的渴望和对妇女命运的思考。
作品以“妇女人格”这一崭新的命题,向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挑战。
《简·爱》是一部女性主义作品,通过这部作品,夏洛蒂不只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而是给我们提供了广阔丰富的女性生活图景。
所以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是简·爱,其他女性一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里要说的就是小说中一言未发的疯女人—伯莎·梅森。
失语症原指在医学上因大脑左部受伤而造成的言语功能障碍或丧失。
我们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指妇女在生理上受到损伤而导致其言语功能障碍或丧失,实际上,“说不出”,难以说,无从述说自己经验的困境,就是典型的女性失语症。
肖沃尔特曾经说过:“问题不是语言不足以表达女人的意识,而是女人未能得到充分运用语言的手段,故而被迫沉默,或陈述婉约、迂曲。
目录【摘要】 ...................................................................................................... - 2 -一、“疯女人”形象呈现 ............................................................................ - 3 -二、“疯女人”写作隐喻 ............................................................................ - 3 -(一)、“疯女人”在小说中作用 ........................................................ - 3 - (二)、男权压迫与“疯癫”的产生 .................................................. - 5 -三、“疯女人”形象与女性写作的关联.................................................... - 6 -四、结语 ...................................................................................................... - 8 - 参考文献 ...................................................................................................... - 9 -【摘要】伯莎.梅森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性人物,是潜藏在桑菲尔德庄园的一座阁楼上的带有精神病史的一朵罂粟花。
她困守在无爱的婚姻牢笼中,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幸福,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她努力过、抗争过,但在强大的男权大厦的压迫下,其微弱渺小的反抗,最后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
然而,在无声的抗争中,她打破了权威,颠仆了伦理,成为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疯女人”。
那么,在本文中,主要展现了伯莎的形象特点与作用,分析出导致她疯狂的原因,以及对我们的深刻启示,并通过对“疯女人”形象的深入了解,揭示女性应当如何更好地生存与生活。
【关键词】:疯女人女性意识男权压迫话语权写作一、“疯女人”形象呈现“疯女人”是《简爱》作品里的一个边缘化的角色,相对于罗切斯特的故事存在而存在。
这个在西班牙以美貌著称的美人,生于富商之家,本来该是锦衣玉食、富丽堂皇的一生,然而,她的父亲和罗切斯特那爱财如命的父亲暗中交易,用三万英镑的陪嫁把她许配给了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的,后来竟被和自己生活了四年的丈夫禁闭在没有窗户的冰冷的桑菲尔德庄园长达十年。
她的人生由此陷入沼泽。
在作品中,夏洛蒂勃朗特重点描写了她的四次暴力行为:第一次是深夜闯入罗切斯特的房间放了一把火;第二次是刺伤了前来看望她的哥哥梅森;第三次是阻碍罗切斯特与简的婚礼,罗切斯特带着众人闯入“疯女人”的囚禁室,伯莎与罗切斯特搏斗,最后被捆绑。
第四次是纵火烧毁了桑菲尔德庄园,使罗切斯特成了残废,自己也葬身火海。
从《简爱》中很容易发现:伯莎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坏女人的形象,而是一个挣扎的女人形象。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
婚前,伯莎是美丽、热情、生机勃勃的富家小姐,婚后的她却变成了不可理喻的冷酷的复仇女人,最终以自我毁灭而告终。
倘若,伯莎如果能得到丈夫的爱和体贴是不至于疯的,即使疯也不会这么严重。
可以发现,是罗切斯特毁了她的一切,她怎能不奋起报复那个薄情寡义的男人。
伯莎为什么要嫁给他呢?通过罗切斯特向简爱谈论自己当年的婚姻时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伯莎在西班牙城以美貌著称,有众多的追求者,罗切斯特也极愿参与到男人们对伯莎追逐的队伍中,并且承认“我以为我爱她”。
其实“我并不爱她。
我强烈地需要她,可那并不是爱。
”罗切斯特内心无意识的独白暴露了他人面兽心的本质。
可见,罗切斯特决定娶伯莎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的伯莎有魅力和才华,重要的,她有钱。
当他知道她有家族疯病史后,不但不同情和保护妻子,反而更加藐视和讨厌她,以致后来毫不犹豫的抛弃了她。
最终,这个曾在西班牙以美貌著称的美人变成了“四肢发达、腰圆膀大、没有光泽”,一脸“凶相”的幽禁在阁楼里的疯女人,彻底成了一个酗酒、纵欲、残暴、狡猾、世代遗传的疯子形象。
“魔鬼”、“怪物”、“妖妇”,对一个女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容貌殆尽、受丈夫无情诋毁和侮辱更可悲了。
二、“疯女人”写作隐喻(一)、“疯女人”在小说中作用伯莎被称作是第一个女性主义的“疯女人”原型形象,这个带有荒诞色彩的疯女人为什么会引进象《简·爱》这样现实气息浓厚的小说中来,我想,女作家大概是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从最浅近的、表层的创作意图来说,深更半夜、行动诡异的疯女人,造成了强烈的悬念,可以增添作品的吸引力,满足了那些在阅读中寻求刺激的读者。
这样,疯女人就成了搅拌在作品中的浓烈的酱料。
不过,女作家在表层的创作意图下面还蕴藏着一个核心思想。
疯女人所要担负起的最重要的、不能由旁人代替的任务:就是让她点燃起一把熊熊烈火,把豪华的大宅院烧为灰烬。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就指出:“女作家通过把她们的愤怒和疾病投射在可怕的人物身上,为她们和自己的女主角创造出一个黑暗的替身(dark double),她们便与父权制文化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等同起来,同时又加以修正。
”②这样,疯女人不再单纯是历史的牺牲品,而是女作家们与父权制社会斗争的利器。
我们知道,自古水火不形容。
“火”象征着刚强粗烈;“水”代表着温润纯洁。
在这里“火”这一意象相对以往“水”的意象就是一个突破与转折。
但,同时也投射了男性对女性的幻想:在男性眼中,女性应柔情似“水”,而伯莎却放了两把火,彻底颠覆了男性的期待。
这两场火是被镇压的女性企图烧毁男权牢笼的愤怒之火,是女性企图摈弃父权制社会诱惑的净化与重生之火。
当疯女人被男性代言,温顺听话的“疯女人”则被捧上天堂奉为天使,而叛逆不羁的则被打下地狱贬为魔鬼。
然而,伯莎.梅森玩火自焚,实际上是她的功成身退。
她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打开终年被紧闭多年的疯女人的顶楼,意味着把女主人公简·爱内心深处、暗处的潜意识亮出来了。
再深一层次,疯女人还表现了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自身的焦虑和疯狂。
女作家既要实现逃离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望,又难以摆脱其自卑情结,所以她们不是通过塑造一位浪漫的女强人而是一个巫婆或恶魔的疯女人来进行情感宣泄。
同时,“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糕的是这身体曾经被供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成了她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
”③通过这种“寓意读法”,把失去理智控制的疯女人认同于明理懂事、有主见的简·爱,推出这么一个被极度陌生化了的女主人公。
所以“疯女人”形象成了作家们在文化和社会中被压制的东西得到恢复时那一种爆炸性,彻底破坏性的力量的恢复与释放的突破口。
除此之外,这把火还让《简爱》这部作品中显现出了几许基督教的色彩。
用基督教的观点来解释“火”,即上帝之子耶稣用圣灵与火为世人的灵魂施洗以涤除她们的罪孽,或者说是上帝以此作为对人类的进行的最后审判和惩罚。
因此,“火”包含的双重含义是既可毁灭一切,又可带来新生。
这把火成为了传统婚姻的突破口,摧毁了男权社会的中心地位,罗切斯特不再为贵族,简也不再是他的附属品,从而实现真正实现了人格上的平等。
因此,在《简爱》这部著作里,伯莎展现的不仅仅是毁灭、破坏性的力量,也是建设性的力量。
(二)、男权压迫与“疯癫”的产生作为一个配角,伯莎在文学批评史中长期被藐视,被误读,对她的论述和研究也一次次地被搁浅被埋没。
桑菲尔德阁楼上是一个疯女人吗?伯莎真的是精神错乱吗?仔细分析疯女人的四次行动,她的矛头所指的都是小说中的几个男人,而对小说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未直接伤害过。
“火烧罗切斯特”,刺杀哥哥梅森,撕毁婚纱,如果她真的疯了,又如何能够干净利落,从容不迫地完成行动?“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安静”④。
虽然她的行为怪异极端,但似乎她的头脑是清醒的。
而究竟是真疯还是假疯,她无法展示、无法证明,更无法辩解,她有的只是几声低语或呢喃。
朱虹先生在纪念《简·爱》、《呼啸山庄》问世一百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使人耳目一新:“婚变后的罗彻斯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他的种种自我辩白其实是读者所能听到的一面之词,对于那做妻子的无异是缺席审判,因为疯女人被永远剥夺了她的发言权。
如果从字里行间细细读去,那么不难看出,受害者其实是他的妻子,不是通过当时不平等的婚姻法把妻子的财产占为己有的那个丈夫。
而这贪图妻财的动机,罗切斯特讳莫如深,因此他的形象其实并不那么光彩。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伯莎清楚地知道是谁造成了她今天的悲惨生活,她要斗争的对象是男权大厦的统治者们——父兄和丈夫。
要知道,伯莎还未出场就被罗切斯特宣告她是个疯子。
伯莎的缺席与不在场恰巧给罗切斯特一个随意建构她的机会,因而,伯莎成了一个永恒沉默的“他者”,被挤入边缘地带。
在事实上,伯莎是扭曲的、被压迫的、令人同情的,是被误解的,但她并没有疯。
在男权世界里,“疯”只是她保护自己的一个面具。
这些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疯”是追求独立的女性自身潜在或显在的因素,是为了突显女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而运用的夸张、变形的方式。
在此,朱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简·爱和疯女人应该是共同受男性压迫的姐妹;但《简·爱》是主流文学和通俗小说的结合体,为了迎合读者对通俗小说所要求的刺激,于是疯女人被打发到顶楼上去充当坏女人这一角色了,又丑又恶的她只能作为简的善与美的陪衬物、对立面而存在于小说中。
”⑤当“疯女人”形象逐渐洗去了恶魔的污垢后,就露出了遭受父权制家庭严酷摧残的不幸女性的本来面目。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勾勒了两极化的女性形象:一类是天使型,集美丽高贵、温柔可爱为一身,且生活的无忧无虑,幸福快乐;另一类恰恰相反,属于魔鬼型,阴险狡猾、狠毒淫荡且经常被仇恨与抱复缠住。
显然,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伯莎被罗切斯特妖魔化了,而实际她与“疯癫”有显著地不同。
每一个觉醒的女性身上都有一种因叛逆而来的疯狂,在她的身上残存着些许魔鬼的影子,但她的内心更多的有着天使的智慧光芒。
这类女人往往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疯女人”是被侮辱、被戕害的孤独女性形象,是生活在男性社会底层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