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构筑的永恒传奇——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月亮意象
- 格式:pdf
- 大小:195.48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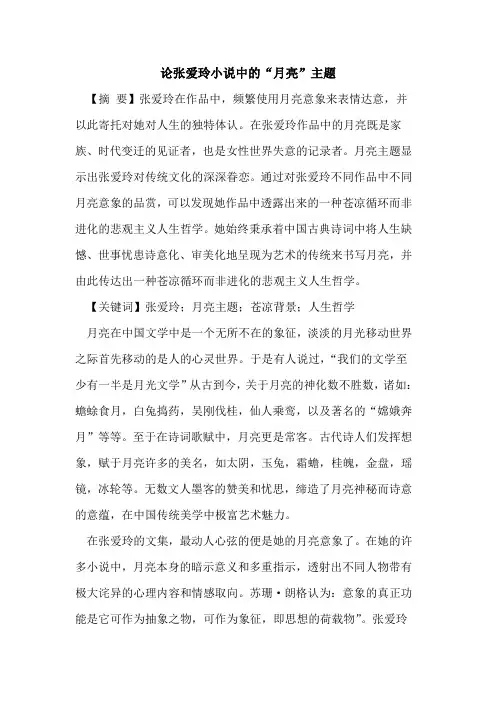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主题【摘要】张爱玲在作品中,频繁使用月亮意象来表情达意,并以此寄托对她对人生的独特体认。
在张爱玲作品中的月亮既是家族、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女性世界失意的记录者。
月亮主题显示出张爱玲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
通过对张爱玲不同作品中不同月亮意象的品赏,可以发现她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一种苍凉循环而非进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
她始终秉承着中国古典诗词中将人生缺憾、世事忧患诗意化、审美化地呈现为艺术的传统来书写月亮,并由此传达出一种苍凉循环而非进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
【关键词】张爱玲;月亮主题;苍凉背景;人生哲学月亮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象征,淡淡的月光移动世界之际首先移动的是人的心灵世界。
于是有人说过,“我们的文学至少有一半是月光文学”从古到今,关于月亮的神化数不胜数,诸如:蟾蜍食月,白兔捣药,吴刚伐桂,仙人乘鸾,以及著名的“嫦娥奔月”等等。
至于在诗词歌赋中,月亮更是常客。
古代诗人们发挥想象,赋于月亮许多的美名,如太阴,玉兔,霜蟾,桂魄,金盘,瑶镜,冰轮等。
无数文人墨客的赞美和忧思,缔造了月亮神秘而诗意的意蕴,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极富艺术魅力。
在张爱玲的文集,最动人心弦的便是她的月亮意象了。
在她的许多小说中,月亮本身的暗示意义和多重指示,透射出不同人物带有极大诧异的心理内容和情感取向。
苏珊·朗格认为:意象的真正功能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
张爱玲之所以选择月亮作为其小说文本的主导意象之一,这和中国历史传统中悠久的月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而张爱玲还渗透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元素,通过现代性转换激活了月亮这个古老的原型,从而建构起自己关于月亮意象的独特的艺术话语,赋予了月亮以新的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
1 目睹家庭兴衰《金锁记》中,以月亮描写作为文章开端、结尾,意蕴丰富,令人感慨万千:作者借助月亮在升起和降落,过去和现在的时光流走岁月更换中,表现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变化,以及对人生的了悟、对命运的揭示、对生命的哲思。
![[摘录]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意象](https://uimg.taocdn.com/03568a5fc950ad02de80d4d8d15abe23492f035d.webp)
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意象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意象“一粒沙里看出世界, 一朵野花里见天国。
”我愿意尝试着走进张爱玲的一花一沙,探究那些已经过时了的死去了的人物,看他们的灵魂是怎样的颠簸喘息过,而今是否还幽幽地、伴着月光在夜的窗外窥视我们文明的浮华和升华。
自古文人多爱月,而爱月的女文人更多,且爱得痴迷。
张爱玲自己也说,她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因此,她看月亮的次数比世上所有的人都多,故而她的文字世界里,月亮绵绵地纠缠着她,空灵地引领着她,清高地提升着她。
今天我们打开《张爱玲文集》,其间关于月亮的意象俯拾皆是,有些如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有些则浓墨重彩,精雕细琢,无不流淌成一条动人的月亮河。
月光的意象中融进了她对人生的灰暗理解所谓“意象”,也就是在一个个有着色彩、光泽、声音的物象形态中,包含着隐喻、象征、暗示等深层的意蕴。
张爱玲的小说中意象纷呈,多如繁星,不胜枚举,如她反复写到的镜子、墙、电车、屏风等等,就连很多别人已经写过、写滥的事和物在她的笔下,也突然就与其他事物发生了联系,有了绝妙的象征、暗示等意义,变成了她任意驱使表达爱憎的工具。
比如月亮,月亮的意象在张爱玲笔下出现得最多、最典型,也最有特色。
“月亮”不仅出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心理之间的关系有着鲜明的对应,带着不同的感情色彩,而且“月亮”在张爱玲世界中的每一次升起,都具有不同的象征意蕴。
通过对月亮的描写,使许多原本抽象的东西,如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感觉等,像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具有了具体的形态。
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圆白、光泽,有着森森逼人的阴气,是带着杀气的蓝光,这样一反常规的描述,融进了她对苍凉人生的全部感悟。
自身命运的不幸,天才般的观察生命的独特视角,使她的文笔所表现的生活处处充满了不信任与怀疑, 充满悲观、绝望、冷漠的格调,她说“人生的底色是苍凉的”,“沾着了人沾着脏”。
在散文《私语》中,表现少年时期因反叛父亲被关禁长达小半年时,是这样感受月光的,“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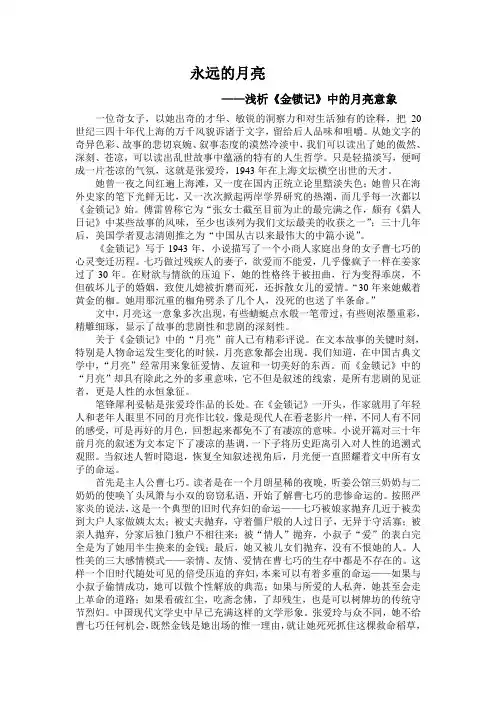
永远的月亮——浅析《金锁记》中的月亮意象一位奇女子,以她出奇的才华、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活独有的诠释,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万千风貌诉诸于文字,留给后人品味和咀嚼。
从她文字的奇异色彩、故事的悲切哀婉、叙事态度的漠然冷淡中,我们可以读出了她的傲然、深刻、苍凉,可以读出乱世故事中蕴涵的特有的人生哲学。
只是轻描淡写,便呵成一片苍凉的气氛,这就是张爱玲,1943年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天才。
她曾一夜之间红遍上海滩,又一度在国内正统立论里黯淡失色;她曾只在海外史家的笔下光鲜无比,又一次次掀起两岸学界研究的热潮,而几乎每一次都以《金锁记》始。
傅雷曾称它为“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三十几年后,美国学者夏志清则推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
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
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
“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
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文中,月亮这一意象多次出现,有些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有些则浓墨重彩,精雕细琢,显示了故事的悲剧性和悲剧的深刻性。
关于《金锁记》中的“月亮”前人已有精彩评说。
在文本故事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人物命运发生变化的时候,月亮意象都会出现。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月亮”经常用来象征爱情、友谊和一切美好的东西。
而《金锁记》中的“月亮”却具有除此之外的多重意味,它不但是叙述的线索,是所有悲剧的见证者,更是人性的永恒象征。
笔锋犀利妥帖是张爱玲作品的长处。
在《金锁记》一开头,作家就用了年轻人和老年人眼里不同的月亮作比较,像是现代人在看老影片一样,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可是再好的月色,回想起来都免不了有凄凉的意味。

张爱玲《传奇》里的月意作者:方波陈骞沈娟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17期摘要:在张爱玲《传奇》里,月亮形态各异、色彩纷呈,少了传统月意的浪漫柔和,多了些苍凉、诡谲。
这些“月亮”悄无声息地见证着人世间纠结的情感,不管是大而白的满月,还是一钩白色月牙,黄的也好,红的也罢,它们都深隐着其独特丰富的意蕴。
月亮在《传奇》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环境的渲染及故事情节的安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表现在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折射、扭曲心理的象征以及复杂情爱的反思等方面。
关键词:《传奇》;月亮;悲剧作者简介:方波,彝族,滇中文化保护与研究中心成员,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审美教育;陈骞,汉族,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03月亮在中国文学里被赋予了独特的意味,一轮平常的明月,引人无限的感想,触动文人对生命哲理的思考。
张爱玲在《传奇》中,运用月亮呈现扭曲人性变态心理,见证人生不断上演的悲剧,也从另一面映衬人与人之间或真诚或卑微的爱情。
一、折射悲剧命运在张爱玲《传奇》这部小说里,月亮悄无声息地见证着世间的情感和人物的命运。
《金锁记》以月亮开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有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1]小说以此作为全篇的开端,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解释了人生的艰辛和悲哀。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岁月轮转,月亮依旧。
《传奇》里张爱玲多次安排长安和芝寿这两个悲剧人物看见月亮。
“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
墨灰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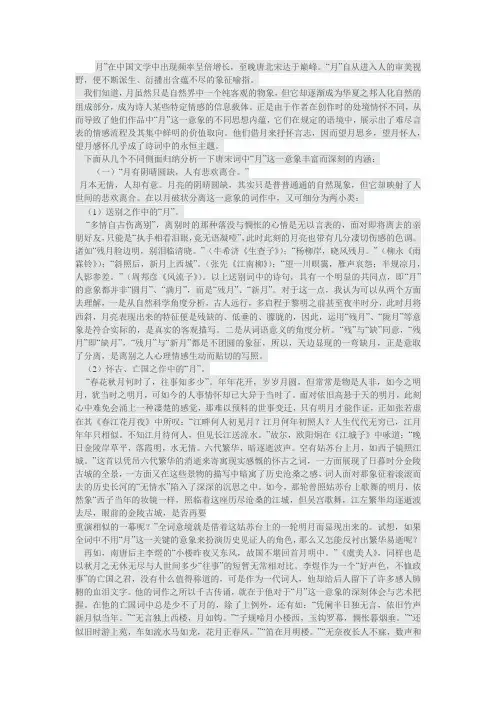
月”在中国文学中出现频率呈倍增长,至晚唐北宋达于巅峰。
“月”自从进入人的审美视野,便不断派生、衍播出含蕴不尽的象征喻指。
我们知道,月虽然只是自然界中一个纯客观的物象,但它却逐渐成为华夏之邦人化自然的组成部分,成为诗人某些特定情感的信息载体。
正是由于作者在创作时的处境情怀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作品中“月”这一意象的不同思想内蕴,它们在规定的语境中,展示出了难尽言表的情感流程及其集中鲜明的价值取向。
他们借月来抒怀言志,因而望月思乡,望月怀人,望月感怀几乎成了诗词中的永恒主题。
下面从几个不同侧面归纳分析一下唐宋词中“月”这一意象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一)“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月本无情,人却有意。
月亮的阴晴圆缺,其实只是普普通通的自然现象,但它却映射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在以月破状分离这一意象的词作中,又可细分为两小类:(1)送别之作中的“月”。
“多情自古伤离别”,离别时的那种落没与惆怅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面对即将离去的亲朋好友,只能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此时此刻的月亮也带有几分凄切伤感的色调。
诸如“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牛希济《生查子》);“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雨霖铃》);“斜照后,新月上西城”。
(张先《江南柳》);“望一川暝霭,雁声哀怨;半规凉月,人影参差。
”(周邦彦《风流子》)。
以上送别词中的诗句,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月”的意象都并非“圆月”、“满月”,而是“残月”、“新月”。
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分析,古人远行,多启程于黎明之前甚至夜半时分,此时月将西斜,月亮表现出来的特征便是残缺的、低垂的、朦胧的,因此,运用“残月”、“陇月”等意象是符合实际的,是真实的客观描写。
二是从词语意义的角度分析。
“残”与“缺”同意,“残月”即“缺月”,“残月”与“新月”都是不团圆的象征,所以,天边显现的一弯缺月,正是意取了分离,是离别之人心理情感生动而贴切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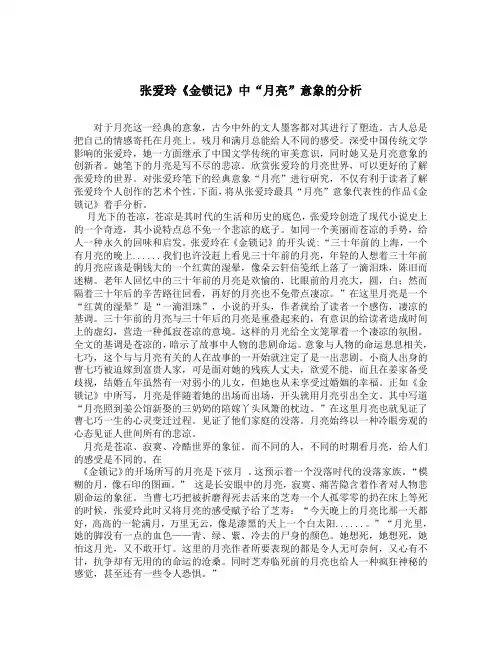
张爱玲《金锁记》中“月亮”意象的分析对于月亮这一经典的意象,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都对其进行了塑造。
古人总是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月亮上。
残月和满月总能给人不同的感受。
深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的张爱玲,她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审美意识,同时她又是月亮意象的创新者。
她笔下的月亮是写不尽的悲凉。
欣赏张爱玲的月亮世界,可以更好的了解张爱玲的世界。
对张爱玲笔下的经典意象“月亮”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读者了解张爱玲个人创作的艺术个性。
下面,将从张爱玲最具“月亮”意象代表性的作品《金锁记》着手分析。
月光下的苍凉,苍凉是其时代的生活和历史的底色,张爱玲创造了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其小说特点总不免一个悲凉的底子。
如同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给人一种永久的回味和启发。
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在这里月亮是一个“红黄的湿晕”是“一滴泪珠”,小说的开头,作者就给了读者一个感伤,凄凉的基调。
三十年前的月亮与三十年后的月亮是重叠起来的,有意识的给读者造成时间上的虚幻,营造一种孤寂苍凉的意境。
这样的月光给全文笼罩着一个凄凉的氛围。
全文的基调是苍凉的,暗示了故事中人物的悲剧命运。
意象与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七巧,这个与与月亮有关的人在故事的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出悲剧。
小商人出身的曹七巧被迫嫁到富贵人家,可是面对她的残疾人丈夫,欲爱不能,而且在姜家备受歧视,结婚五年虽然有一对弱小的儿女,但她也从未享受过婚姻的幸福。
正如《金锁记》中所写,月亮是伴随着她的出场而出场,开头就用月亮引出全文。
其中写道“月亮照到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头凤箫的枕边。
”在这里月亮也就见证了曹七巧一生的心灵变迁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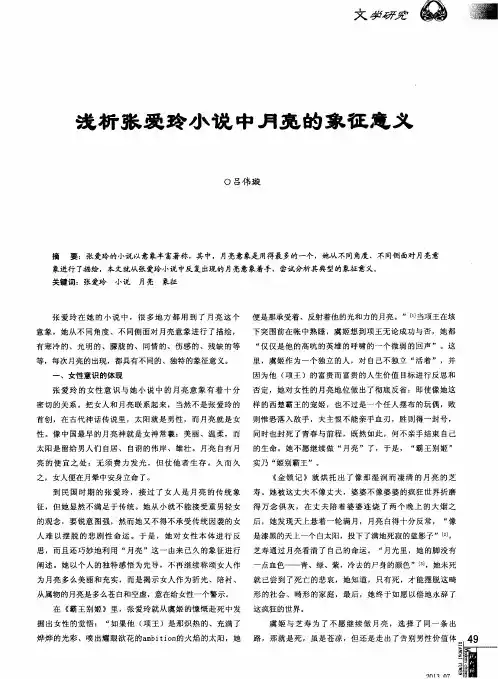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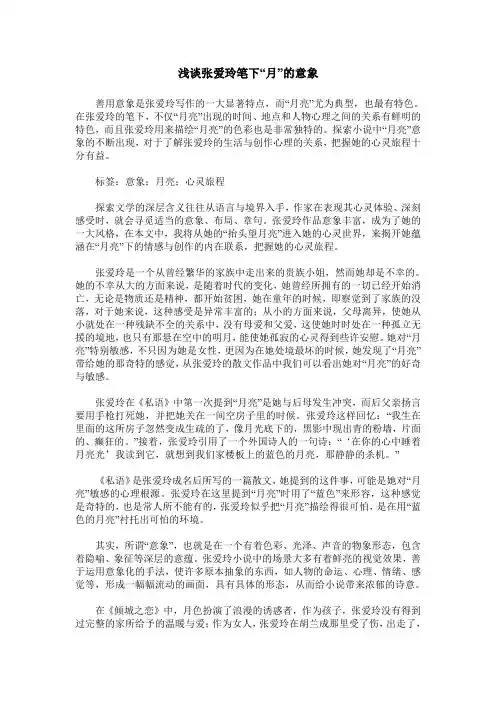
浅谈张爱玲笔下“月”的意象善用意象是张爱玲写作的一大显著特点,而“月亮”尤为典型,也最有特色。
在张爱玲的笔下,不仅“月亮”出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心理之间的关系有鲜明的特色,而且张爱玲用来描绘“月亮”的色彩也是非常独特的。
探索小说中“月亮”意象的不断出现,对于了解张爱玲的生活与创作心理的关系,把握她的心灵旅程十分有益。
标签:意象;月亮;心灵旅程探索文学的深层含义往往从语言与境界入手,作家在表现其心灵体验、深刻感受时,就会寻觅适当的意象、布局、章句。
张爱玲作品意象丰富,成为了她的一大风格,在本文中,我将从她的“抬头望月亮”进入她的心灵世界,来揭开她蕴涵在“月亮”下的情感与创作的内在联系,把握她的心灵旅程。
张爱玲是一个从曾经繁华的家族中走出来的贵族小姐,然而她却是不幸的。
她的不幸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她曾经所拥有的一切已经开始消亡,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开始贫困,她在童年的时候,即察觉到了家族的没落,对于她来说,这种感受是异常丰富的;从小的方面来说,父母离异,使她从小就处在一种残缺不全的关系中,没有母爱和父爱,这使她时时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也只有那悬在空中的明月,能使她孤寂的心灵得到些许安慰。
她对“月亮”特别敏感,不只因为她是女性,更因为在她处境最坏的时候,她发现了“月亮”带给她的那奇特的感觉,从张爱玲的散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月亮”的好奇与敏感。
张爱玲在《私语》中第一次提到“月亮”是她与后母发生冲突,而后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并把她关在一间空房子里的时候。
张爱玲这样回忆:“我生在里面的这所房子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接着,张爱玲引用了一个外国诗人的一句诗:“‘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亮,那静静的杀机。
”《私语》是张爱玲成名后所写的一篇散文,她提到的这件事,可能是她对“月亮”敏感的心理根源。
张爱玲在这里提到“月亮”时用了“蓝色”来形容,这种感觉是奇特的,也是常人所不能有的,张爱玲似乎把“月亮”描绘得很可怕,是在用“蓝色的月亮”衬托出可怕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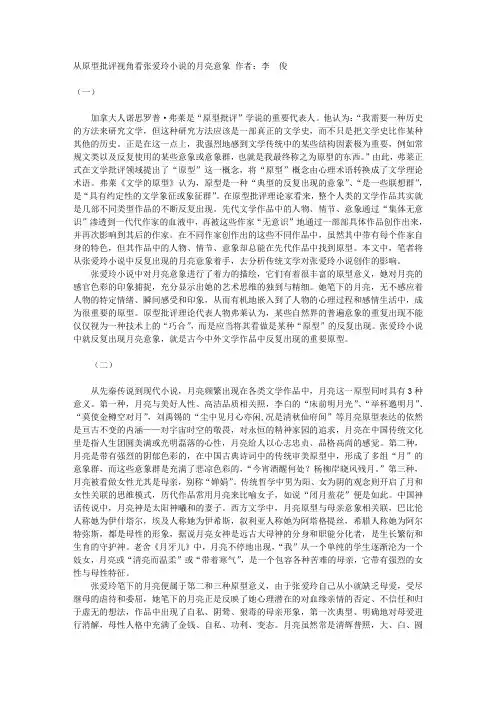
从原型批评视角看张爱玲小说的月亮意象作者:李俊(一)加拿大人诺思罗普·弗莱是“原型批评”学说的重要代表人。
他认为:“我需要一种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但这种研究方法应该是一部真正的文学史,而不只是把文学史比作某种其他的历史。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强烈地感到文学传统中的某些结构因素极为重要,例如常规文类以及反复使用的某些意象或意象群,也就是我最终称之为原型的东西。
”由此,弗莱正式在文学批评领域提出了“原型”这一概念,将“原型”概念由心理术语转换成了文学理论术语。
弗莱《文学的原型》认为,原型是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是一些联想群”,是“具有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
在原型批评理论家看来,整个人类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几部不同类型作品的不断反复出现。
先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意象通过“集体无意识”渗透到一代代作家的血液中,再被这些作家“无意识”地通过一部部具体作品创作出来,并再次影响到其后的作家。
在不同作家创作出的这些不同作品中,虽然其中带有每个作家自身的特色,但其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意象却总能在先代作品中找到原型。
本文中,笔者将从张爱玲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月亮意象着手,去分析传统文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小说中对月亮意象进行了着力的描绘,它们有着很丰富的原型意义,她对月亮的感官色彩的印象捕捉,充分显示出她的艺术思维的独到与精细。
她笔下的月亮,无不感应着人物的特定情绪、瞬间感受和印象,从而有机地嵌入到了人物的心理过程和感情生活中,成为很重要的原型。
原型批评理论代表人物弗莱认为,某些自然界的普遍意象的重复出现不能仅仅视为一种技术上的“巧合”,而是应当将其看做是某种“原型”的反复出现。
张爱玲小说中就反复出现月亮意象,就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型。
(二)从先秦传说到现代小说,月亮频繁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月亮这一原型同时具有3种意义。
第一种,月亮与美好人性、高洁品质相关照,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举杯邀明月”、“莫使金樽空对月”,刘禹锡的“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等月亮原型表达的依然是亘古不变的内涵——对宇宙时空的敬畏,对永恒的精神家园的追求,月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指人生团圆美满或光明磊落的心性,月亮给人以心志忠贞、品格高尚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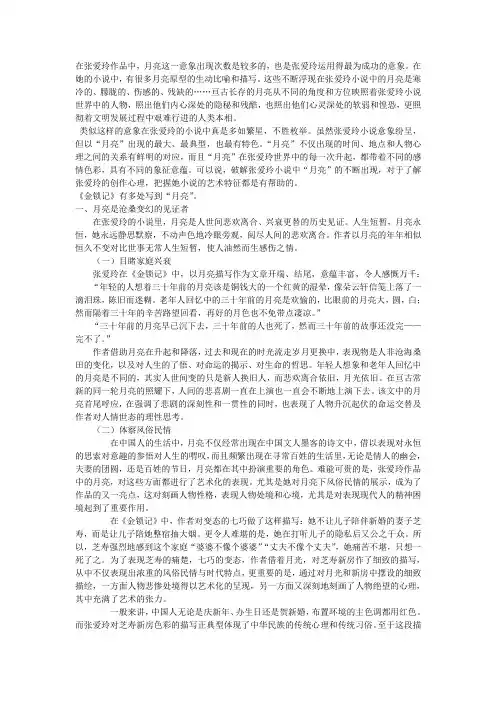
在张爱玲作品中,月亮这一意象出现次数是较多的,也是张爱玲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意象。
在她的小说中,有很多月亮原型的生动比喻和描写。
这些不断浮现在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是寒冷的、朦胧的、伤感的、残缺的……亘古长存的月亮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映照着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人物,照出他们内心深处的隐秘和残酷,也照出他们心灵深处的软弱和惶恐,更照彻着文明发展过程中艰难行进的人类本相。
类似这样的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真是多如繁星,不胜枚举。
虽然张爱玲小说意象纷呈,但以“月亮”出现的最大、最典型,也最有特色。
“月亮”不仅出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心理之间的关系有鲜明的对应,而且“月亮”在张爱玲世界中的每一次升起,都带着不同的感情色彩,具有不同的象征意蕴。
可以说,破解张爱玲小说中“月亮”的不断出现,对于了解张爱玲的创作心理,把握她小说的艺术特征都是有帮助的。
《金锁记》有多处写到“月亮”。
一、月亮是沧桑变幻的见证者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月亮是人世间悲欢离合、兴衰更替的历史见证。
人生短暂,月亮永恒,她永远静思默察,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阅尽人间的悲欢离合。
作者以月亮的年年相似恒久不变对比世事无常人生短暂,使人油然而生感伤之情。
(一)目睹家庭兴衰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以月亮描写作为文章开端、结尾,意蕴丰富,令人感慨万千:“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作者借助月亮在升起和降落,过去和现在的时光流走岁月更换中,表现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变化,以及对人生的了悟、对命运的揭示、对生命的哲思。
年轻人想象和老年人回忆中的月亮是不同的,其实人世间变的只是新人换旧人,而悲欢离合依旧,月光依旧。
在亘古常新的同一轮月亮的照耀下,人间的悲喜剧一直在上演也一直会不断地上演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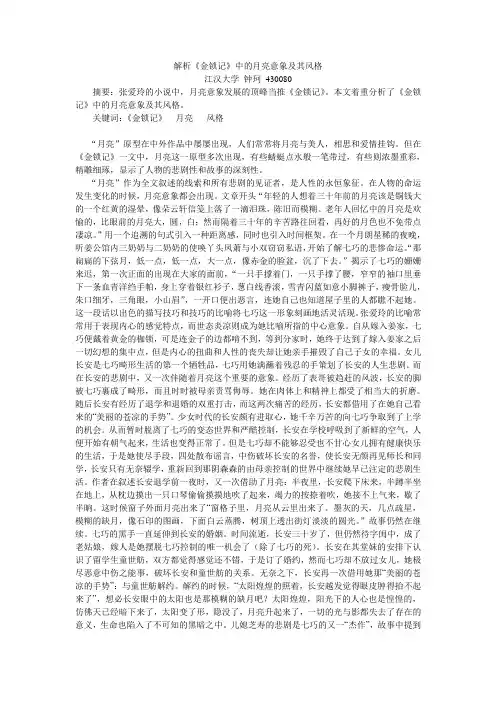
解析《金锁记》中的月亮意象及其风格江汉大学钟珂430080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中,月亮意象发展的顶峰当推《金锁记》。
本文着重分析了《金锁记》中的月亮意象及其风格。
关键词:《金锁记》月亮风格“月亮”原型在中外作品中屡屡出现,人们常常将月亮与美人,相思和爱情挂钩。
但在《金锁记》一文中,月亮这一原型多次出现,有些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有些则浓墨重彩,精雕细琢,显示了人物的悲剧性和故事的深刻性。
“月亮”作为全文叙述的线索和所有悲剧的见证者,是人性的永恒象征。
在人物的命运发生变化的时候,月亮意象都会出现。
文章开头“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用一个追溯的句式引入一种距离感,同时也引入时间框架。
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听姜公馆内三奶奶与二奶奶的使唤丫头凤萧与小双窃窃私语,开始了解七巧的悲惨命运。
“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
”揭示了七巧的姗姗来迟,第一次正面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血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一开口便出恶言,连她自己也知道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
这一段话以出色的描写技巧和技巧的比喻将七巧这一形象刻画地活灵活现。
张爱玲的比喻常常用于表现内心的感觉特点,而世态炎凉则成为她比喻所指的中心意象。
自从嫁入姜家,七巧便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等到分家时,她终于达到了嫁入姜家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但是内心的扭曲和人性的丧失却让她亲手摧毁了自己子女的幸福。
女儿长安是七巧畸形生活的第一个牺牲品,七巧用她满蘸着残忍的手策划了长安的人生悲剧。
而在长安的悲剧中,又一次伴随着月亮这个重要的意象。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月亮的象征意义作者:吕伟璇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07期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以意象丰富著称,其中,月亮意象是用得最多的一个,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月亮意象进行了描绘,本文就从张爱玲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月亮意象着手,尝试分析其典型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月亮象征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很多地方都用到了月亮这个意象,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月亮意象进行了描绘,有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残缺的等等,每次月亮的出现,都具有不同的、独特的象征意义。
一、女性意识的体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与她小说中的月亮意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把女人和月亮联系起来,当然不是张爱玲的首创,在古代神话传说里,太阳就是男性,而月亮就是女性。
像中国最早的月亮神就是女神常羲:美丽、温柔,而太阳是留给男人们自居、自诩的伟岸、雄壮。
月亮自有月亮的便宜之处:无须费力发光,但仗他者生存。
久而久之,女人便在月晕中安身立命了。
到民国时期的张爱玲,接过了女人是月亮的传统象征,但她显然不满足于传统。
她从小就不能接受重男轻女的观念,要锐意图强,然而她又不得不承受传统因袭的女人难以摆脱的悲剧性命运。
于是,她对女性本体进行反思,而且还巧妙地利用“月亮”这一由来已久的象征进行阐述。
她以个人的独特感悟为先导,不再继续称颂女人作为月亮多么美丽和充实,而是揭示女人作为折光、陪衬、从属物的月亮是多么苍白和空虚,意在给女性一个警示。
在《霸王别姬》里,张爱玲就从虞姬的慷慨赴死中发掘出女性的觉悟:“如果他(项王)是那炽热的、充满了烨烨的光彩、喷出耀眼欲花的ambition的火焰的太阳,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
”[1]当项王在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
这里,虞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对自己不独立“活着”,并因为他(项王)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目标进行反思和否定,她对女性的月亮地位做出了彻底反省:即使像她这样的西楚霸王的宠姬,也不过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败则惟恐落入敌手,夫主恨不能亲手血刃,胜则得一封号,同时也封死了青春与前程,既然如此,何不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读张爱玲小说《金锁记》里的月亮意象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意象不胜枚举,描写独特,意蕴深刻。
月亮也是进入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一个门槛,跨过这个门槛,在总体上就可以把握张爱玲小说基本的艺术特征。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月亮这一意象的发展顶峰当推《金锁记》。
在这篇小说,小说一切深刻的悲剧内涵都包蕴贯穿于月亮意象之中。
这种意象体现着张爱玲对月亮独特的审美心态,也是一个永恒的女人的神话。
月亮意象反复出现,成为贯穿人物心理的重要线索。
全篇多处写到月亮,或一笔带过,或浓墨重彩。
月亮总在人物命运的关键时刻出现,与人物一同分享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金锁记》的开头和结尾,都是以月亮作比,首尾互相照应。
开头从30年前的上海的月亮起:“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月亮”的意象把30年前与30年后打通,30年前的月亮,年青人未曾经历,只能想象,所以陈旧而迷糊;“相聚、离散,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故事的主体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写曹七巧的大家庭生活及她和小叔姜季泽之间的“爱情”;第二部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她因孤寂而疯狂,又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
她是一个为金钱所困而丧失了整个青春的年轻女子,她一生的失误即在于被金钱所困,以全部人生的幸福作为代价。
上半部的故事开始时,让读者在一个月亮明朗的夜晚,听姜公馆三奶奶与二奶奶的使唤丫头风箫与小双的月夜私语。
谈话的中心是一个与月亮有关的人,这人便是七巧。
七巧即七夕乞巧。
七夕是牛郎织女的佳期,也是旧时妇女的节日。
七巧,这个与月亮有关的人在故事的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出悲剧,她嫁到了富贵人家,可是处处因自己的出身受到歧视,她结婚5年了,有了一对弱小的儿女,可是从未享受过婚姻的幸福,她自以为是她爱上了丈夫的弟弟——姜季泽,可是平日走马章台的三少爷对她却严叔嫂之防。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积淀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的月亮是备受中国文人青睐的典型意象之一,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当经年不变的月光投洒到张爱玲身边的时候, 作为审美主体, 他自觉地对月亮这一审美客体做出能动反映, 达到情景相融, 从而使月亮成为张爱玲小说中别具韵味的意象。
一方面, 他在小说中借月抒情, 赋予了月亮多种文化象征意义。
而张爱玲小说中弥漫着苍凉的生命色彩;,她在写法上以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和女性视角, 给予月亮以新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加工, 使小说中月亮意象超越传统, 散发出令人回味的现代气息。
月亮是中国文人心中永远割舍不掉的爱, 并吸引着他们的审美目光, 不断地品月、弄月、吟月、伤月..。
古人今人如逝水一样, 而明月却亘古如斯。
于是, 月亮便引起人们对人生哲理的探求。
因而, 月亮就产生了象征爱、女性、团圆与美好、朦胧、落寞失意与凄凉孤独、等意义。
钟情于古典文学张爱玲, 都自觉地禀承了古人的审美文化取向。
对于出生于没落的贵族之家张爱玲, 旧式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和经历也势必对他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贵族家庭给予了他们贵族血脉, 但家族的衰败与灭亡, 也同样给予了她们与生俱来的悲剧命运。
个人遭际的不幸与悲哀, 命运的坎坷与多舛,反映到对月的抒写上,就借月为小说着上了悲凄与苍凉的生命底色。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的年轻人总会“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3], 表现出她挖掘生命意识时惊人的洞察力。
《倾城之恋》中, 月亮反复总关情。
月亮首次出现, 正是范柳原向白流苏发起爱情攻势之时; 当月亮在白流苏的“泪眼中”变得“大而模糊”时, 月亮就象征了他二人滋长着的模糊的爱情; 然而“柳原既能抗拒浅水湾的月色, 就能抗拒甲板上的月色”, 可见二人“防范多于相爱”; 范、白二人已婚后, 只有一弯“纤月”, 象征了二人并没有得到真正完整的爱情。
月亮在白流苏的眼里不断变化, 这不恰恰是她“模糊”变化的人生的写照吗? 在小说《牛》中, 禄兴的渺小的脆弱的生命无情陨灭后, “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 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就令人深感萧瑟与悲惨。
解读张爱玲《金锁记》月亮意象-2019年文档解读张爱玲《金锁记》月亮意象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
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以表示。
这是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对张爱玲小说里频频出现的月亮意象的关注,就像一首诗有个“诗眼”一样,那么一篇小说也应该有个“文眼”。
无疑“月亮”就是张爱玲《金锁记》的“文眼”。
透过这轮永恒而凄清的月亮笼罩的诗意文本,时隔六十多年,我们又能从中发现些什么呢?月亮意象之一:象征主题意蕴这轮中国的“月亮”究竟有哪些中国特色?在中国文化里,月亮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星体,它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信息,凝聚着我们古老民族深厚的生命感情和审美理想。
首先,中国文化里月亮最基本的象征意义是母亲与女性。
《礼记》中说:“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
大明即太阳,代表男性,意味着阳刚、强壮和力量;月亮代表女性,意味着温柔、阴柔、温馨、婉约和缠绵。
月亮是贞洁、洁净、爱与美的象征。
其次,在我国古人的观念中,月是水的结晶,水是月的灵魂,是贞洁纯净的象征,是美的化身。
月亮在中国审美的深层结构中,始终流露着神秘的永恒的女性微笑。
因此古典诗词里,常常以美人似月,佳人月下作为基本抒情意象。
再次,月亮是永恒的象征。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月亮时晦时明,时圆时缺,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启示着人们对宇宙永恒的思考和人生短暂的喟叹。
月亮有如此多的含义,那么在《金锁记》中它主要有哪些意义呢?从月亮的视角看,曹七巧具有忧郁的气质和反生命色彩的悲剧美,这也是小说主题蕴涵所在。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总共七次描写了月亮,尤其是首尾均以“三十年前的月亮”遥相呼应,那么由此可见作者以月亮来作为小说主题象征的用意是非常显豁的。
为什么“月亮”有着如此大的魅力呢?是因为曹七巧她只是二少爷的姨奶奶,地位比丫鬟高,命运比小姐差,一直被姜家大小都瞧不起,而她又是姜家最要强的女人,她的个性真正得以表现是在婆婆过世后,九老太爷出面分割姜家财产的会上,她义愤填膺地要求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家产,“维持了几天的僵局,到底还是无声无臭照原计划分了家。
日月交织下的情爱世界——张爱玲小说中的日月意象分析
陈蕾;蒲娟
【期刊名称】《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8(002)001
【摘要】被抹上了“荒凉”的底色、背后时刻感受着“惘惘的威胁”、用女性特
有的细腻感触到的那样一种日月的意象,构成了张爱玲情爱小说的“传奇”,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这不仅源于张爱玲一生中不幸的情感,也是她独特的女性视觉对情感的悲凉体验。
其后有许多作家受此影响,日、月的情爱“传奇”不断上演。
【总页数】5页(P63-67)
【作者】陈蕾;蒲娟
【作者单位】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内江641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相关文献】
1.民间传说中“日月食”考趣 [J], 钟海柱
2."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简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情爱世界 [J], 余培敏;杨永
军
3."走,到日月山川里去"--也说张爱玲的世俗与虚无 [J], 唐宇东
4.理想情爱视野下男性形象的塑造——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解读 [J], 刘乳连
5.张爱玲《小团圆》的情爱世界 [J], 叶澜涛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