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
- 格式:doc
- 大小:54.00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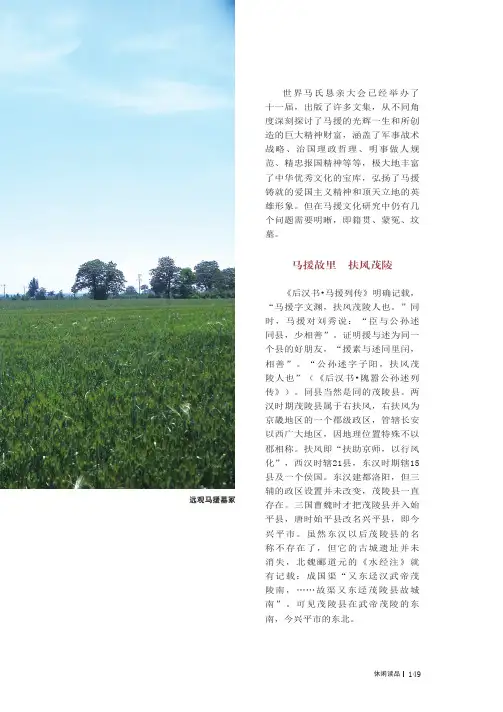
149远观马援墓冢世界马氏恳亲大会已经举办了十一届,出版了许多文集,从不同角度深刻探讨了马援的光辉一生和所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涵盖了军事战术战略、治国理政哲理、明事做人规范、精忠报国精神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宝库,弘扬了马援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
但在马援文化研究中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明晰,即籍贯、蒙冤、坟墓。
马援故里 扶风茂陵《后汉书•马援列传》明确记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
”同时,马援对刘秀说:“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
证明援与述为同一个县的好朋友,“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
同县当然是同的茂陵县。
两汉时期茂陵县属于右扶风,右扶风为京畿地区的一个郡级政区,管辖长安以西广大地区,因地理位置特殊不以郡相称。
扶风即“扶助京师,以行风化”,西汉时辖21县,东汉时期辖15县及一个侯国。
东汉建都洛阳,但三辅的政区设置并未改变,茂陵县一直存在。
三国曹魏时才把茂陵县并入始平县,唐时始平县改名兴平县,即今兴平市。
虽然东汉以后茂陵县的名称不存在了,但它的古城遗址并未消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记载:成国渠“又东迳汉武帝茂陵南,……故渠又东迳茂陵县故城南”。
可见茂陵县在武帝茂陵的东南,今兴平市的东北。
150另外,明确记载茂陵县的主要历史文献有《汉书•武帝纪》《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后汉书•马援列传、隗嚣公孙述列传》《水经注•渭水注》《太平寰宇记》《陕西省志•地理志》《陕西地名沿革》《陕西精神》《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有关《一统志》《通志》《府县志》等等,都认定两汉茂陵县位于今兴平市东北。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不同意见,这就很值得深思和研究了。
看来只有挖根刨底,才能让那些所谓的定论不攻自破。
其一为家谱论。
现存于世的马氏家谱,在北方地区以山西柳林县明代撰修的《马氏家谱》为最早。
我所见到的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扶风县政府派人从柳林抄回的该家谱,石州马氏宗谱序说:“余始祖名援字文渊,东汉光武时伏波大将军,新息侯,谥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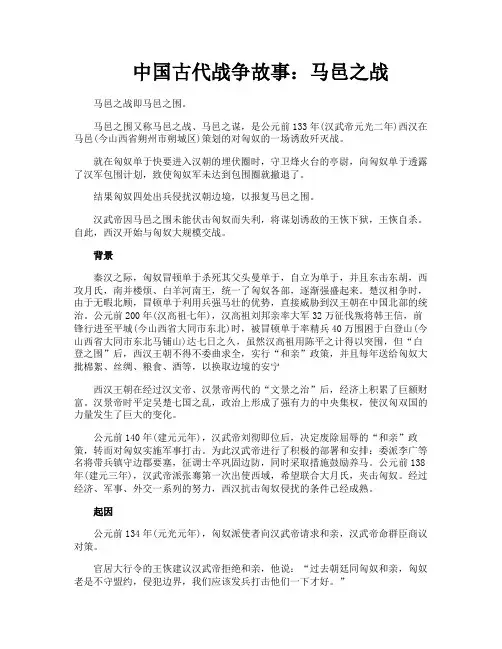
中国古代战争故事:马邑之战马邑之战即马邑之围。
马邑之围又称马邑之战、马邑之谋,是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元光二年)西汉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策划的对匈奴的一场诱敌歼灭战。
就在匈奴单于快要进入汉朝的埋伏圈时,守卫烽火台的亭尉,向匈奴单于透露了汉军包围计划,致使匈奴军未达到包围圈就撤退了。
结果匈奴四处出兵侵扰汉朝边境,以报复马邑之围。
汉武帝因马邑之围未能伏击匈奴而失利,将谋划诱敌的王恢下狱,王恢自杀。
自此,西汉开始与匈奴大规模交战。
背景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杀死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并且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统一了匈奴各部,逐渐强盛起来。
楚汉相争时,由于无暇北顾,冒顿单于利用兵强马壮的优势,直接威胁到汉王朝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32万征伐叛将韩王信,前锋行进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时,被冒顿单于率精兵40万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达七日之久,虽然汉高祖用陈平之计得以突围,但“白登之围”后,西汉王朝不得不委曲求全,实行“和亲”政策,并且每年送给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以换取边境的安宁西汉王朝在经过汉文帝、汉景帝两代的“文景之治”后,经济上积累了巨额财富。
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政治上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使汉匈双国的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决定废除屈辱的“和亲”政策,转而对匈奴实施军事打击。
为此汉武帝进行了积极的部署和安排:委派李广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征调士卒巩固边防,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养马。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希望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经过经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西汉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成熟。
起因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匈奴派使者向汉武帝请求和亲,汉武帝命群臣商议对策。
官居大行令的王恢建议汉武帝拒绝和亲,他说:“过去朝廷同匈奴和亲,匈奴老是不守盟约,侵犯边界,我们应该发兵打击他们一下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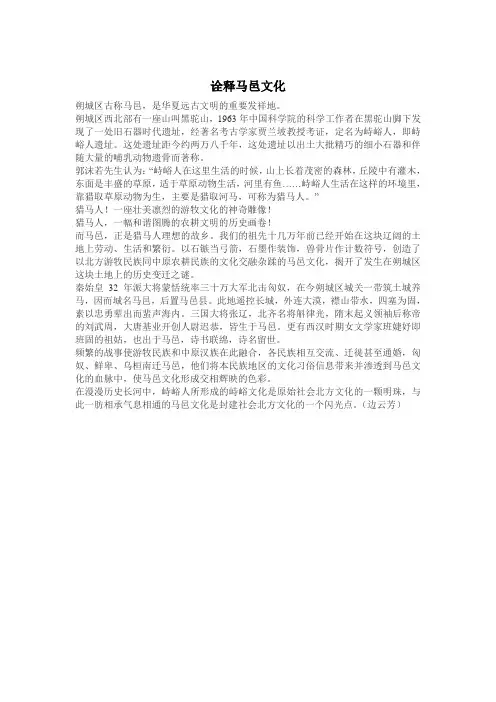
诠释马邑文化朔城区古称马邑,是华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朔城区西北部有一座山叫黑驼山,1963年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在黑驼山脚下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考证,定名为峙峪人,即峙峪人遗址。
这处遗址距今约两万八千年,这处遗址以出土大批精巧的细小石器和伴随大量的哺乳动物遗骨而著称。
郭沫若先生认为:“峙峪人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丘陵中有灌木,东面是丰盛的草原,适于草原动物生活,河里有鱼……峙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靠猎取草原动物为生,主要是猎取河马,可称为猎马人。
”猎马人!一座壮美凛烈的游牧文化的神奇雕像!猎马人,一幅和谐图腾的农耕文明的历史画卷!而马邑,正是猎马人理想的故乡。
我们的祖先十几万年前已经开始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劳动、生活和繁衍。
以石镞当弓箭,石墨作装饰,兽骨片作计数符号,创造了以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的文化交融杂蹂的马邑文化,揭开了发生在朔城区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变迁之谜。
秦始皇32年派大将蒙恬统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在今朔城区城关一带筑土城养马,因而城名马邑,后置马邑县。
此地遥控长城,外连大漠,襟山带水,四塞为固,素以忠勇辈出而蜚声海内。
三国大将张辽,北齐名将斛律光,隋末起义领袖后称帝的刘武周,大唐基业开创人尉迟恭,皆生于马邑。
更有西汉时期女文学家班婕妤即班固的祖姑,也出于马邑,诗书联绵,诗名留世。
频繁的战事使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在此融合,各民族相互交流、迁徙甚至通婚,匈奴、鲜卑、乌桓南迁马邑,他们将本民族地区的文化习俗信息带来并渗透到马邑文化的血脉中,使马邑文化形成交相辉映的色彩。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峙峪人所形成的峙峪文化是原始社会北方文化的一颗明珠,与此一肪相承气息相通的马邑文化是封建社会北方文化的一个闪光点。
(边云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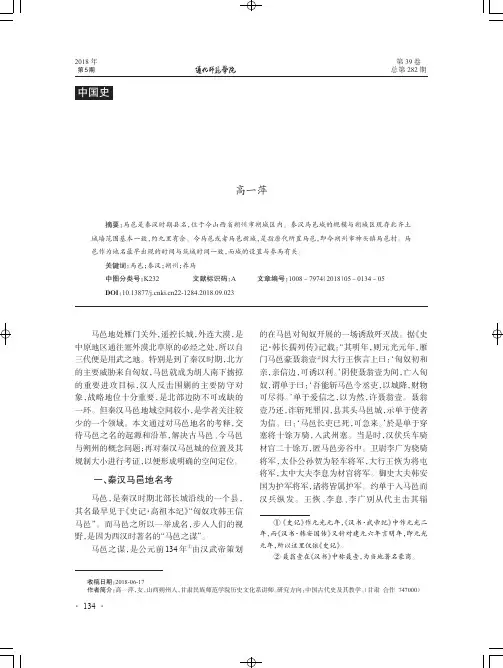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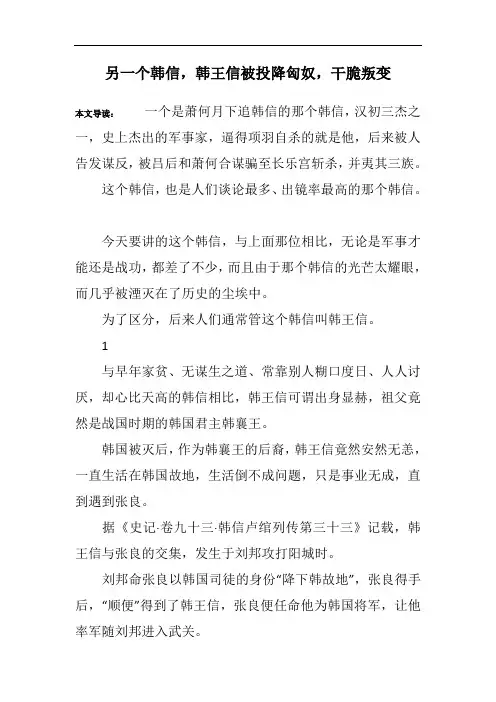
另一个韩信,韩王信被投降匈奴,干脆叛变本文导读:一个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那个韩信,汉初三杰之一,史上杰出的军事家,逼得项羽自杀的就是他,后来被人告发谋反,被吕后和萧何合谋骗至长乐宫斩杀,并夷其三族。
这个韩信,也是人们谈论最多、出镜率最高的那个韩信。
今天要讲的这个韩信,与上面那位相比,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战功,都差了不少,而且由于那个韩信的光芒太耀眼,而几乎被湮灭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为了区分,后来人们通常管这个韩信叫韩王信。
1与早年家贫、无谋生之道、常靠别人糊口度日、人人讨厌,却心比天高的韩信相比,韩王信可谓出身显赫,祖父竟然是战国时期的韩国君主韩襄王。
韩国被灭后,作为韩襄王的后裔,韩王信竟然安然无恙,一直生活在韩国故地,生活倒不成问题,只是事业无成,直到遇到张良。
据《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记载,韩王信与张良的交集,发生于刘邦攻打阳城时。
刘邦命张良以韩国司徒的身份“降下韩故地”,张良得手后,“顺便”得到了韩王信,张良便任命他为韩国将军,让他率军随刘邦进入武关。
公元前206年鸿门宴之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带着韩王信进入关中。
为了报答刘邦的知遇之恩,一到关中,韩王信就给刘邦出主意说:“项羽这人厚此薄彼,把中原附近的好地方,都封给了自己的部下,却把您打发到这个偏远之地,这简直是对您的侮辱!你的士兵家乡都在崤山以东,他们被迫来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内心是抗拒的,都急切地想回到家乡,大王您若利用这一点带领他们向东进军,别说当王,把天下夺到手都不成问题。
”刘邦回军平定三秦后,许韩王信做韩王,先拜他为韩太尉,让他率军攻取韩国故地。
2从这个安排来看,刘邦采纳了韩王信的建议,让他先去攻取韩国故地,是让他为他打前站,替他扫清东进道路上的障碍。
那时的韩国故地老大是韩王成,也是项羽封的,但因韩王成无战功,项羽就没让他到自己的封地去,还把他改封为列侯。
刘邦派韩王信来打的消息传来,韩王成有点着急,因自己不能去封地,只好让吴县县令郑昌做韩王,命他率军抵抗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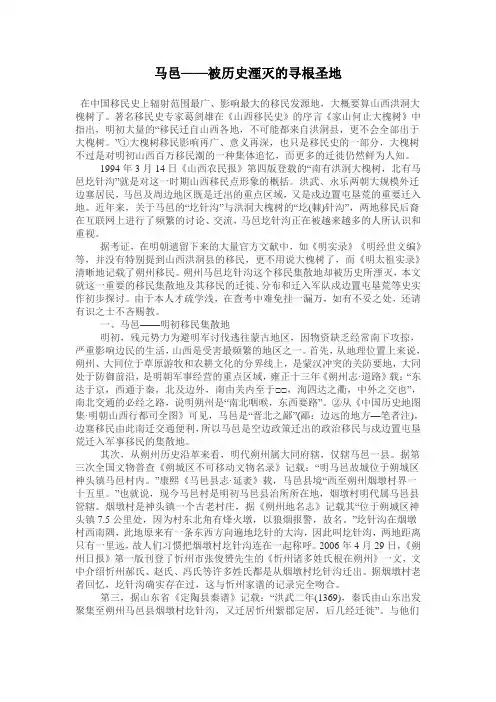
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著名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①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1994年3月14日《山西农民报》第四版登载的“南有洪洞大槐树,北有马邑圪针沟”就是对这一时期山西移民点形象的概括。
洪武、永乐两朝大规模外迁边塞居民,马邑及周边地区既是迁出的重点区域,又是戍边置屯垦荒的重要迁入地。
近年来,关于马邑的“圪针沟”与洪洞大槐树的“圪(棘)针沟”,两地移民后裔在互联网上进行了频繁的讨论、交流,马邑圪针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
据考证,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清晰地记载了朔州移民。
朔州马邑圪针沟这个移民集散地却被历史所湮灭,本文就这一重要的移民集散地及其移民的迁徙、分布和迁入军队戍边置屯垦荒等史实作初步探讨。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在查考中难免挂一漏万,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马邑——明初移民集散地明初,残元势力为避明军讨伐逃往蒙古地区,因物资缺乏经常南下攻掠,严重影响边民的生活,山西是受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朔州、大同位于草原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上,是蒙汉冲突的关防要地,大同处于防御前沿,是明朝军事经营的重点区域,雍正十三年《朔州志·道路》载:“东达于京,西通于秦,北及边外,南由关内至于□□,洵四达之衢,中外之交也”,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说明朔州是“南北咽喉,东西要路”。
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朝山西行都司全图》可见,马邑是“晋北之鄙”(鄙:边远的地方—笔者注),边塞移民由此南迁交通便利,所以马邑是空边政策迁出的政治移民与戍边置屯垦荒迁入军事移民的集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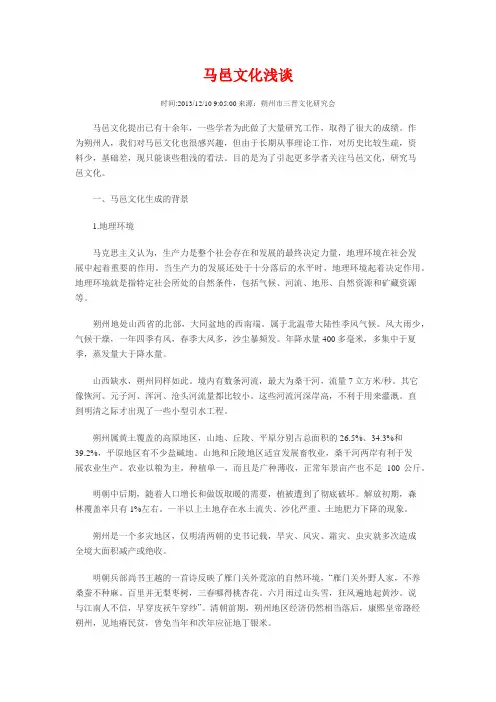
马邑文化浅谈时间:2013/12/10 9:05:00来源: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马邑文化提出已有十余年,一些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作为朔州人,我们对马邑文化也很感兴趣,但由于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对历史比较生疏,资料少,基础差,现只能谈些粗浅的看法。
目的是为了引起更多学者关注马邑文化,研究马邑文化。
一、马邑文化生成的背景1.地理环境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时,地理环境起着决定作用。
地理环境就是指特定社会所处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河流、地形、自然资源和矿藏资源等。
朔州地处山西省的北部,大同盆地的西南端。
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风大雨少,气候干燥,一年四季有风,春季大风多,沙尘暴频发。
年降水量400多毫米,多集中于夏季,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山西缺水,朔州同样如此。
境内有数条河流,最大为桑干河,流量7立方米/秒。
其它像恢河、元子河、浑河、沧头河流量都比较小。
这些河流河深岸高,不利于用来灌溉。
直到明清之际才出现了一些小型引水工程。
朔州属黄土覆盖的高原地区,山地、丘陵、平原分别占总面积的26.5%、34.3%和39.2%,平原地区有不少盐碱地。
山地和丘陵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桑干河两岸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以粮为主,种植单一,而且是广种薄收,正常年景亩产也不足100公斤。
明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做饭取暖的需要,植被遭到了彻底破坏。
解放初期,森林覆盖率只有1%左右。
一半以上土地存在水土流失、沙化严重、土地肥力下降的现象。
朔州是一个多灾地区,仅明清两朝的史书记载,旱灾、风灾、霜灾、虫灾就多次造成全境大面积减产或绝收。
明朝兵部尚书王越的一首诗反映了雁门关外荒凉的自然环境,“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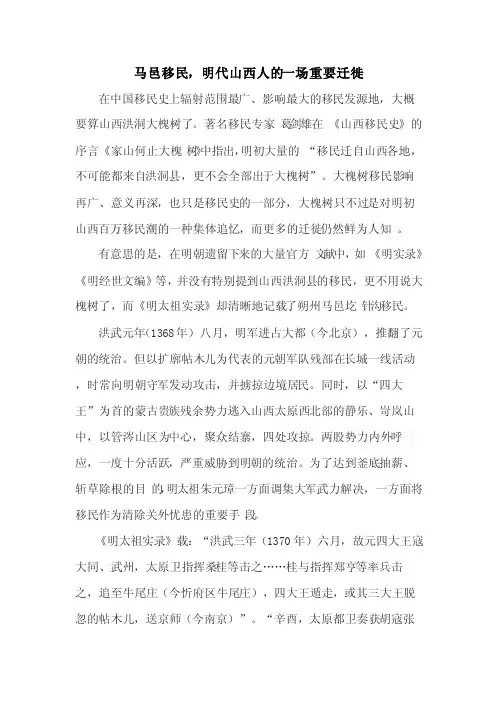
马邑移民,明代山西人的一场重要迁徙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著名移民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只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有意思的是,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却清晰地记载了朔州马邑圪针沟移民。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进占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但以扩廓帖木儿为代表的元朝军队残部在长城一线活动,时常向明朝守军发动攻击,并掳掠边境居民。
同时,以“四大王”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逃入山西太原西北部的静乐、岢岚山中,以管涔山区为中心,聚众结寨,四处攻掠。
两股势力内外呼应,一度十分活跃,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统治。
为了达到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目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调集大军武力解决,一方面将移民作为清除关外忧患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故元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卫指挥桑桂等击之……桂与指挥郑亨等率兵击之,追至牛尾庄(今忻府区牛尾庄),四大王遁走,或其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送京师(今南京)”。
“辛酉,太原都卫奏获胡寇张成等十六人,上命询胡人潜伏之所,欲用兵剿绝,勿容再聚其寨,外夷人皆令迁入内地”。
按照“外夷人皆迁入内地”的政策,朱元璋把归降和被俘虏的蒙古人,全部迁入到京师(今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等地,后来又对蒙古人进行集中安顿,除“隶军籍”外,一般“占籍为民”,即等同于汉民,就地安顿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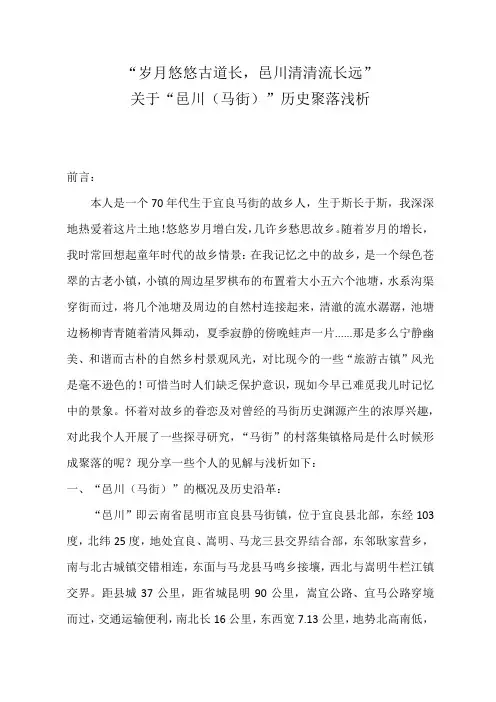
“岁月悠悠古道长,邑川清清流长远”关于“邑川(马街)”历史聚落浅析前言:本人是一个70年代生于宜良马街的故乡人,生于斯长于斯,我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悠悠岁月增白发,几许乡愁思故乡。
随着岁月的增长,我时常回想起童年时代的故乡情景:在我记忆之中的故乡,是一个绿色苍翠的古老小镇,小镇的周边星罗棋布的布置着大小五六个池塘,水系沟渠穿街而过,将几个池塘及周边的自然村连接起来,清澈的流水潺潺,池塘边杨柳青青随着清风舞动,夏季寂静的傍晚蛙声一片......那是多么宁静幽美、和谐而古朴的自然乡村景观风光,对比现今的一些“旅游古镇”风光是毫不逊色的!可惜当时人们缺乏保护意识,现如今早已难觅我儿时记忆中的景象。
怀着对故乡的眷恋及对曾经的马街历史渊源产生的浓厚兴趣,对此我个人开展了一些探寻研究,“马街”的村落集镇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聚落的呢?现分享一些个人的见解与浅析如下:一、“邑川(马街)”的概况及历史沿革:“邑川”即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马街镇,位于宜良县北部,东经103度,北纬25度,地处宜良、嵩明、马龙三县交界结合部,东邻耿家营乡,南与北古城镇交错相连,东面与马龙县马鸣乡接壤,西北与嵩明牛栏江镇交界。
距县城37公里,距省城昆明90公里,嵩宜公路、宜马公路穿境而过,交通运输便利,南北长16公里,东西宽7.13公里,地势北高南低,中部开阔,东西山峦起伏。
海拔2226米,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冬夏无寒暑,春秋气候长,早午温差大,一雨变成冬”的特点。
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雨量充足,年降雨量为1000—1200毫米,集中在5—10月份,全年日照时数为2121—2154小时,全年无霜期246天。
全镇总面积114.8平方公里,辖马街、前卫、西边、马家冲四个社区居委会和兴隆、平田、洋喜、华家营四个村民委员会。
宜良县马街历史悠久,在曾经悠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马街”被称为“邑市、邑川、邑和”,据《县志》及相关文献记载:西汉时,属益州郡昆泽县,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邑市县(驻所堡子);明弘治三年(1490年)撤邑市县...民国十三年(1924年)设邑川分县(二等县)属宜良县;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撤邑川分县,设邑和乡;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为北东区;民国三十年(1941年)为邑川乡;1949年8月,建立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邑和乡人民政府...人民公社...之后改为“马街区”,1987年正式建乡,2009年12月撤乡设立马街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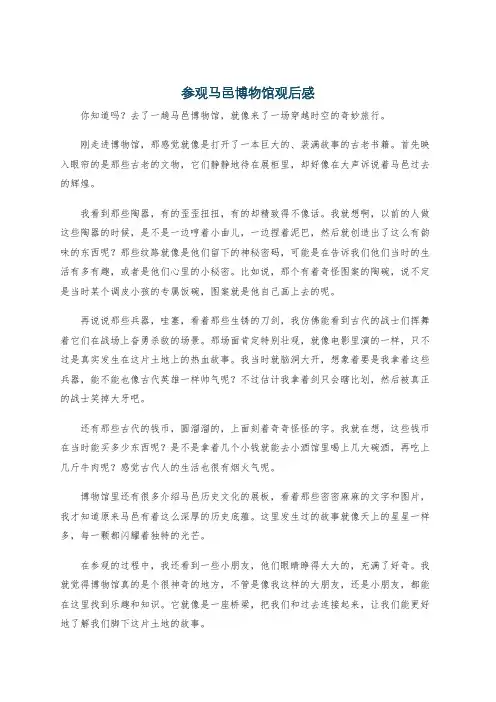
参观马邑博物馆观后感你知道吗?去了一趟马邑博物馆,就像来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刚走进博物馆,那感觉就像是打开了一本巨大的、装满故事的古老书籍。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古老的文物,它们静静地待在展柜里,却好像在大声诉说着马邑过去的辉煌。
我看到那些陶器,有的歪歪扭扭,有的却精致得不像话。
我就想啊,以前的人做这些陶器的时候,是不是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捏着泥巴,然后就创造出了这么有韵味的东西呢?那些纹路就像是他们留下的神秘密码,可能是在告诉我们他们当时的生活有多有趣,或者是他们心里的小秘密。
比如说,那个有着奇怪图案的陶碗,说不定是当时某个调皮小孩的专属饭碗,图案就是他自己画上去的呢。
再说说那些兵器,哇塞,看着那些生锈的刀剑,我仿佛能看到古代的战士们挥舞着它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场景。
那场面肯定特别壮观,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只不过是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热血故事。
我当时就脑洞大开,想象着要是我拿着这些兵器,能不能也像古代英雄一样帅气呢?不过估计我拿着剑只会瞎比划,然后被真正的战士笑掉大牙吧。
还有那些古代的钱币,圆溜溜的,上面刻着奇奇怪怪的字。
我就在想,这些钱币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是不是拿着几个小钱就能去小酒馆里喝上几大碗酒,再吃上几斤牛肉呢?感觉古代人的生活也很有烟火气呢。
博物馆里还有很多介绍马邑历史文化的展板,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片,我才知道原来马邑有着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
这里发生过的故事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每一颗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还看到一些小朋友,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好奇。
我就觉得博物馆真的是个很神奇的地方,不管是像我这样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和知识。
它就像是一座桥梁,把我们和过去连接起来,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故事。
总之呢,这次参观马邑博物馆真的是一次超级有趣的经历。
我就像一个寻宝者,在博物馆里发现了无数的宝藏,这些宝藏不是金银珠宝,而是马邑的历史、文化和那些被遗忘的美好回忆。
参观马邑博物馆观后感前几天去了马邑博物馆,那可真是一场超级有趣又长见识的经历呢。
刚走到博物馆门口,就感觉一股浓浓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那建筑风格,有点古朴又透着威严,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一进馆,就像是跳进了一个时光机,直接被拉回到了过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琳琅满目的文物,哇塞,真的是开了眼了。
那些陶器啊,虽然看起来灰扑扑的,但你仔细瞅,上面的纹路那可都是古人的巧思呢。
有的纹路像波浪,感觉是在描绘当时的河流或者大海;有的纹路像神秘的符号,说不定是古人之间传递信息的密码呢,就好像是他们在跟我们玩一场跨越千年的猜谜游戏。
还有那些青铜器,一看到就觉得震撼。
锈迹斑斑的外表下,藏着的是当年的辉煌。
摸着那些铜器,我就在想,这东西在古代得是多金贵啊,估计就像现在的限量版豪车一样拉风。
而且它们的造型也是千奇百怪,有个像小动物的青铜器,那小眼睛,小耳朵,做得栩栩如生,感觉下一秒就要从展台上蹦跶起来了。
再说说那些古代的兵器,好家伙,看起来就很有杀伤力。
我拿着旁边的小讲解器听了听,才知道原来古代打仗用的武器有这么多讲究。
什么剑啊,刀啊,斧啊,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用途。
我就想象着古代的勇士们拿着这些兵器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样子,那场面肯定特别热血沸腾。
不过我也在想,要是让我拿着这些兵器去打仗,估计我还没举起武器就被敌人给吓跑了,毕竟这些家伙看起来就很重呢。
馆里还有关于马邑地区民俗文化的展示。
那些传统的服饰、手工艺品啥的,真是美轮美奂。
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刺绣,我就感叹古人可真是心灵手巧啊。
我这种连缝个扣子都能把线缠成一团乱麻的人,简直没法比。
那些民俗故事也特别有趣,讲的都是马邑老百姓以前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感觉就像走进了一本活着的历史书。
在博物馆里转着转着,我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探险家,在挖掘马邑这片土地上的宝藏。
每一个展品都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串起了马邑的历史长河。
而且通过这次参观,我对马邑这个地方有了更深的感情,就好像是认识了一位多年的老友,了解了他的过去,就更珍惜他现在的样子了。
马邑之变名词解释
马邑之变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在公元720年的一次战役,发生在唐朝时期。
下面是对马邑之变的名词解释:
1. 马邑:马邑,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境内,是唐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也是与突厥等北方民族进行边防战斗的重要位置。
2. 之变:之变指的是在马邑发生的一次重大变动或事件。
3. 背景:唐朝时期,中国北方经常遭到来自北方的突厥等少数民族的入侵。
马邑作为边境要地,经常成为抵御北方侵略的前线据点。
4. 参与方:马邑之变主要涉及到唐朝的军队与突厥的军队。
唐朝派遣了大将李晟率领军队前往马邑,突厥则由吐蕃支持,派遣尉迟惇领兵进攻。
5. 过程:马邑之变发生在720年。
唐朝军队在李晟的指挥下进行了坚决抵抗,最终成功击退了突厥军队,取得了胜利。
6. 影响:马邑之变的胜利使得唐朝在边境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势,稳固了北方的防线。
这次胜利也显示出唐朝的军事实力,提升了朝廷的声望。
总之,马邑之变是唐朝时期发生的一次重要战役,它对中国北方边境的稳定产生了积极而持久的影响。
探寻独特的母系社会——阿美族
金磊
【期刊名称】《社会观察》
【年(卷),期】2008(000)009
【摘要】母系社会对于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们来说是那么的神秘,她们到底是
怎样的一种存在方式呢?本期旅游我们走进台湾,来探寻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群落。
【总页数】2页(P78-79)
【作者】金磊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29
【相关文献】
1.探寻人类母系社会的最后一块领地 [J], 王芃懿;段小玲
2.独特的"江淮重镇"——合肥城市特质历史探寻 [J], 徐亚哲
3.探寻“独特体验”的价值——让“独特体验”走向“自主建构” [J], 张雷
4.以独特的视角探寻明清小说名著的艺术魅力——评《明清小说名著导读》 [J],
程国赋
5.母系社会残余的又一例证!——台湾省阿美族简介 [J], 蔡家骐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四海一家地名中的民族历史印记
郭晔旻
【期刊名称】《国家人文历史》
【年(卷),期】2022()11
【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在960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大地上,也有不少兄弟民族创造的地名。
与汉民族创造的地名一样,这些非汉语来源的地名同样承载着丰厚的历史积淀,成为留存至今的宝贵文化财富。
【总页数】9页(P118-126)
【作者】郭晔旻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1.民族交融的印记——柳州地名历史层次寻踪
2.论历史地名在地名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北京市历史地名为例
3.徐州地名的历史印记
4.广西地名中的骆越印记——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三十三
5.贵阳地名中的工业印记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滑县妹村:一国都一座城一个村的变迁文郑国联辛丑岁末,我终于站在了韦城这个神秘的所在,一个写满历史符号,见证历史发展,演绎沧海桑田变迁的地方。
说起这次探寻韦城之旅,也算是“搂草打兔子”,有点捎带的意思。
12月26日,我受白马墙村两委之邀,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中华曹姓文化及白马城遗址研讨会”。
说来也巧,此行的前一天河南省文物局刚刚公布了第八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滑县的“瓠子堤遗址”、“白马城遗址”榜上有名。
再加上白马墙村刚刚被命名为“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白马寻根文化”基地,可谓“双喜临门”。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白马墙村又迎来了山东曹姓文化研究会的客人,这简直就是“锦上添花”。
研讨会上四十多个姓氏专家、文史爱好者共同探讨了曹姓的来源,追溯漕邑的历史,展望“白马古城遗址”的未来前景。
白马墙村的前身是白马城,白马城的前身是曹邑。
这里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同母弟曹叔振铎的封邑之地。
当年曹叔能在此处接受曹国封国仪式说明漕邑的历史更为久远。
曹姓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漕邑理所当然是曹姓发源地。
当天下午曹景官老师一行四人在《滑州文化》编辑胡晓涵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有旧滑县十二景之一之称的“龙井烟迷”的所在地——万古镇妹村探访。
妹村的前身是韦城镇,韦城县。
进一步溯源至上古商周时期此地为“豕韦国”。
舜帝时期,一个叫董父的人曾在“豕韦”这个地方为舜帝养龙,又称豢龙。
董父因为豢龙有功,被舜封为“豢龙氏”。
夏朝在经历了“太康失国”、“少康复国”后。
夏帝少康为感谢彭祖在复国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就将豕韦这块地方封赏给了彭祖的孙子——元哲。
夏朝传到孔甲这一代,孔甲又是一个特喜欢养龙的主。
陶唐氏的后裔刘累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给孔甲养龙的重任。
于是孔甲就赶走彭氏一族,让刘累做了豕韦国君。
谁知道刘累后来把龙给养死了,竟然还烹制熟了给孔甲吃。
刘累害怕孔甲降罪就逃走了。
这样豕韦国又回到彭姓一族手中。
商朝时期刘累的后代再一次将彭姓灭掉,入主豕韦国。
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著名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
”①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1994年3月14日《山西农民报》第四版登载的“南有洪洞大槐树,北有马邑圪针沟”就是对这一时期山西移民点形象的概括。
洪武、永乐两朝大规模外迁边塞居民,马邑及周边地区既是迁出的重点区域,又是戍边置屯垦荒的重要迁入地。
近年来,关于马邑的“圪针沟”与洪洞大槐树的“圪(棘)针沟”,两地移民后裔在互联网上进行了频繁的讨论、交流,马邑圪针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
据考证,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清晰地记载了朔州移民。
朔州马邑圪针沟这个移民集散地却被历史所湮灭,本文就这一重要的移民集散地及其移民的迁徙、分布和迁入军队戍边置屯垦荒等史实作初步探讨。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在查考中难免挂一漏万,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马邑——明初移民集散地明初,残元势力为避明军讨伐逃往蒙古地区,因物资缺乏经常南下攻掠,严重影响边民的生活,山西是受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朔州、大同位于草原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上,是蒙汉冲突的关防要地,大同处于防御前沿,是明朝军事经营的重点区域,雍正十三年《朔州志·道路》载:“东达于京,西通于秦,北及边外,南由关内至于□□,洵四达之衢,中外之交也”,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说明朔州是“南北咽喉,东西要路”。
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朝山西行都司全图》可见,马邑是“晋北之鄙”(鄙:边远的地方—笔者注),边塞移民由此南迁交通便利,所以马邑是空边政策迁出的政治移民与戍边置屯垦荒迁入军事移民的集散地。
其次,从朔州历史沿革来看,明代朔州属大同府辖,仅辖马邑一县。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朔城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记载:“明马邑故城位于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内。
”康熙《马邑县志·延袤》载,马邑县境“西至朔州烟墩村界一十五里。
”也就说,现今马邑村是明初马邑县治所所在地,烟墩村明代属马邑县管辖。
烟墩村是神头镇一个古老村庄,据《朔州地名志》记载其“位于朔城区神头镇7.5公里处,因为村东北角有烽火墩,以狼烟报警,故名。
”圪针沟在烟墩村西南隅,此地原来有一条东西方向遍地圪针的大沟,因此叫圪针沟,两地距离只有一里远,故人们习惯把烟墩村圪针沟连在一起称呼。
2006年4月29日,《朔州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忻州市张俊赟先生的《忻州诸多姓氏根在朔州》一文,文中介绍忻州郝氏、赵氏、冯氏等许多姓氏都是从烟墩村圪针沟迁出。
据烟墩村老者回忆,圪针沟确实存在过,这与忻州家谱的记录完全吻合。
第三,据山东省《定陶县秦谱》记载:“洪武二年(1369),秦氏由山东出发聚集至朔州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又迁居忻州紫郡定居,后几经迁徙”。
与他们同时迁徙的还有定居忻州紫郡的董姓。
此记载印证了马邑是明初移民集散地,移民到此集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空边政策迁出的政治移民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却未能继承元朝的全部政治遗产,直接统治区较元朝大大缩小。
北撤的蒙古人仍占据着大片的土地,他们拥有强大的武装,对明朝构成极大的威胁。
洪武元年(1368),明廷为了悉空草原以防蒙古人南下,实行“移塞外边民入内”的空边政策。
这些北方边境上俘获的将士和遗民大多经马邑迁往北平及周边地区,也有一些迁入京师(今南京市)等政地要地。
至二十一年(1388)内迁活动暂告停止。
这些移民广泛地分布于江苏省、安徽省、北京市、河北省、云南省、山西省、四川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地。
(一)江苏省南京市南京作为明朝首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内迁蒙古人最主要的聚居地,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廷将一批蒙古元故官迁入南京。
3三年(1371)三月,迁塞外元太尉沙不丁及其将士家属3000余人于京师卫所。
④五年(1373),有1840名蒙古降官士卒迁至南京。
⑤次年十一月,“送大同边民寡妇及遗弃人口六十一户至京师。
”⑥七年一月,迁朔州故元官民200人于京师卫所;⑦四月,迁塞外故元官属1323人于京师卫所;另有3230名故元官、军、民从塞外迁入。
⑧同年,朱元璋甚至下令:“其塞外夷民,皆令入内地”;“官属送京师,军民居之塞内”。
⑨从洪武元年(1368)开始,先后有1万余人经马邑迁往南京。
朱元璋很重视对这些人的安排,于十二年(1380)十二月下令对京师内部的蒙古人进行集中安顿,除“隶军籍”外,其余“占籍为民”,即等同于一般汉民,就地安顿下来。
(二)安徽省淮河两岸是元末农民战争的首义之区,人口损失非常严重,朱元璋的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更是凄惶之至。
明初,朱元璋曾建都临濠,虽不久即废,但他还是从全国各地向故乡移民。
洪武五年(1372),来降的鞑靼五千九百余人,“命居临濠”。
⑩次年八月,迁朔州民自故元士卒及家属于凤阳地区泗州;九月,“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澧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今安徽凤阳)”⑪,“凡八千二百二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
”⑫“这是明朝初年山西居民首次大规模向外迁徙”,⑬涉及的地区以大同为中心。
由此可见,马邑大规模的移民早于洪洞大槐树。
按《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正月“戊申,山西丰州、东胜州、太原兴县以今年旱灾诏免其田租”,可见,明初区划基本沿袭元末之制,大同府包括这些州县,这件史实在《内蒙古自治区史·大事记》中也有记载。
洪武七年(1372)七月,“广西护卫指挥佥事脱剌伯于朔州等处招集旧部。
故元卒1360余人,家属3460余口,俾之编伍。
”⑭这些故元士卒及家属按照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迁到凤阳的泗州、虹县屯田。
十月,又“迁朔州故元士卒及家属往泗州虹县”,共4820人。
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在淮河的宿州、灵璧等地。
洪武初年,马邑周边地区先后迁往安徽省的约有5万余人。
部分《山西刘氏家谱》也记载了这一史实。
《中国移民史》记载,“寿县寿州回族边、马、赵、朱、陶、哈六大姓氏,很可能是迁入凤阳府的39000人中的一支”。
⑮(三)北京市(原北平及周边地区)北平为元朝之故都,经元末群雄争斗几乎成为一座空城,退守塞北的蒙古人还时常想策马南下,明朝的北部边境存在巨大的压力,所以必须通过大量移民以实之,故从沙漠、山后及山西其他地区移民,开发北平地区。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山后,宋指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地区,即代北(今朔州地区)、大同等地。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编修的朔州《王氏家谱·祖茔碑志》载:“我王氏,山后人也,俗传为刘武(周)之民,然武乃唐之伪将,占据山后,似恐误传,考朔之南沿革,即今朔州是也。
”这段文字也证明,山后包括朔州附近地区。
洪武三年(1370)六月,移徙边民68664户于北平诸卫府州县。
⑯次年六月,“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卫府,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
”这批移民主要来自于今朔州市、大同市各县。
“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
”四年,令内蒙古、晋北一带“沙漠移民”3200余户到北平屯种。
十年(1377),山后降民530户,2100人迁入北平和永平两府。
⑰十四年(1381)七月,“故元将校火里火真等四十一人及遗民一百七十七户自沙漠来归……命居北平。
” ⑱据统计,洪武初年约60万人移入北平及附近州府。
据《顺天府志》记载,从塞外移入北平府的约为27万人,而迁往其他府的约为14万人。
这些移民包括以满族为主的蒙古、色目等各族百姓,主要分布在顺天、永平、保定三府,其后裔分布在北京门头沟、石景山、房山、大兴、宛平、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通州等地。
明正德五年(1515)顾东齿、顾赞襄所立的《顾氏祖先考刘公、崔氏之墓碑》记载:“原籍山西乌邑县,移居北平河间县”。
查山西并无乌邑县,繁体的“乌”和“马”区别很小,笔者考虑,会不会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辨认有误,顾氏的原籍应为马邑县。
(四)河北省金元之际,河北是北方民族厮杀的战场,蒙古骑兵所过,“人民杀戳几尽”⑲,明廷强行从马邑等地向河北移民。
河北省石家庄鹿泉市李村镇李村谢氏、大城县白马堂村马氏(由马邑县临成村迁出)、沧州陈氏、石家庄新乐市相家庄相氏,均是明初迁出。
这些移民多数仍编入民户,也有籍为军人。
据《明实录》《中国移民史》等文献资料记载,洪武四、五、六年河北塞内地区接受塞外的移民总数达60万人之多,他们大都来自北部边境山西朔州、张家口等地,迁入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北三河、滦州、固安、保定等地。
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迁山西大同贫民于北京广平等地。
20栾城县郭氏就是永乐年间由马驿(邑)迁栾城岗头村。
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论述到真定府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塞外移民成为当时顺天府的人口主体。
河北的其他地区也存在着移民垦荒的迫切需要,然而在当时,除了武力强制迁移的塞外移民外,很难再找到其他移民来源。
迁入真定府的移民,发现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有可能经真定府之东部向山东一带迁移,这可能也是日后在真定府难于发现洪武时期马邑移民的缘故。
”(五)云南省“上以其元之子孙,闵而宥之,且厚赐与,命随西平侯沐英戍守云南。
”21当时确有一部分鞑靼军士,随明军前往云南征战,被时人称为“征南鞑靼官军”。
这批军人及其家眷至少在600户以上,又形成一批数量不小的移民。
(六)四川省洪武三年(1370),明廷还将边塞的蒙古降军迁于四川。
22(七)山西省据《忻县志》载,由于连年混战,加之元至正末年瘟疫传染,使境内十室九空,几无人烟。
于是“县主奉令到朔州马邑县,领诸移民来忻落户”23。
现在,忻州很多村庄或姓氏都自称来自马邑县,迁入时间多称“明初”或“洪武”,有关记载很多。
《五台徐氏宗谱》记载:“始祖才甫,明洪武间由马邑迁五台之大建安村。
才甫祖兄弟三人,曰意甫,曰通甫,长幼行次无考。
通甫复迁河间,意甫迁河南,或曰仍回马邑。
”朔州《马邑徐氏家谱》也记载了这一史实:“洪武初年,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徐氏兄弟三人……连家眷迁于五台东堰村(即今东冶镇——笔者注)。
”《郝氏家族史》记载:先祖郝完同其本家郝从裕及其表弟张澄、张敬等从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迁来忻州,郝从裕分配到合索村;而郝完到董村落户;而他的表弟张澄、张敬迁往今忻府区高城乡辛庄,张监迁往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