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平和他的肠道微生物
- 格式:doc
- 大小:30.5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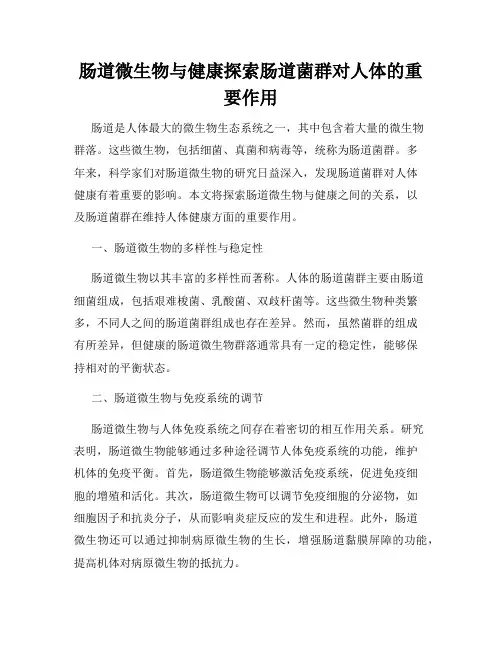
肠道微生物与健康探索肠道菌群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之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微生物群落。
这些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和病毒等,统称为肠道菌群。
多年来,科学家们对肠道微生物的研究日益深入,发现肠道菌群对人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探索肠道微生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肠道菌群在维持人体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与稳定性肠道微生物以其丰富的多样性而著称。
人体的肠道菌群主要由肠道细菌组成,包括艰难梭菌、乳酸菌、双歧杆菌等。
这些微生物种类繁多,不同人之间的肠道菌群组成也存在差异。
然而,虽然菌群的组成有所差异,但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群落通常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能够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
二、肠道微生物与免疫系统的调节肠道微生物与人体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维护机体的免疫平衡。
首先,肠道微生物能够激活免疫系统,促进免疫细胞的增殖和活化。
其次,肠道微生物可以调节免疫细胞的分泌物,如细胞因子和抗炎分子,从而影响炎症反应的发生和进程。
此外,肠道微生物还可以通过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增强肠道黏膜屏障的功能,提高机体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
三、肠道微生物与新陈代谢的调控肠道微生物对人体新陈代谢的调控也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
肠道微生物可以通过代谢产物的产生和调控,影响人体的能量代谢、脂质代谢、糖代谢等重要生理过程。
例如,肠道微生物能够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丙酸、丁酸等,这些短链脂肪酸可以提供能量,促进肠道上皮细胞的生长和修复,并调节肠道蠕动,维持肠道功能的正常运作。
此外,肠道微生物还可以参与胆固醇代谢、维生素合成等重要代谢过程,对人体健康起到积极的影响。
四、肠道微生物与心脑血管健康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与心脑血管健康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肠道微生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心脑血管系统的功能和疾病的发生。
首先,肠道微生物能够参与胆固醇代谢,影响血脂水平,从而调节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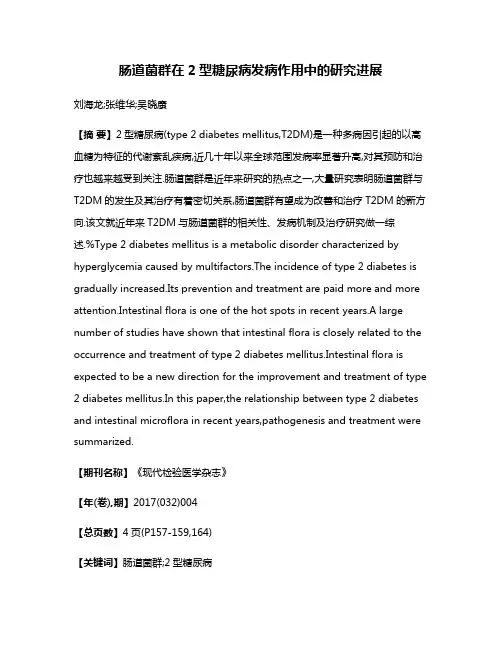
肠道菌群在2型糖尿病发病作用中的研究进展刘海龙;张维华;吴晓康【摘要】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是一种多病因引起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紊乱疾病,近几十年以来全球范围发病率显著升高,对其预防和治疗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肠道菌群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大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与T2DM的发生及其治疗有着密切关系,肠道菌群有望成为改善和治疗T2DM的新方向.该文就近年来T2DM与肠道菌群的相关性、发病机制及治疗研究做一综述.%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s a metabolic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hyperglycemia caused by multifactors.The incidence of type 2 diabetes is gradually increased.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r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Intestinal flora is one of the hot spots in recent years.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testinal flor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Intestinal flora is expected to b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In this pap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 2 diabetes and intestinal microflora in recent years,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were summarized.【期刊名称】《现代检验医学杂志》【年(卷),期】2017(032)004【总页数】4页(P157-159,164)【关键词】肠道菌群;2型糖尿病【作者】刘海龙;张维华;吴晓康【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西安 710004;陕西省人民医院血液科,西安710068;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西安 71000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587.1;R446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又称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是以胰岛素抵抗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约占糖尿病人数的9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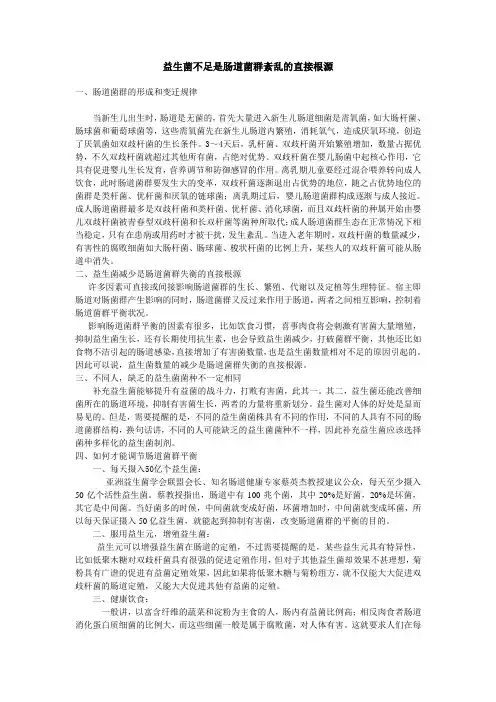
益生菌不足是肠道菌群紊乱的直接根源一、肠道菌群的形成和变迁规律当新生儿出生时,肠道是无菌的,首先大量进入新生儿肠道细菌是需氧菌,如大肠杆菌、肠球菌和葡萄球菌等,这些需氧菌先在新生儿肠道内繁殖,消耗氧气,造成厌氧环境,创造了厌氧菌如双歧杆菌的生长条件。
3~4天后,乳杆菌、双歧杆菌开始繁殖增加,数量占据优势,不久双歧杆菌就超过其他所有菌,占绝对优势。
双歧杆菌在婴儿肠菌中起核心作用,它具有促进婴儿生长发育,营养调节和防御感冒的作用。
离乳期儿童要经过混合喂养转向成人饮食,此时肠道菌群要发生大的变革,双歧杆菌逐渐退出占优势的地位,随之占优势地位的菌群是类杆菌、优杆菌和厌氧的链球菌;离乳期过后,婴儿肠道菌群构成逐渐与成人接近。
成人肠道菌群最多是双歧杆菌和类杆菌、优杆菌、消化球菌,而且双歧杆菌的种属开始由婴儿双歧杆菌被青春型双歧杆菌和长双杆菌等菌种所取代;成人肠道菌群生态在正常情况下相当稳定,只有在患病或用药时才被干扰,发生紊乱。
当进入老年期时,双歧杆菌的数量减少,有害性的腐败细菌如大肠杆菌、肠球菌、梭状杆菌的比例上升,某些人的双歧杆菌可能从肠道中消失。
二、益生菌减少是肠道菌群失衡的直接根源许多因素可直接或间接影响肠道菌群的生长、繁殖、代谢以及定植等生理特征。
宿主即肠道对肠菌群产生影响的同时,肠道菌群又反过来作用于肠道,两者之间相互影响,控制着肠道菌群平衡状况。
影响肠道菌群平衡的因素有很多,比如饮食习惯,喜事肉食将会刺激有害菌大量增殖,抑制益生菌生长,还有长期使用抗生素,也会导致益生菌减少,打破菌群平衡,其他还比如食物不洁引起的肠道感染,直接增加了有害菌数量,也是益生菌数量相对不足的原因引起的。
因此可以说,益生菌数量的减少是肠道菌群失衡的直接根源。
三、不同人,缺乏的益生菌菌种不一定相同补充益生菌能够提升有益菌的战斗力,打败有害菌,此其一。
其二,益生菌还能改善细菌所在的肠道环境,抑制有害菌生长,两者的力量将重新划分。

膳食纤维通过增加肠道有益菌可改善2型糖尿病临床症状?膳食干预改善肠道菌群可有效治疗肥胖?肠道菌群与抗衰老有显著关系?通过在肠道菌群与肥胖等代谢疾病关系领域近10年的矢力同心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张晨虹博士团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人体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同生活在自身体内的微生物保持友好互利的‘共生关系’。
”张晨虹这样说道。
张晨虹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多年来,主要进行人体及动物肠道菌群的研究。
以元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等手段,分析肠道菌群的结构与功能,节食及功能性食品对肠道菌群的影响,肠道菌群与宿主之间的互作,及肠道菌群在肥胖等复杂代谢性疾病以及衰老中的作用。
“我读硕士时的导师就是赵立平教授,他是国内最早系统开展微生物分子生态学研究的第一批学者。
”在10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张晨虹不仅学到了最前沿的专业知识,更被赵立平教授严谨治学、踏实科研、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感染。
一直以来,她也将这种宝贵的学者品质继承了下来,并成为了其治学和科研道路上攻坚克难的不二法宝。
保送大学,结缘肠道菌群张晨虹,1983年3月生。
高中因成绩优异保送本科上海交通大学。
踏入大学那年,她刚满18岁。
初来乍到,张晨虹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生物技术专业。
因有着学习深造的打算,大二那年,她又成功申请了生物技术专业基地班(本硕连读)。
“硕士开始,我的研究方向就是肠道菌群,多年来一直没变过。
”因为专业及研究方向的一致性,所以张晨虹有着比其他同学更扎实的理论知识、更丰富的研究经验及更深刻的心得体会。
很快,她便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位论文还被评为了2012年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2011年6月,张晨虹前往法国国家农业科学院肠道生态系统功能研究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
工作期间,张晨虹一边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努力掌握前沿的技术和理念,一边结合国内微生物生态研究情况探索自己的技术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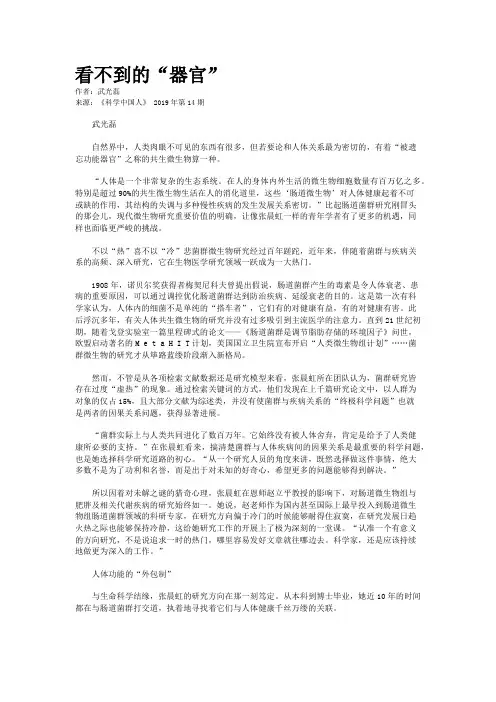
看不到的“器官”作者:武光磊来源:《科学中国人》 2019年第14期武光磊自然界中,人类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有很多,但若要论和人体关系最为密切的,有着“被遗忘功能器官”之称的共生微生物算一种。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
在人的身体内外生活的微生物细胞数量有百万亿之多。
特别是超过90%的共生微生物生活在人的消化道里,这些‘肠道微生物’对人体健康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结构的失调与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比起肠道菌群研究刚冒头的那会儿,现代微生物研究重要价值的明确,让像张晨虹一样的青年学者有了更多的机遇,同样也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不以“热”喜不以“冷”悲菌群微生物研究经过百年蹉跎,近年来,伴随着菌群与疾病关系的高频、深入研究,它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一跃成为一大热门。
19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曾提出假说,肠道菌群产生的毒素是令人体衰老、患病的重要原因,可以通过调控优化肠道菌群达到防治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
这是第一次有科学家认为,人体内的细菌不是单纯的“搭车者”,它们有的对健康有益,有的对健康有害。
此后浮沉多年,有关人体共生微生物的研究并没有过多吸引到主流医学的注意力。
直到21世纪初期,随着戈登实验室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肠道菌群是调节脂肪存储的环境因子》问世,欧盟启动著名的M e t a H I T计划,美国国立卫生院宣布开启“人类微生物组计划”……菌群微生物的研究才从筚路蓝缕阶段渐入新格局。
然而,不管是从各项检索文献数据还是研究模型来看,张晨虹所在团队认为,菌群研究皆存在过度“虚热”的现象。
通过检索关键词的方式,他们发现在上千篇研究论文中,以人群为对象的仅占15%,且大部分文献为综述类,并没有使菌群与疾病关系的“终极科学问题”也就是两者的因果关系问题,获得显著进展。
“菌群实际上与人类共同进化了数百万年。
它始终没有被人体舍弃,肯定是给予了人类健康所必要的支持。
”在张晨虹看来,搞清楚菌群与人体疾病间的因果关系是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也是她选择科学研究道路的初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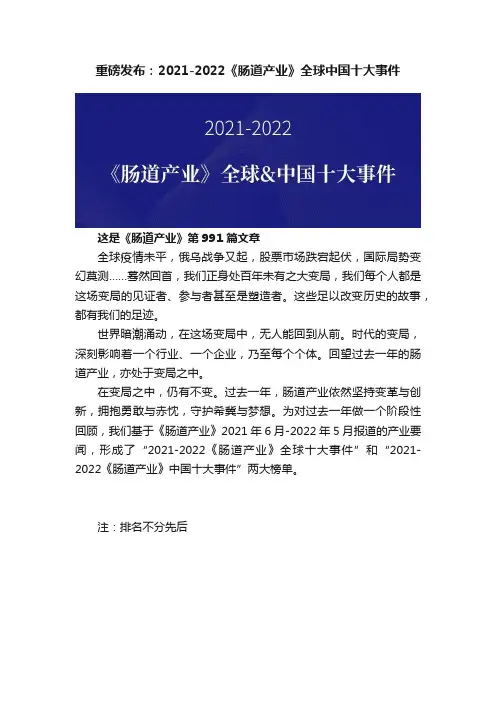
重磅发布:2021-2022《肠道产业》全球中国十大事件这是《肠道产业》第 991 篇文章全球疫情未平,俄乌战争又起,股票市场跌宕起伏,国际局势变幻莫测……蓦然回首,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变局的见证者、参与者甚至是塑造者。
这些足以改变历史的故事,都有我们的足迹。
世界暗潮涌动,在这场变局中,无人能回到从前。
时代的变局,深刻影响着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乃至每个个体。
回望过去一年的肠道产业,亦处于变局之中。
在变局之中,仍有不变。
过去一年,肠道产业依然坚持变革与创新,拥抱勇敢与赤忱,守护希冀与梦想。
为对过去一年做一个阶段性回顾,我们基于《肠道产业》2021年6月-2022年5月报道的产业要闻,形成了“2021-2022《肠道产业》全球十大事件”和“2021-2022《肠道产业》中国十大事件”两大榜单。
注:排名不分先后上述榜单仅代表热心肠生物技术研究院基于自身数据所做的评选,可能存在主观因素干扰等不足,仅供参考。
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提出批评、建议和意见。
下面我们将一一回顾上述事件:① 治疗CDI的活菌制剂喜讯不断,多家企业先后进入3期艰难梭菌感染(CDI)已经成为活菌制剂进展最快速的领域,多家企业在过去一年先后进入、完成3期临床试验。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公司在近期举办的DDW 2022上公布了RBX2660的2b期和3期临床结果,并已向FDA提交了RBX2660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
2021年5月,Seres Therapeutics公司公布了SER-109治疗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rCDI)的3期阳性详细结果。
2个月后,2021年7月,Seres公司表示与雀巢健康科学(NHS)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完成候选药物SER-109 的商业化事宜,并计划于2022年年中提交SER-109的BLA。
而另一家微生物组名企Finch Therapeutics公司紧随其后,其旗下治疗CDI的候选药物CP101于2021年11月迈入3期临床试验PRISM4研究。

肠道菌群与肥胖症的关系研究进展
赵立平;费娜
【期刊名称】《微生物与感染》
【年(卷),期】2013(008)002
【摘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与肥胖、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具体分子机制也正被逐步揭示出来.肠道菌群不仅可调节能量代谢,促进脂肪过度积累,还是宿主全身性低度慢性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紊乱的诱发因素之一.肠道菌群有可能成为预防和治疗肥胖症的新靶点.
【总页数】5页(P67-71)
【作者】赵立平;费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上海,200240;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上海,200240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肠道菌群与肥胖症关联性的研究进展 [J], 刘新彩
2.肥胖症肠道菌群与炎症的研究进展 [J], 曹战江;于健春;康维明;马志强
3.肠道菌群与肥胖症相互关系的研究现状 [J], 楚治良;龚慧;王晓娜;张占铎
4.肥胖症儿童微炎症状态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关系研究进展 [J], 赵萱
5.孕妇肠道菌群与婴幼儿肠道菌群及肥胖的关系研究进展 [J], 王颖;余昀;陈晓莉;刘燕群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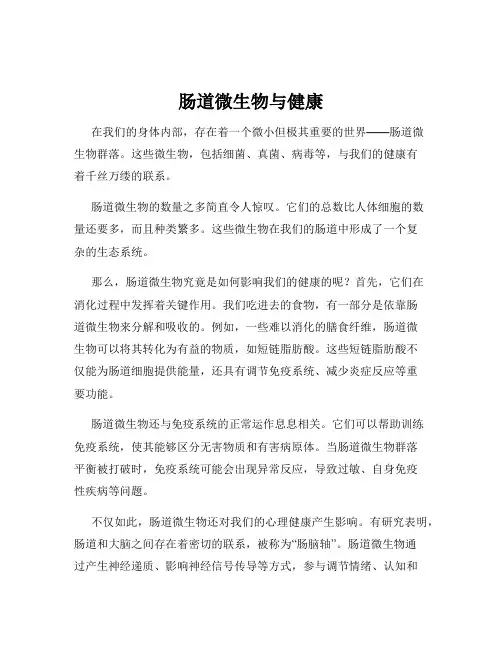
肠道微生物与健康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存在着一个微小但极其重要的世界——肠道微生物群落。
这些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与我们的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肠道微生物的数量之多简直令人惊叹。
它们的总数比人体细胞的数量还要多,而且种类繁多。
这些微生物在我们的肠道中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那么,肠道微生物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呢?首先,它们在消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有一部分是依靠肠道微生物来分解和吸收的。
例如,一些难以消化的膳食纤维,肠道微生物可以将其转化为有益的物质,如短链脂肪酸。
这些短链脂肪酸不仅能为肠道细胞提供能量,还具有调节免疫系统、减少炎症反应等重要功能。
肠道微生物还与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息息相关。
它们可以帮助训练免疫系统,使其能够区分无害物质和有害病原体。
当肠道微生物群落平衡被打破时,免疫系统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导致过敏、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问题。
不仅如此,肠道微生物还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有研究表明,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被称为“肠脑轴”。
肠道微生物通过产生神经递质、影响神经信号传导等方式,参与调节情绪、认知和行为。
例如,一些肠道微生物可以产生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影响心情和睡眠的神经递质。
当肠道微生物失衡时,可能会增加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的发生风险。
影响肠道微生物平衡的因素有很多。
饮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长期摄入高脂肪、高糖、低纤维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下降,有害菌增多。
而富含膳食纤维、蔬菜、水果和发酵食品的饮食,则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物的健康平衡。
生活方式也会对肠道微生物产生影响。
缺乏运动、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睡眠不足等,都可能导致肠道微生物群落的改变。
此外,抗生素的使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抗生素在治疗细菌感染时非常有效,但它们同时也会无差别地杀死有益菌和有害菌,从而破坏肠道微生物的平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肠道微生物的健康呢?首先,要保持均衡的饮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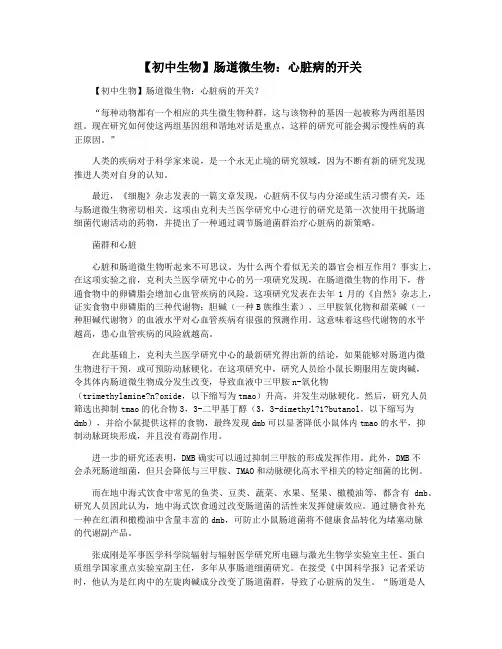
【初中生物】肠道微生物:心脏病的开关【初中生物】肠道微生物:心脏病的开关?“每种动物都有一个相应的共生微生物种群,这与该物种的基因一起被称为两组基因组。
现在研究如何使这两组基因组和谐地对话是重点,这样的研究可能会揭示慢性病的真正原因。
”人类的疾病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研究领域,因为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推进人类对自身的认知。
最近,《细胞》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现,心脏病不仅与内分泌或生活习惯有关,还与肠道微生物密切相关。
这项由克利夫兰医学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是第一次使用干扰肠道细菌代谢活动的药物,并提出了一种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治疗心脏病的新策略。
菌群和心脏心脏和肠道微生物听起来不可思议。
为什么两个看似无关的器官会相互作用?事实上,在这项实验之前,克利夫兰医学研究中心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肠道微生物的作用下,普通食物中的卵磷脂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项研究发表在去年1月的《自然》杂志上,证实食物中卵磷脂的三种代谢物:胆碱(一种B族维生素)、三甲胺氧化物和甜菜碱(一种胆碱代谢物)的血液水平对心血管疾病有很强的预测作用。
这意味着这些代谢物的水平越高,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
在此基础上,克利夫兰医学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得出新的结论,如果能够对肠道内微生物进行干预,或可预防动脉硬化。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给小鼠长期服用左旋肉碱,令其体内肠道微生物成分发生改变,导致血液中三甲胺n-氧化物(trimethylamine?n?oxide,以下缩写为tmao)升高,并发生动脉硬化。
然后,研究人员筛选出抑制tmao的化合物3,3-二甲基丁醇(3,3-dimethyl?1?butanol,以下缩写为dmb),并给小鼠提供这样的食物,最终发现dmb可以显著降低小鼠体内tmao的水平,抑制动脉斑块形成,并且没有毒副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DMB确实可以通过抑制三甲胺的形成发挥作用。
此外,DMB不会杀死肠道细菌,但只会降低与三甲胺、TMAO和动脉硬化高水平相关的特定细菌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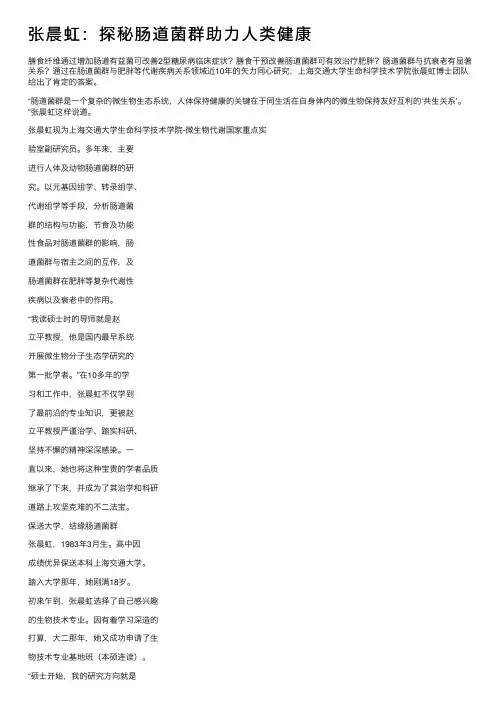
张晨虹:探秘肠道菌群助⼒⼈类健康膳⾷纤维通过增加肠道有益菌可改善2型糖尿病临床症状?膳⾷⼲预改善肠道菌群可有效治疗肥胖?肠道菌群与抗衰⽼有显著关系?通过在肠道菌群与肥胖等代谢疾病关系领域近10年的⽮⼒同⼼研究,上海交通⼤学⽣命科学技术学院张晨虹博⼠团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肠道菌群是⼀个复杂的微⽣物⽣态系统,⼈体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同⽣活在⾃⾝体内的微⽣物保持友好互利的‘共⽣关系’。
”张晨虹这样说道。
张晨虹现为上海交通⼤学⽣命科学技术学院-微⽣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多年来,主要进⾏⼈体及动物肠道菌群的研究。
以元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等⼿段,分析肠道菌群的结构与功能,节⾷及功能性⾷品对肠道菌群的影响,肠道菌群与宿主之间的互作,及肠道菌群在肥胖等复杂代谢性疾病以及衰⽼中的作⽤。
“我读硕⼠时的导师就是赵⽴平教授,他是国内最早系统开展微⽣物分⼦⽣态学研究的第⼀批学者。
”在10多年的学习和⼯作中,张晨虹不仅学到了最前沿的专业知识,更被赵⽴平教授严谨治学、踏实科研、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感染。
⼀直以来,她也将这种宝贵的学者品质继承了下来,并成为了其治学和科研道路上攻坚克难的不⼆法宝。
保送⼤学,结缘肠道菌群张晨虹,1983年3⽉⽣。
⾼中因成绩优异保送本科上海交通⼤学。
踏⼊⼤学那年,她刚满18岁。
初来乍到,张晨虹选择了⾃⼰感兴趣的⽣物技术专业。
因有着学习深造的打算,⼤⼆那年,她⼜成功申请了⽣物技术专业基地班(本硕连读)。
“硕⼠开始,我的研究⽅向就是肠道菌群,多年来⼀直没变过。
”因为专业及研究⽅向的⼀致性,所以张晨虹有着⽐其他同学更扎实的理论知识、更丰富的研究经验及更深刻的⼼得体会。
很快,她便获得了上海交通⼤学的博⼠学位,学位论⽂还被评为了2012年上海市优秀博⼠论⽂。
2011年6⽉,张晨虹前往法国国家农业科学院肠道⽣态系统功能研究实验室做博⼠后研究。
⼯作期间,张晨虹⼀边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努⼒掌握前沿的技术和理念,⼀边结合国内微⽣物⽣态研究情况探索⾃⼰的技术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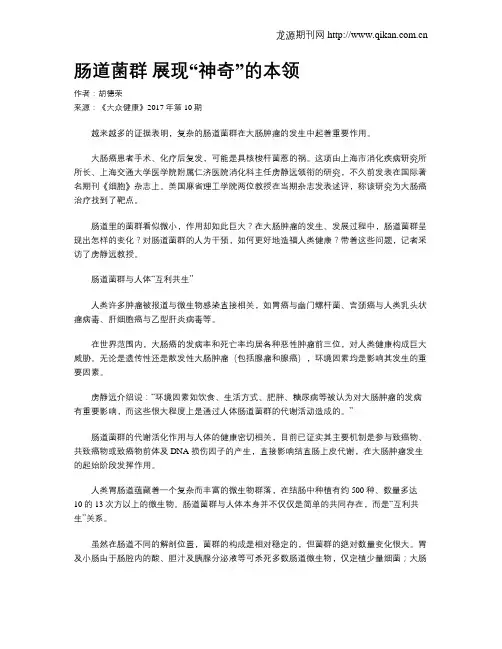
龙源期刊网 肠道菌群展现“神奇”的本领作者:胡德荣来源:《大众健康》2017年第10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复杂的肠道菌群在大肠肿瘤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
大肠癌患者手术、化疗后复发,可能是具核梭杆菌惹的祸。
这项由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主任房静远领衔的研究,不久前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细胞》杂志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两位教授在当期杂志发表述评,称该研究为大肠癌治疗找到了靶点。
肠道里的菌群看似微小,作用却如此巨大?在大肠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肠道菌群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对肠道菌群的人为干预,如何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房静远教授。
肠道菌群与人体“互利共生”人类许多肿瘤被报道与微生物感染直接相关,如胃癌与幽门螺杆菌、宫颈癌与人类乳头状瘤病毒、肝细胞癌与乙型肝炎病毒等。
在世界范围内,大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各种恶性肿瘤前三位,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
无论是遗传性还是散发性大肠肿瘤(包括腺瘤和腺癌),环境因素均是影响其发生的重要因素。
房静远介绍说:“环境因素如饮食、生活方式、肥胖、糖尿病等被认为对大肠肿瘤的发病有重要影响,而这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体肠道菌群的代谢活动造成的。
”肠道菌群的代谢活化作用与人体的健康密切相关,目前已证实其主要机制是参与致癌物、共致癌物或致癌物前体及DNA损伤因子的产生,直接影响结直肠上皮代谢,在大肠肿瘤发生的起始阶段发挥作用。
人类胃肠道蕴藏着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微生物群落,在结肠中种植有约500种、数量多达10的13次方以上的微生物。
肠道菌群与人体本身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共同存在,而是“互利共生”关系。
虽然在肠道不同的解剖位置,菌群的构成是相对稳定的,但菌群的绝对数量变化很大。
胃及小肠由于肠腔内的酸、胆汁及胰腺分泌液等可杀死多数肠道微生物,仅定植少量细菌;大肠。
“第七大营养素”作者:来源:《华声文萃》2018年第05期纤维被医学专家们誉为“第七大营养素”。
日前,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上海交通大学赵立平研究团队的一项新研究:膳食纤维利于促进肠道益生菌生长,增加摄入量对防治糖尿病有好处。
多吃纤维可助控血糖研究招募了43名Ⅱ型糖尿病患者,均口服阿卡波糖(拜糖平)控制血糖。
研究人员将他们分为两组:第一组日常饮食遵循中国糖尿病学会膳食指南的推荐;第二组尝试高纤维饮食,每天摄入纤维将近40克。
3个月后,第二组中89%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降到7%以下,达标了。
第一组只有50%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达标。
研究人员认为,富含纤维的饮食可调节Ⅱ型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增加特定肠道有益菌菌株,从而分泌更多短链脂肪酸,帮助控制血糖水平。
纤维如此神奇,但国人却吃得越来越少。
国人纤维摄入不足主要和全谷物、果蔬吃得不够有关。
纤维的三大功能整体来看,纤维有三大功能:1.促进肠道蠕动,防治便秘,减少有害物在肠道的存留时间,科学研究发现,摄入充足纤维可使患结直肠癌风险降低28%。
2.纤维能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降低餐后血糖。
3.本身没有热量,饱腹感又很强,利于控制食量和减肥。
多吃纤维可使中风风险降低7%,使心脏病风险降低9%,使肾结石风险降低22%,还能降低慢阻肺等炎性疾病的发病风险。
日常如何多吃纤维主食类《中国食物成分表》显示,每百克大米所含纤维仅为0.7克,比莜麦面、玉米面、黑米少很多。
紅小豆、绿豆等杂豆类和薯类也富含纤维。
这些食物很容易加到三餐主食中。
蔬菜类菌类富含纤维,鲜香菇、金针菇、木耳都是佼佼者。
鲜豆类也不错,比如毛豆、蚕豆、豌豆等。
富含纤维的蔬菜还有蒜薹、茭白、芦笋等。
水果类水果中也有不少纤维高手,比如石榴、桑葚等。
每人每天应至少摄入200克水果。
坚果类黑芝麻、松子、干杏仁、干核桃都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它们普遍热量较高,要控制量,每天20克左右足够了。
(摘自《生命时报》)。
科学家称肠道菌群致病机理是今后医学研究重点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曾说,“任何动物是与其共生的微生物构成的超级生物。”体内寄生着各种微生物,光是在肠道里,就有几千种、总重达1.5公斤的细菌。一直以来,科学家们只是隐约知道肠道菌群影响机体健康,但对于究竟有什么影响、如何发挥作用却不够了解。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学者,几乎都没有医学背景,大多数都是像赵立平一样的微生物学家。医学家习惯于从某一种病原菌出发,去寻找特定的微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而面对肠道菌群这样一团杂乱无章的细菌混合体时,只有熟悉微生物生态学的科学家们才能游刃有余。随着肠道菌群的基本情况越来越清楚,肠道菌群的致病机理将会是研究的重点。这一研究也必将影响动物肠道微生态制剂对调整肠道中益生菌平衡理念。 人类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早在100多年前就有了。但新的研究手段令这个古老的课题又焕发出生命之光。它是时下最热门的科学前沿,对它的探索,已使国际科学界联合起来,着手进行“人类第二基因组计划” 最早研究肠道菌群的是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细胞免疫学说的建立者梅契尼科夫。这位流亡到法国的俄国动物学家晚年开始琢磨衰老与长寿。他发现保加利亚有很多长寿老人,而他们的共同点是爱喝酸奶。通过进一步研究他认为,拥有健康的肠道菌群有助于长寿,就此写了一本名为《延长生命》的书,可算作是肠道菌群领域最早的论述,但这是本未经同行审议的学术著作。 尽管如此,人们在治疗中已零星地运用肠道菌群的概念。做完手术的病人,由于术后大量使用抗生素,破坏了肠道菌群,易出现腹泻不止的情况。而这种腹泻又很难再用药物来止住。有的医生灵机一动,将健康人的粪便装进胶囊,让病人服下去,结果发现效果不错。于是,这种思路得到推广,并加以规范。后来,医生们就开始采用经过处理的粪便悬浮液来为病人灌肠。这方法听起来有些“重口味”,因此它有一个含蓄的名称:细 菌疗法。这种治疗腹泻和肠道炎症的做法,最早在1970年代就有报道,并延续至今,尽管也发了不少学术文章,不过并非主流的治疗方法。在临床上,肠道菌群也不是常规的诊断项目。 很长一段时间内,肠道菌群理论一直没有成为学术界认真对待的课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手段所限。在过去,要想认识一个细菌,先要将它分离培养,再用显微镜去鉴定。但肠道菌群有几千个,且都是厌氧菌,一遇到有氧环境就迅速死掉,人们很难把它们逐一分离出来并识别。有些细菌是共生关系,也无法单独培养。即使是现在,在技术上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此外,肠道菌群本身的复杂也增加了人们认识它真面目的难度,就像指纹与眼睛虹膜一样,这世上没有哪两个人的肠道菌群一模一样。 肠道菌群研究领域随着生物医学进入基因时代而变得活跃起来。尤其是自2005年左右第二代基因测序技术出现以后,快速、一次性、大规模地解码DNA成为现实。科学家们从此可以扔下显微镜,转而从基因的层面了解肠道细菌。 生物学家曾经以为,机体是一座自给自足的生物孤岛,然而在过去10年里,研究人员证明,机体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网络”,其中有数以万亿的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寄居在我们的皮肤、阴部、口腔,尤其是肠道里。事实上,人体当中细菌的细胞数量是人体自身细胞的十倍之多。而且,这些微生物细胞及其基因(被称为“元基因组”)形成一个混合的小社会,不仅不会危害人类健康,还会在消化、生长和自我防御等方面成为我们基本生理机能的助手。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丁酸盐。机体肠道的上皮细胞每3天脱落更新一次,这一代谢过程需要一种名叫丁酸盐的物质。但食物中很少直接含有丁酸盐,人体自身也不能合成,它的主要来源是肠道菌群的代谢废弃物。更有趣的是,肠道细菌要靠“吃”膳食纤维才能产生丁酸盐,而膳食纤维又恰恰是人体不能自身消化的。因此,人对膳食纤维的需要,不仅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这些细菌,否则肠道上皮细胞长不好,就容易长出息肉乃至患结肠癌。 鉴于人与寄生于其体内的微生物的关系如此密切,2005年,美、德、日、中等13国在法国召开人类微生物组圆桌会议,会议发表的《巴黎宣言》宣布启动人类第二基因组计划——“人类元基因组计划”。在上世纪90年代,历时13年、耗费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曾测定了人类自身的25000多个基因。而人类第二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量,预计至少相当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0倍。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赵立平代表中国参加了上述会议。根据这个会议,各国自2007年始陆续开展了行动。其中比较大的项目有,美国斥资1亿美元的“人体微生物群系项目”,欧盟总经费达1200万欧元的“人类元基因组第七框架项目”。2008年,根据中法签署的《中法肠道元基因组研究联合声明》,上海交大联合中科院几家单位,与法国农科院联合启动了“中法肠道元基因组合作项目”,着眼于肠道菌群与肥胖及糖尿病的研究,由赵立平任项目负责人。目前,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完成。 在过去10年,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学者,几乎都没有医学背景,大多数都是像赵立平一样的微生物学家。医学家习惯于从某一种病原菌出发, 去寻找特定的微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而面对肠道菌群这样一团杂乱无章的细菌混合体时,只有熟悉微生物生态学的科学家们才能游刃有余。“这实际上是两种思维模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赵立平说。在最开始,大家需要把肠道菌群本身的情况摸清楚,共有多少种菌都有什么基因。而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要研究与疾病相关的都有哪些关键菌群,它们都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2012年1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会议,探讨未来中国的肠道菌群研究该怎么走。与会专家,除了赵立平等两三位微生物学者,绝大部分都是临床各科的医生。对此,赵立平坦承,“随着肠道菌群的基本情况越来越清楚,肠道菌群的致病机理将会是研究的重点。医学家在这个天地大有作为,未来他们将占据主流。”
赵立平:我和我的肠道菌群
1987 年,赵立平跟刘英结婚。
两年不到,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赵立平还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
新的压力加上美食——藉刘英做得一手好菜——我们的微生物学家长胖了。
到 1990 年,体重从60 公斤增至 80 公斤。
后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博士后期间,他又长胖了 10 公斤。
1995 年腰围量110 厘米,整个人的健康状况也极为糟糕。
赵立平认为,调节肠道菌群是他减肥成功的关键。
进入平台期的科研
转机2004 年,他读到一篇论文。
论文的主要作者戈登,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微生物学家。
用实验表明,肥胖症和小鼠肠道中的菌群存有关联。
2006 年,他开始了一种饮食疗法,食谱中包括山药和苦瓜,同时对自己的体重以及肠道中的菌群进行监测。
山药和苦瓜里面含有益生元,可以被肠道细菌发酵利用,据说有调节人体肠道菌群生长的功效。
再加上以粗粮为主的饮食,在两年内减掉了 20 公斤。
他的血压、心率和胆固醇水平也都降了下来。
抗炎细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的数量大幅增加,从最开始根本检测不到,到后来增加为他肠道细菌总量的 14.5%。
这些变化使赵立平决定,集中研究微生物在他身体状况转变中所发挥的影响。
从小鼠身上做起的实验,赵立平把它扩展到了人的身上。
寻找新的启发
有一天,一位兽医学的同事问他要一些芽孢杆菌的菌株,说是这种细菌能缓解猪和鸡的腹泻。
赵立平意识到,自己研究的菌株里面,很可能就有能抗植物感染,甚至抗人类感染功效的。
20 世纪 90 年代,赵立平涉足猪的微生物研究,试图探究用菌株来控制猪身上的感染这一设想,但无法获得资金。
在此期间,他家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本来就偏胖的父亲胆固醇水平激增,还得遭遇了两次中风。
赵立平的两个弟弟也都成了大胖子。
几年后,赵立平看到了戈登的论文,对他来说,这是“肠道菌群可以调节宿主的基因的首个证据”。
于是,赵立平拿自己当小白鼠,试图找出体重增加可能跟哪些微生物有关。
要从生活在人体肠道内上百种不同的微生物中,找出让体重增加的那一种,确实是个棘手的大难。
低热量饮食结合剧烈运动的减肥方法,在他看来完全说不通。
“从营养上讲,你的身体是在压力状态下的,”赵立平说,“然后你再加上生理上的压力。
也许这样你是能减肥,但同时也减掉了你的健康。
”
腰围变小之后,他开始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试图筛选出与肥胖有关的细菌。
今年 4 月,赵立平《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将小鼠从正常饮食转换到高脂肪饮食,然后再换回到正常饮食上来,期间每两周监测一
次小鼠肠道中菌群的变化。
观测发现,大约有 80 种细菌与饮食的转变存在关联。
更为可喜的是,由高脂肪饮食所引发的菌群改变,是完全可逆的。
但小鼠的微生物研究有其局限性。
要在微生物和肥胖症之间确立起联系,就必须在人身上做实验:
在人身上的测试
2009 年,赵立平回到太原,开始进行他的第一项临床试验。
那时候,可供他选择的测试对象比比皆是。
当时的中国糖尿病发病率、肥胖率激增。
走访了当地几家医院以后,赵立平有了 123 名临床上肥胖的志愿者,平均身体质量指数(BMI)不少于 30。
他给这些志愿者每人制定了一套 9 周长的减肥饮食计划,其中包括含有益生元的食品,让他们定期回来复查,以监测肠道菌群和代谢参数的变化。
在完成 9 周饮食治疗之后,对90 名患者做了14 周的跟踪调查。
在研究中的 3 个阶段点,志愿者还提供了粪便样本,供赵立平评估肠道菌群情况。
共有 93 名志愿者坚持完成了试验,体重呈中等水平下降,减轻了大约 7 公斤;同时,肠道中产生毒素的细菌减少,有益细菌数量增加。
赵立平又在另外 3 个中国城市共超过 1000 名患者身上进行了试验。
赵立平希望通过这项研究确立起一条基础代谢转移的分子途径。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帕特里斯·卡尼(Patrice D. Cani)等人的研究已经表明,摄入高脂肪饮食后,动物肠道环境发生的一系列明显变化。
有害细菌数量增加,肠黏膜屏障功能下降、渗透性增加,血液中的毒素水平增加,进而引发炎症,促使人体的新陈代谢率下降。
现在,赵立平希望在健康饮食之后,他能在志愿者身上观察到这种变化的反向过程。
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所的朱宝利,向来对中医药不甚感冒(他认为中药“就是些草”),他一贯公开批评夸大宣传中医药疗效的做法。
但是,朱宝利认为,赵立平的研究令人鼓舞。
他列举了赵立平及同事在北京开展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侧重于对糖尿病病人的肠道菌种进行观测,以找出标志性菌种,好将人的糖尿病跟细菌联系起来。
“他[指赵立平]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朱宝利说。
科罗拉多大学的微生物学家罗布·奈特(Rob Knight)表示,他非常期待看到赵立平临床研究发表出的结果。
“其他样本数量更少的饮食及微生物研究已经取得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宝贵结果,”奈特说。
像赵立平这样大规模的益生菌临床试验,在中国开展起来可能容易得多。
一天晚上,在上海闹市区一家熙熙攘攘的素食餐厅里,‘哦,这都是吃的嘛,没问题。
’”而在欧洲和北美,许多这些物质还没有作为食品或药品被当地人接受,他补充说,
不过,赵立平的目光已经投向亚洲以外的市场,他相信这份工作将比从基因组研究中研发减肥药物更富有成效。
温斯托克也表示,赵立平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找到
有效成分,而不是证明“只有什么虫粪里长出的真菌才能拿来治人”。
在赵立平的实验室里,温斯托克说,“这是西方还原论科学与传统中医的结合。
”
目前,赵立平正在研究是黄连素,用于中药的药材黄连的主要成分。
给老鼠高脂肪饮食的同时喂养小檗碱,老鼠便不会发展为肥胖,其肠道中的已知病原体种群数量下降,有益菌数量也出现上升。
“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来了解黄连素是如何影响营养和新陈代谢的。
”
如果有一天赵立平证明了肠道菌群和健康之间存在联系,那对他来说将是苦乐参半。
他的父亲现正躺在病床上,经受着炎症和中风后遗症的折磨,老人剩下的时日已经不多。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赵立平大半时间都守在父亲的病榻旁边。
“我真希望自己 10 年前就开始这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