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对小人物形象的继承与发展
- 格式:doc
- 大小:30.0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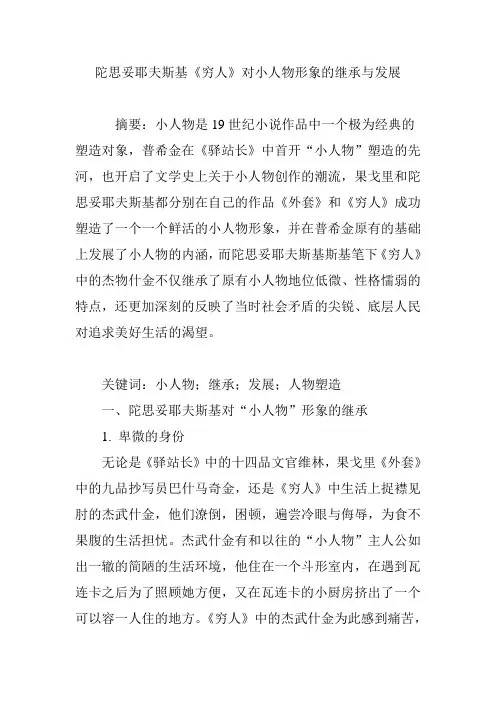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对小人物形象的继承与发展摘要:小人物是19世纪小说作品中一个极为经典的塑造对象,普希金在《驿站长》中首开“小人物”塑造的先河,也开启了文学史上关于小人物创作的潮流,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分别在自己的作品《外套》和《穷人》成功塑造了一个一个鲜活的小人物形象,并在普希金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了小人物的内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基笔下《穷人》中的杰物什金不仅继承了原有小人物地位低微、性格懦弱的特点,还更加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底层人民对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
关键词:小人物;继承;发展;人物塑造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人物”形象的继承1. 卑微的身份无论是《驿站长》中的十四品文官维林,果戈里《外套》中的九品抄写员巴什马奇金,还是《穷人》中生活上捉襟见肘的杰武什金,他们潦倒,困顿,遍尝冷眼与侮辱,为食不果腹的生活担忧。
杰武什金有和以往的“小人物”主人公如出一辙的简陋的生活环境,他住在一个斗形室内,在遇到瓦连卡之后为了照顾她方便,又在瓦连卡的小厨房挤出了一个可以容一人住的地方。
《穷人》中的杰武什金为此感到痛苦,他深知自己的卑微,也曾坦言“狠狠折磨我的倒不是钱,而是这些日常的烦恼。
”由于贫穷所导致的人性中的卑微,这其中就会潜藏着一种人格上的懦弱。
在俄国等级明确的官僚体制中,小官员们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尽管人们仍旧称他们是“先生”,但是底层文官并未得到他们应有的尊重与社会地位。
“小人物”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中诞生出来并逐渐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文学主题,这并非偶然,作家们一针见血的文字都无一例外地控诉着当时俄国腐败的社会官僚体制。
在这些作品中都多多少少地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呈现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的差距,我们在书中看到明斯基对维林要回女儿的请求时冷漠的嘴脸,将军对丢失外套的巴什马奇金毫无同情之心,大人眼见杰武什金出尽洋相却袖手一边,这样的情节反差相比对他们窘迫生活的描写,更深切的体现了“小人物”们的渺小卑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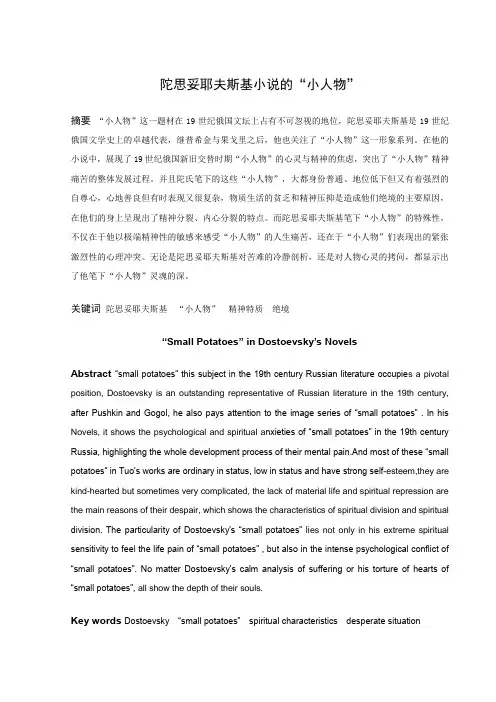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小人物”摘要“小人物”这一题材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卓越代表,继普希金与果戈里之后,他也关注了“小人物”这一形象系列。
在他的小说中,展现了19世纪俄国新旧交替时期“小人物”的心灵与精神的焦虑,突出了“小人物”精神痛苦的整体发展过程。
并且陀氏笔下的这些“小人物”,大都身份普通、地位低下但又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心地善良但有时表现又很复杂,物质生活的贫乏和精神压抑是造成他们绝境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的身上呈现出了精神分裂、内心分裂的特点。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他以极端精神性的敏感来感受“小人物”的人生痛苦,还在于“小人物”们表现出的紧张激烈性的心理冲突。
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难的冷静剖析,还是对人物心灵的拷问,都显示出了他笔下“小人物”灵魂的深。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精神特质绝境“Small Potatoes” in Dostoevsky’s NovelsAbstract “small potatoes” this subject in the 19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occupie s a pivotal position, Dostoevsky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after Pushkin and Gogol, he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image series of “small potatoes” . In his Novels, it shows the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a nxieties of “small potatoes” in the 19th century Russia, highlighting the whol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ir mental pain.And most of these “small potatoes” in Tuo's works are ordinary in status, low in status and have strong self-esteem,they are kind-hearted but sometimes very complicated, the lack of material life and spiritual repress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their despair, which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iritual division and spiritual division. The particularity of Dostoevsky's “small potatoes” li es not only in his extreme spiritual sensitivity to feel the life pain of “small potatoes” , but also in the intense psychological conflict of “small potatoes”. No matter Dostoevsky's calm analysis of suffering or his torture of hearts of “small potatoes”, all show the depth of their souls.Key words Dostoevsky “small potatoes”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desperate situation目录引言 (1)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 (2)(一)进退无门的小人物 (2)(二)自我牺牲的小人物 (3)(三)铤而走险的小人物 (4)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精神特质 (5)(一)精神特质 (5)(二)由精神到行为 (7)(三)精神变态 (9)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绝境 (9)(一)物质的绝境 (10)(二)精神的绝境 (11)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人物”与其他“小人物” (12)(一)普希金笔下小人物的身份之“小” (12)(二)果戈里笔下小人物的物质之“小” (13)(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精神之“小” (13)小结 (14)参考文献 (15)致谢 (15)引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鲁迅称作为“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因为陀氏拥有别的作家无法比拟的力量,可以“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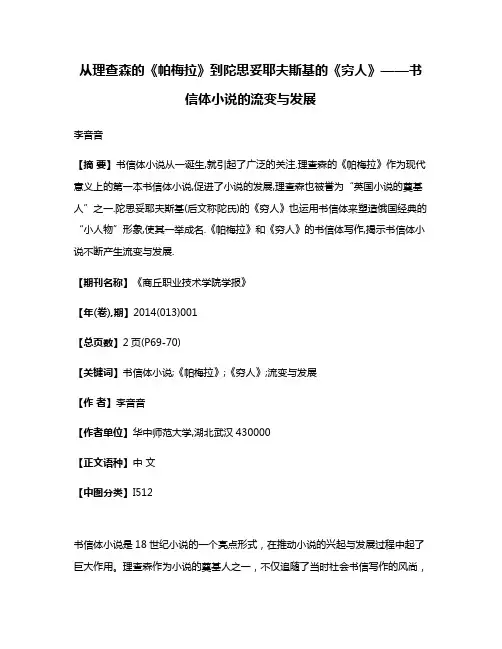
从理查森的《帕梅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书信体小说的流变与发展李音音【摘要】书信体小说从一诞生,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理查森的《帕梅拉》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信体小说,促进了小说的发展,理查森也被誉为“英国小说的奠基人”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文称陀氏)的《穷人》也运用书信体来塑造俄国经典的“小人物”形象,使其一举成名.《帕梅拉》和《穷人》的书信体写作,揭示书信体小说不断产生流变与发展.【期刊名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13)001【总页数】2页(P69-70)【关键词】书信体小说;《帕梅拉》;《穷人》;流变与发展【作者】李音音【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512书信体小说是18世纪小说的一个亮点形式,在推动小说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
理查森作为小说的奠基人之一,不仅追随了当时社会书信写作的风尚,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书信体小说的发展,《帕梅拉》一经发表,在英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理查森赢得极大的声誉,影响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陀氏的《穷人》在俄国发表之后,获得许多评论家的支持,他成功运用书信体这一小说创作方法,通过下等文官杰符什金和所救孤女瓦尔瓦拉的通信,深化了俄国“小人物”写作。
本文通过对两个文本的对比分析,试图探讨书信体这一小说新手法在流变过程中的传播与发展。
一、比较的基础《帕梅拉》与《穷人》同样作为书信体小说,有很强的可比性。
两本著作都有一定程度的首创意义并给作者带来巨大的声誉。
作为文学的自觉者,理查森曾说,他希望能够引进一种新的写作形式。
《帕梅拉》采用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少女帕梅拉给女贵族当仆人,善良的贵妇人教她语言、书写。
女主人去世后,她跟随女主人的儿子B先生,可是B先生对她心存邪念,面对邪恶的男主人的侵犯,帕梅拉为了保护忠贞,毅然拒绝。
最终帕梅拉的忠贞美德打动了他,帕梅拉接受了他的求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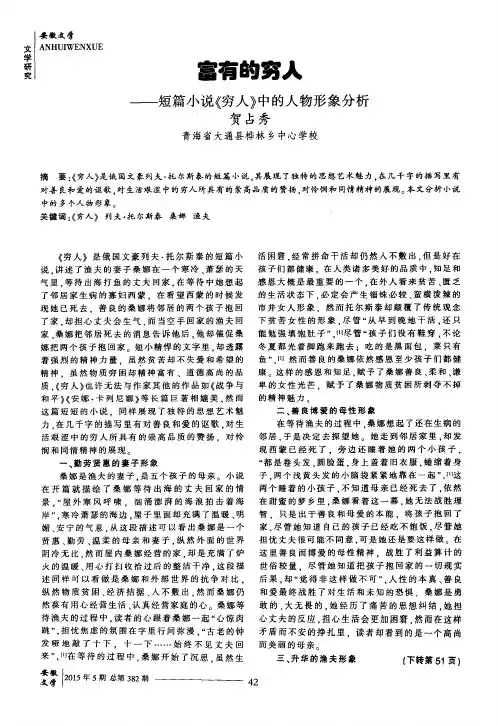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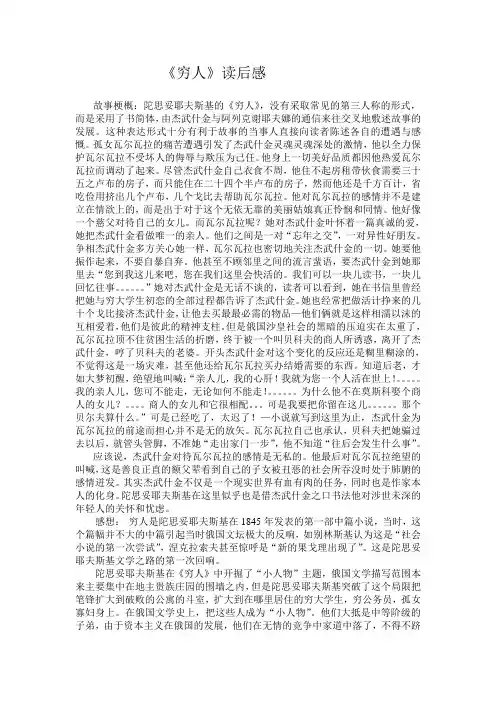
《穷人》读后感故事梗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没有采取常见的第三人称的形式,而是采用了书简体,由杰武什金与阿列克谢耶夫娜的通信来往交叉地敷述故事的发展。
这种表达形式十分有利于故事的当事人直接向读者陈述各自的遭遇与感慨。
孤女瓦尔瓦拉的痛苦遭遇引发了杰武什金灵魂灵魂深处的激情,他以全力保护瓦尔瓦拉不受坏人的侮辱与欺压为己任。
他身上一切美好品质都因他热爱瓦尔瓦拉而调动了起来。
尽管杰武什金自己衣食不周,他住不起房租带伙食需要三十五之卢布的房子,而只能住在二十四个半卢布的房子,然而他还是千方百计,省吃俭用挤出几个卢布,几个戈比去帮助瓦尔瓦拉。
他对瓦尔瓦拉的感情并不是建立在情欲上的,而是出于对于这个无依无靠的美丽姑娘真正怜悯和同情。
他好像一个慈父对待自己的女儿。
而瓦尔瓦拉呢?她对杰武什金叶怀着一篇真诚的爱,她把杰武什金看做唯一的亲人。
他们之间是一对“忘年之交”,一对异性好朋友。
争相杰武什金多方关心她一样,瓦尔瓦拉也密切地关注杰武什金的一切。
她要他振作起来,不要自暴自弃。
他甚至不顾邻里之间的流言蜚语,要杰武什金到她那里去“您到我这儿来吧,您在我们这里会快活的。
我们可以一块儿读书,一块儿回忆往事。
”她对杰武什金是无话不谈的,读者可以看到,她在书信里曾经把她与穷大学生初恋的全部过程都告诉了杰武什金。
她也经常把做活计挣来的几十个戈比接济杰武什金,让他去买最最必需的物品—他们俩就是这样相濡以沫的互相爱着,他们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但是俄国沙皇社会的黑暗的压迫实在太重了,瓦尔瓦拉顶不住贫困生活的折磨,终于被一个叫贝科夫的商人所诱惑,离开了杰武什金,哼了贝科夫的老婆。
开头杰武什金对这个变化的反应还是糊里糊涂的,不觉得这是一场灾难,甚至他还给瓦尔瓦拉买办结婚需要的东西。
知道后老,才如大梦初醒,绝望地叫喊:“亲人儿,我的心肝!我就为您一个人活在世上!。
我的亲人儿,您可不能走,无论如何不能走!。
为什么他不在莫斯科娶个商人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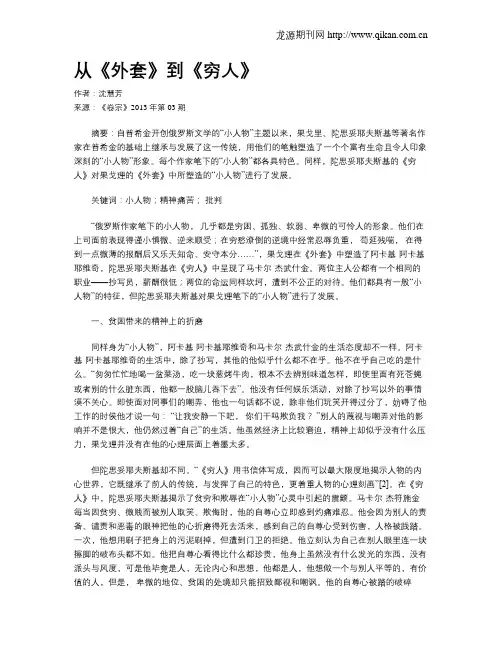
从《外套》到《穷人》作者:沈慧芳来源:《卷宗》2013年第03期摘要:自普希金开创俄罗斯文学的“小人物”主题以来,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作家在普希金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传统,用他们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富有生命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小人物”形象。
每个作家笔下的“小人物”都各具特色。
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对果戈理的《外套》中所塑造的“小人物”进行了发展。
关键词:小人物;精神痛苦;批判“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几乎都是穷困、孤独、软弱、卑微的可怜人的形象。
他们在上司面前表现得谨小慎微、逆来顺受;在穷愁潦倒的逆境中经常忍辱负重,苟延残喘,在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后又乐天知命、安守本分……”,果戈理在《外套》中塑造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中呈现了马卡尔·杰武什金。
两位主人公都有一个相同的职业——抄写员,薪酬很低;两位的命运同样坎坷,遭到不公正的对待。
他们都具有一般“小人物”的特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进行了发展。
一、贫困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同样身为“小人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和马卡尔·杰武什金的生活态度却不一样。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生活中,除了抄写,其他的他似乎什么都不在乎。
他不在乎自己吃的是什么。
“匆匆忙忙地喝一盆菜汤,吃一块葱烤牛肉,根本不去辨别味道怎样,即使里面有死苍蝇或者别的什么脏东西,他都一股脑儿吞下去”。
他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对除了抄写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
即使面对同事们的嘲弄,他也一句话都不说,除非他们玩笑开得过分了,妨碍了他工作的时侯他才说一句:“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别人的蔑视与嘲弄对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他仍然过着“自己”的生活。
他虽然经济上比较窘迫,精神上却似乎没有什么压力,果戈理并没有在他的心理层面上着墨太多。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同。
“《穷人》用书信体写成,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它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与发挥了自己的特色,更着重人物的心理刻画”[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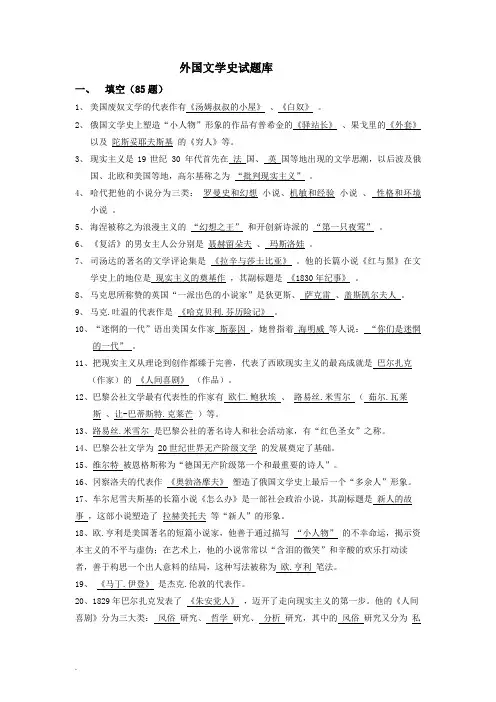
外国文学史试题库一、填空(85题)1、美国废奴文学的代表作有《汤姆叔叔的小屋》、《白奴》。
2、俄国文学史上塑造“小人物”形象的作品有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里的《外套》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等。
3、现实主义是19世纪 30 年代首先在法国、英国等地出现的文学思潮,以后波及俄国、北欧和美国等地,高尔基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
4、哈代把他的小说分为三类:罗曼史和幻想小说、机敏和经验小说、性格和环境小说。
5、海涅被称之为浪漫主义的“幻想之王”和开创新诗派的“第一只夜莺”。
6、《复活》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聂赫留朵夫、玛斯洛娃。
7、司汤达的著名的文学评论集是《拉辛与莎士比亚》。
他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其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
8、马克思所称赞的英国“一派出色的小说家”是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
9、马克.吐温的代表作是《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10、“迷惘的一代”语出美国女作家斯泰因,她曾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11、把现实主义从理论到创作都臻于完善,代表了西欧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是巴尔扎克(作家)的《人间喜剧》(作品)。
12、巴黎公社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欧仁.鲍狄埃、路易丝.米雪尔(茹尔.瓦莱斯、让-巴蒂斯特.克莱芒)等。
13、路易丝.米雪尔是巴黎公社的著名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有“红色圣女”之称。
14、巴黎公社文学为 20世纪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5、维尔特被恩格斯称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
16、冈察洛夫的代表作《奥勃洛摩夫》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多余人”形象。
17、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其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部小说塑造了拉赫美托夫等“新人”的形象。
18、欧.亨利是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善于通过描写“小人物”的不幸命运,揭示资本主义的不平与虚伪;在艺术上,他的小说常常以“含泪的微笑”和辛酸的欢乐打动读者,善于构思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这种写法被称为欧.亨利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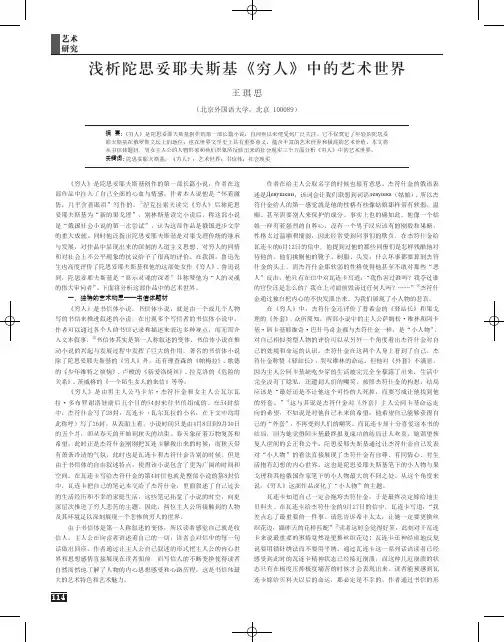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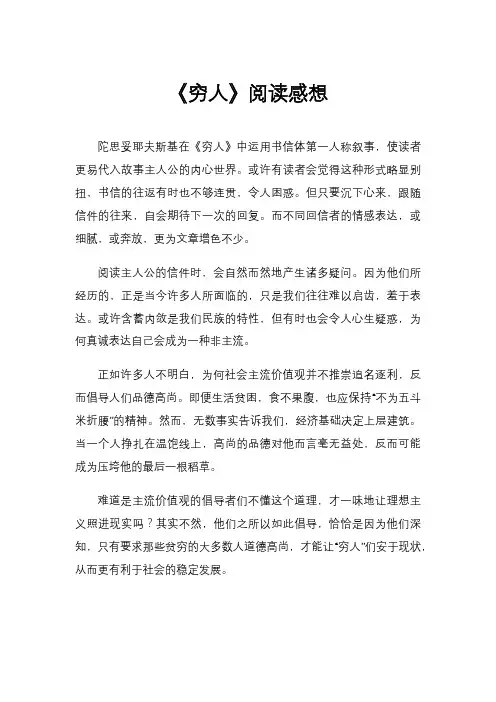
《穷人》阅读感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中运用书信体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更易代入故事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或许有读者会觉得这种形式略显别扭,书信的往返有时也不够连贯,令人困惑。
但只要沉下心来,跟随信件的往来,自会期待下一次的回复。
而不同回信者的情感表达,或细腻,或奔放,更为文章增色不少。
阅读主人公的信件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诸多疑问。
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正是当今许多人所面临的,只是我们往往难以启齿,羞于表达。
或许含蓄内敛是我们民族的特性,但有时也会令人心生疑惑,为何真诚表达自己会成为一种非主流。
正如许多人不明白,为何社会主流价值观并不推崇追名逐利,反而倡导人们品德高尚。
即便生活贫困,食不果腹,也应保持“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然而,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一个人挣扎在温饱线上,高尚的品德对他而言毫无益处,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难道是主流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不懂这个道理,才一味地让理想主义照进现实吗?其实不然,他们之所以如此倡导,恰恰是因为他们深知,只有要求那些贫穷的大多数人道德高尚,才能让“穷人”们安于现状,从而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穷人》中的男女主人公,无疑是被驯化得很好的一群人。
他们虽贫困潦倒,备受白眼,却只是一味忍让,将此视为高尚美德的标准,任由可怜而又可恨的自尊心支配,被动地接受着生活给予的更多苦难。
马卡尔在给瓦尔瓦拉的回信中写道:“是啊,穷人总是纠缠不休的,也许他们的饥饿呻吟会打扰有钱人的睡眠吧!”这句话虽尖刻,却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社会关系。
然而,即便他明白这一现实,他为之骄傲的,却是勤劳、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
一个人游手好闲,只知向他人索取,是可耻的;但路遇穷困潦倒之人,囊中羞涩,无法伸出援手,亦会令自己羞愧。
为何那些有钱人能心安理得地忽视这些苦难?这难道就是“穷大方,富小气”的真实写照吗?然而,纵使读再多的书,也未必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因为许多事情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我们可怜的自尊心也不允许我们做出格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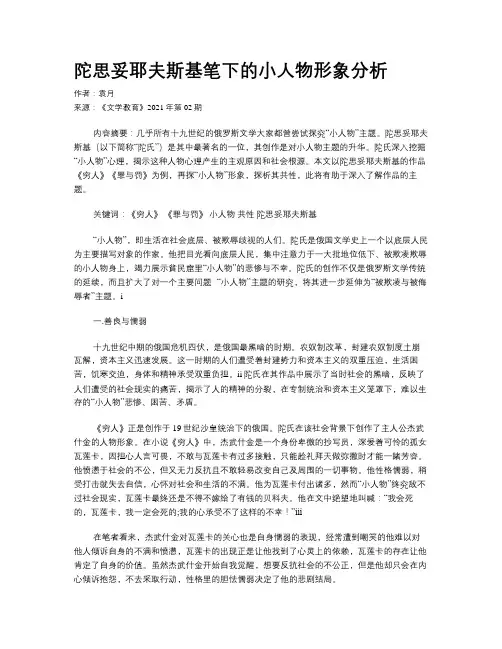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形象分析作者:袁月来源:《文学教育》2021年第02期内容摘要:几乎所有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大家都曾尝试探究“小人物”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其创作是对小人物主题的升华。
陀氏深入挖掘“小人物”心理,揭示这种人物心理产生的主观原因和社会根源。
本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穷人》《罪与罚》为例,再探“小人物”形象,探析其共性,此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作品的主题。
关键词:《穷人》《罪与罚》小人物共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底层、被欺辱歧视的人们。
陀氏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以底层人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
他把目光看向底层人民,集中注意力于一大批地位低下、被欺凌欺辱的小人物身上,竭力展示貧民窟里“小人物”的悲惨与不幸。
陀氏的创作不仅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延续,而且扩大了对一个主要问题--“小人物”主题的研究,将其进一步延伸为“被欺凌与被侮辱者”主题。
i一.善良与懦弱十九世纪中期的俄国危机四伏,是俄国最黑暗的时期。
农奴制改革,封建农奴制度土崩瓦解,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的人们遭受着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生活困苦,饥寒交迫,身体和精神承受双重负担。
ii陀氏在其作品中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人们遭受的社会现实的痛苦,揭示了人的精神的分裂,在专制统治和资本主义笼罩下,难以生存的“小人物”悲惨、困苦、矛盾。
《穷人》正是创作于19世纪沙皇统治下的俄国。
陀氏在该社会背景下创作了主人公杰武什金的人物形象。
在小说《穷人》中,杰武什金是一个身份卑微的抄写员,深爱着可怜的孤女瓦莲卡,因担心人言可畏,不敢与瓦莲卡有过多接触,只能趁礼拜天做弥撒时才能一睹芳容。
他愤懑于社会的不公,但又无力反抗且不敢轻易改变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事物。
他性格懦弱,稍受打击就失去自信,心怀对社会和生活的不满。
他为瓦莲卡付出诸多,然而“小人物”终究敌不过社会现实,瓦莲卡最终还是不得不嫁给了有钱的贝科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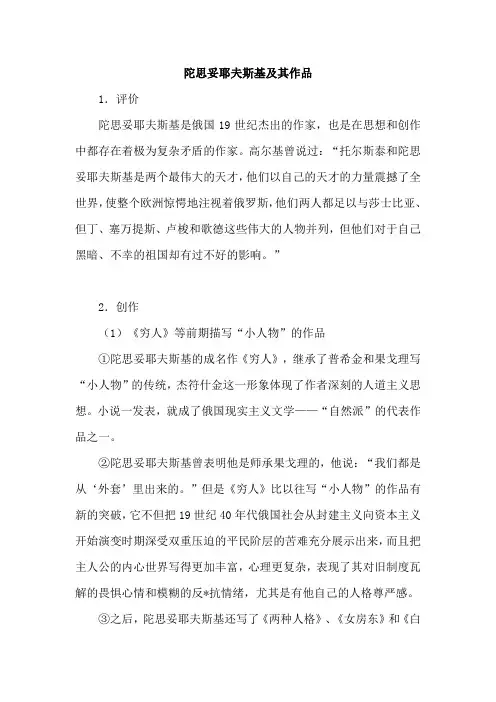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1.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作家,也是在思想和创作中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矛盾的作家。
高尔基曾说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的人物并列,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却有过不好的影响。
”2.创作(1)《穷人》等前期描写“小人物”的作品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穷人》,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写“小人物”的传统,杰符什金这一形象体现了作者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
小说一发表,就成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的代表作品之一。
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表明他是师承果戈理的,他说:“我们都是从‘外套’里出来的。
”但是《穷人》比以往写“小人物”的作品有新的突破,它不但把19世纪40年代俄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开始演变时期深受双重压迫的平民阶层的苦难充分展示出来,而且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写得更加丰富,心理更复杂,表现了其对旧制度瓦解的畏惧心情和模糊的反*抗情绪,尤其是有他自己的人格尊严感。
③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写了《两种人格》、《女房东》和《白夜》等小说。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已表现出刻画心理的卓越才能。
不过,他描写“小人物”的病*态心理有时失之过细,往往使人物带有神经质和悲*观绝*望情绪,所以调子显得低沉。
(2)流放期间这一时期他逐渐形成一种反动的“土壤派”理论。
他认为有文化的上层已经脱离了人民(即“土壤”),人民也不接受贵族革命家的理想,所以俄国不具有接受革命宣传的“土壤”,人民只能忍耐、顺从和笃信宗J。
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皈依了宗J。
这些思想在他动手于流放期间、完成于流放之后的小说《死屋手记》里已有所表现。
(3)后期创作①《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这仍是作者继续描写“小人物”的作品。
作者满怀同情地写出了一群被凌辱的小人物,指出他们具有正直、善良的品德,却又强调了他们的驯良,甚至通过娜塔莎和涅莉等形象宣扬基D教的受苦受难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者简介: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
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
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
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
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
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
《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
《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
161列夫· 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一并被世人誉为俄罗斯文学的“双子星”。
托翁具有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罗斯生活图画,可以从中窥见“托尔斯泰对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最深切关注和同情。
”[1]《穷人》是托尔斯泰以维克多·雨果的叙事诗《可怜的人们》为蓝本创作的短篇小说。
故事讲述了生活贫瘠的渔妇桑娜发现邻居寡妇去世后,主动收养两个遗孤的故事。
小说创作于1908年,正值俄罗斯历史上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人民对沙皇专制的反抗斗争日趋高涨,逐渐形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然而他们的道德情操却高尚淳朴,《穷人》这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他们的高尚品德。
”[2]《穷人》是托尔斯泰小说创作中难得的短小精悍之作,因其语言生动质朴,情节跌宕起伏,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品中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一、多维立体的形象层面托尔斯泰可谓当之无愧的塑造人物形象的大师,十分擅长将细节、环境、语言、动作等多种元素融合到一起,从多维度塑造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
小说《穷人》中的主要人物有女主人公桑娜、其丈夫和死去的邻居西蒙三人。
简单的人物设置构成了瓷实的三角结构,为全文的叙事搭建起扎实稳固的框架结构。
1.桑娜托尔斯泰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经典的女性形象,诸如,《童年》中的娜塔丽雅·萨维什娜、《战争与和平》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瓦伦加、《复活》中的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等形象。
尽管托翁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身份、性格、命运各不相同,但他们普遍具有善良、博爱、禁欲、拥有严肃的精神生活等共同品质和特点。
在具有强烈宗教倾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指导下, 托尔斯泰在描绘女性的美好品格时,一直都坚持着宗教精神这一主要原则,其笔下的理想女性都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圣母玛丽亚式的人物。
19世纪俄国文学中“小人物”形象的嬗变“小人物”形象的艺术刻画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社会地位而言“小人物”是与统治者权贵们相对而言,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们。
“小人物”承载着作家对那个黑暗时代的社会阶层小官吏、小职员、小知识分子等底层社会民众的性格特点、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的关心与思考,但是“小人物”形象成功的背后又潜存着作家们一定的局限性。
一、“小人物”形象的崛起19世纪30年代正值俄罗斯社会变革期,在俄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思潮。
革命活动却没有唤起广大人民的觉醒意识,这引起了普希金的关注,于是将触笔伸向了底层民众的灵魂深处,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小人物”。
从此,“小人物”的描写便贯穿于19世纪俄国文学界。
作者以故事叙述人的身份描写他三次遇到驿站长维林命运的变化。
主人公是个十四品的小文官,年迈体衰,与女儿杜妮亚相依为命。
后来女儿被一位贵族军官拐骗,他徒步去彼得堡想“把迷途的羔羊带回家来”,可是被拒之门外。
至此,维林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和希望,含恨而终。
小说以深刻的思想、严谨的结构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描述驿站长凄苦的一生,批判了俄国森严的等级制度,揭示了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善良且懦弱的性格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在维林身上,作者寄寓了一定的同情和怜悯,但也表现了作者对其懦弱忍让和卑躬屈膝的深刻反思。
然而,普希金的伟大不只是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小人物”形象,而且作为一个贵族能够跨越阶级刻画出一个平凡的人物形象,通过维林几次寻找女儿的过程逐步展示了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悲哀,真实地反映了沙皇时代底层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可见当时作者思想之进步。
二、“小人物”形象的发展四十年代后,果戈理进一步发展了“小人物”的主题。
作者曾在彼得堡当过小职员,但薪俸微薄,常靠借钱度日。
在那里他目睹了腐败黑暗的专制统治下的人情冷漠,对小人物的卑微地位和悲惨命运予以深切的同情,并用文字抨击并讽刺了当时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
穷人陀思妥耶妥夫斯基读后感案例一:在这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令我很感动的课文,名字叫《穷人》,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
这篇文章讲的是:渔夫的妻子桑娜自己已有五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她看到邻居西蒙死了,而且身旁还有两个熟睡的孩子时,就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抱回家。
经过丈夫的同意,他们打算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课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桑娜想的一句话:“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嗯,揍我一顿也好!”桑娜宁可自己挨揍,也不愿让西蒙的两个孩子饿死,充分地表现了她善良的心灵。
渔夫说的一句话也使我感动:“得把他们抱来,同死人呆在一起怎么行!哦,我们,我们总能熬过去的!”这几句话是那么坚定,也表现了渔夫助人为乐的品质。
虽然这些话都很朴素,但能体现他们的善良和伟大。
渔夫一家的生活那么困难,还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而我们呢?有些人有很多钱却不为那些有困难的人着想,渔夫和桑娜是我们的好榜样,他们善良的心感动了我。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但还是有许多失学儿童上不了学,我们应该像桑娜和渔夫一样,伸出援助之手,让他们也能学到知识、文化,希望所有的人都充满爱心,去帮助他们,让世界更美好!案例二:个人过得好不好,全靠穷与富来决定。
有一件东西,是用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一个人的品质。
一个人即使很有钱,但他的品质不好,也不会有人去爱戴他的;一个人很穷,但他品质高尚,人们会永远记住他。
《穷人》这一篇课文讲述的是在海边,住着一户贫苦的人家,渔夫早上出海打鱼,天黑仍未归来,她便想起了邻居西蒙,到了西蒙家,桑娜发现西蒙早已死去了,但西蒙的两个孩子还未死,原来母亲在临死的时候,拿自己的衣服盖在他们身上,还用旧头巾包住他们的小脚。
桑娜看那两个孩子实在可怜,就把他们抱回了自己的家里。
渔夫回来时,桑娜把西蒙的事全告诉了渔夫,并告诉了他那两个孩子的事情,就这样渔夫接受了。
从这篇课文中让我明白了,不光桑娜是好心的人,她的丈夫也是,他们宁可自己和受累,也不能让孩子跟着一起。
19世纪俄国“小人物”之流变论文摘要:在俄国19世纪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史上,“小人物”的主题一直深受作家们的喜爱。
在这一范畴颇有造诣的作家有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
他们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都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描绘,从产生、发展到深化最后到升华的过程中,小人物也由任人摧残最后上升到了新的境界。
形象刻画也从最初的可怜转变成了可怕。
但小人物的性格却从未逃脱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奴性特点,这也映射了俄国19世纪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俄国;小人物;奴性;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种典型的人物形象——“小人物”,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与统治阶级地位相对的平民阶级,如小职员、小官吏等。
小人物的文学概念中蕴含着对文化和历史的解读,同样还包含了作者对当时社会阶级的底层民众的个性行为以及心理的深刻体会。
“小人物”形象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就在于鲜活而形象地展示出人类天生矛盾的本性。
在成功塑造出这些鲜明的个体的同时,作者还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利用人物本身的思维逻辑展现出人类在寻求生存过程中引发的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
“小人物”身上的矛盾性也就注定了他们悲剧性的结尾。
《驿站长》中维林因心爱的女儿被拐跑,整日思念最后一病不起抑郁而终;《外套》中的阿卡基耶维奇因外套被抢后寻助无果而一命呜呼,他化作鬼魂却不断抢别人的外套;《穷人》中的杰武什金心地善良的帮助别人,但是最后却人格受到了践踏而失去挚爱,整日酗酒身亡;《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一生都生活在“害怕”中,最后实现了装在套中的“理想”。
在传统思想里,看待“小人物”的立场一直以来都是以同情为标榜。
但更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小人物”身上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是促成其悲剧的原因之一。
他们身上持有的性格缺陷不仅由于时代的局限还有社会制度的禁锢。
对待这些人物形象,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一、“小人物”形象的崛起19世纪30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巩固发展的时期,俄罗斯也面临着变革性的转型,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从《外套》到《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笔下
“小人物”之发展
沈慧芳
【期刊名称】《卷宗》
【年(卷),期】2013(000)003
【摘要】自普希金开创俄罗斯文学的“小人物”主题以来,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作家在普希金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传统,用他们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富有生命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小人物”形象.每个作家笔下的“小人物”都各具特色.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对果戈理的《外套》中所塑造的“小人物”进行了发展.
【总页数】1页(P5)
【作者】沈慧芳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迟子建笔下的小人物叙述——分析小人物及小人物的叙述内涵 [J], 刘雪梅;
2.从理查森的《帕梅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书信体小说的流变与发展 [J], 李音音
3.宗教文化语境下的小人物——以《驿站长》、《外套》和《罪与罚》中的小人物为例 [J], 惠继东
4.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 [J], 克冰
5.小人物“痛彻肺腑”的悲剧——漫话果戈理短篇小说《外套》 [J], 彭启华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对小人物形象的继承与发展
摘要:小人物是19世纪小说作品中一个极为经典的塑造对象,普希金在《驿站长》中首开“小人物”塑造的先河,也开启了文学史上关于小人物创作的潮流,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分别在自己的作品《外套》和《穷人》成功塑造了一个一个鲜活的小人物形象,并在普希金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了小人物的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基笔下《穷人》中的杰物什金不仅继承了原有小人物地位低微、性格懦弱的特点,还更加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底层人民对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
关键词:小人物;继承;发展;人物塑造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人物”形象的继承
1. 卑微的身份
无论是《驿站长》中的十四品文官维林,果戈里《外套》中的九品抄写员巴什马奇金,还是《穷人》中生活上捉襟见肘的杰武什金,他们潦倒,困顿,遍尝冷眼与侮辱,为食不果腹的生活担忧。
杰武什金有和以往的“小人物”主人公如出一辙的简陋的生活环境,他住在一个斗形室,在遇到瓦连卡之后为了照顾她方便,又在瓦连卡的小厨房挤出了一个可以容一人住的地方。
《穷人》中的杰武什金为此感到痛苦,
他深知自己的卑微,也曾坦言“狠狠折磨我的倒不是钱,而是这些日常的烦恼。
”由于贫穷所导致的人性中的卑微,这其中就会潜藏着一种人格上的懦弱。
在俄国等级明确的官僚体制中,小官员们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尽管人们仍旧称他们是“先生”,但是底层文官并未得到他们应有的尊重与社会地位。
“小人物”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中诞生出来并逐渐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文学主题,这并非偶然,作家们一针见血的文字都无一例外地控诉着当时俄国腐败的社会官僚体制。
在这些作品中都多多少少地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呈现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的差距,我们在书中看到明斯基对维林要回女儿的请求时冷漠的嘴脸,将军对丢失外套的巴什马奇金毫无同情之心,大人眼见杰武什金出尽洋相却袖手一边,这样的情节反差相比对他们窘迫生活的描写,更深切的体现了“小人物”们的渺小卑微。
2. 悲惨的命运
《驿站长》、《外套》和《穷人》,三部作品可以看作“小人物”在三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把现实主义的涵寓于不同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中。
三者的相似之处可以归为不仅生活穷困,又失去了自己生命中最心爱的部分。
老维林尽管日子不甚宽裕但是他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小女儿杜妮娅,但明斯基却骗走了他的女儿并拒绝把她还给维林,自此他郁郁寡欢,
含恨而终;巴什马奇金对物质生活本来无欲无求,当他省吃俭用做了新外套之后,新外套变成了他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当他丢失外套后表现得十分紧焦急,甚至为此而死,即使化作鬼魂时还是要抢走别人的外套得到慰藉;杰武什金,一个善良富有爱心的小公务员,即使生活拮据,依然无怨无悔的照顾着命运悲惨的瓦连卡,然而在故事最后,瓦连卡嫁给了地主贝科夫,小说结局以杰武什金给瓦里安卡的一封信作为句点,信中他希望瓦连卡保持与他书信联系,唯恐笔下的这封信成为最后的联系,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瓦连卡无限的眷恋。
每个故事的情节都显得那么沉重,他们对于自己的心爱的人或物爱意越深,那么在他们失去挚爱的时候,带给读者的心酸之感就愈加浓烈,在残酷社会现实面前他们都无力抗争,而他们眼中的挚爱对于大人物来说却只是寻常,由此便使读者也随之产生了一种为“小人物”抱不平的心理,同时又会将主人公悲剧式的命运与他们生存的那个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作家所要真正想启示读者的。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人物”形象的发展
1. 文学创作手法上的创新
小说是通过五十四封书信来展开整个故事情节的,寄信人是一位做了三十年抄写工作的五十岁九等文官杰武什金,收信人则是一位家庭由富裕转向败落的十七岁少女瓦连卡。
通篇读者都是通过主人公杰武什金和瓦连卡来转述情结,而并不是用主人公“我”的口吻。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仅仅是让我们看到发生在信笺背后的客观事实,作者把自己个人情感融入在叙述的小说情节中,似乎将所听所闻的事件毫无主观意识的反映给读者。
另外一方面,杰武什金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处于平行位置,主人公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他作为独立于作者而存在的另一个意识,同样可以有无限的思想空间,并不受到限制,因此主人公参与的情节也不能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观色彩。
这种“复调”的创作手法是普希金和果戈里在“小人物”小说中未尝试过的,这一创新文学作品创作上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式。
2.大量的心理分析
无论是普希金,还是果戈里,他们的笔墨运用多重于对情节的支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大量文字是用来表达人物心感受的。
《穷人》中出现了大量主人公思想的剖白,杰武什金的心暗辩,挣扎时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无奈伤悲时的独白,所思所想,让他们的情绪直观的表达出来,把面对每个情节中主人公的心态毫无遗落的呈现在纸上,这都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强调。
由于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脱离作者,所以这样的心理剖析也更加丰富了人物在的多样性,他对自己的表达更加自由,当情节推进,矛盾出现,主人公出现表情动作的转变,读者
不需进行更多的推敲,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告诉了我们答案,在理解上更利于读者抓住作品的主旨展示出了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人。
3.小人物对生活的追求
《穷人》中对“小人物”不再是维林时候的面对显贵懦弱胆怯,不再是巴什马奇金时候死后化作鬼魂来夺取别人的外套,此时的杰武什金是一个对生活有着热情和追求的人,即使薪资微薄,还是想着穿着体面,还是要给心爱的瓦连卡买花,制造浪漫,他有自己的生活情调,并不是枯燥如巴什马奇金那般,一味的只知道埋头在文字抄写当中,他在乎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他在知道瓦连卡悲苦的经历后不求回报的照顾她的生活,他努力工作获得报酬,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主人公,这样的生命显得更加有意义和价值。
另外,杰武什金居住的大杂院好像是一个底层人物的万花筒,多棱镜一样,对每种工作,每种性格的人都做了描写,他代表的这个阶层和流连于各大舞会的贵族一样,有独立意识,有进步思想,有自我诉求,底层人民也有自己丰富的精神财富,也在渴望能够得到无差别的尊重和尊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进步性,《穷人》一书的问世给“小人物”一种思想启蒙,为自己的幸福抗争,面对社会的不平等,不再忍气吞声。
三、结语
通过对三个作家三部以“小人物”为题材的作品的分析,对比和研究,我们看到了俄国社会小人物由自我沉浸到后来开始有了觉醒意识,这个阶级在文学中的崛起,也从侧面反应了俄国社会制度的矛盾走向激化,这样的社会背景有利我们分析文学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在俄罗斯文坛带有拓荒性,无论是小说情节,还是创作手法都开辟了一个与之前作家完全不同的空间,我们看到陀氏对“小人物”的继承,更是看到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他带来了思想启蒙,也让我们对人性有了新的反思,这不仅是我们研究作家作品的意义所在,而且这也是文学作品价值的体现。
(作者单位:师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时代.1952年
[2]穷人.文颖译.人民文学.1982年.第146页
[3]浅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人物刻画.大学学报.2014
[4]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叙事模式研究[D].:华中师大学.2004
[5]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