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敬琏商榷“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
- 格式:doc
- 大小:14.50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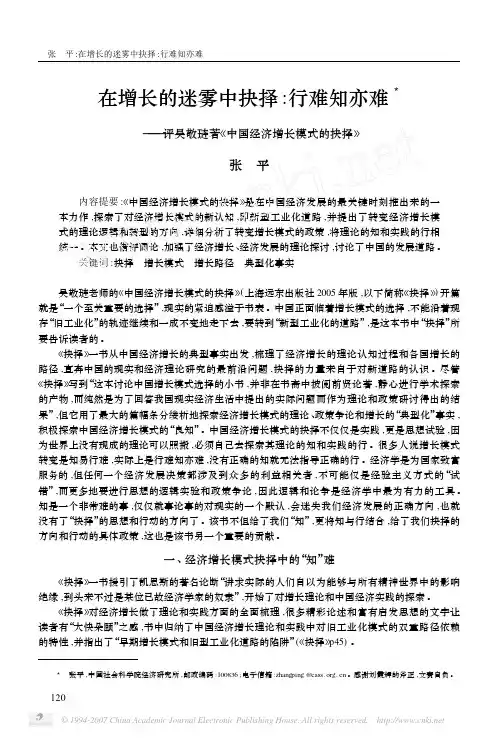
在增长的迷雾中抉择:行难知亦难3———评吴敬琏著《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张 平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关键时刻推出来的一本力作,探索了对经济增长模式的新认知,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逻辑和转型的方向,详细分析了转变增长模式的政策,将理论的知和实践的行相统一。
本文也借评而论,加强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理论探讨,讨论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抉择 增长模式 增长路径 典型化事实 吴敬琏老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抉择》)开篇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现实的紧迫感溢于书表。
中国正面临着增长模式的选择,不能沿着现存“旧工业化”的轨迹继续和一成不变地走下去,要转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是这本书中“抉择”所要告诉读者的。
《抉择》一书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出发,梳理了经济增长的理论认知过程和各国增长的路径,直奔中国的现实和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抉择的力量来自于对新道路的认识。
尽管《抉择》写到“这本讨论中国增长模式选择的小书,并非在书斋中披阅前贤论著,静心进行学术探索的产物,而纯然是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而作为理论和政策研讨得出的结果”,但它用了最大的篇幅条分缕析地探索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政策争论和增长的“典型化”事实,积极探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良知”。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不仅仅是实践,更是思想试验,因为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必须自己去探索其理论的知和实践的行。
很多人说增长模式转变是知易行难,实际上是行难知亦难,没有正确的知就无法指导正确的行。
经济学是为国家致富服务的,但任何一个经济发展决策都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不可能仅是经验主义方式的“试错”,而更多地要进行思想的逻辑实验和政策争论,因此逻辑和论争是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
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仅仅就事论事的对现实的一个默认,会迷失我们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也就没有了“抉择”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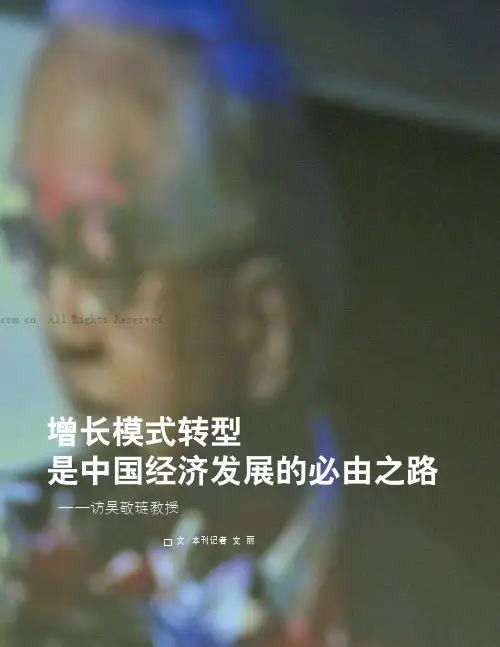
| ECONOMY高端访谈Interview.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Rights Reserved.摄/朋张者记ECONOMY | 本刊| ECONOMY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吴敬琏教授从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机理、分析短期问题和分析长期问题的不同理论框架、增长模式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等几个方面作了深入细致分析。
吴敬琏说,在顺利度过2009年的难关之后,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各方的意见见仁见智。
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很大,其中最大的变数在于政策不同会导致结果的差异。
吴敬琏指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久已存在而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机理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之间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对此,吴敬琏指出:“面对危机这种情况,适宜的做法,应是综合运用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
在经济和市场面临崩溃的情况下,用短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撑市场,保证经济不崩盘,是必要的。
同时,必须对导致经济出现危机的原因有清晰的认识,认真解决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而不能将救急的短期政策视为能够治愈长期问题的灵丹妙药。
”吴老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产泡沫的突然破灭和虚拟财富的蒸发导致一些重要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崩溃,引发了债务危机,于是大家都捂紧自己的钱袋,刹那间流动性极度短缺,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救市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用政府信用替补民间信用来维持市场的运转。
然而,虚拟资产泡沫的破灭只是长期以来世界经济本刊记者张朋/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编者按: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和长期积累的经济矛盾。
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要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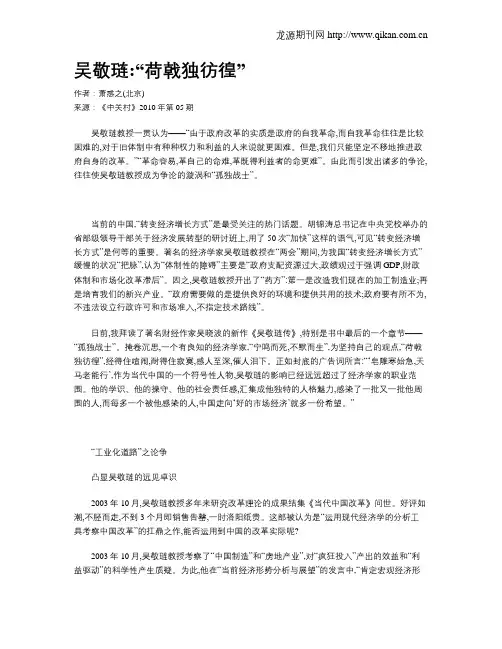
吴敬琏:“荷戟独彷徨”作者:萧惑之(北京)来源:《中关村》2010年第05期吴敬琏教授一贯认为——“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困难。
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
”“革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革既得利益者的命更难”。
由此而引发出诸多的争论,往往使吴敬琏教授成为争论的漩涡和“孤独战士”。
当前的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经济发展转型的研讨班上,用了50次“加快”这样的语气,可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何等的重要。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两会”期间,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慢的状况“把脉”,认为“体制性的障碍”主要是“政府支配资源过大,政绩观过于强调GDP,财政体制和市场化改革滞后”。
因之,吴敬琏教授开出了“药方”:第一是改造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再是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
“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提供共用的技术;政府要有所不为,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不指定技术路线”。
日前,我拜读了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新作《吴敬琏传》,特别是书中最后的一个章节——“孤独战士”。
掩卷沉思,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荷戟独彷徨”,经得住喧闹,耐得住寂寞,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正如封底的广告词所言:“‘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
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工业化道路”之论争凸显吴敬琏的远见卓识2003年10月,吴敬琏教授多年来研究改革理论的成果结集《当代中国改革》问世。
好评如潮,不胫而走,不到3个月即销售告罄,一时洛阳纸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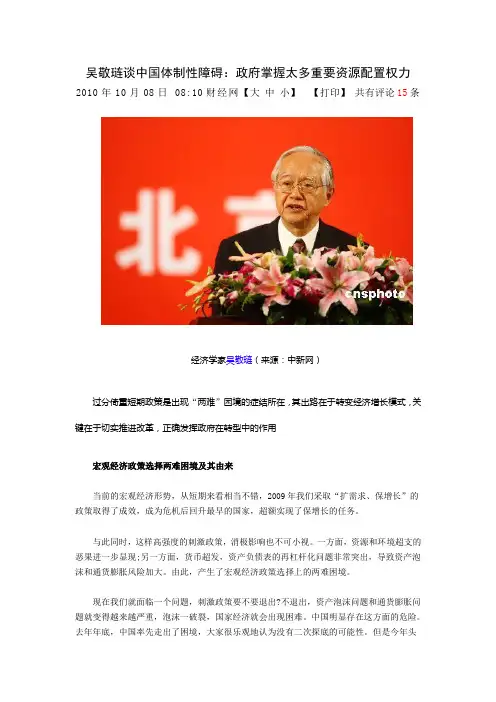
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2010年10月08日08:10财经网【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15条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源:中新网)过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现“两难”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正确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
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
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
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
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
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
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
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
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
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
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
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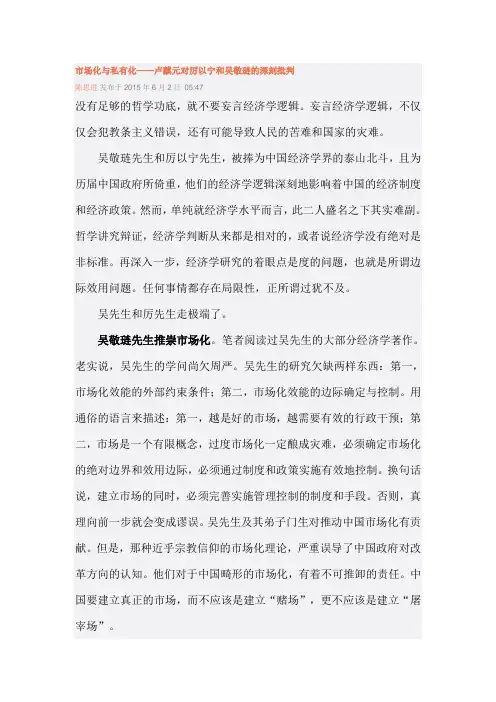
市场化与私有化——卢麒元对厉以宁和吴敬琏的深刻批判陈思进发布于2015年6月2日05:47没有足够的哲学功底,就不要妄言经济学逻辑。
妄言经济学逻辑,不仅仅会犯教条主义错误,还有可能导致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灾难。
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被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且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倚重,他们的经济学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然而,单纯就经济学水平而言,此二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哲学讲究辩证,经济学判断从来都是相对的,或者说经济学没有绝对是非标准。
再深入一步,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度的问题,也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问题。
任何事情都存在局限性,正所谓过犹不及。
吴先生和厉先生走极端了。
吴敬琏先生推崇市场化。
笔者阅读过吴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
老实说,吴先生的学问尚欠周严。
吴先生的研究欠缺两样东西:第一,市场化效能的外部约束条件;第二,市场化效能的边际确定与控制。
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第一,越是好的市场,越需要有效的行政干预;第二,市场是一个有限概念,过度市场化一定酿成灾难,必须确定市场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必须通过制度和政策实施有效地控制。
换句话说,建立市场的同时,必须完善实施管理控制的制度和手段。
否则,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吴先生及其弟子门生对推动中国市场化有贡献。
但是,那种近乎宗教信仰的市场化理论,严重误导了中国政府对改革方向的认知。
他们对于中国畸形的市场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而不应该是建立“赌场”,更不应该是建立“屠宰场”。
厉以宁先生推崇私有化。
笔者阅读过厉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
老实说,厉先生的学问不仅仅欠缺周严,还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
厉先生对股份制情有独钟。
很遗憾,厉先生却没有搞清楚公有制、股份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
厉先生戮力推行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股份制,而是狭义私有制。
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制,本质上是公有制的一种模式。
厉先生所倡导的畸形股份制改革,是将国有资产通过违宪和违法的方式转变成为私有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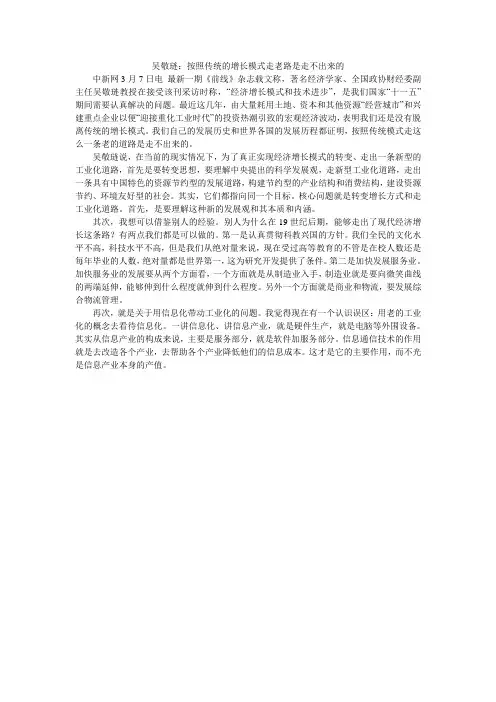
吴敬琏:按照传统的增长模式走老路是走不出来的中新网3月7日电最新一期《前线》杂志载文称,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财经委副主任吴敬琏教授在接受该刊采访时称,“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是我们国家“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和兴建重点企业以便“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投资热潮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表明我们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
我们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都证明,按照传统模式走这么一条老的道路是走不出来的。
吴敬琏说,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为了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首先是要转变思想,要理解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其实,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核心问题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和走工业化道路。
首先,是要理解这种新的发展观和其本质和内涵。
其次,我想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
别人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能够走出了现代经济增长这条路?有两点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第一是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
我们全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从绝对量来说,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是在校人数还是每年毕业的人数,绝对量都是世界第一,这为研究开发提供了条件。
第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入手,制造业就是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能够伸到什么程度就伸到什么程度。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商业和物流,要发展综合物流管理。
再次,就是关于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认识误区:用老的工业化的概念去看待信息化。
一讲信息化、讲信息产业,就是硬件生产,就是电脑等外围设备。
其实从信息产业的构成来说,主要是服务部分,就是软件加服务部分。
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就是去改造各个产业,去帮助各个产业降低他们的信息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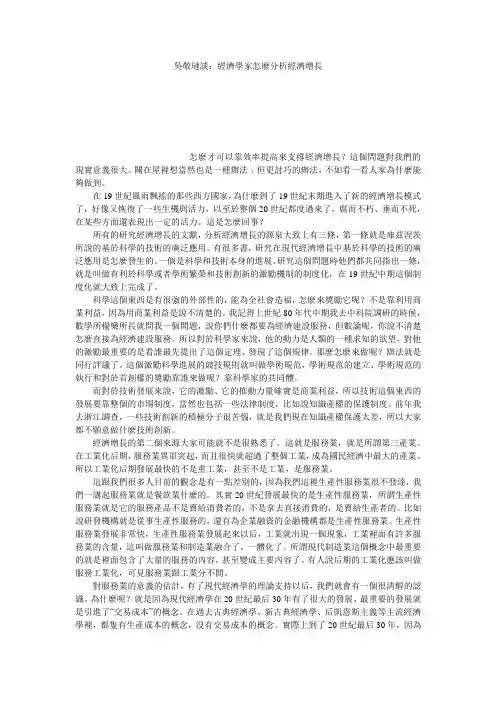
吳敬璉談:經濟學家怎麼分析經濟增長怎麼才可以靠效率提高來支撐經濟增長?這個問題對我們的現實意義很大。
關在屋裡想當然也是一種辦法﹔但更討巧的辦法,不如看一看人家為什麼能夠做到。
在19世紀風雨飄搖的那些西方國家,為什麼到了19世紀末期進入了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了,好像又恢復了一些生機與活力,以至於整個20世紀都度過來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在某些方面還表現出一定的活力。
這是怎麼回事?所有的研究經濟增長的文獻,分析經濟增長的源泉大致上有三條,第一條就是庫茲涅茨所說的基於科學的技術的廣泛應用。
有很多書,研究在現代經濟增長中基於科學的技術的廣泛應用是怎麼發生的。
一個是科學和技術本身的進展。
研究這個問題時他們都共同指出一條,就是叫做有利於科學或者學術繁榮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的制度化,在19世紀中期這個制度化就大致上完成了。
科學這個東西是有很強的外部性的,能為全社會造福,怎麼來獎勵它呢?不是靠利用商業利益,因為用商業利益是說不清楚的。
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去中科院調研的時候,數學所楊樂所長就問我一個問題,說你們什麼都要為經濟建設服務,但數論呢,你說不清楚怎麼直接為經濟建設服務。
所以對於科學家來說,他的動力是人類的一種求知的欲望,對他的激勵最重要的是看誰最先提出了這個定理、發現了這個規律。
那麼怎麼來做呢?辦法就是同行評議了。
這個激勵科學進展的競技規則就叫做學術規范,學術規范的建立、學術規范的執行和對於首創權的獎勵靠誰來做呢?靠科學家的共同體。
而對於技術發展來說,它的激勵、它的推動力量確實是商業利益,所以技術這個東西的發展要靠整個的市場制度,當然也包括一些法律制度,比如說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
前年我去浙江調查,一些技術創新的積極分子很苦惱,就是我們現在知識產權保護太差,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做什麼技術創新。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來源大家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
這就是服務業,就是所謂第三產業。
在工業化后期,服務業異軍突起,而且很快就超過了整個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大的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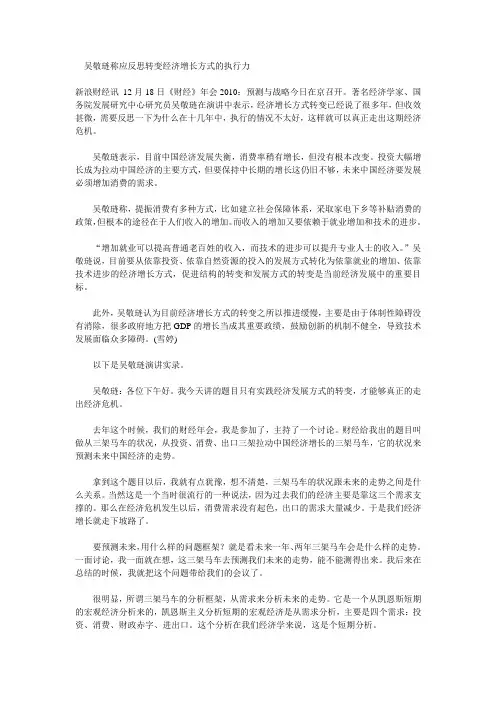
吴敬琏称应反思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执行力新浪财经讯12月18日《财经》年会2010:预测与战略今日在京召开。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演讲中表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说了很多年,但收效甚微,需要反思一下为什么在十几年中,执行的情况不太好,这样就可以真正走出这期经济危机。
吴敬琏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失衡,消费率稍有增长,但没有根本改变。
投资大幅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方式,但要保持中长期的增长这仍旧不够,未来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增加消费的需求。
吴敬琏称,提振消费有多种方式,比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采取家电下乡等补贴消费的政策,但根本的途径在于人们收入的增加。
而收入的增加又要依赖于就业增加和技术的进步。
“增加就业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而技术的进步可以提升专业人士的收入。
”吴敬琏说,目前要从依靠投资、依靠自然资源的投入的发展方式转化为依靠就业的增加、依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结构的转变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目标。
此外,吴敬琏认为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之所以推进缓慢,主要是由于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很多政府地方把GDP的增长当成其重要政绩,鼓励创新的机制不健全,导致技术发展面临众多障碍。
(雪婷)以下是吴敬琏演讲实录。
吴敬琏:各位下午好。
我今天讲的题目只有实践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真正的走出经济危机。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的财经年会,我是参加了,主持了一个讨论。
财经给我出的题目叫做从三架马车的状况,从投资、消费、出口三架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它的状况来预测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
拿到这个题目以后,我就有点犹豫,想不清楚,三架马车的状况跟未来的走势之间是什么关系。
当然这是一个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因为过去我们的经济主要是靠这三个需求支撑的。
那么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消费需求没有起色,出口的需求大量减少。
于是我们经济增长就走下坡路了。
要预测未来,用什么样的问题框架?就是看未来一年、两年三架马车会是什么样的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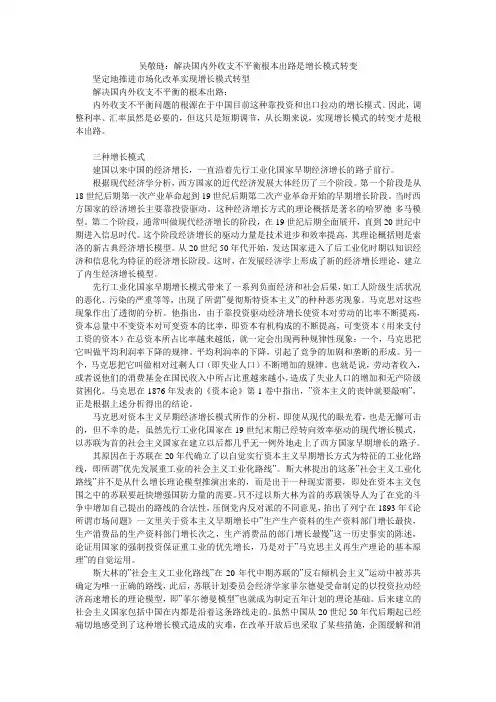
吴敬琏:解决国内外收支不平衡根本出路是增长模式转变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增长模式转型解决国内外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出路:内外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目前这种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
因此,调整利率、汇率虽然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短期调节,从长期来说,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才是根本出路。
三种增长模式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沿着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经济增长的路子前行。
根据现代经济学分析,西方国家的近代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起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的早期增长阶段。
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概括是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
第二个阶段,通常叫做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在19世纪后期全面展开,直到20世纪中期进入信息时代。
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其理论概括则是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
这时,在发展经济学上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经济和社会后果,如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污染的严重等等,出现了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种种恶劣现象。
马克思对这些现象作出了透彻的分析。
他指出,由于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使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在总资本所占比率越来越低,就一定会出现两种规律性现象:一个,马克思把它叫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引起了竞争的加剧和垄断的形成。
另一个,马克思把它叫做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
也就是说,劳动者收入,或者说他们的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和无产阶级贫困化。
马克思在1876年发表的《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正是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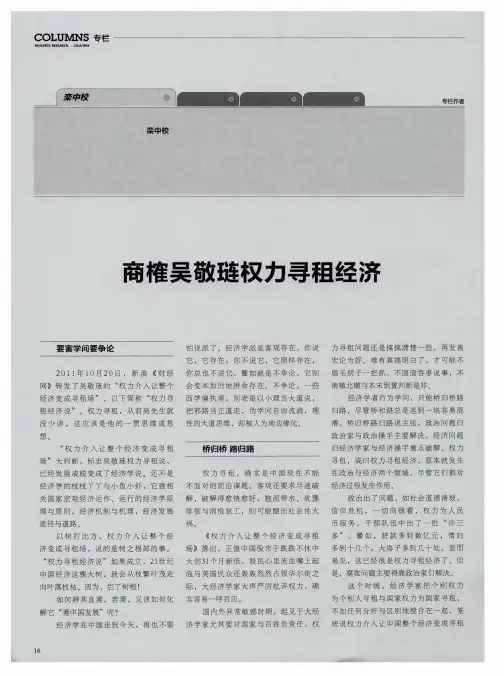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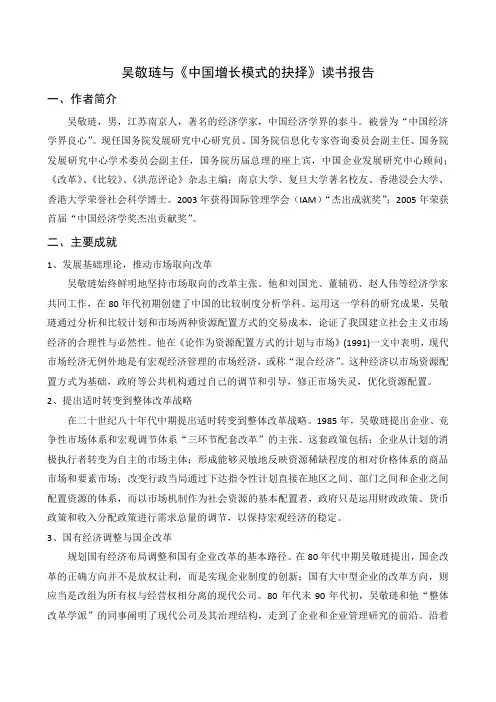
吴敬琏与《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读书报告一、作者简介吴敬琏,男,江苏南京人,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历届总理的座上宾,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二、主要成就1、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
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
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
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2、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
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3、国有经济调整与国企改革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
吴敬琏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经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很大成效;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
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国情和发展阶段,还取决于发展观。
在环境与资源的约束日渐严峻的今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为任务提出来呢?吴敬琏:首先,我们应当搞清楚“转变增长方式”问题的由来。
所谓经济增长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实行其在1959年党代表大会通过15年赶超美国的计划后,发现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但增长质量很差,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
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即增长方式有问题,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从60年代开始,苏联每个五年计划都包含转变增长方式内容,但是,直至苏联解体也未转过来。
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由留苏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引入此概念后,曾有过一段时期的讨论,但在政策上并没有实际举措,直至“九五”计划。
国家计委拟定“九五”计划时提出,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要从外延、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内涵方向转化。
中央吸取了苏联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教训,在制定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完善了计委的提法。
主持人: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给我们哪些启示?吴敬琏:了解人家的发展之路很有必要,但应警惕一些地方依据西方过时理论调整结构带来的严重后果。
萨缪尔森将工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发展道路和增长道路也分为三种。
其中,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以英国为主。
主要是依靠土地投入,局限性很大,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土地资源被完全占用后,经济无法再继续增长但19世纪经济起飞后,英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原因是经济增长靠的是物质资本投入,用机器代替人工,发展重工业。
吴敬琏教授如何误导中国的经济转型吴敬琏教授如何误导中国的经济转型曾飞吴敬琏教授引导国人说:“当前社会普遍将经济转型解释为由投资出口带动转变为由消费内需带动,这是一种误读。
经济转型的核心应是将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其实质是提高产品附加值。
”“唯一的出路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提高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这样也就同时提高了普通劳动者和白领的劳动价值与收入,否则消费不可能提高。
”(网易财经《吴敬琏:提高产品附加值是经济转型核心》)一句话,依照吴敬琏教授的逻辑,经济转型就是提高产品附加值。
似乎是只有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才能提高劳动收入,才能提高消费,才能由内需拉动经济。
什么是“产品附加值”呢?主要有两种理论界定。
一种是A.W.Rucker的界定:“由总销售额减掉原材料费、动力费、消耗品费后得到的附加值数值。
”附加值是由总销售额减去费用后的剩余。
M.R.Lehman的界定是劳动工资、资本利益和税收三部分之和。
以深圳的骄傲富士康公司所代工的苹果产品为例,富士康等给苹果代工的毛利仅2%。
iPad以499美金的价位在全球疯狂售卖,但iPad的零部件成本不足100美元。
16G的iPhone零部件费用大约是180美金,美国的售价为499美元。
苹果的毛利率大约在60%到70%之间。
iPad利润比iPhone还要高。
(来源: 人民网,《揭秘台湾富士康等给苹果代工企业:毛利仅2%》)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转型”,苹果产品如何“提高产品附加值”,富士康员工的劳动收入也不可能随之提高,中国的消费也不可能随之提高,也不可能随之由出口拉动经济转变成由内需拉动经济。
道理很简单,要分给富士康多少利益,完全决定于苹果的恩赐,而不决定于苹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
其关键在于“依附性经济”,而不在于“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的多少。
富士康员工眼下劳动收入的少量提高,是由于外界的压力,老板减少了自己“资本利益”所占份额的结果,根本不是苹果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结果。
反腐影响经济增长是个伪命题
作者:吴敬琏
来源:《创新科技》 2014年第9期
吴敬琏反腐影响经济增长是个伪命题
反腐的根本是要建立制度,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
从改革获得利益的人,并不会顽强的阻
挡进一步的改革。
可能有思想上不能适应时代的想法,真正会阻碍进一步改革的人,就是特殊
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既得利益来自于哪里,不是来自于市场化的改革,而是来自于不改革,
也就是说这种利益来自于权力寻租。
当我们进一步要实行市场化和法制化,就侵犯了他们的
“命根子”。
不可避免的,其中一部分人就会阻碍改革,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反腐的根本是要建立制度,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汽车牌照往往
就要由交通部门发牌,这就会产生寻租。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办法就是公开拍卖,另一个办法
就是将行政干预的范围缩到很小的范围之后进行严格监控,把它关在法制的笼子里。
有人认为,反腐会影响经济发展。
我想引用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说法,他说这是一个伪命题,比如从北京的情况看,有一些印证。
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在北京不少高档餐厅关门,但是中档
和低档的消费现在发展得非常快,很繁荣。
以至于过去一些豪华的消费也降格了,适应大众的
需求。
吴敬琏:中国经济结构如何过渡到新常态作者:来源:《财经界》2015年第12期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
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政府去调结构往往加剧资源误配优化经济结构问题是在20年前正式提出的。
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一个“九五”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优化产业结构。
“九五”建议提出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十五”计划期间,又出现了回潮。
“十五”计划提出的产业结构跟“九五”计划的要求有一点逆向,就是进一步强化了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化工业,鼓励大规模地投资。
这个结构扭曲,不仅是三个产业结构上的扭曲,更深入的问题是投资和消费失衡,投资率超过了所有历史阶段的高度。
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这个讨论。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6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会议。
论坛上,大家一致同意内外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很严重。
内部经济最主要的失衡,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外部经济的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外汇存底超常的增加。
结构失衡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说法和做法。
“九五”计划的建议里提了一个应对问题的路子,叫做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向集约型的增长;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第二个根本转变是实现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制度基础。
“九五”计划执行得不错,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结构优化都有一定的推进。
可是“十五”计划期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投资率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一业独大更加突出,所以制定“十一五”的时候又重新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型和结构优化的问题。
各界人士讨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不如意的原因。
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增长体制性障碍,主要是政府拥有过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把GDP增长速度看作衡量政绩的标准。
“十一五”规划重申要靠改革打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皇甫平对话吴敬琏:20年来经济处于半统制半市场状态解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路线,在开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重要一夜。
30年中国的经济成长成绩斐然,同时舆论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年前改革鼓吹手,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作客《震海听风录》,梳理分析过去20年中国的成就与问题。
(编者注:1991年2月-4月期间周瑞金组织撰写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最新指示精神。
这4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有关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讲话系列节目的第二部分周瑞金对话吴敬琏。
如果说上一部分大家看到的是有关南巡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尤其是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细节,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周瑞金先生和吴敬琏先生的一个详细的对话,来充分的梳理、提炼过去20年中国的成功与某些的失误,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个短篇。
解说:距离邓小平南巡已经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达到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道路可以归纳成为一种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在近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令中国持续稳定发展,还有供其他国家参考的价值。
不过在20年改革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国进民退,征地纠纷,贪污问题,社会群体事件等等,在国内各地层出不穷,期待社会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希望改革能够继续贯彻,成为舆论的焦点。
就此,中国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小康社会等社会改革目标,希望为社会层面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有学者认为,现今的中国社会急需重新凝聚共识,坚定改革的步伐,才能确保经济改革的持续发展和转型。
邱震海:好,正如节目开头我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除了周瑞金先生之外,还有吴敬琏先生,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二位嘉宾的一个情况介绍。
解说: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与吴敬琏商榷“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
吴敬琏先生在《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人民网》等主流媒体发表了数篇文章——“经济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论述经济增长的来源,几篇稿子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基本意思相同,无非是说“科技、服务业、信息业,三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我从“小猪派”的“产经联”理论出发,认为吴先生的结论比较粗糙,犯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错误,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好坏不分”的指导性意见,特此做出以下分析,向吴老讨教一下,希望吴老回应。
所谓经济增长,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物品生产的增长,一种是经济交易金额的增长,因此,“国民生产”和“国民经济(交换)”是有差别的两个概念。
有的“生产”不是经济,比如农民生产的用于自己食用的粮食;有的“经济”不是生产,比如餐饮业的服务,保姆的家政工业,股市上的买卖,期货的买卖。
以前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学的主要指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市场化以后用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数值之间的内涵差异巨大。
工农业生产总值统计计算的目标是物,媒、钢、油、棉等多少多少吨,国内生产总值统计计算的目标是钱,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是物品数量的大幅增长,到了今天市场经济的建设成就就是钱的高额数值,人民银行存了多少多少钱。
为了让人民银行多存点美元,中国可以把国家的重工业支柱工厂卖掉换钱,这叫“引进战略投资者”,还可以把国家工商银行等廉价卖掉股权,换取美元货币的存储增加,这些“重钱不重物”现象就是改革开放的误区。
吴文说,“所有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大致上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库兹涅茨所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来源大家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
这就是服务业,就是所谓第三产业。
……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来源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信息化。
”吴先生所谓的科学技术、服务业、信息业三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论述经济增长具有三个成因,您分清楚这三个成因的所在领域差别了吗?如果说这三个成因就是经济增长源泉,这个分析也太表面化了,难道制造业、交通业、娱乐业难道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了,芜湖市当前是靠奇瑞汽车制造业增长的,石家庄历史上是京汉铁路和石太铁路交汇从农村增长为城市的,拉斯维加斯是靠赌博娱乐业增长的。
按照吴敬琏所说的科学技术、服务业、信息业三种“增长”拉动,是具有不同行业效果的,科学技术领域发展拉动的多是生产性增长,比如能源、材料、交通等行业多需要科学技术的创新飞越来拉动生产能力;而服务业发展多拉动的是交易性增长,如第三产业的餐饮、娱乐、传媒等行业的增长多属于商业交易的增长,这些行业在具体生产方面往往不增加物品产出,而只是增加了“经济交易”。
当代信息产业的兴盛于全世界,源于个人计算机PC和互联网的诞生,因此信息产业有两个分支“传媒信息和科技信息”,因此信息产业的两个分支拉动了两个产业方向的发展,一是传统领域的信息化技术改造,二是传媒领域的新型媒体信息,前者是生产性增长,后者是交易性增长。
所谓“党中央提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吴文望文生义的原话),本质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原来运行模式的优化,优化带来了工业化的效率,进而带来了生产的增长,比如电力系统中的SCADA系统就是最典型的电力信息化。
为什么吴先生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从不分析不同行业增长的拉动效果,而现在我们的民族产业经济学需要分析行业差异呢?这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历史现象决定的,由于当代中国出现了“空心GDP”、“血汗GDP”现象,增长货币价值,不增长国家实力,也不增长民众
福利,因此就必须区分好的经济增长和坏的经济增长。
苏州地区的经济就是一个代表,GDP 快速增长而GNP(人均消费)十年来不增长,这就是坏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就是增长领域里面,只有经济交易的增长,而没有本土民众福利和消费物品生产的增长,或者说本国消费物品的生产增长比重过少。
而好的经济增长呢?就是带来全人类和全中国人民福利的共同提高。
因此,在吴先生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结论当中,就分不清楚什么是好的增长,什么是坏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江湖上人称“吴市场”所误导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
科技行业拉动的增长既有提高传统产业效率的,也有淘汰就业人数的问题,服务业中金融服务业拉动的增长有时可以掏空制造业需要的资金,信息业拉动的传媒增长没有带来更多的物质产出。
所谓“科技、服务业、信息业,三者拉动增长”实在是一笔“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糊涂账”!
分不清经济增长的好和坏,中国的GDP增长到底是世界第四,还是世界第六,就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方法和联合国接轨也没有意义。
加上尚未计算在内的几千个亿娼妓业交易值,也许中国经济规模就是世界GDP第二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没有关系,和民众福利也没有关系,这些结论请吴先生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