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蛇故事中法海的形象变迁》
- 格式:doc
- 大小:142.00 KB
- 文档页数: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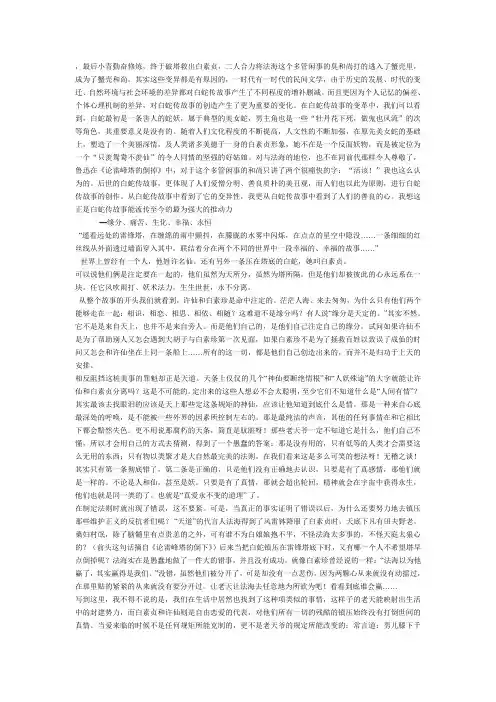
,最后小青勤奋修炼,终于破塔救出白素贞,二人合力将法海这个多管闲事的臭和尚打的逃入了蟹壳里,成为了蟹壳和尚。
其实这些变异都是有原因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民间文学,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都对白蛇传故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增补删减。
而且更因为个人记忆的偏差、个体心理机制的差异,对白蛇传故事的创造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变化。
在白蛇传故事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到,白蛇最初是一条害人的蛇妖,属于典型的美女蛇,男主角也是一些“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次等角色,其重要意义是没有的。
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文性的不断加强,在原先美女蛇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美丽深情,及人类诸多美德于一身的白素贞形象,她不在是一个反面妖物,而是被定位为一个“只羡鸳鸯不羡仙”的令人同情的坚强的好姑娘。
对与法海的地位,也不在同前代那样令人尊敬了,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对于这个多管闲事的和尚只讲了两个很痛快的字:“活该!”我也这么认为的。
后世的白蛇传故事,更体现了人们爱憎分明、善良质朴的美丑观,而人们也以此为原则,进行白蛇传故事的创作。
从白蛇传故事中看到了它的变异性,我更从白蛇传故事中看到了人们的善良的心。
我想这正是白蛇传故事能流传至今的最为强大的推动力—缘分、痛苦、生化、幸福、永恒“遥看远处的雷锋塔,在缠绵的雨中颤抖,在朦胧的水雾中闪烁,在点点的星空中隐没……一条细细的红丝线从外面透过墙面穿入其中,联结着分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段幸福的、幸福的故事……”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他姓许名仙。
还有另外一条压在塔底的白蛇,她叫白素贞。
可以说他们俩是注定要在一起的,他们虽然为天所分,虽然为塔所隔。
但是他们却被彼此的心永远系在一块。
任它风吹雨打、妖术法力,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从整个故事的开头我们就看到,许仙和白素珍是命中注定的。
茫茫人海、来去匆匆,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能够走在一起:相识,相恋、相思、相依、相随?这难道不是缘分吗?有人说“缘分是天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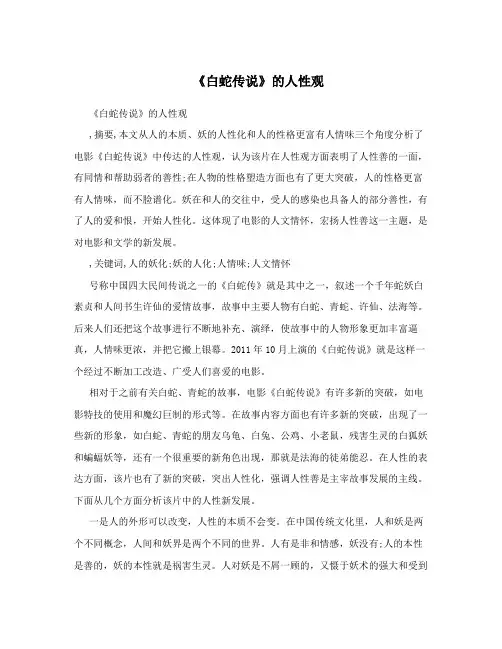
《白蛇传说》的人性观《白蛇传说》的人性观,摘要,本文从人的本质、妖的人性化和人的性格更富有人情味三个角度分析了电影《白蛇传说》中传达的人性观,认为该片在人性观方面表明了人性善的一面,有同情和帮助弱者的善性;在人物的性格塑造方面也有了更大突破,人的性格更富有人情味,而不脸谱化。
妖在和人的交往中,受人的感染也具备人的部分善性,有了人的爱和恨,开始人性化。
这体现了电影的人文情怀,宏扬人性善这一主题,是对电影和文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人的妖化;妖的人化;人情味;人文情怀号称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白蛇传》就是其中之一,叙述一个千年蛇妖白素贞和人间书生许仙的爱情故事,故事中主要人物有白蛇、青蛇、许仙、法海等。
后来人们还把这个故事进行不断地补充、演绎,使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逼真,人情味更浓,并把它搬上银幕。
2011年10月上演的《白蛇传说》就是这样一个经过不断加工改造、广受人们喜爱的电影。
相对于之前有关白蛇、青蛇的故事,电影《白蛇传说》有许多新的突破,如电影特技的使用和魔幻巨制的形式等。
在故事内容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突破,出现了一些新的形象,如白蛇、青蛇的朋友乌龟、白兔、公鸡、小老鼠,残害生灵的白狐妖和蝙蝠妖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角色出现,那就是法海的徒弟能忍。
在人性的表达方面,该片也有了新的突破,突出人性化,强调人性善是主宰故事发展的主线。
下面从几个方面分析该片中的人性新发展。
一是人的外形可以改变,人性的本质不会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和妖是两个不同概念,人间和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人有是非和情感,妖没有;人的本性是善的,妖的本性就是祸害生灵。
人对妖是不屑一顾的,又慑于妖术的强大和受到的迫害,人对妖一直持有厌恶、恐惧的心理。
这样,人和妖两重天,本是水火不容的两个世界。
但在《白蛇传说》这部电影里,法海的徒弟能忍追随法海多年,已从法海那学来一身降魔捉妖的好本领,也誓从师父除妖安民。
没想到在同蝙蝠妖的一场恶战中,能忍竟然被蝙蝠妖咬伤,中了妖毒,渐渐地变成了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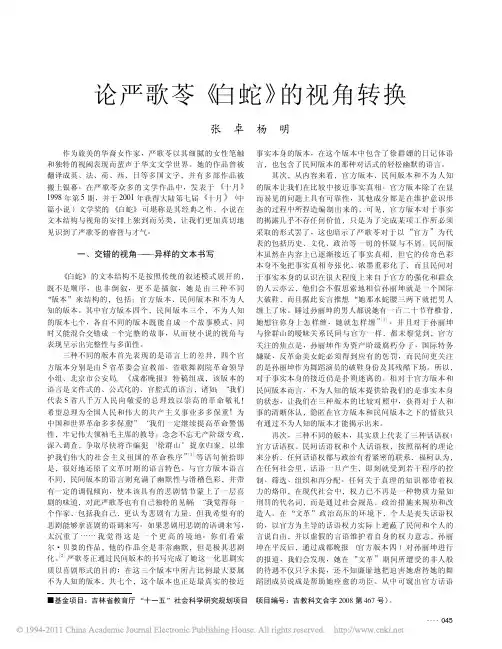
(045)论严歌苓《白蛇》的视角转换张卓杨明■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08第467号)。
作为旅美的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以其细腻的女性笔触和独特的视阈表现而蜚声于华文文学世界。
她的作品曾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并有多部作品被搬上银幕。
在严歌苓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发表于《十月》1998年第5期,并于2001年获得大陆第七届《十月》(中篇小说)文学奖的《白蛇》可堪称是其经典之作,小说在文本结构与视角的安排上独到而另类,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见识到了严歌苓的睿智与才气。
一、交错的视角———异样的文本书写《白蛇》的文本结构不是按照传统的叙述模式展开的,既不是顺序,也非倒叙,更不是插叙,她是由三种不同“版本”来结构的,包括:官方版本、民间版本和不为人知的版本。
其中官方版本四个,民间版本三个,不为人知的版本七个,各自不同的版本既能自成一个故事模式,同时又能混合交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而使小说的视角与表现呈示出完整性与多面性。
三种不同的版本首先表现的是语言上的差异,四个官方版本分别是由S 省革委会宣教部、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北京市公安局、《成都晚报》特稿组成,该版本的语言是文件式的、公式化的、官腔式的语言,诸如:“我们代表S 省八千万人民向敬爱的总理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希望总理为全国人民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多多保重!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多多保重!”“我们一定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深入调查,争取尽快将诈骗犯‘徐群山’捉拿归案,以维护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秩序”[1]等语句俯拾即是,很好地还原了文革时期的语言特色。
与官方版本语言不同,民间版本的语言则充满了幽默性与滑稽色彩,并带有一定的调侃倾向,使本该具有的悲剧情节蒙上了一层喜剧的味道,对此严歌苓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觉得每一个作家,包括我自己,更认为悲剧有力量,但我希望有的悲剧能够拿喜剧的语调来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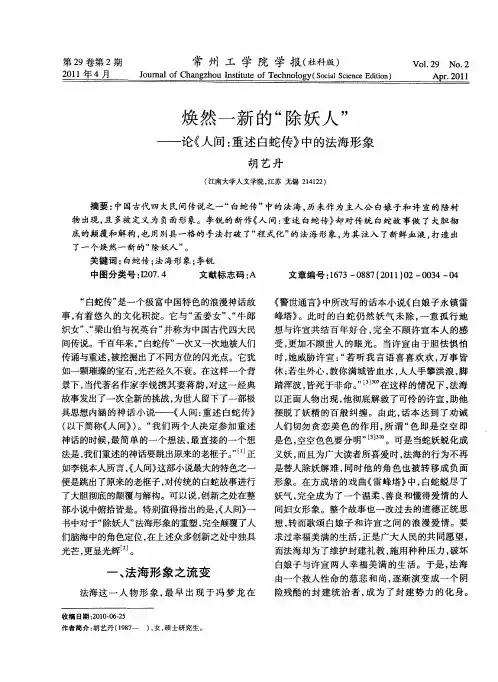

白蛇传中的法海善恶与正义的斗争江南小镇上,有一个名叫许仙的年轻人,一日,他在湖边救下一只受伤的白蛇。
白蛇便化做一个仙女,名叫白娘子,和许仙相爱并结为夫妻。
他们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法海的出现。
法海,是个称职的和尚,他信奉佛教,一心维护正义。
看到白蛇与许仙之间的爱情,他心生厌恶。
法海认为白娘子的化身不过是个妖怪,不可能有真正的情感。
于是,他决定以佛法为武器,将白蛇赶走。
与白蛇不同,法海的信念是善与正义。
在他看来,白蛇的存在是邪恶的,是破坏人间和谐的力量。
因此,他将自己视为人间的守护者,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清除邪恶。
然而,当法海开始与白娘子斗争时,他渐渐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
白蛇是一个拥有感情的生物,她与许仙之间的爱情是真实而深刻的。
法海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是否真的可以决定别人的幸福?在白蛇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法海的内心斗争。
他是善良的,他希望维护正义,但他又不希望伤害无辜的人。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为何佛教意味着排除与妖怪之间的真爱。
他是否应该选择宽容和善良,给予白蛇与许仙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种善恶与正义的斗争也体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道德与正义的选择。
有时,我们的信念可能与他人相悖,但我们是否要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立场呢?还是应该更加审慎地思考,尊重他人的选择,给予他人一些空间和宽容呢?就像法海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到,善恶是相对的,正义也不是唯一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我们不能因为与自己的不同而将其排斥。
相反,我们应该尝试理解他人,尊重他人的选择,为一个充满包容和宽容的社会做出贡献。
回到白蛇传,最终,法海还是选择了宽容和善良。
他意识到,爱情是伟大的,它能够消除恶意和仇恨。
法海选择放过白蛇与许仙,并祝福他们的幸福。
这是一个印证了人性尊严和价值的选择,也是一个赞美了善与正义的胜利。
在白蛇传中,法海善恶与正义的斗争并非简单的是非对错。
它给我们带来了对人性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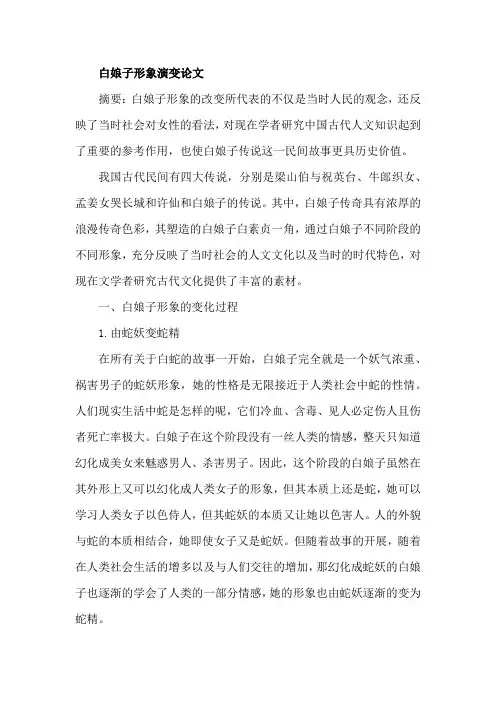
白娘子形象演变论文摘要:白娘子形象的改变所代表的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观念,还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对现在学者研究中国古代人文知识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也使白娘子传说这一民间故事更具历史价值。
我国古代民间有四大传说,分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和许仙和白娘子的传说。
其中,白娘子传奇具有浓厚的浪漫传奇色彩,其塑造的白娘子白素贞一角,通过白娘子不同阶段的不同形象,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文文化以及当时的时代特色,对现在文学者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白娘子形象的变化过程1.由蛇妖变蛇精在所有关于白蛇的故事一开始,白娘子完全就是一个妖气浓重、祸害男子的蛇妖形象,她的性格是无限接近于人类社会中蛇的性情。
人们现实生活中蛇是怎样的呢,它们冷血、含毒、见人必定伤人且伤者死亡率极大。
白娘子在这个阶段没有一丝人类的情感,整天只知道幻化成美女来魅惑男人、杀害男子。
因此,这个阶段的白娘子虽然在其外形上又可以幻化成人类女子的形象,但其本质上还是蛇,她可以学习人类女子以色侍人,但其蛇妖的本质又让她以色害人。
人的外貌与蛇的本质相结合,她即使女子又是蛇妖。
但随着故事的开展,随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增多以及与人们交往的增加,那幻化成蛇妖的白娘子也逐渐的学会了人类的一部分情感,她的形象也由蛇妖逐渐的变为蛇精。
2.由蛇精变蛇仙蛇精与蛇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蛇妖是有害人之心的,而蛇精则是没有害人之心。
随着故事的开展,随着白娘子与一凡人男子感情的发展,白娘子也由一个只知以美色害人的蛇妖变为了一个没有了害人之心的痴情于男主的蛇精。
在这一个过程中,笔者赋予了白娘子为爱坚强的性格以及向往自由最求幸福的美好愿望。
不过在这个时期,白娘子的形象转变还不够彻底,属于蛇妖的那部分性格还会时不时的出现,蛇妖的本性对白娘子的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她还是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沉迷于和男主的色欲以及爱情中。
因此,这个时期的白娘子虽说谈不上人人喜爱,但也不会遭到人们的厌恶,人们对这一时期的白娘子的形象是喜爱与讨厌参半,有时还会可怜这个陷入爱情的白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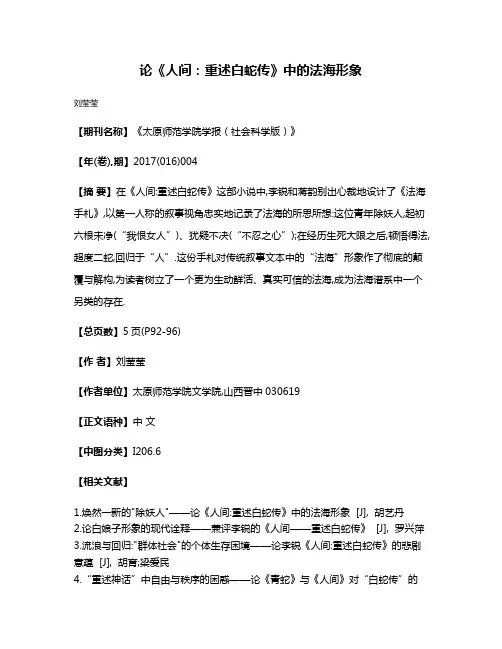
论《人间:重述白蛇传》中的法海形象
刘莹莹
【期刊名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16)004
【摘要】在《人间:重述白蛇传》这部小说中,李锐和蒋韵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法海手札》,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忠实地记录了法海的所思所想:这位青年除妖人,起初六根未净(“我恨女人”)、犹疑不决(“不忍之心”);在经历生死大限之后,顿悟得法,超度二蛇,回归于“人”.这份手札对传统叙事文本中的“法海”形象作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为读者树立了一个更为生动鲜活、真实可信的法海,成为法海谱系中一个另类的存在.
【总页数】5页(P92-96)
【作者】刘莹莹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晋中03061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焕然一新的"除妖人"——论《人间:重述白蛇传》中的法海形象 [J], 胡艺丹
2.论白娘子形象的现代诠释——兼评李锐的《人间——重述白蛇传》 [J], 罗兴萍
3.流浪与回归:"群体社会"的个体生存困境——论李锐《人间:重述白蛇传》的悲剧意蕴 [J], 胡育;梁爱民
4.“重述神话”中自由与秩序的困惑——论《青蛇》与《人间》对“白蛇传”的
“神话重述” [J], 李小娟
5.从排斥异己到自我救赎——评李锐、蒋韵长篇小说《人间:重述白蛇传》 [J], 宋睿;李传友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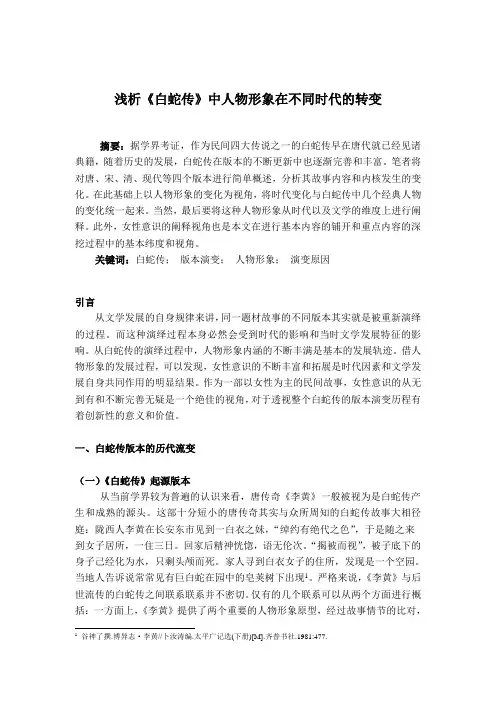
浅析《白蛇传》中人物形象在不同时代的转变摘要:据学界考证,作为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早在唐代就已经见诸典籍,随着历史的发展,白蛇传在版本的不断更新中也逐渐完善和丰富。
笔者将对唐、宋、清、现代等四个版本进行简单概述,分析其故事内容和内核发生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以人物形象的变化为视角,将时代变化与白蛇传中几个经典人物的变化统一起来。
当然,最后要将这种人物形象从时代以及文学的维度上进行阐释。
此外,女性意识的阐释视角也是本文在进行基本内容的铺开和重点内容的深挖过程中的基本纬度和视角。
关键词:白蛇传;版本演变;人物形象;演变原因引言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讲,同一题材故事的不同版本其实就是被重新演绎的过程。
而这种演绎过程本身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当时文学发展特征的影响。
从白蛇传的演绎过程中,人物形象内涵的不断丰满是基本的发展轨迹。
借人物形象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女性意识的不断丰富和拓展是时代因素和文学发展自身共同作用的明显结果。
作为一部以女性为主的民间故事,女性意识的从无到有和不断完善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视角,对于透视整个白蛇传的版本演变历程有着创新性的意义和价值。
一、白蛇传版本的历代流变(一)《白蛇传》起源版本从当前学界较为普遍的认识来看,唐传奇《李黄》一般被视为是白蛇传产生和成熟的源头。
这部十分短小的唐传奇其实与众所周知的白蛇传故事大相径庭:陇西人李黄在长安东市见到一白衣之妹,“绰约有绝代之色”,于是随之来到女子居所,一住三日。
回家后精神恍惚,语无伦次。
“揭被而视”,被子底下的身子己经化为水,只剩头颅而死。
家人寻到白衣女子的住所,发现是一个空园。
当地人告诉说常常见有巨白蛇在园中的皂荚树下出现1。
严格来说,《李黄》与后世流传的白蛇传之间联系联系并不密切。
仅有的几个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概括:一方面上,《李黄》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原型,经过故事情节的比对,1谷神了撰.博异志·李黄//卜汝涛编.太平广记选(下册)[M].齐普书社.1981:477.李黄可以看做是后来的许仙的原型,相对的,那位白衣女子就是后世的白娘子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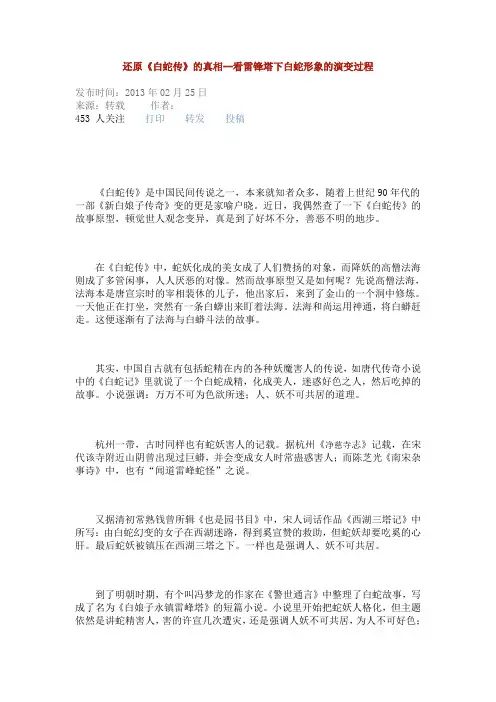
还原《白蛇传》的真相--看雷锋塔下白蛇形象的演变过程发布时间:2013年02月25日来源:转载作者:453 人关注打印转发投稿《白蛇传》是中国民间传说之一,本来就知者众多,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一部《新白娘子传奇》变的更是家喻户晓。
近日,我偶然查了一下《白蛇传》的故事原型,顿觉世人观念变异,真是到了好坏不分,善恶不明的地步。
在《白蛇传》中,蛇妖化成的美女成了人们赞扬的对象,而降妖的高僧法海则成了多管闲事,人人厌恶的对像。
然而故事原型又是如何呢?先说高僧法海,法海本是唐宣宗时的宰相裴休的儿子,他出家后,来到了金山的一个洞中修炼。
一天他正在打坐,突然有一条白蟒出来盯着法海。
法海和尚运用神通,将白蟒赶走。
这便逐渐有了法海与白蟒斗法的故事。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包括蛇精在内的各种妖魔害人的传说,如唐代传奇小说中的《白蛇记》里就说了一个白蛇成精,化成美人,迷惑好色之人,然后吃掉的故事。
小说强调:万万不可为色欲所迷;人、妖不可共居的道理。
杭州一带,古时同样也有蛇妖害人的记载。
据杭州《净慈寺志》记载,在宋代该寺附近山阴曾出现过巨蟒,并会变成女人时常蛊惑害人;而陈芝光《南宋杂事诗》中,也有“闻道雷峰蛇怪”之说。
又据清初常熟钱曾所辑《也是园书目》中,宋人词话作品《西湖三塔记》中所写:由白蛇幻变的女子在西湖迷路,得到奚宣赞的救助,但蛇妖却要吃奚的心肝。
最后蛇妖被镇压在西湖三塔之下。
一样也是强调人、妖不可共居。
到了明朝时期,有个叫冯梦龙的作家在《警世通言》中整理了白蛇故事,写成了名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短篇小说。
小说里开始把蛇妖人格化,但主题依然是讲蛇精害人,害的许宣几次遭灾,还是强调人妖不可共居,为人不可好色;法海和尚依然是正面人物。
在这里我只引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结尾部分,大家一看即知。
许宣游玩西湖遇着美女白娘子,因执于色欲,便结为夫妻。
但白娘子乃蛇精所化,多次给许宣带来祸害。
许宣从高僧法海禅师处知道白娘子乃蛇妖后,便坚决要求除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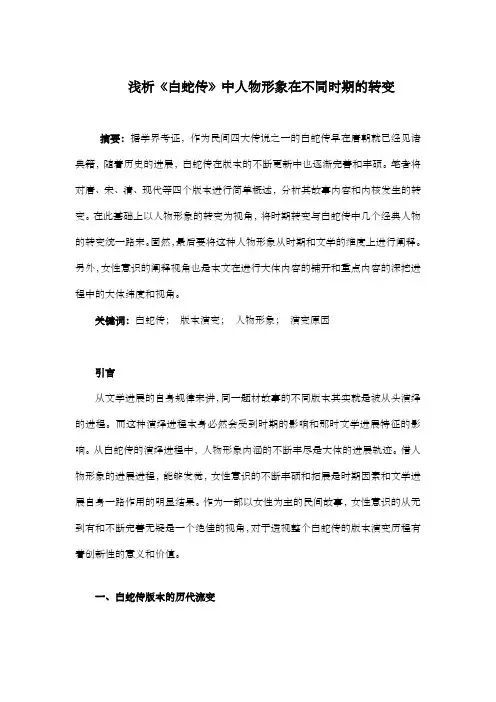
浅析《白蛇传》中人物形象在不同时期的转变摘要:据学界考证,作为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早在唐朝就已经见诸典籍,随着历史的进展,白蛇传在版本的不断更新中也逐渐完善和丰硕。
笔者将对唐、宋、清、现代等四个版本进行简单概述,分析其故事内容和内核发生的转变。
在此基础上以人物形象的转变为视角,将时期转变与白蛇传中几个经典人物的转变统一路来。
固然,最后要将这种人物形象从时期和文学的维度上进行阐释。
另外,女性意识的阐释视角也是本文在进行大体内容的铺开和重点内容的深挖进程中的大体纬度和视角。
关键词:白蛇传;版本演变;人物形象;演变原因引言从文学进展的自身规律来讲,同一题材故事的不同版本其实就是被从头演绎的进程。
而这种演绎进程本身必然会受到时期的影响和那时文学进展特征的影响。
从白蛇传的演绎进程中,人物形象内涵的不断丰尽是大体的进展轨迹。
借人物形象的进展进程,能够发觉,女性意识的不断丰硕和拓展是时期因素和文学进展自身一路作用的明显结果。
作为一部以女性为主的民间故事,女性意识的从无到有和不断完善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视角,对于透视整个白蛇传的版本演变历程有着创新性的意义和价值。
一、白蛇传版本的历代流变(一)《白蛇传》起源版本从当前学界较为普遍的熟悉来看,唐传奇《李黄》一般被视为是白蛇传产生和成熟的源头。
这部十分短小的唐传奇其实与众所周知的白蛇传故事截然不同:陇西人李黄在长安东市见到一白衣之妹,“绰约有旷世之色”,于是随之来到女子居所,一住三日。
回家后精神恍忽,语无伦次。
“揭被而视”,被子底下的身子己经化为水,只剩头颅而死。
家人寻到白衣女子的居处,发觉是一个空园。
本地人告知说常常见有巨白蛇在园中的皂荚树下出现1。
严格来讲,《李黄》与后世流传的白蛇传之间联系联系并非紧密。
仅有的几个联系能够从两个方面进行归纳:一方面上,《李黄》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原型,通过故情形节的比对,李黄能够看做是后来的许仙的原型,相对的,那位白衣女子就是后世的白娘子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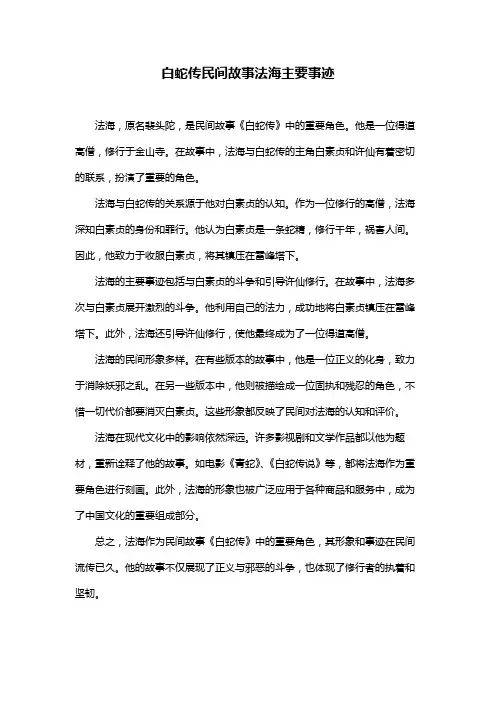
白蛇传民间故事法海主要事迹
法海,原名裴头陀,是民间故事《白蛇传》中的重要角色。
他是一位得道高僧,修行于金山寺。
在故事中,法海与白蛇传的主角白素贞和许仙有着密切的联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法海与白蛇传的关系源于他对白素贞的认知。
作为一位修行的高僧,法海深知白素贞的身份和罪行。
他认为白素贞是一条蛇精,修行千年,祸害人间。
因此,他致力于收服白素贞,将其镇压在雷峰塔下。
法海的主要事迹包括与白素贞的斗争和引导许仙修行。
在故事中,法海多次与白素贞展开激烈的斗争。
他利用自己的法力,成功地将白素贞镇压在雷峰塔下。
此外,法海还引导许仙修行,使他最终成为了一位得道高僧。
法海的民间形象多样。
在有些版本的故事中,他是一位正义的化身,致力于消除妖邪之乱。
在另一些版本中,他则被描绘成一位固执和残忍的角色,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消灭白素贞。
这些形象都反映了民间对法海的认知和评价。
法海在现代文化中的影响依然深远。
许多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都以他为题材,重新诠释了他的故事。
如电影《青蛇》、《白蛇传说》等,都将法海作为重要角色进行刻画。
此外,法海的形象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商品和服务中,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法海作为民间故事《白蛇传》中的重要角色,其形象和事迹在民间流传已久。
他的故事不仅展现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也体现了修行者的执着和坚韧。
白蛇传人物形象分析(3)二、白蛇:明朝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白》吸收了很多鲜活因素,反映了时代内容。
这时的白娘子真诚地爱着许宣,生活美满幸福。
但蛇妖总是妖怪,当面对许宣感情背叛时,白娘子拿杭州城内所有百姓的身家性命威胁许宣,整个话本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白娘子的决绝,但这也是其妖性的充分体现。
《雷峰塔》中的白娘子已经有了自己的名字白素贞,并且增加了极其重要的情节,“盗草”、“水斗”、“断桥”,完美了白娘子的性格形象。
这个时候的白娘子已经脱尽了妖气,完全成了善良的人。
李碧华的《青蛇》应该算是一个诡异的另类书写。
书中的白素贞虽然变成了人样,但一举一动仍不失蛇样,但也更像一个人。
白蛇在知道许仙懦弱、负情、狡猾的真面目后,还哀戚请求青蛇成全,只因她已经怀了他的孩子,这些给予了她在情感背叛时自欺欺人的极大讽刺。
《新白》中的白娘子已经成为百姓心中最完美女人的代名词,对小青情同手足,对许仙温柔体贴,对夫家亲戚尊敬谦让。
这时的白蛇形象也最具有人性化,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充分体现了当今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
三、青蛇:《白》中,丫鬟青青由乌鸡精变成了青鱼精,拉近了与白蛇的关系,但是着墨不多,甚至能说她可有可无,只是象征性地需要而已。
《雷峰塔》中青儿被定位成了青蛇精,更加拉近了与白蛇的关系。
她们虽为主仆,却情同手足。
性格上,一个温柔贤惠,一个嫉恶如仇。
白蛇传的故事到了李碧华笔下变得饶有新意,小青反客为主成为故事的主角。
这个版本中的小青是个天真直率、性格冲动、讲义气、有点任性懒散的妖精,她不了尘世,却是白素贞最忠实的姐妹,小青告戒素贞:“人类一朝比一朝差劲,一代比一代奸狡,再也没有真情义了——但我永远都有。
”这时的小青应该是一位先锋派人物,是一个至情至理干练干脆的女子。
与李碧华笔下的青蛇相比,《新白》中的小青就单纯可爱的多了,是一个有情有义、敢爱敢恨、忠心耿耿的形象,其率真活泼的性格与白娘子的妩媚温柔形成了鲜明对比。
法海的人物形象在同名电影和话剧《青蛇》之比较研究法海是经典神话故事《白蛇传》中的著名反派角色,他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也广为人知。
在同名电影和话剧《青蛇》中,法海的人物形象也得到了不同展现。
本文将对这两个版本中的法海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从外貌和形象上看,电影《青蛇》中的法海形象更加魁梧威猛。
他身着黑色僧衣,头戴僧帽,脸色黝黑,并且留有一把修长的胡须,整个人给人一种沉稳且充满威严的感觉。
与之相比,《青蛇》话剧中的法海形象则更加年轻、帅气。
他身穿红色袈裟,头戴金冠,面容清秀,举止轻盈,给人一种高雅狡黠之感。
两个版本中的法海形象都各具特色,根据不同的舞台效果,都能够唤起观众不同的视觉体验。
其次,在个性塑造上,《青蛇》电影中的法海更具阴险狡诈的特点。
他心机深沉,鬼计多端,对待白蛇一直心怀恶意,不断设法把她逼上绝境。
而话剧《青蛇》中的法海则更加善良正义。
他师法自然,对待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平和与保护。
他对待白蛇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帮助”白蛇走向正道的意图。
两个版本中的法海个性的不同,凸显了对于角色形象的不同演绎,使得观众能够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思考这一经典人物。
第三,从法海与其他角色的互动来看,《青蛇》电影中的法海与青蛇的关系更加紧张与矛盾。
青蛇对法海恨之入骨,一直设法对付法海;而法海则不惜动用手段来追捕青蛇,斩尽杀绝。
相比之下,《青蛇》话剧中的法海与青蛇的关系则更加复杂与纠结。
法海在对待青蛇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
他对待青蛇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和保护,尽管最后仍为了维持正义而选择了对抗青蛇。
无论是电影还是话剧,法海与青蛇之间的情感纠葛都是故事中最关键的一部分,也是观众最为关注的点之一。
最后,从故事结局来看,《青蛇》电影和话剧中的法海命运都截然不同。
电影中的法海最终被白蛇化解,而他的心机也被揭穿,最后被众人所唾弃。
而话剧中的法海则在白蛇的帮助下,逐步走向悔过与正义,最终放下屠刀而成为观世音菩萨的一员。
白蛇传读书笔记从小就听大人们讲过《白蛇传》的故事,那时候只觉得白素贞和许仙的爱情很凄美,法海很可恶。
最近重新读了这个故事,又有了许多不一样的感受。
在《白蛇传》中,白素贞本是一条修行千年的蛇妖,因感念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前来报恩。
她美丽、温柔、善良,与许仙在西湖边相遇,借伞定情,结为夫妻。
他们一起开了一家药店,治病救人,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然而,法海却认为人妖殊途,强行拆散了他们。
白素贞为了救许仙,水漫金山,最终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
白素贞和许仙的爱情让我感动不已。
他们的爱情不是那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而是细水长流、相濡以沫的。
白素贞为了许仙,甘愿放弃千年的修行,化作凡人,承受生老病死之苦。
她操持家务,照顾许仙的生活起居,还帮助他经营药店。
许仙也对白素贞一心一意,即使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也没有丝毫的嫌弃和害怕。
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纯粹和坚定,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记得有一次,许仙生病了,白素贞心急如焚。
她亲自熬药,守在许仙的床边,一刻也不敢离开。
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许仙的额头,眼中满是关切和担忧。
那眼神,仿佛能滴出水来,让人看了心里暖暖的。
她轻声地对许仙说:“相公,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我们还要一起过日子呢。
”许仙看着白素贞,虚弱地笑了笑,说:“娘子,有你在我身边,我一定会好起来的。
”白素贞听了,眼中闪烁着泪花,她紧紧地握住许仙的手,仿佛那是她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白素贞不仅对许仙深情款款,对周围的人也充满了爱心。
她经常免费为穷人看病,送药,深受百姓的爱戴。
有一次,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得了重病,没钱医治。
白素贞得知后,不仅亲自上门为孩子看病,还送了很多药。
孩子的父母感激涕零,要给白素贞下跪道谢。
白素贞连忙扶起他们,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孩子能好起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她的善良和慈悲,让人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
然而,法海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平静和美好。
法海固执地认为妖都是邪恶的,必须要被收服。
他不顾白素贞和许仙的爱情,强行将他们分开。
Fa Hai Image:Evolution and Its Causes 作者: 彭健[1]
作者机构: [1]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阳550025
出版物刊名: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98-104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6期
主题词: 白蛇故事;法海;演变;主流思潮;审美愿望
摘要:白蛇故事经历文本到影视的演绎,其中重要人物法海之形象,经历了正义的除妖人到虚伪的卫道者再到情欲化、世俗化降魔者之演变,完成了从模糊到单一再到复杂的形象转变。
究其成因,不仅是社会主流思潮影响的结果,同时还是接受主体审美心理和审美愿望在作品中的显现。
论法海与沙威形象的异同——解读《白蛇传》、《悲惨世界》董宗梅汉语言(教育)20092947摘要:由于民间传说及媒体的传播,法海的故事在人们看来是耳熟能详,而其形象也似乎早已定型,而沙威作为雨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之一,熟悉的人也不少。
这篇文章将把这两者进行对比比较,从中挖掘出他们人物形象的价值。
关键字:法海;沙威;异同;形象价值前言《白蛇传》与《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并称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而法海的存在是白素贞与许仙爱情的一大考验,所以他的形象一般都被定位为冷酷无情、多管闲事。
而沙威作为《悲惨世界》中主人翁冉•阿让纠缠一生的对手———警察,大多数的评议也都是集中在“残酷无情”“丑陋凶恶”“、忠实的鹰犬”、“黑暗统治秩序的死忠”、“政府的忠实走狗”等等道德和政治的鼓吹者上面。
但是很显然,法海和沙威的形象都远远并不只是这些。
一、法海与沙威的相同点身为僧人,并把降妖除魔作为己任的法海,与身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警察的沙威,在沙威的前期生活,他们对待他们的职责和信仰上是一致的——执法如山,且工作能力很强。
法海右握法杖,左端法钵,严肃端庄,以降妖除魔、维护社会治安为己责。
在他看来,妖不属于人间的范畴,必须在自己的疆界内恪守本分。
妖入人间,必然会打破人间生活的安宁,扰乱社会的合法秩序。
法海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嗅出妖气,甄别人妖,且法术高深并拥有如来钦赐的禅杖和法钵,在收妖的过程中几乎无往不胜,即使是有千年道行的白蛇都畏他三分。
作为一名肩负神界使命的人间执法者,降妖除魔是天职,必须尽己之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因此,法海对妖的态度是很决绝冷酷的——凡入人间的妖魔,必除之。
甚至偏执的认为凡是妖,皆须收复——“妖就是妖,没有善恶”。
雨果对沙威这一人物的形象描写是很出色的,“黑色的高筒礼帽永远齐眉戴在他的头上,而黑色衣服的高领子紧紧地围住他那短而粗的脖子,并将他那方形的下巴卡住,向上托起;帽檐又是那么宽,以至于即使一个人和他面对面地站着,也只能看到他的三分之一张脸———那双目光极其阴冷的眼睛和他那丑陋如狮虎的鼻子,还有那无疑会给人留下凶恶印象的方形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