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
- 格式:pdf
- 大小:2.49 MB
- 文档页数: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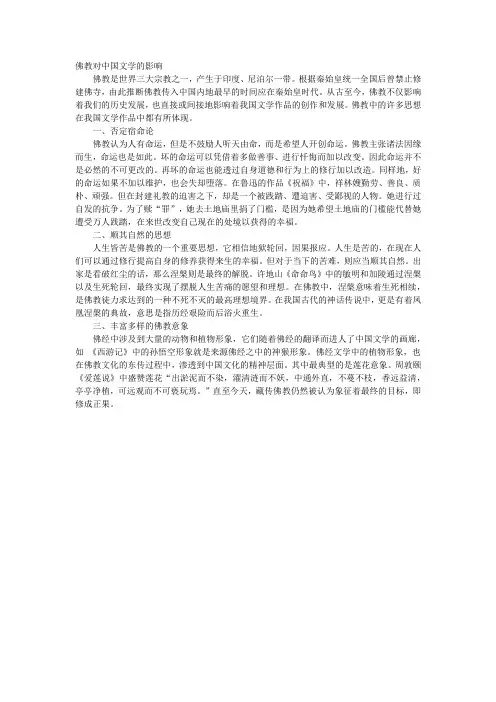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印度、尼泊尔一带。
根据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推断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早的时间应在秦始皇时代。
从古至今,佛教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
佛教中的许多思想在我国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一、否定宿命论佛教认为人有命运,但是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开创命运。
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命运也是如此。
坏的命运可以凭借着多做善事、进行忏悔而加以改变。
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
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自身道德和行为上的修行加以改造。
同样地,好的命运如果不加以维护,也会失却堕落。
在鲁迅的作品《祝福》中,祥林嫂勤劳、善良、质朴、顽强。
但在封建礼教的迫害之下,却是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的人物。
她进行过自发的抗争。
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是因为她希望土地庙的门槛能代替她遭受万人践踏,在来世改变自己现在的处境以获得的幸福。
二、顺其自然的思想人生皆苦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它相信地狱轮回,因果报应。
人生是苦的,在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修行提高自身的修养获得来生的幸福。
但对于当下的苦难,则应当顺其自然。
出家是看破红尘的话,那么涅槃则是最终的解脱。
许地山《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通过涅槃以及生死轮回,最终实现了摆脱人生苦痛的愿望和理想。
在佛教中,涅槃意味着生死相续,是佛教徒力求达到的一种不死不灭的最高理想境界。
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更是有着凤凰涅槃的典故,意思是指历经艰险而后浴火重生。
三、丰富多样的佛教意象佛经中涉及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它们随着佛经的翻译而进人了中国文学的画廊,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就是来源佛经之中的神猴形象。
佛经文学中的植物形象,也在佛教文化的东传过程中,渗透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
其中最典型的是莲花意象。
周敦颐《爱莲说》中盛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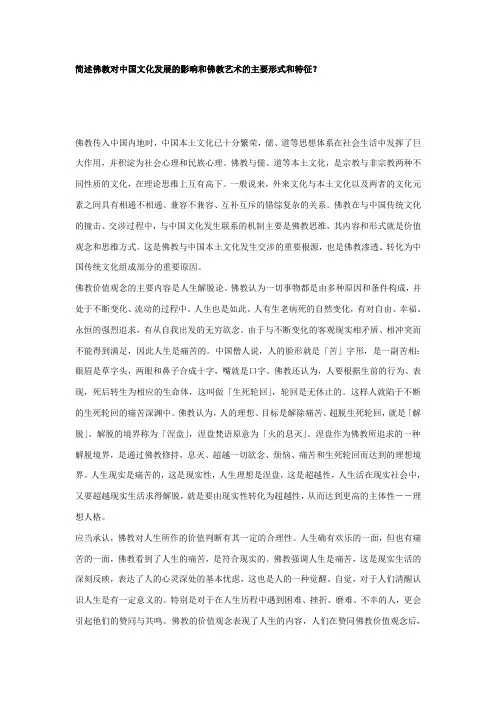
简述佛教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佛教艺术的主要形式和特征?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时,中国本土文化已十分繁荣,儒、道等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积淀为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
佛教与儒、道等本土文化,是宗教与非宗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在理论思维上互有高下。
一般说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以及两者的文化元素之间具有相通不相通、兼容不兼容、互补互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交涉过程中,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的机制主要是佛教思维,其内容和形式就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这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交涉的重要根源,也是佛教渗透、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
佛教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是人生解脱论。
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原因和条件构成,并处于不断变化、流动的过程中。
人生也是如此。
人有生老病死的自然变化,有对自由、幸福、永恒的强烈追求,有从自我出发的无穷欲念。
由于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相矛盾、相冲突而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人生是痛苦的。
中国僧人说,人的脸形就是「苦」字形,是一副苦相:眼眉是草字头,两眼和鼻子合成十字,嘴就是口字。
佛教还认为,人要根据生前的行为、表现,死后转生为相应的生命体,这叫做「生死轮回」,轮回是无休止的。
这样人就陷于不断的生死轮回的痛苦深渊中。
佛教认为,人的理想、目标是解除痛苦、超脱生死轮回,就是「解脱」。
解脱的境界称为「涅盘」,涅盘梵语原意为「火的息灭」。
涅盘作为佛教所追求的一种解脱境界,是通过佛教修持,息灭、超越一切欲念、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而达到的理想境界。
人生现实是痛苦的,这是现实性,人生理想是涅盘,这是超越性,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又要超越现实生活求得解脱,就是要由现实性转化为超越性,从而达到更高的主体性--理想人格。
应当承认,佛教对人生所作的价值判断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人生确有欢乐的一面,但也有痛苦的一面,佛教看到了人生的痛苦,是符合现实的。
佛教强调人生是痛苦,这是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表达了人的心灵深处的基本忧虑,这也是人的一种觉醒、自觉,对于人们清醒认识人生是有一定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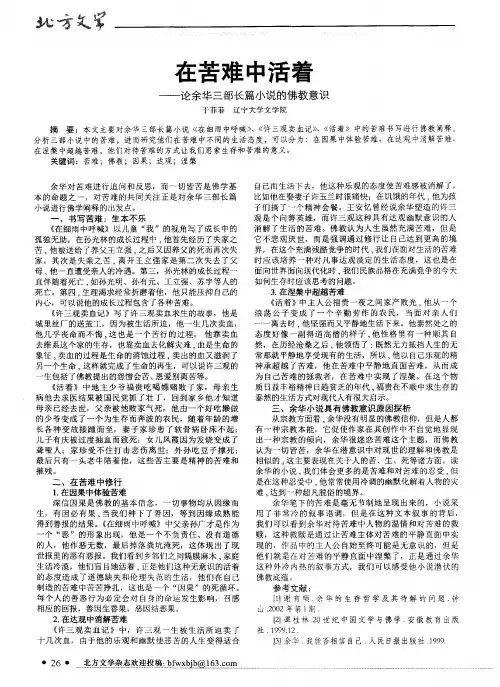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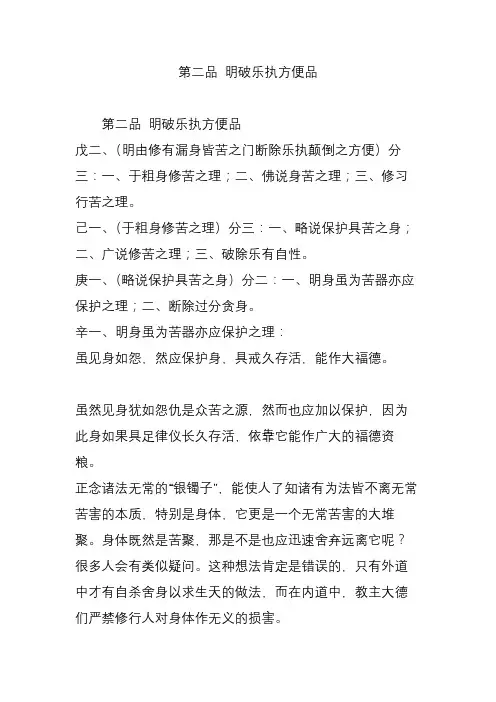
第二品明破乐执方便品第二品明破乐执方便品戊二、(明由修有漏身皆苦之门断除乐执颠倒之方便)分三:一、于粗身修苦之理;二、佛说身苦之理;三、修习行苦之理。
己一、(于粗身修苦之理)分三:一、略说保护具苦之身;二、广说修苦之理;三、破除乐有自性。
庚一、(略说保护具苦之身)分二:一、明身虽为苦器亦应保护之理;二、断除过分贪身。
辛一、明身虽为苦器亦应保护之理:虽见身如怨,然应保护身,具戒久存活,能作大福德。
虽然见身犹如怨仇是众苦之源,然而也应加以保护,因为此身如果具足律仪长久存活,依靠它能作广大的福德资粮。
正念诸法无常的“银镯子”,能使人了知诸有为法皆不离无常苦害的本质,特别是身体,它更是一个无常苦害的大堆聚。
身体既然是苦聚,那是不是也应迅速舍弃远离它呢?很多人会有类似疑问。
这种想法肯定是错误的,只有外道中才有自杀舍身以求生天的做法,而在内道中,教主大德们严禁修行人对身体作无义的损害。
有漏的身体内有风胆涎四百零四种疾病的逼恼,外有刀杖兵器的击打、寒暑的侵袭等等无量损恼,它实际上是众苦的源泉,如果不是它拖累,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多苦恼。
所以有智者见身,如同专门给自己带来损害的怨敌一般,是苦源,是苦蕴,是苦器,不应对它执著。
但是,这种认识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而言,智者们对身体也会加以合理保护,不让它无义地受损伤。
对修行者而言,身体也是解脱道上必不可少的工具,依靠暇满人身,守持清净律仪,这样的身体若能长久存活,就可以广行善法,积聚起广大的福德资粮。
佛陀在《三昧王经》中说过:“经恒沙数劫,无量诸佛前,供养诸幢幡,灯鬘饮食等;若于正法坏,佛教将灭时,日夜持一戒,其福胜于彼。
”在末法时代,持守一条戒律一昼夜,其功德也不可思议,但只有依靠暇满人身,才有机会积累这不可思议的功德。
因而智者们既了知身体有害的一面,也了知身体有益的一面,古德云:“此身行善即是解脱舟,此身造恶便是轮回锚,此身一切善恶之奴仆。
”为了让身体能长久行持善法,理应断除各种非理损害,而对其善加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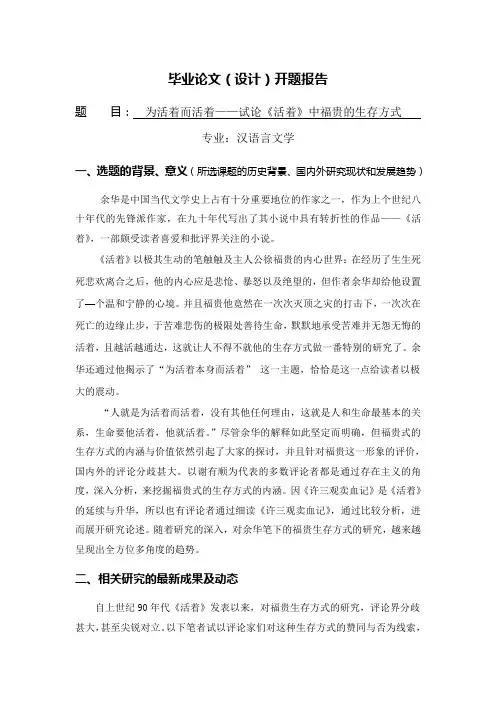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题目:为活着而活着——试论《活着》中福贵的生存方式专业:汉语言文学一、选题的背景、意义(所选课题的历史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作家之一,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派作家,在九十年代写出了其小说中具有转折性的作品——《活着》,一部颇受读者喜爱和批评界关注的小说。
《活着》以极其生动的笔触触及主人公徐福贵的内心世界:在经历了生生死死悲欢离合之后,他的内心应是悲怆、暴怒以及绝望的,但作者余华却给他设置了—个温和宁静的心境。
并且福贵他竟然在一次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下,一次次在死亡的边缘止步,于苦难悲伤的极限处善待生命,默默地承受苦难并无怨无悔的活着,且越活越通达,这就让人不得不就他的生存方式做一番特别的研究了。
余华还通过他揭示了“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这一主题,恰恰是这一点给读者以极大的震动。
“人就是为活着而活着,没有其他任何理由,这就是人和生命最基本的关系,生命要他活着,他就活着。
”尽管余华的解释如此坚定而明确,但福贵式的生存方式的内涵与价值依然引起了大家的探讨,并且针对福贵这一形象的评价,国内外的评论分歧甚大。
以谢有顺为代表的多数评论者都是通过存在主义的角度,深入分析,来挖掘福贵式的生存方式的内涵。
因《许三观卖血记》是《活着》的延续与升华,所以也有评论者通过细读《许三观卖血记》,通过比较分析,进而展开研究论述。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余华笔下的福贵生存方式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的趋势。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自上世纪90年代《活着》发表以来,对福贵生存方式的研究,评论界分歧甚大,甚至尖锐对立。
以下笔者试以评论家们对这种生存方式的赞同与否为线索,作一回顾与综述。
一派以姜飞、洪治纲等人为代表的赞同者们认为,余华“为没有任何外在于生命的名利追求可能的百姓提供生存下去的信念和意义”,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活着本身,并体现了“深切的意义追问和民间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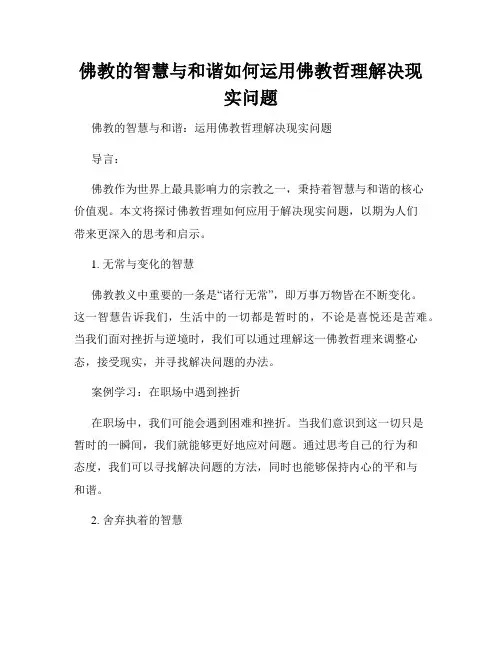
佛教的智慧与和谐如何运用佛教哲理解决现实问题佛教的智慧与和谐:运用佛教哲理解决现实问题导言:佛教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秉持着智慧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
本文将探讨佛教哲理如何应用于解决现实问题,以期为人们带来更深入的思考和启示。
1. 无常与变化的智慧佛教教义中重要的一条是“诸行无常”,即万事万物皆在不断变化。
这一智慧告诉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不论是喜悦还是苦难。
当我们面对挫折与逆境时,我们可以通过理解这一佛教哲理来调整心态,接受现实,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案例学习:在职场中遇到挫折在职场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一瞬间,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应对问题。
通过思考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我们可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和谐。
2. 舍弃执着的智慧佛教哲理教导我们舍弃执着,释放心灵。
执着于物质财富或者对他人的情感绑架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痛苦。
只有通过放下执着,我们才能体验到内心的自由和和谐。
案例学习:处理感情问题在处理感情问题时,我们常常陷入执着的陷阱中。
而佛教哲理告诉我们,只有舍弃执着,放下过去的伤害和情感包袱,我们才能够进入和谐的关系。
通过理解佛教哲理中的舍弃执着的智慧,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感情问题。
3. 善与利他的智慧佛教教义强调善的行为和利他的精神。
通过关注他人的需求,并以善意和慈悲心态去帮助他人,我们能够建立和谐的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
案例学习:建立和谐社区在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运作的直接体现。
通过运用佛教哲理中的善与利他的智慧,我们可以建立起和谐的社区。
通过关爱他人,理解他人的需求,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共同发展和融洽相处的社区。
4. 悟性与觉知的智慧佛教鼓励我们通过悟性与觉知来提升自我认知和理解。
只有掌握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人,并与之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
案例学习:解决人际冲突在面对人际冲突时,佛教哲理中的悟性与觉知的智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需求,从而化解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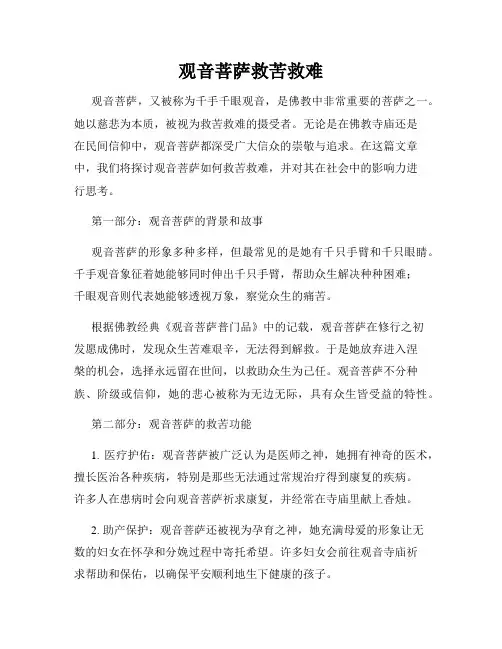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观音菩萨,又被称为千手千眼观音,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菩萨之一。
她以慈悲为本质,被视为救苦救难的摄受者。
无论是在佛教寺庙还是在民间信仰中,观音菩萨都深受广大信众的崇敬与追求。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观音菩萨如何救苦救难,并对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进行思考。
第一部分:观音菩萨的背景和故事观音菩萨的形象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是她有千只手臂和千只眼睛。
千手观音象征着她能够同时伸出千只手臂,帮助众生解决种种困难;千眼观音则代表她能够透视万象,察觉众生的痛苦。
根据佛教经典《观音菩萨普门品》中的记载,观音菩萨在修行之初发愿成佛时,发现众生苦难艰辛,无法得到解救。
于是她放弃进入涅槃的机会,选择永远留在世间,以救助众生为己任。
观音菩萨不分种族、阶级或信仰,她的悲心被称为无边无际,具有众生皆受益的特性。
第二部分:观音菩萨的救苦功能1. 医疗护佑:观音菩萨被广泛认为是医师之神,她拥有神奇的医术,擅长医治各种疾病,特别是那些无法通过常规治疗得到康复的疾病。
许多人在患病时会向观音菩萨祈求康复,并经常在寺庙里献上香烛。
2. 助产保护:观音菩萨还被视为孕育之神,她充满母爱的形象让无数的妇女在怀孕和分娩过程中寄托希望。
许多妇女会前往观音寺庙祈求帮助和保佑,以确保平安顺利地生下健康的孩子。
3. 庇护灾厄:观音菩萨被广大信众视为能够保佑人们远离灾难和不幸的菩萨。
人们相信,只要真诚地祈求观音菩萨的庇佑,她就会保护他们免受自然灾害、疾病、事故和其他危险的侵害。
第三部分:观音菩萨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观音菩萨的救苦功能和慈悲本质使她在社会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首先,观音菩萨作为信仰对象,成为了人们追求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的重要来源。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群,对观音菩萨的信仰都能够为人们带来安抚和勇气。
其次,观音菩萨的救援形象在社会救助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很多寺庙和慈善组织以观音菩萨的名义开展各种救援活动,帮助那些面临困境的人们。
观音菩萨的慈悲形象激励了更多的人们参与到救助行动中,共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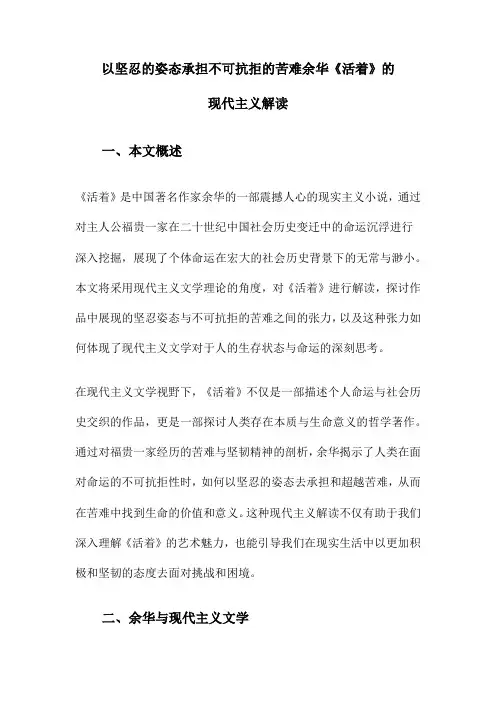
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余华《活着》的现代主义解读一、本文概述《活着》是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一部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福贵一家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命运沉浮进行深入挖掘,展现了个体命运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无常与渺小。
本文将采用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活着》进行解读,探讨作品中展现的坚忍姿态与不可抗拒的苦难之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如何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对于人的生存状态与命运的深刻思考。
在现代主义文学视野下,《活着》不仅是一部描述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交织的作品,更是一部探讨人类存在本质与生命意义的哲学著作。
通过对福贵一家经历的苦难与坚韧精神的剖析,余华揭示了人类在面对命运的不可抗拒性时,如何以坚忍的姿态去承担和超越苦难,从而在苦难中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现代主义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活着》的艺术魅力,也能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以更加积极和坚韧的态度去面对挑战和困境。
二、余华与现代主义文学余华的作品《活着》无疑可以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典范。
现代主义文学,起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强调对个体经验和主观现实的深入探索,以及对传统叙事方式和美学观念的颠覆。
余华在《活着》中所展现出的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对苦难和生存的独特理解,以及叙事手法的创新,都使得这部作品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紧密相连。
余华通过《活着》展现了对个体经验和主观现实的深刻关注。
他让主人公福贵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他一生的苦难和经历。
这种自述的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福贵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他面对苦难时的无奈和坚韧。
这与现代主义文学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和对个体经验的重视不谋而合。
余华在《活着》中对传统叙事方式和美学观念的颠覆,也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
他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的方式,将福贵的一生碎片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叙事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顺序和空间结构,也使得作品更加具有张力和深度。
同时,余华还通过荒诞和幽默的手法,对苦难和生存进行了独特的解读,这也与现代主义文学对现实世界的质疑和对传统美学观念的挑战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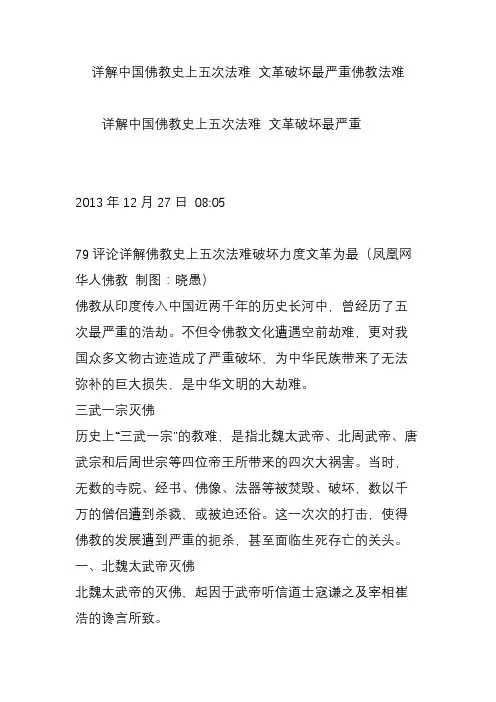
详解中国佛教史上五次法难文革破坏最严重佛教法难详解中国佛教史上五次法难文革破坏最严重2013年12月27日08:0579评论详解佛教史上五次法难破坏力度文革为最(凤凰网华人佛教制图:晓愚)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了五次最严重的浩劫。
不但令佛教文化遭遇空前劫难,更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是中华文明的大劫难。
三武一宗灭佛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教难,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带来的四次大祸害。
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
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起因于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及宰相崔浩的谗言所致。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后,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并兴建不少寺院。
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
北魏灭北凉后,还带回许多沙门到京师,当时对北魏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沙门玄高、师贤、昙曜等人都是来自凉州。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
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霄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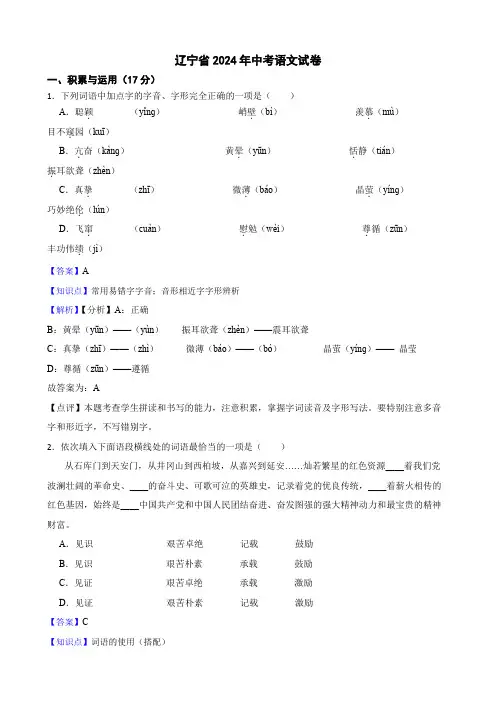
辽宁省2024年中考语文试卷一、积累与运用(17分)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字音、字形完全正确的一项是()A.聪颖.(yǐnɡ)峭壁.(bì)羡慕.(mù)目不窥.园(kuī)B.亢.奋(kànɡ)黄晕.(yūn)恬.静(tián)振.耳欲聋(zhèn)C.真挚.(zhī)微薄.(báo)晶萤.(yínɡ)巧妙绝伦.(lún)D.飞窜.(cuàn)慰.勉(wèi)尊.循(zūn)丰功伟绩.(jì)【答案】A【知识点】常用易错字字音;音形相近字字形辨析【解析】【分析】A:正确B:黄晕(yūn)——(yùn)振耳欲聋(zhèn)——震耳欲聋C:真挚(zhī)——(zhì)微薄(báo)——(bó)晶萤(yínɡ)—— 晶莹D:尊循(zūn)——遵循故答案为:A【点评】本题考查学生拼读和书写的能力,注意积累,掌握字词读音及字形写法。
要特别注意多音字和形近字,不写错别字。
2.依次填入下面语段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从嘉兴到延安……灿若繁星的红色资源____着我们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____的奋斗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记录着党的优良传统,____着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始终是____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进、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A.见识艰苦卓绝记载鼓励B.见识艰苦朴素承载鼓励C.见证艰苦卓绝承载激励D.见证艰苦朴素记载激励【答案】C【知识点】词语的使用(搭配)【解析】【分析】见证,当场目睹可以做证。
指证人或证物。
第一空写石库门、天安门、井冈山、西柏坡、嘉兴、延安等红色资源是我党发展的证物,用“见证”。
见识,接触事物,扩大见闻。
见闻;知识。
看待和认识问题。
艰苦卓绝,形容坚忍不拔、顽强刻苦的精神无与伦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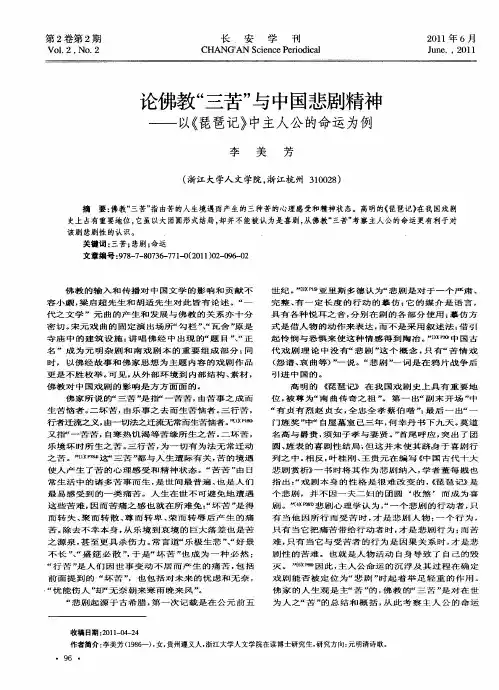
内容提要: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思想和他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的思考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他同情和参与政治社会革命,并在此刺激下进行佛教革命。
但他对世俗革命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革命思想是中国近代历史与佛法智慧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佛法、佛教革命、革命一前言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在不断的革命中度过的。
从推翻满清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相续不断。
与革命的历史实践活动相关,鼓吹革命的理论、思想也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话语。
对于此一问题的反思和探讨,近些年来已有人在进行,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论”和刘小枫先生基于基督教神学所进行的思考(1)都是很有影响的。
我在此文中所要叙述的是一位近代著名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革命的深度、广度及其局限性。
二、佛教革命在民国年间,太虚可以说是一位风云人物,人称“政治和尚”。
“政治和尚”的称号当然含有浓重的贬意,意指太虚与政府要人来往密切,有巴结权贵之嫌。
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点评论:第一,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政治和尚”的说法也有些道理,在近代佛教领袖中,太虚的政治关怀确实最为强烈,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也最深,而太虚之卷入政治,既因为一般的时代因素的影响,也因为个人的一些特殊机缘。
第二,太虚的参与政治,是有限度的,是谨守佛教的立场的,他始终是为了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他的政治理想也始终是建设一个佛化的新世界,世俗的财富与权位在太虚的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
太虚表现了20世纪佛教徒对政治现实的态度,以及对佛教与社会政治现实的关系的理解。
其实,就其一生而言,太虚是一个佛教的改革家,他的大部分生命活动都是在从事中国佛教的革新与改良。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使用的却是激进的革命语汇。
这本来不难理解,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一切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都必然会打上革命的烙印,佛教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也是如此。
13B净土组第一课《怎样面对痛苦》思考题参考答案1、如果说三界轮回是痛苦的本性,那是不是完全否定了世间的一切快乐?为什么?参考答案:虽说三界轮回是痛苦的本性,但没有完全否定世间的一切快乐。
第一:总的来讲,世间行为有两种,一是高尚的行为,一是卑劣的行为。
如果行持高尚的行为,即生中快乐,来世也会快乐;如果行持卑劣的行为,即生中痛苦,来世也会痛苦。
这是一中因果规律。
佛学讲因缘,有三项内涵、四种关系。
三项内含即是善缘、恶缘、无记缘。
今生相遇的夫妻子女同事朋友等这些都是因自己的业力感召而来的,行持高尚的行为感召的善缘就多也就过得比较快乐;相反就感召的恶缘比较多。
第二:世间快乐源自感官享受。
比如身体的接触、悦耳的声音、漂亮的东西,这些都可以带来快乐。
但这种快乐特别肤浅,有时候通过药物也可以获得。
聚是快乐的,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相聚的快乐里隐含着分离的痛苦;恋爱是快乐的,而相爱容易相处难,恋爱的快乐里隐含着争吵、猜忌、怨恨的痛苦;年轻貌美是快乐的,只是岁月无情催人老,年轻的快乐里隐含着衰老的痛苦;为人父母是快乐的,可把娇小脆弱的生命抚养成人,要付出多少精力,提心吊胆、不寝不食,这其中又有多少辛苦;升职加薪是快乐的,不过压力和焦虑也随之升级,生活里每一项快乐都含带着日后的痛苦,每个人感觉幸福的尺度也会不一样。
即使你有财产、有地位、有名声,或是怎样的利养恭敬,除了个别具修证境界的人以外,始终保持快乐心境很难办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三界轮回是虽是痛苦的本性,但没有完全否定世间的一切快乐。
虽然世间可能眼前有一些所谓的快乐,但这种快乐是暂时的无常的,都是变相的痛苦。
2、遇到痛苦时,世间人一般是怎么对待的?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例子?参考答案:我们人类有苦苦、坏苦、行苦这三大根本苦,以及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等八大支分苦。
印度伟大学者圣天论师,还将人类的痛苦归摄为两种:身苦与意苦。
遇到痛苦时,世间人一般有3种对待方法。
第25卷第2期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Vo l 25 No 22009年6月J OURNAL OF JI AOZ UO TEACHERS COLLEGE Jun 2009收稿日期:2008-10-28作者简介:赵彩霞(1973-),河南焦作人,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生本不乐!!!浅谈史铁生作品中的佛学思想赵彩霞(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河南焦作454000)摘要:史铁生由于个人身体的不幸,对痛苦的体会比起普通人来,尤为深刻。
他认识到痛苦不仅源于肉体,更源于精神。
只要有局限,就会有困境和磨难。
这和佛学认为人生本苦的教义有了很多相通之处。
关键词:史铁生;困境;佛学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65(2009)02-0029-03当代作家中,史铁生是为数不多的纯文学作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踏入文坛后便以其作品对人之存在的深层思考、对人的困境的深切关注而蜚声海外,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丰厚的哲学内涵日益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从21岁开始,史铁生便身处人生的困境,这使他产生了要在自己的生命中发现某些值得活下去的意义的强烈的感情需要,正如他自己所说,创作 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 [1]408。
这促使他对生命的意义、对存在的不断发问。
这种发问构成了他写作的源头和方向,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具有自发的哲学气质的小说家,他的这种文学方式的哲学思考,是从他苦难的命运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在对人生深刻的体悟中,他看到了人生的盲目性、荒诞性,以及人自身对科学和宇宙认识的局限性,于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就产生了 宗教精神 这个概念。
史铁生认为宗教和宗教精神是有显著区别的:宗教是人们面对 不知 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而宗教精神是清醒时依然保存的坚定信念,是人类知其不可为而决不放弃的理想,它根源于人对本原的向往,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感悟。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姓名:左文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罗成琰20030501摘要y663872文学是人类言说苦难的诗学方式,宗教是苦难世界的人们幻想幸福的意识形态。
对苦难的共同关注是佛教文化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首要契合点。
在随缘中承担苦难、在还灭消解苦难、在度化中救赎苦难这三种佛教应对苦难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阐释佛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文章以佛教“三三法印”、“四圣谛”及禅宗理论为宗教理论背景,来论述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同时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带有佛教色彩的如鲁迅、沈从文、丰子恺、废名、许地山、施蛰存、李叔同、苏曼殊、徐志摩、汪曾祺、史铁生、马原、余华、阿来、阎真等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案分析和系统梳理来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对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在价值观上的选择、亲近与背离,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论述中,文章认为,因为对苦难及应对苦难的方式的共同关注,佛教获得了现实层面的可行性和终极层面的永恒性,20世纪中国文学因此获得了一种可贵的人本主义品质。
菩提之花与缪斯之光必将在未来继续照亮人们选离人生苦难、重返精神家园的漫漫旅程。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佛教苦难随缘还灭度化ABSTRACTLiteratureiSthepoeticalwayforthehumanbeingstonarratethesuffering,religionisakindofideologyforpeopleinthesufferingtoimaginehappiness.FocusingonthesufferingtogetheristhefirstfusionpointbetweenBuddhismcultureandChineseliteratureof20“1century.Therearethree.13uddhismwaystodealwiththesuffering.bearingsufferingthroughobeyingthedestiny、dispellingthesufferingthroughextinguishingthedestinyandsavingthesufferingthroughsalvingthesufferingpeopletothenirvana,whichprovideUSwithanewperspectivetointerprettherelationshipbetweenBuddhismandChineseliteratureof20址century.Thisarticletook“ThreeDharmas”、“FourSaint.doctr.ines”andZenasitsreligioustheorybackgrand,todiscusshowthethreewayshadaffectedandpermeatedintotheChineseliteratureof20仙century.Atthesametime,throughindividuallyandsystematiclyanalyzingthefamouswritersofChinain20”centurywhohadtheBuddhismcharacteristicsuchasLu-xun、.Shen—congwen、Feng.zikai、Fei.ruing、Xu-dishan、Shi-zhecun、Li—shutong、Su—manshu、Xu.zhimo、Wang—zengqi、Shi—tiesheng、Ma—yuan、Yu—hua、A-lai、Yan.zhenetc.thisarticlediscussedhowtheChineseliteratureof20mcenturyhadchosen、closedtoanddeviatedfromthethreeways.Inthediscussingofmutualinfluence,thisarticledrewitsconclusion:becauseoffoeusingonthesufferingandthewaystodealwiththesuffering,Buddhismhadgottentherealisticfeasibilityandtheultimateandperpetualvalue,andChineseliteratureof20‘“centuryhadgottenapreciouscharacterofhuman‘centeredthought.TheflowerofBuddhiandthelightofMusewillbeboundtoilluminatetheendlessjourneyforpeopletodepartfromthesufferingandtoreturntotheirspiritualhomelandinthefutureKeywords:ChineseSufferingObeyingtheSalvingliteratureof20‘“centurydestinyExtinguishingIIBuddhismthedestiny引言文学是人类言说苦难的诗学方式,宗教是苦难世界的人们幻想幸福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开头部分就指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n1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而言,20世纪都是一个文明与灾难交织的世纪,这个世纪,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但同时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表现人类一个世纪的苦难,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谢有顺认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苦难史,因为除了苦难,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殚精竭虑地去书写呢?雎1而佛教文化价值观中以“一切皆苦”为核心的“三法印”这三个富含哲学思辨色彩的命题,为创立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苦难主题提供了具有宗教意义上的参照,中国作家对佛教文化自觉或不自觉的亲近,对“三法印”命题有意或无意的认同与表现,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苦难主题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这是文学与佛学共鸣共振而产生的和谐乐章。
但是,正如谭桂林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一书中所言:“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佛教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关系,佛教文化对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都几乎是一个盲点。
”在佛教研究领域,有的将之当成一种单纯的宗教,如荷兰汉学家许里和著的《佛教征服中国》、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和陈兵、邓子美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史》等;有的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的,如戴康生、彭耀、美国的托马斯·F·奥戴等人的著作;有的是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的,如葛兆光、麻天祥、日本的阿部正雄等人:有的是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的,如魏承思、方立天、罗马尼亚的亚·泰纳谢等人;有的是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研究的,如铃木大拙、弗洛姆、马蒂诺等人,还有如俄国的舍尔巴茨基是从逻辑学角度来研究的,这些研究几乎没有涉及佛学与文学的关系。
而孙昌武、陈允吉、日本的加地哲定以及覃召文、王志敏、方珊等人对文学与佛学关系的研究虽然成就斐然,但这些研究几乎全部局限在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上,没有涉及现代文学。
随着研究的深入,佛教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出现了一系列以学术论文为主的研究成果,较早的如罗成琰、谭桂林的相关论文,接下来又出现了哈迎飞、姚锡佩、潘正文、陈健等人对鲁迅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成果,另外,石杰、青平等人对佛教与新时期文学关系的研究也较为引人注目。
谭桂林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出版,是这一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性成果。
但是,这些成果或为作家专论,或为’整体整合,几乎没有对“苦难”这一文学与佛学共同关注的焦点和主题作过系统研究,凸显20世纪中国文学在应对人类苦难时所留下的佛迹禅影,正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原始佛教提出了被称为“三法印”的三个命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
诸行无常是佛教对整个世界、人生的看法,行,即迁流转变的意思,指一切展转相依,生死相继的无限活动,诸行无常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种流转,一切事物都只在永恒的流动中存在,犹如水流火焰,迁流不息、瞬息即变,无始无终;诸法无我是佛教对主体的独特意识,法的梵交强Dharam(达摩),本义为轨持,即“轨生物解,任持自性。
”诸法无我认为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不变的主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没有起着主宰作用的自我或灵魂,世界上没有单一独立、自我存在的、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生,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一切皆苦是佛教对人生命运的体认,这里的所谓“苦”,不单指肉体上的病痛生死之苦,也泛指怜惜人类感情、精神上的逼迫烦恼。
佛教认为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是~切皆苦的根源,认为人所处的环境导致了人的苦难,“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因为一切都是变幻无常的,人又不能自我主宰,故常为无常患累所逼,’常为外界引诱和自身欲望所惑,从而导致诸多苦难,于是广宇悠宙,无不是苦集之场;芸芸众生,无不是苦难之人。
佛教通常所讲的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乃至一百一十种苦等无量诸苦,把人生的苦处渲染到了极致。
佛教四圣谛一~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苦谛,认为一切皆苦。
方立天认为“人生是苦的命题,是佛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石。
”b1这是有道理的,正是由于佛教这近乎病态的理论,把人生渲染为苦难的历程,视大干世界、滚滚红尘为火宅,从而由此奠定了佛教应对人生苦难的基本立场和策略。
确实,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看,苦难仅仅是人的某种经历、某种遭遇、某种感受,但如果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苦难就成为了一种可以清醒地意识到但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存在的局限与伤痛。
在价值层面上对苦难的共同关注,成为了佛教文化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首要契合点。
20世纪的中国作家,似乎比任何时代的作家都要更敏感、更深刻地感受这诸行无常的世界。
晚清以来,朝政敝败,强敌益迫,割土赔款,国家有累卵之危,民众有倒悬之苦,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导致了六君子血洒刑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又混战连连,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三年你死我活的国共战争,伴随着空前丰富的物质而来的信仰和道德危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巨大而混乱的历史转变面前,作家的困惑与迷惘、失落与愤恨油然而生,他们痛感自己无法把握这个无常的世界,无法主宰人自身的命运,一切皆苦的人生感悟让他们亲近佛教,佛教的价值观又愈发使他们觉得一切皆苦,20世纪中国文学的苦难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即由此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