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尊碑五说”的几点反思
- 格式:doc
- 大小:19.50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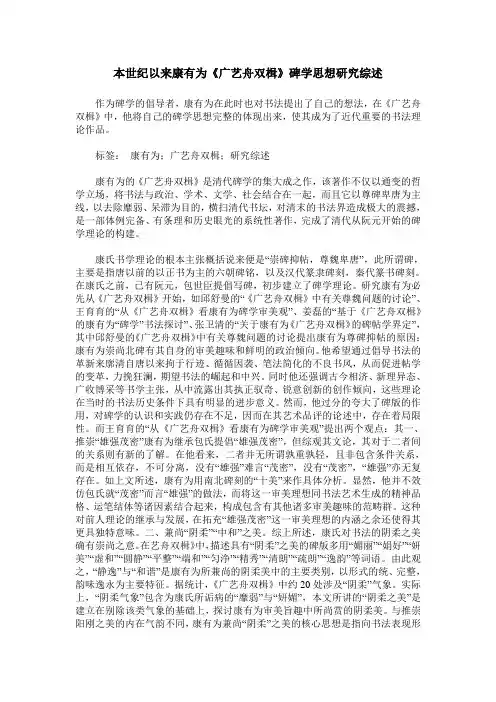
本世纪以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学思想研究综述作为碑学的倡导者,康有为在此时也对书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广艺舟双楫》中,他将自己的碑学思想完整的体现出来,使其成为了近代重要的书法理论作品。
标签: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研究综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清代碑学的集大成之作,该著作不仅以通变的哲学立场,将书法与政治、学术、文学、社会结合在一起,而且它以尊碑卑唐为主线,以去除靡弱、呆滞为目的,横扫清代书坛,对清末的书法界造成极大的震撼,是一部体例完备、有条理和历史眼光的系统性著作,完成了清代从阮元开始的碑学理论的构建。
康氏书学理论的根本主张概括说来便是“崇碑抑帖,尊魏卑唐”,此所谓碑,主要是指唐以前的以正书为主的六朝碑铭,以及汉代篆隶碑刻,秦代篆书碑刻。
在康氏之前,已有阮元,包世臣提倡写碑,初步建立了碑学理论。
研究康有为必先从《广艺舟双楫》开始,如邱舒曼的“《广艺舟双楫》中有关尊魏问题的讨论”、王育育的“从《广艺舟双楫》看康有为碑学审美观”、姜磊的“基于《广艺舟双楫》的康有为“碑学”书法探讨”、张卫清的“关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碑帖学界定”,其中邱舒曼的《广艺舟双楫》中有关尊魏问题的讨论提出康有为尊碑抑帖的原因:康有为崇尚北碑有其自身的审美趣味和鲜明的政治倾向。
他希望通过倡导书法的革新来廓清自唐以来拘于行迹、循循因袭、笔法简化的不良书风,从而促进帖学的变革,力挽狂澜,期望书法的崛起和中兴。
同时他还强调古今相济、新理异态、广收博采等书学主张,从中流露出其执正驭奇、锐意创新的创作倾向,这些理论在当时的书法历史条件下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然而,他过分的夸大了碑版的作用,对碑学的认识和实践仍存在不足,因而在其艺术品评的论述中,存在着局限性。
而王育育的“从《广艺舟双楫》看康有为碑学审美观”提出两个观点:其一、推崇“雄强茂密”康有为继承包氏提倡“雄强茂密”,但综观其文论,其对于二者间的关系则有新的了解。
在他看来,二者并无所谓孰重孰轻,且非包含条件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没有“雄强”难言“茂密”,没有“茂密”,“雄强”亦无复存在。

【导读】康有为是碑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广艺舟双楫》即是一部重要的碑学理论著作。
这部著作体系完备,架构恢宏,阅读起来是有难度的。
俞建华先生从“清人尚质”的角度对这部著作进行了解读与梳理,亦分析了其中的弊病,颇多真知灼见。
这篇30年前的文章,对于今天的书法教育工作者来说,仍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清人尚质”浅探——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读后俞建华康有为从1888年腊月开始广购碑帖作资料的积累,到1889年除夕写成《广艺舟双楫》,这部书论名著为后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也为“清人尚质”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乾隆年间的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一文中的观点尽管不很科学,但经他对尊碑进行有力鼓吹后,大大地启发了以后的一些书论家和书法家。
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论书部分,就是在自己的实践上,尤其是在邓石如等人写碑成功的实践成果上,进一步开创了尊碑的风气。
到了康有为,就在以往尊碑的基础上更充实和提高了对“碑学”的认识。
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书法在美学上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书法新天地的勤奋探求。
处于政治大变革前夜的晚清,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同样存在这个“变法”的课题。
康有为就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书法的“变”是现实的需要,“变法”是不可逆转的书坛潮流以及求新的途径。
康有为认为,自有文字以来,甲骨、大小篆、八分、隶、草、楷、行各种书体无不遵循着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己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
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
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变,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
”文字为人们所用,就在于它有实际功用性,运用“便捷”。
从“婉而通”的圆笔篆书变成“精而密”的方笔隶书是这样;从方严的楷书变成连绵的行草也是这样。
实用,就是促使书体发展变化、促使书法艺术萌生的强大动力。
虽然汉字起源于绘画而成象形文字,但并没有走上拼音化的道路。
只是随着自身的演化规律,越来越减弱、消泯象形的痕迹,成为具有“意象”性的文字。

康梁碑帖思想之比较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明末清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不仅因戊戌变法而蜚声海内外,而且在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书法理论中关于碑帖的看法,他们虽然是师徒,但是对于碑帖的态度有着各自的见解。
康有为特别倡导“尊碑抑帖”,而梁启超尊碑但不贬帖,反对“北碑南帖”之争。
标签:北碑南帖;尊碑;碑帖跋自从嘉庆道光以来,中国书法史出现了“北碑南帖”之争,各执一端,难分轩轾。
阮元提出了碑学的见解,开辟了新的道路,但他自己的书法却是帖派,实践仍是很薄弱的。
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对碑学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大批人加入碑派,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则较为全面,他不仅倡导理论而且身体力行。
康有为与吴昌硕、沈增植并称为清末民初书画“三大家”。
在《广艺舟双楫》中,他提出“尊魏卑唐”的主张。
他精通书法,早年临习王羲之《乐毅论》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并遍临《虞恭公碑》、《玄秘塔碑》、《颜家庙碑》等,尤得力于《石门铭》和《经石峪》,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世称“康体”。
康有为撰写《广艺舟双楫》的时候年仅三十一二岁,他的书法和书法理论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晚清碑学再度兴起及其对近百年来的碑帖学不断变化发展的影响,对近现代中国书法的影响和发展相当深远。
康有为的“尊碑抑帖”思想在早年的时候是十分强烈的。
在《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中提到“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
物极必反,天理固然。
”[1]对于帖康有为认为现如今看到的帖大都是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虽然是羲献之帖,但是已经面目全非,精神有所懈怠。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并没有完全复制老师的书学理论,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写道:“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
自纵流之运河既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于统一;而唐代君主上下,复努力以联贯之。
”[2]这里说明书法自唐代再分南北,实属勉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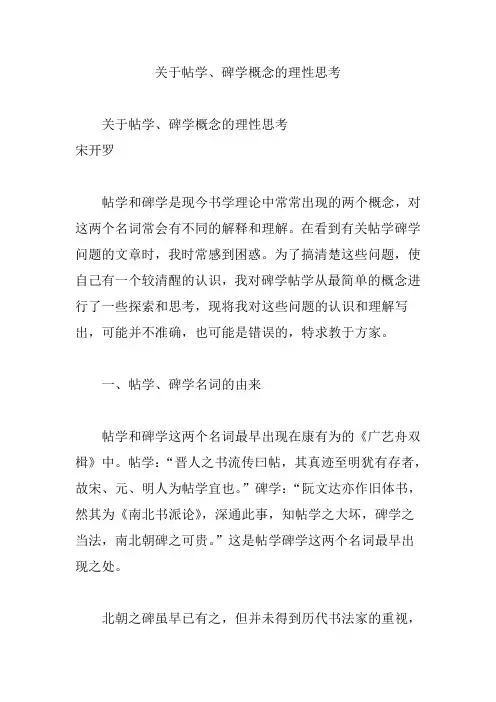
关于帖学、碑学概念的理性思考关于帖学、碑学概念的理性思考宋开罗帖学和碑学是现今书学理论中常常出现的两个概念,对这两个名词常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在看到有关帖学碑学问题的文章时,我时常感到困惑。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使自己有一个较清醒的认识,我对碑学帖学从最简单的概念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现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写出,可能并不准确,也可能是错误的,特求教于方家。
一、帖学、碑学名词的由来帖学和碑学这两个名词最早出现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
帖学:“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为帖学宜也。
”碑学:“阮文达亦作旧体书,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此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
”这是帖学碑学这两个名词最早出现之处。
北朝之碑虽早已有之,但并未得到历代书法家的重视,也很少有人习写北碑。
从阮元开始,人们才认识到北碑的书法美学价值,进而有人在书法创作中进行艺术实践。
阮元、包世臣等人提出北碑南帖之分别,开始有了尊碑思想。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辑》中都有扬碑抑帖之意,但他们并未提出帖学和碑学这两个词,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看不出帖学到了“大坏”的程度。
他们认为北碑和南帖是来自同一源流的两个艺术流派,各有所长,只是以往人们对北碑的艺术美不够重视,所以他们才提出尊碑思想。
阮元、包世臣及以后一些人对北碑的研究,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对碑学的发展以至成熟开辟了一条道路。
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首先提出了碑学这个概念。
为了与碑学相对应,他把以前的书学主流派,即以南帖和“二王”为宗的书学流派称为帖学,并突出了碑帖之间的对立。
他明确提出尊碑卑帖思想,断言帖学大坏,碑学当兴。
这两个名词概念的提出,是碑学作为书学流派正式诞生的宣言书,它从理论上完成了碑学帖学这两个书学流派之间的对立统一体系的构建。
二、帖学碑学中帖与碑的含义帖字的读音有三种,每种读音的声调不同,其含义也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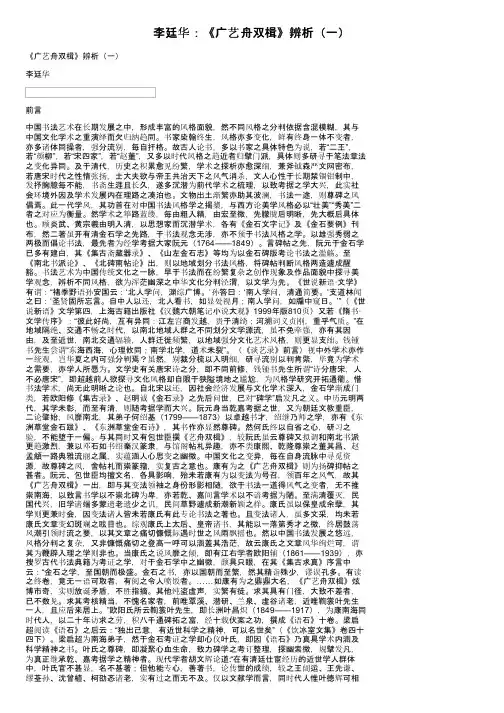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辨析(一)《广艺舟双楫》辨析(一)李廷华前言中国书法艺术在长期发展之中,形成丰富的风格面貌,然不同风格之分判依据含混模糊,其与中国文化学术之重演绎而欠归纳趋同。
书家染翰终生,风格亦多变化,鲜有终身一体不变者,亦多诸体同操者,强分流别,每自扞格。
故古人论书,多以书家之具体特色为说,若“二王”,若“颜柳”,若“宋四家”,若“赵董”,又多以时代风格之趋近者归擘门派,具体则多研寻于笔法章法之变化异同。
及于清代,历史之积累愈见纷繁,学术之探析亦愈深细,兼斧钺森严文网密布,若唐宋时代之性情张扬,士大夫欲与帝王共治天下之风气消杀,文人心性于长期禁锢钳制中,发抒胸臆每不能,书斋生涯且长久,遂多沉潜为前代学术之梳理,以致考据之学大兴,此实社会环境外因及学术发展内在理路之凑泊也。
文物出土渐繁亦助其波澜,书法一途,则尊碑之风倡焉。
此一代学风,其功首在对中国书法风格学之揭橥,与西方论美学风格必以“壮美”“秀美”二者之对应为衡量。
然学术之筚路蓝缕,每由粗入精,由宏至微,先朦胧后明晰,先大概后具体也。
顾炎武、黄宗羲由明入清,以思想家而沉潜学术,各有《金石文字记》及《金石要例》刊布,然二著虽开有清金石学之先路,于书法观念无涉,亦不预于书法风格之学。
以雄强秀弱之两极而倡论书法,最先者为经学考据大家阮元(1764——1849)。
言碑帖之先,阮元于金石学已多有建白,其《集古斋藏器录》、《山左金石志》等均为以金石碑版考论书法之滥觞。
至《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出,则以地域划分书法风格,将碑帖判断风格两造遽成醒豁。
书法艺术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脉,早于书法而在纷繁复杂之创作现象及作品面貌中探寻美学观念,辨析不同风格,欲为浑茫幽深之中华文化分判泾渭,以文学为先。
《世说新语·文学》有谓:“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
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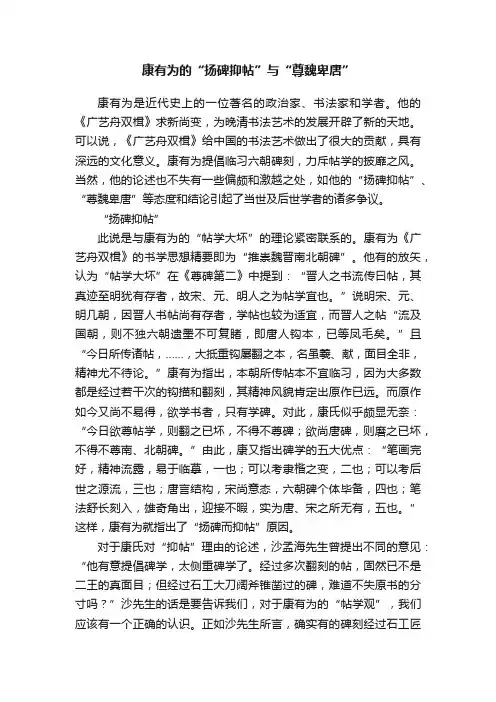
康有为的“扬碑抑帖”与“尊魏卑唐”康有为是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学者。
他的《广艺舟双楫》求新尚变,为晚清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可以说,《广艺舟双楫》给中国的书法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康有为提倡临习六朝碑刻,力斥帖学的披靡之风。
当然,他的论述也不失有一些偏颇和激越之处,如他的“扬碑抑帖”、“尊魏卑唐”等态度和结论引起了当世及后世学者的诸多争议。
“扬碑抑帖”此说是与康有为的“帖学大坏”的理论紧密联系的。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书学思想精要即为“推崇魏晋南北朝碑”。
他有的放矢,认为“帖学大坏”在《尊碑第二》中提到:“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
”说明宋、元、明几朝,因晋人书帖尚有存者,学帖也较为适宜,而晋人之帖“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
”且“今日所传诸帖,……,大抵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
”康有为指出,本朝所传帖本不宜临习,因为大多数都是经过若干次的钩描和翻刻,其精神风貌肯定出原作已远。
而原作如今又尚不易得,欲学书者,只有学碑。
对此,康氏似乎颇显无奈:“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由此,康又指出碑学的五大优点:“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个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
”这样,康有为就指出了“扬碑而抑帖”原因。
对于康氏对“抑帖”理由的论述,沙孟海先生曾提出不同的意见:“他有意提倡碑学,太侧重碑学了。
经过多次翻刻的帖,固然已不是二王的真面目;但经过石工大刀阔斧锥凿过的碑,难道不失原书的分寸吗?”沙先生的话是要告诉我们,对于康有为的“帖学观”,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如沙先生所言,确实有的碑刻经过石工匠人的锥凿,笔画都已经面目全非,横折撇捺抛刃露尖,断非挥毫而为,实乃刀凿所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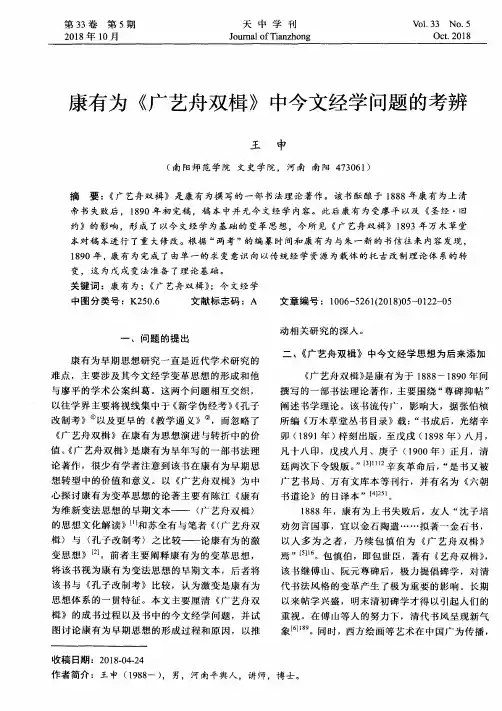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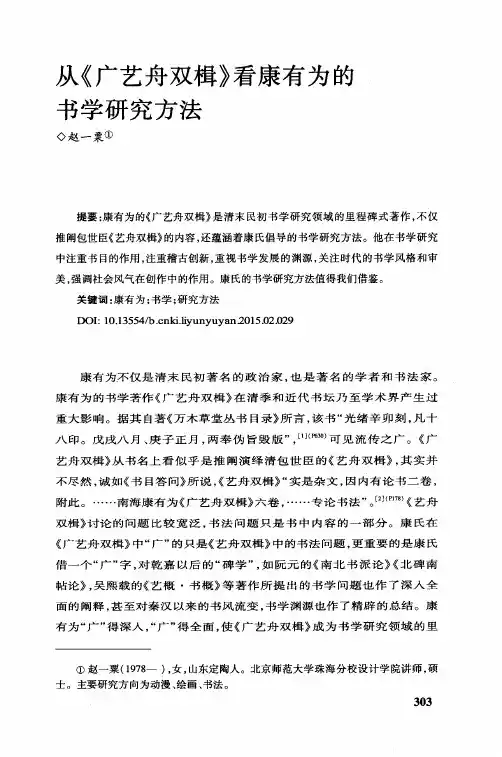

论康有为碑学思想作者:杨迎来源:《美与时代·中》2021年第06期摘要: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受其家学背景与西学知识的深刻影响。
在帖学式微之势下,康有为提倡碑学,取其雄强阳刚之风。
康有为碑学思想的代表作为《广艺舟双楫》,此书的问世,标志着康有为碑学思想的成熟。
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总结了中国碑学史,提出书学应体现“求变”的社会规律,碑学正是借帖学的衰微之机发展起来的;书学应该“经世致用”,而非一味无用或媚俗,在民族危机下应提倡碑学以提振民族信心;书学应该表现个人和民族的“气力”,表现人的本质力量。
同时,康有为认为碑学的粗拙强健之风,正符合当时时代的需要。
康有为的碑学思想与改制革新的政治思想以及追求民族富强的爱国理想密切相关。
关键词:康有为;碑学;帖学;求变一、康有为生平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佛山南海人,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书法理论家,世称“南海先生”或“康圣人”。
康有为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发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公车上书”,请求变法图强,其后参与“百日维新”。
作为一位教育家与思想家,康有为曾开设万木草堂,收徒授业,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引领一时之风尚。
但除了著名的政治家与教育家外,康有为作为书法理论家与一代碑学大师的身份,却并不被世人所熟知。
本文试图根据康有为书学思想兴起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书学思想的诸项要点,对康有为书学思想展开研究。
康有为独特且具有建设性的书学思想与其家学传统与西学知识是分不开的。
康有为曾自许“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1]。
优秀的家学背景,再加上极高的天赋,使得少年康有为不甘于平庸,从年轻时期起即立下成为圣贤的志向。
在成长期间,康有为就渴望进步,竭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并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了西学。
随着对西学了解和研究的深入,康有为认为如果要解除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就必须借助新的知识对古老僵化的制度进行革新。
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康有为认为宇宙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变者天也”[2],求学治道,都要追求“变”,要顺应时代之变化而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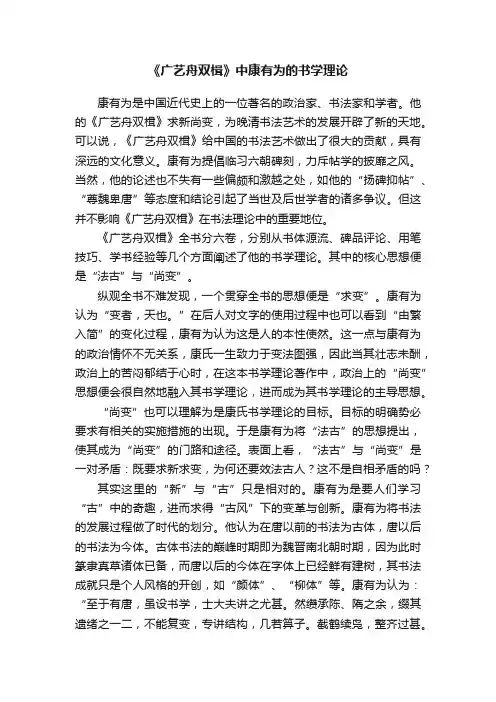
《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的书学理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学者。
他的《广艺舟双楫》求新尚变,为晚清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可以说,《广艺舟双楫》给中国的书法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康有为提倡临习六朝碑刻,力斥帖学的披靡之风。
当然,他的论述也不失有一些偏颇和激越之处,如他的“扬碑抑帖”、“尊魏卑唐”等态度和结论引起了当世及后世学者的诸多争议。
但这并不影响《广艺舟双楫》在书法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广艺舟双楫》全书分六卷,分别从书体源流、碑品评论、用笔技巧、学书经验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他的书学理论。
其中的核心思想便是“法古”与“尚变”。
纵观全书不难发现,一个贯穿全书的思想便是“求变”。
康有为认为“变者,天也。
”在后人对文字的使用过程中也可以看到“由繁入简”的变化过程,康有为认为这是人的本性使然。
这一点与康有为的政治情怀不无关系,康氏一生致力于变法图强,因此当其壮志未酬,政治上的苦闷郁结于心时,在这本书学理论著作中,政治上的“尚变”思想便会很自然地融入其书学理论,进而成为其书学理论的主导思想。
“尚变”也可以理解为是康氏书学理论的目标。
目标的明确势必要求有相关的实施措施的出现。
于是康有为将“法古”的思想提出,使其成为“尚变”的门路和途径。
表面上看,“法古”与“尚变”是一对矛盾:既要求新求变,为何还要效法古人?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其实这里的“新”与“古”只是相对的。
康有为是要人们学习“古”中的奇趣,进而求得“古风”下的变革与创新。
康有为将书法的发展过程做了时代的划分。
他认为在唐以前的书法为古体,唐以后的书法为今体。
古体书法的巅峰时期即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此时篆隶真草诸体已备,而唐以后的今体在字体上已经鲜有建树,其书法成就只是个人风格的开创,如“颜体”、“柳体”等。
康有为认为:“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
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能复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启示录——对当代书法创新的几点思
考
靳继君;张繁文
【期刊名称】《艺术百家》
【年(卷),期】2008(024)003
【摘要】@@ 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现实意义rn当翻开中国书法史,康有为的名字也是赫然醒目.他在书学上的变法思想是亘古未有的,其变法思想在<广艺舟
双楫>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的问世奏响了清代"碑学中兴"的最强音,直接导致了
晚清书学的革命.该文高举"尊碑"大旗,倾注了变革与创新的精神,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支持.虽然文论中有"主观"的倾向,但终不能"夺其所守",使
其书法观念和创作更见个性,更见创造力.
【总页数】2页(P229-230)
【作者】靳继君;张繁文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广东,广州,510665;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292.1
【相关文献】
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今文经学问题的考辨 [J], 王申
2.古代书论的一种二律背反:有限想像和无限想像--以《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
为例 [J], 张学峰
3.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与近代\"书法革命\" [J], 唐卫萍
4.浅析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书主张 [J], 李卓霖
5.“清人尚质”浅探——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读后 [J], 俞建华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广艺舟双楫》浅论康有为的书学思想摘要: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一部在中国书法史上极有理论特色的著作。
书中集中反映了他的书学思想。
他在政治上的观念对书学影响甚大,并在其书学思想及实践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康有为书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坚持以退为进的原则,着眼于书法艺术的表现性特征,确立了以变为核心的基本内容。
欲用多变的体势,取代陈旧保守的书风,意在通过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的倡导,进行书风的改良。
因而提出了“尊卑抑帖,重魏卑唐”的根本主张。
关键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书学思想;变;碑;帖康有为的书论主要见于《广艺舟双楫》,这是晚清碑学在理论上的一个总结,是当时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本书学著作。
全书虽然是在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基础上推而广之,但它是有计划、有体系、一气呵成地写就的,这一点,与包世臣将平日零碎的信札、论文辑录成《艺舟双楫》完全不同。
康氏通过自己大量收集评骘汉魏六朝碑刻的经验,于前人之说颇多匡正,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新见,遂写成这部六万余字的论书名著。
全书除去《自叙》一篇之外,共六卷二十七章,卷一、卷二论书体源流,卷三、卷四评骘历代碑版,卷五、卷六讨论笔墨技巧与学书经验。
全书虽涉及之面极广,然要在通过尊卑抑帖而体现了他的变法求新的思想。
一、求变思想贯穿于《广艺舟双楫》中的思想可一言以蔽之曰:变。
康有为以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他于书中第一章《原书》中就指出:“变者,天也。
”以为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规律,它是出于自然,不可更易的。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各种书体发展的认识之中。
他说:“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
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
”人由于天生的灵智,不仅能创造文字,而且一定会发展文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康氏甚至举西洋文字发展的例字来说明这一道理,英、法、德、俄的文字各异,“其至古者,有阿拉伯文字,变为犹太文字焉,有叙利亚文字、巴比伦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变为拉丁文字焉;又变为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
从《广艺舟双楫》中体会书法之“变”作者:马晗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1期从古至今,不同时期的书法呈现着不同的面貌与精神。
汉魏尚象,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清尚朴,这是对各个时期书法状态最好的诠释。
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以独立且不可分割的姿态延续着。
时代的变迁,时风的变化,书家的个人追求无不影响着书法历史进程的演变。
而在此过程中,清代是重要的书法总结与反思时期,这时重新树立了篆、隶、北碑的重要书史地位和美学价值,并进而在审美上实现了重大的突破,改变了宋代以来以文人趣味为基础取向的格局。
在此过程中包世臣、康有为、阮元、刘熙载的书法理论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书法的变革。
我想通过对《广艺舟双楫》的分析,谈一谈中国书法之“变”。
这个“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朝代的更迭引起书法时风的变化;另一个方面是同一时期不同书家的各自变体。
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康有为在书法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书学思想核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变革。
用《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中的原话说“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
”这句话告诉我们天地江河这些看似一成不变的事物,其实每天都在变化着,这是自然的规律。
所以,通过时间的推移,书法也是不断地变化、发展和完善的。
但是,是什么引起清朝中后期书法的“变”呢?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给了我们一些启发。
其一,“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尤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
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潮,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
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
”这句话表达了当时书风日下,帖学日渐衰败,不在利于书法的发展。
其二,“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胜也。
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
第卷第期郁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求新还是复古——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淡起杨波河南大学河南省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河南开封摘要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融书法、文学于一炉的著作内容丰富体大思精。
但在书法和文学领域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文章试图从这个特殊文本中去探寻康有为由书学到文学由文学再到社会变革思想演变的内在脉络为进一步研究康有为提供另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关键词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书学求新复古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广艺舟双楫》体大思精宏论迭出影响了一代书风可渭足晚清以来最重要的一部书法理论著作。
但它又非一般意义上的书学论管书中熔铸了康有为的政治理念与文学思想内涌宏富独树一帜。
长期以来研究书法者不通文学史、思想史只看出了“抑贴扬碑”、“尊魏卑唐”的门道治文学者又大多不谙书法以为其意在阐发书学便绝少留意。
于是这部有着更多阐释叮能的著作在书法与文学领域都未得到应有的晕视少人问津。
一、末艺小技与天下大道《广艺舟双楫成书于光绪十五年年共六卷前有《叙目》分《原节》、《尊碑》、《购碑》等凡篇体系宏大论说严密。
康有为自言书名袭自包世臣《艺舟双楫》欲擎之衍之。
此书实际上已为晚清书学理沦另辟疆域不可同日而语。
康有为自述著书缘起“上书惊阙下闭户隐城南。
洗石为僮课摊碑与客淡。
著书销日月忧国自江潭。
日步回廊曲从面壁参。
”诗题甚长《上书不达谣谗高张沈乙直、黄仲瞍皆劝勿谈国事乃却扫汗漫肪以金石碑版自娱著广艺舟双楫成浩然有归志》。
诗句与题目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复杂心境。
光绪十四年年康有为应顺天府乡试不第后竞以布衣之身向光绪帝上《为国势微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即《上清帝第一书》力谏光绪帝。
结果奏折不仅石沉大海康有为也被斥为狂言乱政遭到群臣甚至同乡的诟骂非议。
康有为遂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于是潜心研制金石碑版。
“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迄。
”短短十七天便一气呵成不得不叹服康有为之才华若此。
“夫书小艺耳本不足述。
论康有为碑帖艺术观的维新思想康有为为实现其政治抱负,在碑帖艺术观上提出“变法、变体”。
推崇魏碑而力荐唐碑,追求艺术上的古朴雄强之美,以救帖学妍美媚俗之弊,从中体现其政治上的审时通变维新思想,使碑帖艺术观和政治观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标签:碑帖艺术观;政治观;审时通变;结合康有为,广东南海人。
在近代中国领导“戊戌变法”,力倡维新改革,主张“变器复变道”,影响至深,使其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
同时,康有为又是近代大儒,经、史、诗、文、书法,精研纵横,无所不通。
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为完成其政治抱负,推行其改革主张,他的《广艺舟双辑》虽是书学总结巨著,但碑帖艺术思想中无处不染有强烈的政治投影。
一《广艺舟双辑》虽是书学总结巨著,却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
从其成书的时间和写作背景来说,也正是康有为极力主张进行政治革新之时。
1888年,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时就大声疾呼“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其何以支?”[1]125。
如果继续因循守旧,内忧外患将使统治岌岌可危,要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1]127以挽救危机。
上书失败后,政治上的失意,难发心中愤懑,忧国忧民的热情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来说无疑是一大悲剧,遂不得已暂时转向书法领域排遣苦闷。
康有为虽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但更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多次参与政治上的斗争,依附于某种政治势力,并企图通过政治方式将社会文化导入理想的政治轨道,这就注定了书法是作为践道的工具。
同时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通过学术研究来阐发政治主张,强调个人见解的发挥,是康有为治学的主要特点。
因此,1889年成书的《广艺舟双辑》中多激越之词与变古立异之说,在书学之上推崇魏碑而力荐唐帖,创立碑学以救帖学之弊,提出碑帖艺术观上的“变法、变体”“审时通变”的革新思想,实质是碑帖艺术观上的政治投影。
康有为认为世上万物都“无时不变,无事不变”,“祖宗之法”自然就没有永恒不变的道理。
任何事物都是遵循“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的变化规律,因此,“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2]198,主张通过维新变法以达天下大治。
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尊碑五说”的几点反思作者:段彬彬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5年第03期摘 ; 要:晚清以来,碑学观念深入人心,相继产生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艺舟双楫》等一批鼓吹碑学的书学论著。
其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更是煽焰扬波,将尊碑思想推向最高潮。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体现的尊碑、卑唐、抑帖思想有其书学的进步意义。
然而,由于个人主观感情色彩渗入,《广艺舟双楫》中的一些观点显得有失偏颇。
文章通过对其“尊碑五说”的反思,试图厘清康有为对于帖学、唐碑的误读,以便更好地认识晚清的碑学运动及《广艺舟双楫》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康有为;帖学;尊碑;卑唐;反思中图分类号:J292.26 ; ; ; ;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9-0071-02有清一代,从乾隆年间开始,书法观念发生重大改变,即以碑学为主体的书法理论观念与书法创作观念开始逐步取代千余年的帖学统治地位,进而笼罩整个乾隆朝以后的书坛,影响流波不绝。
从郑谷口,朱彝尊始学汉碑,为清代碑学之盛揭开帷幕开始,金冬心、郑板桥紧随其后,邓石如、伊秉绶更是一代大家,颇多创见,一扫清初颓弱、单薄书风,给当时书坛带来一股强劲的碑派之风。
而活跃在乾嘉之际的大学者阮元则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提出书分南北。
“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把北派书风提到与以二王帖学为主的南派书风同等重要的地位,吹响了晚清尊碑大潮的号角。
其后包世臣接其衣钵,于书艺孜孜不倦,身体力行,著《艺舟双楫》,大力鼓吹北碑,咸、同以后北碑的盛行,斯翁实开其风气。
包世臣之后,对碑派书风统治地位的最终奠基起到重要作用的则是康南海长素,他于光绪十五年著成的《广艺舟双楫》六卷,极尽煽焰扬波之能事,提倡碑学,贬抑帖学,“尊碑”、“卑唐”之论,充斥全书,把清代碑学运动推向最高潮。
康有为(——一九二七),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
南海(今广东广州)人,人称“南海先生”。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
康有为一生著述甚丰,而《广艺舟双楫》,则是其对于清代书法理论的重要建树。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全面梳理书体变迁之迹,论其优劣得失,使碑学从阮、包的散论、札记式论述下脱离出来,渐成系统,遂成一科,其“尊碑”、“卑唐”之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康有为的“尊碑五说”是康有为“尊碑”、“卑唐”观点的直接阐述: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皆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
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广艺舟双楫·尊碑》。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六朝碑版给予热情洋溢的赞扬,同时他也不吝啬于对唐碑及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的批评,他认为“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
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二王帖学已经失去作为时代领航者的独尊地位。
而唐碑则磨之已坏,所以“不得不尊南、北朝也”。
且不说帖学是否真的走到如康氏所认为日薄西山的境地,仅就唐碑而言,恐怕必不尽如康氏所言的“磨之已坏”。
六朝碑版,可以“考隶楷之变”,可以“考后世之源流”,“各体皆备”,康有为是不是言重了?各体皆备,笔法为唐、宋所无,亦是否失之牵强?试分论之。
一、唐碑“磨之已坏”,南、北朝碑“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在“尊碑五说”中,康有为开头便讲“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帖学的翻坏是有晋以来帖学存在的真实状态,大不必论。
但是康氏讲唐碑的“磨之已坏”,却是大为值得商榷的。
通过翻阅资料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康有为的唐碑“磨之已坏”的断语是绝非符合历史真实的。
清代年间,朴学成为学术思想主流,考据训诂之风盛极,大量的碑版墓志被发现,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大量的唐代的碑版墓志,且其中精美者居多。
仅就《金石萃编》所载唐碑墓志就有四百余种,其它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赵之谦《寰宇访碑录补》等。
想以康有为当时的名望及影响力,其获观的碑帖拓片也必不少,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康有为昔日在京师时,几乎过目了当时所有的碑刻拓本。
那么,以康有为的学识和眼力,以及接触到的前人研究成果和碑刻拓本,为何会得出唐碑“磨之已坏”的结论呢?而事实是,康有为是以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对历史真实进行选择性“篡改”的。
因为他觉得唐碑“专讲结构,几若算子”便觉得学唐“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
”因为他觉得欧、颜、柳之碑刻“磨之已坏”,便断言唐碑“磨之已坏。
”这些更像是康有为个人主观好恶的随机宣泄。
康有为在“尊碑五说”中的第一说即是“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
”那么,正如以上所论,唐碑较之北碑实不遑多让。
如唐之《程夫人塔铭》,笔画完好、神完气足,试将其放在康有为中《广艺舟双楫·购碑》中所列举的一百九十七中六朝碑版中,在“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方面是不输任何一碑的。
从另一角度看,若论“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则六朝碑版与唐碑都不如帖学墨迹。
帖学中的短笺长卷,给我们提供一种最真实的书写状态,如怀素《自叙帖》、黄山谷《诸上座帖》、赵孟頫《洛神赋》、王铎大字挑山等等。
试想我们看过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墨迹本后,还会对石刻本产生多大的兴趣呢?所以,康有为以六朝碑版“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作为其“尊碑”的理由之一是不具有理论说服力的。
二、“可以考隶楷之变”、“可以考后世之源流”纵观《广艺舟双楫》洋洋洒洒六万余言,尊碑,尤其是尊南、北朝碑版是占全书的主体的。
在《购碑》一章中,康有为列举一百九十七种碑版,皆是南、北朝碑,《碑品》中所列七十七种亦是,至于康有为“十美”之论,也都是就南、北朝碑版而论的。
在康有为的眼中,南北朝碑版囊括了书法美感的一切特质,尽管今天看来康氏对于有些碑版的评价并不恰当。
一种书体的发展是历史的复杂综合,仅仅以康氏所尊的六朝碑版来考隶楷之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当我们审视某一书体的源流与嬗变时,需要综合各种因素,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到国家的法典颁布,小到一时一朝的丧葬制度,然后上追下溯,于源,于流加以全局性的考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真正的书体流变史,进而了解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
窃以为,考察整个隶、楷的演变过程,应该是综合性的。
至于南、北朝碑可以“考后世之源流”,则讳莫如深,令人不得要领。
如上所论,南、北朝尚不尽能考隶楷之变,何可考后世源流?康有为认为凡北朝刻石皆为佳者,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
”黄惇先生有论:“滥颂魏碑,以碑贬帖,遂使文化层次不分、文野不分、写刻不分、有法度之书与无法度之字不分。
这四个不分造成了对北朝书法的混乱认识。
”北朝石刻由于社会环境、文化基础、地域条件等的局限,从而导致大量低劣作品盛行。
康有为的盲目推崇北朝刻石,显然是与书法发展的规律相悖的。
三、“六朝碑各体毕备”、“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也康有为直言:“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各体毕备。
”细想,觉得这是康有为尊碑之论中最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的言语。
先言“唐言结构,宋尚意态”,紧接着云“六朝碑各体毕备。
”好像是说唐的结构,宋的意态,在六朝碑版中皆已囊括,岂不谬哉!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书风。
唐、宋不必包含南北,南北亦不必囊括唐、宋。
他们不是子与集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
又言六朝碑刻各种风格齐备。
试看:《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
《晖福寺》宽博若贤达之德。
”“《刁遵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
……《李仲璇》如乌衣子弟,神采超俊。
…….《凝禅寺》如曲江风度,骨气峻整。
…….《马鸣寺》若野竹过雨,轻燕侧风。
……在《碑评》中,康有为对所推崇的四十七种六朝碑版做出评价。
文辞优美,令人神往。
有动有静,有人有景。
但是,经过对这四十七种六朝碑版评价的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许多碑版的审美倾向是相似的。
像康对《刁遵志》、《李仲璇》、《高湛碑》、《敬显隽》、《南康简王》、《皇甫》、《朱君山》等,按照康有为的评价,这些碑版的美学倾向似乎更近于二王帖学的美学的特征;从另一方面讲,《碑评》中的对于六朝碑版的笼统而难以把握的评价,给我们认识六朝碑版的风格特征带来了困难。
像“西湖之水”、“乌衣子弟”、“曲江风度”,是何等语?因此,康有为对六朝碑版风格的厘清并不具有真正的参考意义。
六朝碑版各体毕备的结论也就缺乏理论的严密性与说服力。
康有为“尊碑五说”中认为六朝碑版用笔舒展有力,点画雄奇峻峭,令人目不暇接,是唐、宋所无法比拟的。
但是,一个事实我们应该看到,康有为的尊碑思想是建立在他认为一切北碑皆称佳品的基础之上的,是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的。
稚拙、卑陋的北朝石刻在康有为的眼中亦是美的、可学的。
而事实证明,北朝刻石中鱼龙混杂,良莠参半。
这是康有为的认知误区。
从另一种角度看,北朝刻石由于社会环境、文化基础、地理条件的局限,其质朴书风并非书家个体审美意识的自觉,优劣并存,带有强烈的书体及书风的不成熟标签。
而唐、宋书风的形成则是有其时代自觉审美意识的融入,它们给世人呈现的是不同的美学追求及美学意象。
不同时期的书风来相较高低优劣,其本身即是违背书法发展规律的做法。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的自序中说:“永惟作始于戊子之腊……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光绪十五也。
”由此知,康有为始作此书于光绪十四年,辗转于光绪十五年腊月整理旧稿,从腊月十七到除夕完稿成书。
可知,尽管有一年的旧稿积累,但是短短十三日的成书日期不亦匆匆乎?从传世刻本庞杂的谬误失检处可以看出,康氏在此书完成后,未予修改即付梓刊行,可见《广艺舟双楫》中的一些偏激、片面观点的产生,是有其原因的。
康有为在“尊碑五说”中对帖学,唐宋的贬斥,其实是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的。
为了圆满化碑学,康有为不惜以一种鄙夷的眼光来看待帖学。
而这实际上正是晚清倡碑书家学者的共同倾向,即碑眼看帖。
他们是以一种碑学观念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帖学的,而这实际上对于帖学及唐是有失公允与客观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康有为对帖学及唐人书法的误读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整个晚清碑学大势的浪潮汹涌难挡,使学人们为之倾倒。
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原书》中所言:“变者,天也。
”书学的“变”给予碑学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何况康有为一代大家,顺应趋势,领骚时代,自是当然;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局限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加以批判、纠正,只有这样,书学的发展才能是稳步与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