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茹志鹃及其百合花
- 格式:ppt
- 大小:2.30 MB
- 文档页数: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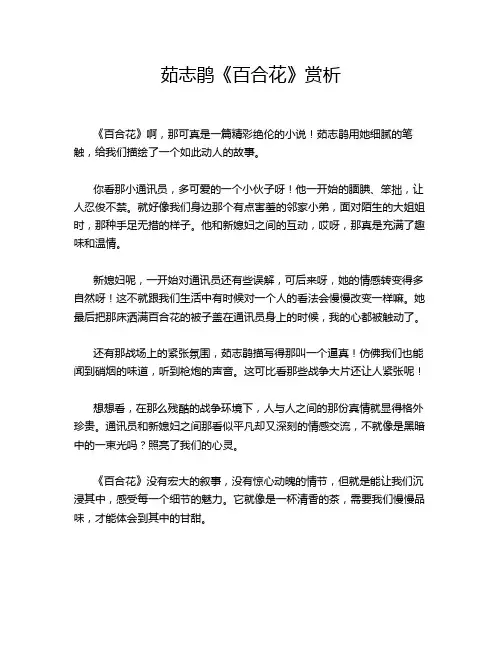
茹志鹃《百合花》赏析
《百合花》啊,那可真是一篇精彩绝伦的小说!茹志鹃用她细腻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如此动人的故事。
你看那小通讯员,多可爱的一个小伙子呀!他一开始的腼腆、笨拙,让人忍俊不禁。
就好像我们身边那个有点害羞的邻家小弟,面对陌生的大姐姐时,那种手足无措的样子。
他和新媳妇之间的互动,哎呀,那真是充满了趣味和温情。
新媳妇呢,一开始对通讯员还有些误解,可后来呀,她的情感转变得多自然呀!这不就跟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对一个人的看法会慢慢改变一样嘛。
她最后把那床洒满百合花的被子盖在通讯员身上的时候,我的心都被触动了。
还有那战场上的紧张氛围,茹志鹃描写得那叫一个逼真!仿佛我们也能闻到硝烟的味道,听到枪炮的声音。
这可比看那些战争大片还让人紧张呢!
想想看,在那么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真情就显得格外珍贵。
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那看似平凡却又深刻的情感交流,不就像是黑暗中的一束光吗?照亮了我们的心灵。
《百合花》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但就是能让我们沉浸其中,感受每一个细节的魅力。
它就像是一杯清香的茶,需要我们慢慢品味,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甘甜。
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战争中的人性光辉,看到了那些平凡人的伟大之处。
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爱和温暖也不会消失。
这不就是文学的力量吗?它能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生活的意义。
总之啊,《百合花》绝对是一篇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佳作,你要是还没读过,那可真是一大憾事呀!赶紧去读一读吧,相信你一定会被它深深吸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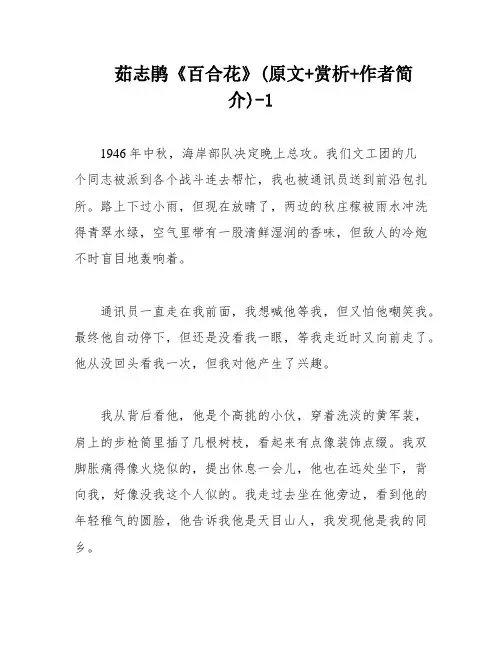
茹志鹃《百合花》(原文+赏析+作者简介)-11946年中秋,海岸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的几个同志被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忙,我也被通讯员送到前沿包扎所。
路上下过小雨,但现在放晴了,两边的秋庄稼被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空气里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但敌人的冷炮不时盲目地轰响着。
通讯员一直走在我前面,我想喊他等我,但又怕他嘲笑我。
最终他自动停下,但还是没看我一眼,等我走近时又向前走了。
他从没回头看我一次,但我对他产生了兴趣。
我从背后看他,他是个高挑的小伙,穿着洗淡的黄军装,肩上的步枪筒里插了几根树枝,看起来有点像装饰点缀。
我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提出休息一会儿,他也在远处坐下,背向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看到他的年轻稚气的圆脸,他告诉我他是天目山人,我发现他是我的同乡。
我随便地问他在家时干什么,他说他帮人拖毛竹。
我看了一眼他宽宽的肩膀,突然眼前浮现出一片竹海,海中央是一条盘旋而上的石级山道。
他肩上垫着一块老蓝布,扛着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着石级哗哗作响。
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生活,感到十分亲切。
我问他:“你多大了?”十九。
”参加革命有多长时间了?”一年。
”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感觉有些像审讯,但还是忍不住问了。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有结婚吧?”他脸上飞红,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带上的扣眼。
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我本想问他是否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好把话咽了下去。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始抬头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催促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开时,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用毛巾擦汗。
这是我的错,他走路时没有流一滴汗,但因为我与他交谈,他却出了一头大汗,我感到十分内疚。
我们到达包扎所时已经下午两点了。
这里离前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所小学里,六个房子组成了一个“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满了野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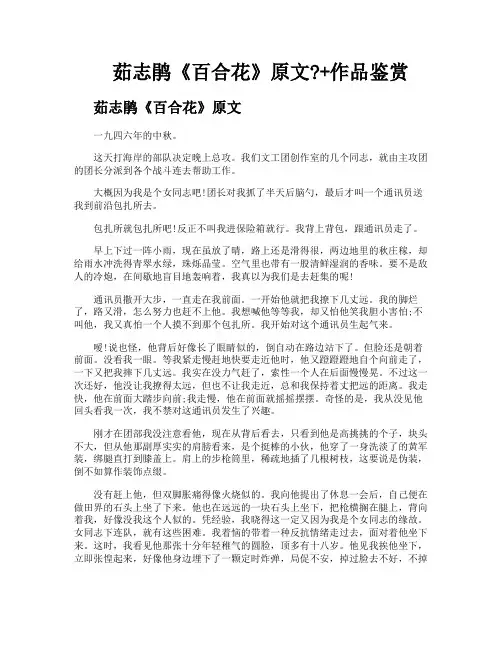
茹志鹃《百合花》原文?+作品鉴赏茹志鹃《百合花》原文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
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
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
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
但脸还是朝着前面。
没看我一眼。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
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
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
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
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
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茹志鹃与她的《百合花》作者:祖丁远来源:《同舟共进》2015年第06期这是一篇53年前采写著名女作家茹志鹃的访问记,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天才拿出来。
现经重新整理校订,与读者见面。
——耄耋之年的作者附言1962年7月,天气十分炎热。
我经历了被错划为“右派”、四年“劳教”、“摘帽”后,又被下放到出生地江苏启东。
从南京乘火车途经上海,我去上海文化会堂看望中学历史老师——时任《萌芽》文学杂志社的诗歌编辑汤茂林。
那天,我们除了谈师生情谊、别后情况外,还谈到上海一些作家、诗人的近况。
1958年以小说《百合花》一举成名的女作家茹志鹃,自然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于是,我产生了造访茹志鹃的想法。
过了几天,我按汤老师提供的地址,在淮海路找到了茹志鹃的家。
那是7月12日下午2点多,我敲门不久,出来开门的正是茹志鹃。
看样子她刚午睡起床,上身穿着黑丝绸短袖衫,下身穿的也是黑绸长裤,赤脚穿着一双黑色拖鞋;高挑身材,乍一看,似三十开外年纪,像只精悍的黑蝴蝶。
我向她说明来意后,她热情地让我进门。
我刚坐下,她就送上一杯凉开水,并对我说,芦芒(著名诗人、报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坚持在苏北一带为新四军办报、写诗、画画)刚从苏北回来,有不少新收获,你应该去釆访他。
《百合花》风波那天,我与茹志鹃的交谈,是从她的小说《百合花》开始的。
她是根据自己在新四军部队卫生队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以“我”和小通讯员的认识过程展开小说情节的。
她对我说,《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亊,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加工的;但小说里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
“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安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
那时候,我确实是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
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
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来越明亮,战斗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多数也是轻伤。
战斗越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是重伤员。

百合花茹志鹃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
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
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
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
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
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
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
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
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
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

百合花茹志鹃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
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
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
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
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
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
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
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
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
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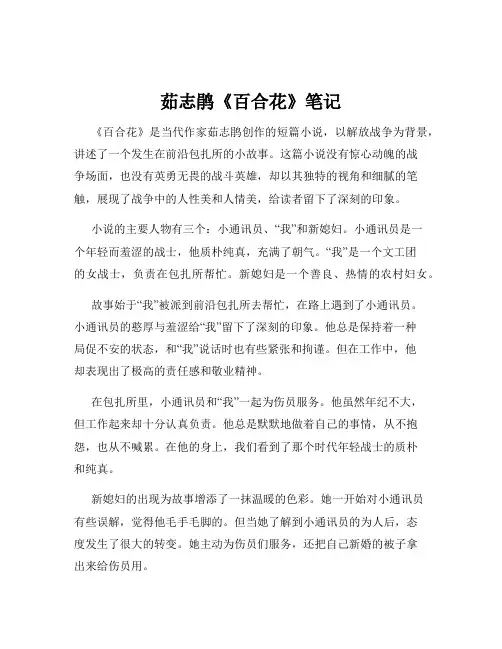
茹志鹃《百合花》笔记《百合花》是当代作家茹志鹃创作的短篇小说,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前沿包扎所的小故事。
这篇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也没有英勇无畏的战斗英雄,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的主要人物有三个:小通讯员、“我”和新媳妇。
小通讯员是一个年轻而羞涩的战士,他质朴纯真,充满了朝气。
“我”是一个文工团的女战士,负责在包扎所帮忙。
新媳妇是一个善良、热情的农村妇女。
故事始于“我”被派到前沿包扎所去帮忙,在路上遇到了小通讯员。
小通讯员的憨厚与羞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局促不安的状态,和“我”说话时也有些紧张和拘谨。
但在工作中,他却表现出了极高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在包扎所里,小通讯员和“我”一起为伤员服务。
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工作起来却十分认真负责。
他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从不抱怨,也从不喊累。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年轻战士的质朴和纯真。
新媳妇的出现为故事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
她一开始对小通讯员有些误解,觉得他毛手毛脚的。
但当她了解到小通讯员的为人后,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她主动为伤员们服务,还把自己新婚的被子拿出来给伤员用。
然而,不幸的是,小通讯员在一次战斗中为了保护战友而英勇牺牲。
新媳妇看到小通讯员的牺牲,悲痛万分。
她默默地为小通讯员擦拭身体,一针一线地缝补他衣服上的破洞,并把那床洒满百合花的新被子盖在了他的身上。
茹志鹃在《百合花》中运用了大量细腻的描写,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比如对小通讯员的外貌描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通过这样的描写,一个年轻、朴实的战士形象跃然纸上。
再如对新媳妇的描写:“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
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
”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了新媳妇的美丽和质朴。

百合花茹志鹃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
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
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
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
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
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
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
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
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
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

百合花茹志鹃1946 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
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
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
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
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
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
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
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
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
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

百合花茹志鹃1946 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
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
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
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
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
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
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
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
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
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

百合花茹志鹃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
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
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
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
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
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
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
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
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
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
百合花茹志鹃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
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
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
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
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
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
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
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
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
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这时,我看见他那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
百合花茹志鹃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
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
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
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
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
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
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
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
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
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
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
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
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
茹志鹃《百合花》《百合花》写于1958年的春天,这篇作品成就了茹志鹃,茅盾曾评论《百合花》,说:“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
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如今人们将茹志鹃与孙犁划为一列,认为茹志鹃与孙犁是创作风格相当接近的作家。
他们都不擅长于在强烈的行动中刻划人物,而往往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展现来把握人物的性格,他们的作品里都少有英雄人物形象,而更多的是普通人,即使写英雄人物,常也通过侧面去反映他们的先进,而不是正面讴歌他们。
他们尤其擅长写女性。
他们的作品色彩柔和,文字清新、俊逸。
《百合花》的抒情性较强,《百合花》里的前线包扎所,是茹志娟待惯了的地方,面对伤亡的战友,并给他们擦去尘土和鲜血,也曾经是茹志娟的工作。
月夜里看着自己的战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这份大悲大痛,大场面大事件,浓烟烈火,茹志娟却用诗一般的笔调娓娓道来,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风,自然、清丽。
读《百合花》,并没有感到那种战争的残酷,更多的有一些温柔,文中写到的小战士背后枪筒中的山菊花,让我莫名想到了班克西那副投掷花束的涂鸦,那是战争中的温柔,但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从女性文学的角度看茹志鹃的小说,其独特性显而易见。
茹志鹃的女性意识表现为关注女性的角色转换,并以人道情怀关注人自身的生命价值。
茹志鹃用女性的眉笔细腻展现了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心灵历程和情感变化,显示了茹志鹃在十七年时期作为女性作家的独特性。
当时的评论界难得从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角度来肯定茹志鹃的小说创作。
当时唯一鲜明地指出茹志鹃小说具有女性文学意义的是女作家冰心,她说:“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在作品中“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冰心还进一步指出女性写作的不可替代性,她说,她看了当时许多关于妇女先进人物的报道和描写,“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因此她说,读了茹志鹃的小说,“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百合花茹志鹃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
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朵野菊花。
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
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
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
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我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
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分头行动。
不一会儿,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哪一家?你带我去。
”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
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我们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地喊,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
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
我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
百合花茹志鹃①一九四六年的中秋,部队决定晚上发起总攻。
我们文工团的几个同志被分配到各个战斗连队帮助工作。
送我去的通讯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高挑挑的个子,厚实实的肩膀,一张稚气的圆脸。
他穿了一身淡淡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的插了几根树枝,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②我们刚到包扎所,卫生员就告诉我们,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
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
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送我来的那位通讯员帮忙,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③不一会,我就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
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④“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⑤“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⑥“哪一家?你带我去。
”⑦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
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地喊。
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
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
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
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
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
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
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地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
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
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
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⑧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⑨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
茹志鹃《百合花》(节选)阅读理解(四)阅读下面的内容,完成下面小题。
百合花茹志鹃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
主攻团的团长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支援。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
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儿向前走了。
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
很久没有赶上他,我的双脚胀痛得像火烧。
我向他提出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坐了下来。
他也在远远的地方坐下,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因为我是个女同志。
我着恼地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
他立即张皇起来,局促不安,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我们到了包扎所,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
不一会儿,我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却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的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哪一家?你带我去。
”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
我们走进院子里,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
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
我看她头上已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向她道歉。
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
她拿出来的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
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
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
①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
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