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乾盛世
- 格式:pdf
- 大小:219.96 KB
- 文档页数:5

康乾盛世的解释
康乾盛世是中国清朝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始于康熙帝在位时期,终于乾隆帝退位之际。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政治上,康乾盛世时期加强了中央集权,平定了三藩之乱、准噶尔部叛乱等重大事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同时,清朝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在经济上,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纺织业、陶瓷业和茶叶贸易等行业,成为了当时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
同时,清朝还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对外贸易,保护了国内市场和经济的发展。
在文化上,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文化艺术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如曹雪芹、纪昀、黄宗羲等。
同时,清朝还加强了对文化事业的管理和控制,实行了文字狱等措施,限制了思想和文化的自由发展。
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列举康乾盛世的具体表现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表现。
下面将从政治稳定、封建制度改革、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等几个方面来详细介绍康乾盛世的具体表现。
一、政治稳定康乾盛世是清朝乾隆、嘉庆和道光三位皇帝在位时期,他们统治期间政治相对稳定。
乾隆皇帝在位60年,嘉庆皇帝在位25年,道光皇帝在位22年。
这三位皇帝都有着强大的统治能力,他们除了加强对内政的控制,还大力加强对外战争的力度,使得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得到了保障。
二、封建制度改革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时期。
乾隆皇帝提出“治理天下,维持万世安宁”的理念,致力于加强封建制度的改革。
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改革,包括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员选拔制度、推行考试制度、修订法律等。
这些改革有效地提高了治理能力和政府效率,为国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经济繁荣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
康乾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十分活跃。
中国的商品出口量大幅增长,对外贸易顺差逐年增加。
同时,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四、科技进步康乾盛世是中国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
乾隆皇帝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亲自参与科技项目的研究和推广。
在他的支持下,许多重要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得以实现,如兵器制造、冶炼技术、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五、文化繁荣康乾盛世是中国文化繁荣的一个时期。
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期,中国的文化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皇帝们对文化艺术的支持和推广,使得文人墨客有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诗词、书画、戏曲、音乐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同时,乾隆皇帝还倡导修史和文献整理工作,使得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
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来看:康乾盛世时的帝王对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变革毫无认识.他们对外紧闭国门,对内压制打击工商业,厉行文化专制,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萌芽。
愚昧自大,固步自封的清帝国与西方强力量的对比速发生逆转。
从中国古代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完成国家统一,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
盛世是中国人不解的情结,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乱,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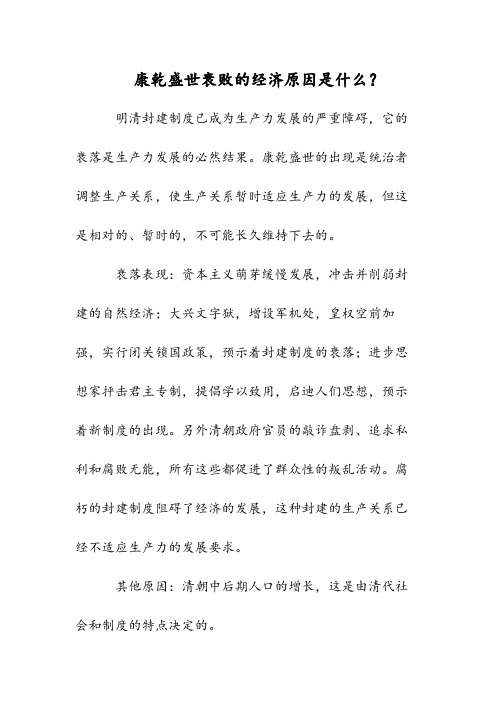
康乾盛世衰败的经济原因是什么?
明清封建制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它的衰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康乾盛世的出现是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暂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这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
衰落表现: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冲击并削弱封建的自然经济;大兴文字狱,增设军机处,皇权空前加强,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预示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进步思想家抨击君主专制,提倡学以致用,启迪人们思想,预示着新制度的出现。
另外清朝政府官员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腐败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
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其他原因:清朝中后期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
人口的大量增长,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资源短缺,同时,人们为了谋求生计,他们不得不寻找出路,这样就给政府部门带来了很大压力。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就可能造成社会动乱乃至农民起义。
如果政府机关要解决这些人口过剩问题就要分担出一部财力、物力、人力。
而政府本身冗员充斥,这样,政府就会越来越腐败,以致于清王朝日益衰败。

清朝康乾盛世的政治与经济清朝康乾盛世,被赋予了一个美好的称号,这个时期的政治与经济也发生着许多重要的变革。
不论是政权的稳定、治理的改革还是经济的繁荣,都为这段历史增光添彩。
一、政治改革在康乾时期,清朝政权日趋稳定,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完整。
乾隆治国之道坚持的是“道德正直、行法忠信、经世致用、垂直启戈”的理念,并通过晋升权贵子弟考取功名,使权贵家族的地位无可撼动。
同时,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积极推行双勘制度,倡导政务透明、廉洁政府。
他们积极设立文案、刑章等机构,不仅使各级政府能够了解和解决问题的实质,也使人民能够直接向政府反映问题。
此外,康乾时期重要的政治改革还包括加强军队管理、朝廷对外贸易、税收管理等方面的改革。
这些改革促使了清朝政权的巩固,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经济繁荣康乾时期是清朝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在政府的激励下,中国各地的经济活动蓬勃发展。
在农业方面,康乾时期实行了多种农业政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康乾时期积极发展水利工程,推广养蚕业和种茶业,并改良农具和农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同时,清朝政府还重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实行了减轻赋税、免除民科等政策,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商业方面,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的商业繁荣也让人瞩目。
康乾时期的中国,商品流通发达,商业发展迅猛,各类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吸引了大量商人和商品。
康乾时期的商业活动不仅为国家带来了财富,也促进了各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
此外,康乾时期也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康乾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工商业家,他们通过创新和发明,推动了许多行业的发展。
例如姚永年在纺织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仇英在煤炭业上的探索为中国的煤炭工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在康乾盛世的背景下,政治与经济相互促进,构建了中国的繁荣时期。
政治上的改革使得政府的执政能力得到提升,相应地政府也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清朝的康乾盛世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康乾盛世: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公元1644年-公元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康乾时期被视为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执政期间,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得以迅猛发展,给中国历史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一、康熙时期:夯实清朝基础康熙皇帝在位61年,对于清朝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在康熙时期,清朝夯实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康熙皇帝通过府院分开、三省六部制度、书院考试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巩固了清朝的政治体制,稳定了社会秩序。
康熙还大力倡导文化交流,提倡汉文化。
他亲自编辑了《康熙字典》,并修订了《南明九辩》、《六部丛书》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化著作,为后世整理汉文化经典奠定了基础。
康熙还赞助了很多学者,并与他们进行深入交流,为清朝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雍正时期:清朝政治和经济的转型康熙去世后,由雍正皇帝继位。
雍正皇帝执政时期,清朝经历了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转型。
雍正皇帝大力整顿政府机构,推行了许多改革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
他开展了许多反贪腐运动,整顿了政府机构,加强了清朝的统治力度。
在经济方面,雍正皇帝实行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他减少赋税,使得农民的负担减轻,同时还鼓励农民进行土地开垦,扩大农田面积。
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为国家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乾隆时期:国力达到巅峰乾隆皇帝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康乾时期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乾隆皇帝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地位。
他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了皇权,使得清朝政治更加稳定。
在经济方面,乾隆皇帝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
他鼓励商业,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了国内外商业的繁荣。
乾隆时期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乾隆还非常注重文化艺术的发展。
他热衷于收藏和赞助艺术品,并且亲自指导了很多艺术作品的制作。
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学繁荣与社会背景考察1. 引言1.1 概述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位于清朝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的统治时期。
这个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制度与等级观念的形成,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从康乾盛世时期的社会背景入手,分析政治稳定与国家发展、经济繁荣与商业兴盛以及社会制度与等级观念对于文学繁荣的影响。
接着,探讨文学繁荣的原因及特点,包括政府的支持与倡导、文化环境的培育与创新意识以及文学流派的多样性与发展。
然后,介绍康乾盛世时期一些代表作品,包括戏曲艺术、诗歌创作以及散文和小说的兴起和突破。
最后,总结文学繁荣带来的积极影响,并探讨康乾盛世对后世文学演变的影响力,并提出对当前文学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1.3 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学繁荣与社会背景的考察,深入了解该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影响力。
通过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因素对于文学繁荣的作用,进一步认识康乾盛世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同时,本文也试图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和启示,为当前的文学发展提供借鉴与思考。
2. 康乾盛世时期的社会背景2.1 政治稳定与国家发展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
由于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有力,清朝政权得以巩固和延续。
充满能力和智慧的康熙帝、雍正帝和乾隆帝,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使得国家逐渐恢复生机并实现了较为持续的发展。
他们注重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沟通,积极与各地方官员交流,并通过改革措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2 经济繁荣与商业兴盛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灌溉设施的完善,农民们取得了可观的收成,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同时,清朝向全国推广种植新作物如马铃薯、玉米等,并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此外,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商业蓬勃发展。
随着交通和运输系统的改善,贸易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康乾盛世何以由盛转衰康乾盛世,指的是清王朝前期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其出现的原因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明末清初的战乱,到了康熙年间逐渐稳定下来,生产开始恢复发展,于是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时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就在这样的盛世下,清朝的统治隐含着严重的危机。
当时的世界已经呈现出了走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如何应对这个历史巨变,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严峻选择。
而清朝统治者对此一无所知,继续在做着天朝大国的虚妄之梦。
康雍乾时期的盛世,只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社会的回光返照而没有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开辟出任何新的路径。
18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
到乾隆朝的中后期,大清帝国的统治迅速地由盛转衰。
经济上,清政府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和政策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已经根深蒂固),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依然是清朝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皇帝和皇室是全国最大的地主。
商品经济发展缓慢,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西方国家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发达,重商主义,开始工业革命。
政治上,清朝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而且开始腐败,在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各级官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日益昏庸腐朽,官场败绩与日俱增,政治日益黑暗,贪污贿赂成风,在中央出现了以和绅为代表的大贪官,地方上更有“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而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西欧封建国家改革。
与政治腐败相联系的是军备废弛,军力衰败。
八旗兵入关以后圈占土地,俸禄优厚,终日悠闲,承平日久,昔日骁勇骠悍的八旗兵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专募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也不堪言战。
总数达百余万人的清军已经丧失了保卫国家,抵御侵略的能力。
思想文化上,满族贵族实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政策。
清朝的康乾盛世最后的封建辉煌
康乾盛世是清朝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最后的繁荣时刻。
本文将探讨清朝康乾盛世的历史背景和封建辉煌的特点。
康乾盛世的历史背景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统治下的康乾盛世,是清朝历史上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辉煌的时期。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国力达到巅峰,国土扩张,政治制度稳定,社会秩序井然。
封建辉煌的特点
在康乾盛世时期,封建社会的辉煌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稳定,清朝实行专制制度,皇帝权力至高无上,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
其次是经济繁荣,康乾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海外贸易兴盛,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再者是文化繁荣,康乾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全盛时期,文学、绘画、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封建辉煌的影响与局限
封建社会的辉煌虽然给清朝带来了一定的繁荣与稳定,但也暴露出了种种矛盾和弊端。
封建制度的僵化使得社会变革受到限制,社会阶级固化,人民生活水平无法实现真正的提升。
康乾盛世时期的强盛也掩盖了清朝内部问题的积聚,为清朝最终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清朝康乾盛世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辉煌,展现了封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优越性和繁荣景象。
然而,封建辉煌的背后也隐藏着种种矛盾和弊端,最终导致了清朝的覆灭。
封建辉煌是历史的一页,我们应当从中汲取教训,不断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走向民主、平等、法治的现代化道路。
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历史研究与评论论 康 乾 盛 世周 武帝国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1644年4月25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北京皇宫后的煤山上吊自杀。
一个半月后,摄政王多尔衮以“为明复仇”的“义师”之名,亲率八旗子弟在京城耆老的“迎视”之下神速地占领了北京,取代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10月9日,年仅6岁的顺治帝正式从盛京移驾北京。
于是,雄居关外的大清国遂由一个边地汗国一跃而为中原王朝,帝国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入主中原之后,清朝立即面临两大严峻的挑战:一个来自中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另一个则来自满汉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冲突。
就前者而言,满人一向被视作蛮夷,因此,他们的入主中原在正统的视野中是“以夷猾夏”,并不代表“天命”所归。
就后者而言,满人是一个少数民族,汉人占绝对多数,以少数统治多数,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纯熟的运作技巧。
面对这两大桃战,清初统治者一方面致全力于中国的再次统一,并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
这个过程总体上说相当顺利,除了在江南遭遇比较持久酷烈的抵抗外,基本上是所向披靡,“传檄而定”。
随着长期军事征服的结束,以及“华夷联合”体制的确立,从康熙中期起,清朝便快速地步入一个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鼎盛时代。
这是帝国时代最恢宏的一个盛世。
这个盛世历康、雍、乾三朝,持续100多年。
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口、财力和事功等各个方面都超迈汉唐规模,并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
论疆域,比明朝扩大了一倍以上,且东西南朔,“四夷咸服”;论财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经济总量占居世界首位;论人口,从1700年到1794年的不足百年时间里已不止翻了一番,达3.13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论文化,则完成了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在内的“御纂诸书”;论城市,当时世界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即北京、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和广州……。
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曾比较中西,推断当日中国的“国家收入”是“英国总收入的四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三倍” 。
而1750年间,“中国一地所出版的书籍就比中国以外整个世界的总量为多” 。
这种量比,从一个侧面写照了盛世的国力和盛世的恢宏。
然而,这又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
实际上,从乾隆中叶开始,这个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盛世已渐渐暮气四起了。
1799年,乾隆驾崩,绵延百余年的盛世便随之一去不复返了,并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时代。
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语)。
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
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和使节在通商和传教的目的驱使下急速地向东方走来,但是,盛世中的君主却对外部世界的历史性变动浑然不知,更不屑于去知,甚至因“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干脆把大门关上,自外于世界。
诚如梁启超在1896年所说:“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
” 一方梯航而来,一方则深闭固拒。
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于是,西方列强便直接诉诸武力,用“坚船利炮”撞破了闭锁的大门,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原有地位。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在毫无应变准备的情况下步入了一个墙倾壁碎的时代。
从18世纪晚期的全盛到19世纪中叶的墙倾壁碎,相距不过50多年。
本来,日中则昃,泰极否来,乃事理之常。
但是,清朝前后期的变化过程已远远超出了所谓“事理之常”,它所包含的沉痛的悲剧意味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费正清教授曾意味深长地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
” 盛衰之变,犹如倚伏。
清朝缔造了“从来所罕有”的百年盛世,而盛世的辉煌又遮蔽了社会内部的衰变。
当盛世天子失却对衰变的警觉的时候,中衰之世便开始浮出水面了。
盛世的声光竟如此奇特地成为一种侵蚀并最终摧毁盛世的力量,还有什么比这种盛衰之变更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呢?盛世下的平庸化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家,必定是一个人才蔚起的国家。
而人才的蔚起,不仅需要宽松的精神气候,更需要鼓励创新的制度保障。
但在康乾盛世,我们看到的不是精神上的宽松,不是制度上的创新,而是“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在精神上日趋蜷缩,并越来越远地疏离了二千年儒学涵育出来的担当世运之气”。
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在那本出色的描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书中认为,乾隆时代的制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禁止革新”,他说:“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
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
” 用龚自珍的话说,就是“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可破之例”,这些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的陈年旧“例”,使整个社会陷于“不闻余言,但闻鼾声”的沉睡状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康熙,特别是雍正与乾隆,以君权的力量收拾和整肃朝野士人的思想,制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于是“诸儒结舌”,噤若寒蝉,惟恐因文字和思想致罪,志节之士因此而荡然无存,“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和社会的良心,当他们思考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所谓革新也就变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而禁止革新,又势必导致帝国的停滞和士气民心的萎顿,于是而有盛世下的平庸化。
龚自珍的《乙丙之际箸议》“引公羊义讥切时政”,力纠雍正、乾隆以来文人不敢议论时政的死寂气氛。
其中有一篇专论人才,读来极耐人寻味 。
龚自珍的文章写于1815到1816年间,但他针砭的则是前此百余年的所谓“盛世”。
读了这篇文章,几乎不需要再说什么你就能明白,“治世”假象下的“衰世”的实质;你也就能明白,龚自珍为什么要那样力竭声嘶地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个“戮心的盛世”里,文祸绵延,朝野士人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不测之祸。
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盛世中的朝野士人与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也就离得越来越远了。
用刑法来界定思想的是非,恐惧也就自然而然地取代了好奇、想象和创造。
当恐惧取代了好奇、想象和创造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一个没有议论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盛世,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像康乾盛世这样文网密织,深文周纳。
在冷酷的思想整肃下,已难听到人们的笑声,自晚明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出现的趋向自由奔放的新气象也荡然无存了。
读书人的思考日益远离四海治乱、民生利病,学术与现实完全脱节。
由此,“他们在另一种世路中趋入了另一种士风”,于是而有所谓朴学时代。
在这个时代,以考据为功夫的实证和博证,在经学、朴学、汉学、古学、实学的名目下蔚为一时显学。
全盛时期,曾涌现出惠栋、戴震、姚鼐那样声名赫赫的考据学大家。
在他们的影响下,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
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承惠学;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承戴学;管同、梅曾亮、方东树等承姚学。
此外,全祖望、章学诚、赵翼、邵晋涵等又异军突起,以史学名家。
他们以自己实实在在的功夫累积起可观的学术成果。
然而,当“穷经考礼”成为显学的时候,这些人又在精神上和学术上日趋偏狭。
从理学到朴学,自有其“内在理路”。
杨国强在《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一文中曾对这种“内在理路”做过缜密的疏理,其中写道:“就学术史自身的脉理而言,儒学既有‘尊德性’的一面;也有‘道问学’的一面。
从宋人到明人,‘尊德性’的一面曾绵延地辉煌了六百余年,‘至于阳明良知之论,鞭辟近里,已达极度’。
‘极度’是理路的巅峰,也是理路的止境。
出现在巅峰和止境后面的实证精神因之而成为一种转捩,它所代表的儒学中‘道问学’一面,在长久沉寂之后遂为天下学术别开生面。
实证精神内含的这些历史合理性,使他能够以学术本身的力量吸引一批一批的学问中人;而文字狱造成的触笔即犯时讳,又会使原本别有抱负的英达之士自愿或不自愿地走入实证精神里,去亲近这种用不着议论的学问。
” 这两路人的合流作育了学术史上的朴学时代。
但是,朴学之成为显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君权的逼拶。
正是在君权的逼拶之下,举国士人除了奉旨编纂所谓“御纂诸书”(如卷帙浩繁的《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那样的文化巨制)者外,率多不得已而群趋于考礼说经一途。
这种远离现实的学问固然可以增添盛世的文华,却不能回应衰世的忧患。
因此,朴学发皇之时,国家却步入江河日下、危机四伏的时代。
没有“发展”的增长衡量盛世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经济的繁荣与否。
从康熙中叶开始,社会经济快速复苏,并进入一个鼎盛时代,历康、雍、乾三朝。
在这一个多世纪里累积起来的人口、物力和事功已迈过汉唐规模,为周秦以来的中国历史再造了一个高峰。
盛世中那令“四夷咸服”的武功无论矣,单就人丁的兴旺和经济的富庶而言,在帝国历史上也可以说是“从来所罕有”的。
其表现为:(一)天下承平,生齿日繁,人口剧增。
据《东华录》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
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以一户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隐瞒未报的人口,实际的总人口大约在6000万上下。
到康熙晚年已突破1亿,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猛增至3亿以上,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超过4亿。
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6倍以上。
人口众多,曾给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成员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写道:“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一哩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
” (二)地耕种面积不断扩大。
康熙初年只有530万顷,雍正二年(1724年)已增至720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又增加到780余万顷。
(三)受恤商政策的推动,商业持续繁荣。
清初曾经“六门紧闭,城中死者相枕藉”的苏州,到康熙中叶,已是“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阊门内外居货山堆,行人流水”;即使是远在东北边陲的宁古塔,亦“商贾大集”,“街市充溢”。
(四)与商业繁荣相对应,手工业空前兴盛。
具体表现在:生产规模明显扩大,工艺技术有所改进,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从业人数大幅度增加。
据统计,南京丝织业全盛时,城内有缎机3万台,而以缎业为生者就达20万人之多。
(五)新兴市镇星罗棋布,江南地区尤为发达。
与传统的消费型市镇不同,这些市镇多属于和工商业生产直接有关的新兴市镇。
(六)财政收入显著增加。
康熙晚年国库存银仅800万两,到雍正五年即增至5000万两,晚年因西北两路用兵,花费甚大,库存有所下降,但仍有3000余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