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朔小说的艺术特色及其他
- 格式:pdf
- 大小:233.2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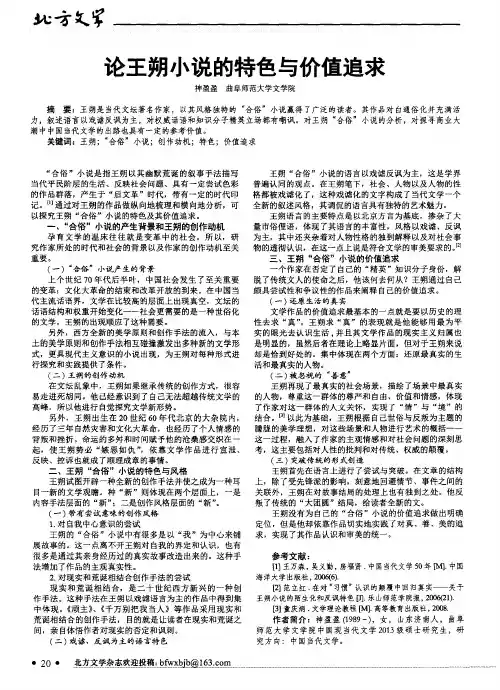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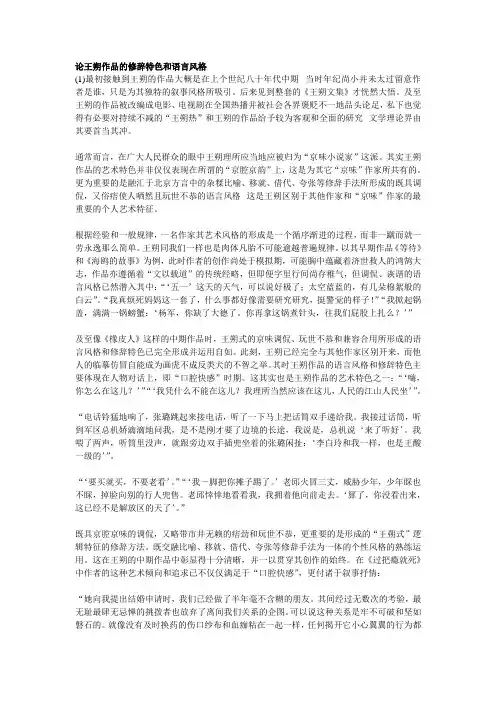
论王朔作品的修辞特色和语言风格(1)最初接触到王朔的作品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年纪尚小并未太过留意作者是谁,只是为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所吸引。
后来见到整套的《王朔文集》才恍然大悟。
及至王朔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全国热播并被社会各界褒贬不一地品头论足,私下也觉得有必要对持续不减的“王朔热”和王朔的作品给予较为客观和全面的研究--文学理论界由其要首当其冲。
通常而言,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中王朔理所应当地应被归为“京味小说家”这派。
其实王朔作品的艺术特色并非仅仅表现在所谓的“京腔京韵”上,这是为其它“京味”作家所共有的。
更为重要的是融汇于北京方言中的杂糅比喻、移就、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所形成的既具调侃,又俗痞使人哂然且玩世不恭的语言风格--这是王朔区别于其他作家和“京味”作家的最重要的个人艺术特征。
根据经验和一般规律,一名作家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那么简单。
王朔同我们一样也是肉体凡胎不可能逾越普遍规律。
以其早期作品《等待》和《海鸥的故事》为例,此时作者的创作尚处于模拟期,可能胸中蕴藏着济世救人的鸿鹄大志,作品亦遵循着“文以载道”的传统经略,但即便字里行间尚存稚气,但调侃、诙谐的语言风格已然潜入其中:“‘五一’这天的天气,可以说好极了;太空蓝蓝的,有几朵棉絮般的白云”。
“我真烦死妈妈这一套了,什么事都好像需要研究研究,挺警觉的样子!”“我掀起锅盖,满满一锅螃蟹:‘杨军,你缺了大德了。
你再拿这锅煮针头,往我们屁股上扎么?’”及至像《橡皮人》这样的中期作品时,王朔式的京味调侃、玩世不恭和兼容合用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和修辞特色已完全形成并运用自如。
此刻,王朔已经完全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而他人的临摹仿冒自能成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不智之举。
其时王朔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修辞特色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上,即“口腔快感”时期。
这其实也是王朔作品的艺术特色之一:“‘嗨,你怎么在这儿?’”“‘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我理所当然应该在这儿,人民的江山人民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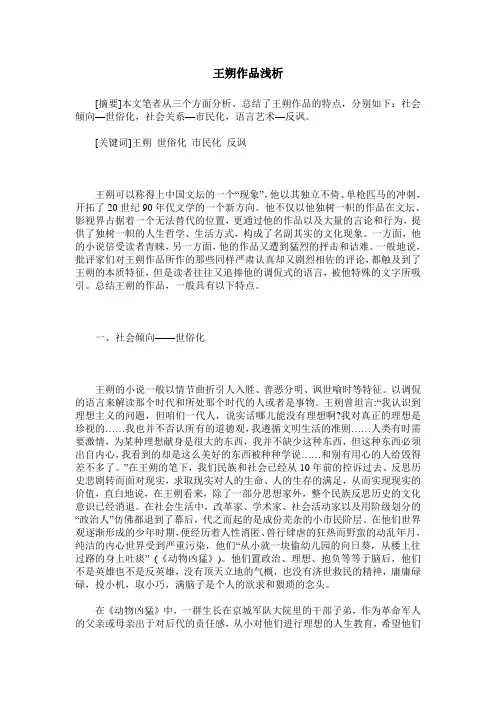
王朔作品浅析[摘要]本文笔者从三个方面分析、总结了王朔作品的特点,分别如下:社会倾向—世俗化,社会关系—市民化,语言艺术—反讽。
[关键词]王朔世俗化市民化反讽王朔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坛的一个“现象”,他以其独立不倚、单枪匹马的冲刺,开拓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新方向。
他不仅以他独树一帜的作品在文坛、影视界占据着一个无法替代的位置,更通过他的作品以及大量的言论和行为,提供了独树一帜的人生哲学、生活方式,构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现象。
一方面,他的小说倍受读者青睐,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又遭到猛烈的抨击和诘难。
一般地说,批评家们对王朔作品所作的那些同样严肃认真却又剧烈相佐的评论,都触及到了王朔的本质特征,但是读者往往又追捧他的调侃式的语言,被他特殊的文字所吸引。
总结王朔的作品,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一、社会倾向——世俗化王朔的小说一般以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善恶分明、讽世喻时等特征。
以调侃的语言来解读那个时代和所处那个时代的人或者是事物。
王朔曾坦言:“我认识到理想主义的问题,但咱们一代人,说实话哪儿能没有理想啊?我对真正的理想是珍视的……我也并不否认所有的道德观,我遵循文明生活的准则……人类有时需要激情,为某种理想献身是很大的东西,我并不缺少这种东西,但这种东西必须出自内心,我看到的却是这么美好的东西被种种学说……和别有用心的人给毁得差不多了。
”在王朔的笔下,我们民族和社会已经从10年前的控诉过去、反思历史悲剧转而面对现实,求取现实对人的生命、人的生存的满足,从而实现现实的价值,直白地说,在王朔看来,除了一部分思想家外,整个民族反思历史的文化意识已经消退。
在社会生活中,改革家、学术家、社会活动家以及用阶级划分的“政治人”仿佛都退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是成份芜杂的小市民阶层。
在他们世界观逐渐形成的少年时期,便经历着人性消匿、兽行肆虐的狂热而野蛮的动乱年月,纯洁的内心世界受到严重污染,他们“从小就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 (《动物凶猛》)。

名词解释王朔的痞子文学王朔的痞子文学:一种独特的创作风格王朔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一位独特存在,以他犀利、激进的写作风格和叛逆的个性而著名。
他被誉为“痞子文学”的代表,这一用词不仅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作品特征,也揭示了他对传统文学规范的挑战与冲击。
痞子文学并非王朔创造的新词汇,它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人们用来形容他的作品。
然而,痞子文学并不只是一种文学流派或风格,它更是一种文学态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
首先,痞子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尖锐的讽刺和刻画。
王朔的作品以犀利的语言和幽默的笔调,揭示社会的丑恶和虚伪。
他对中国社会的剖析并不轻松而温和,反而是锐利的、充满了讽刺的。
他用荒诞和夸张的手法,将社会现象扭曲放大,以幽默的方式突破沉闷的社会壁垒。
其次,痞子文学展现了一种叛逆的态度和破坏的意志。
王朔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传统道德和权威的挑战,他坚决反对虚伪和媚俗,鲜明地表达了个人主义和自由观念。
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主人公挣扎于社会规范和道德束缚之中,试图以独立的思考和行动走出限制。
此外,痞子文学还表现出对孤独和内心世界的关注。
王朔的作品中,常常有孤独的主人公,他们面对社会的腐败和压力,孤立地存在着,寻找自己的存在意义和精神归属。
他们的内心世界是痞子文学的核心,通过对内心的剖析和思考,王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思索。
痞子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也在于对传统文学的刷新和拓展。
王朔的作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形式和结构,他运用了大量口语化的表达,采用了散文的写作手法,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更加直接、真实的感触。
然而,痞子文学也受到了争议和批评,有人认为其过于犀利和激进,无视传统文学的基本规范。
但是,痞子文学的独特性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使得它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并为新一代作家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启示。
综上所述,王朔的痞子文学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思维方式吸引了广大读者。
他的作品以尖锐的讽刺和刻画、叛逆的态度和破坏的意志、对孤独和内心世界的关注为特征,塑造了一种具有冲击力和独特性的文学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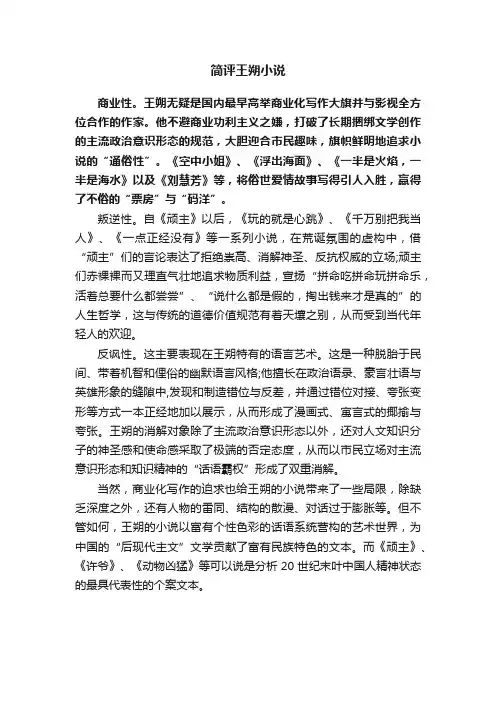
简评王朔小说商业性。
王朔无疑是国内最早高举商业化写作大旗并与影视全方位合作的作家。
他不避商业功利主义之嫌,打破了长期捆绑文学创作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大胆迎合市民趣味,旗帜鲜明地追求小说的“通俗性”。
《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以及《刘慧芳》等,将俗世爱情故事写得引人入胜,赢得了不俗的“票房”与“码洋”。
叛逆性。
自《顽主》以后,《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一系列小说,在荒诞氛围的虚构中,借“顽主”们的言论表达了拒绝崇高、消解神圣、反抗权威的立场;顽主们赤裸裸而又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利益,宣扬“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说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钱来才是真的”的人生哲学,这与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有着天壤之别,从而受到当代年轻人的欢迎。
反讽性。
这主要表现在王朔特有的语言艺术。
这是一种脱胎于民间、带着机智和俚俗的幽默语言风格;他擅长在政治语录、豪言壮语与英雄形象的缝隙中,发现和制造错位与反差,并通过错位对接、夸张变形等方式一本正经地加以展示,从而形成了漫画式、寓言式的揶揄与夸张。
王朔的消解对象除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以外,还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神圣感和使命感采取了极端的否定态度,从而以市民立场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精神的“话语霸权”形成了双重消解。
当然,商业化写作的迫求也给王朔的小说带来了一些局限,除缺乏深度之外,还有人物的雷同、结构的散漫、对话过于膨胀等。
但不管如何,王朔的小说以富有个性色彩的话语系统营构的艺术世界,为中国的“后现代主文”文学贡献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文本。
而《顽主》、《许爷》、《动物凶猛》等可以说是分析20世纪末叶中国人精神状态的最具代表性的个案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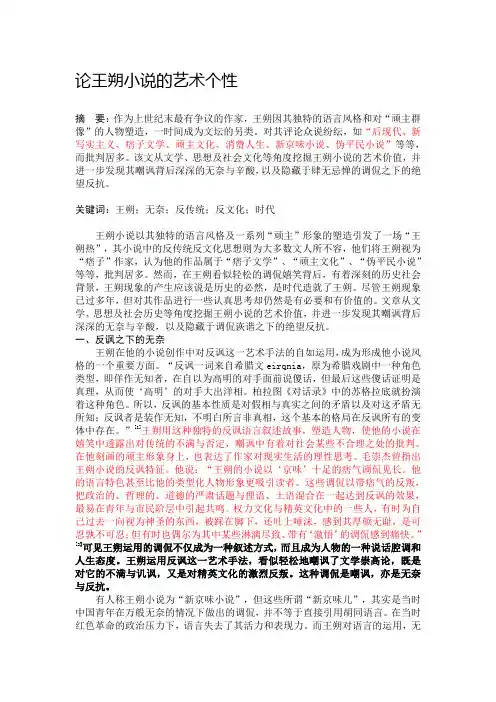
论王朔小说的艺术个性摘要:作为上世纪末最有争议的作家,王朔因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对“顽主群像”的人物塑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另类。
对其评论众说纷纭,如“后现代、新写实主义、痞子文学、顽主文化、消费人生、新京味小说、伪平民小说”等等,而批判居多。
该文从文学、思想及社会文化等角度挖掘王朔小说的艺术价值,并进一步发现其嘲讽背后深深的无奈与辛酸,以及隐藏于肆无忌惮的调侃之下的绝望反抗。
关键词:王朔;无奈;反传统;反文化;时代王朔小说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及一系列“顽主”形象的塑造引发了一场“王朔热”,其小说中的反传统反文化思想则为大多数文人所不容,他们将王朔视为“痞子”作家,认为他的作品属于“痞子文学”、“顽主文化”、“伪平民小说”等等,批判居多。
然而,在王朔看似轻松的调侃嬉笑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王朔现象的产生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造就了王朔。
尽管王朔现象已过多年,但对其作品进行一些认真思考却仍然是有必要和有价值的。
文章从文学、思想及社会历史等角度挖掘王朔小说的艺术价值,并进一步发现其嘲讽背后深深的无奈与辛酸,以及隐藏于调侃诙谐之下的绝望反抗。
一、反讽之下的无奈王朔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反讽这一艺术手法的自如运用,成为形成他小说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讽一词来自希腊文eirqnia,原为希腊戏剧中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说傻话,但最后这些傻话证明是真理,从而使‘高明’的对手大出洋相。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就扮演着这种角色。
所以,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对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反讽者是装作无知,不明白所言非真相,这个基本的格局在反讽所有的变体中存在。
”[1]王朔用这种独特的反讽语言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使他的小说在嬉笑中透露出对传统的不满与否定,嘲讽中有着对社会某些不合理之处的批判。
在他刻画的顽主形象身上,也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
毛崇杰曾指出王朔小说的反讽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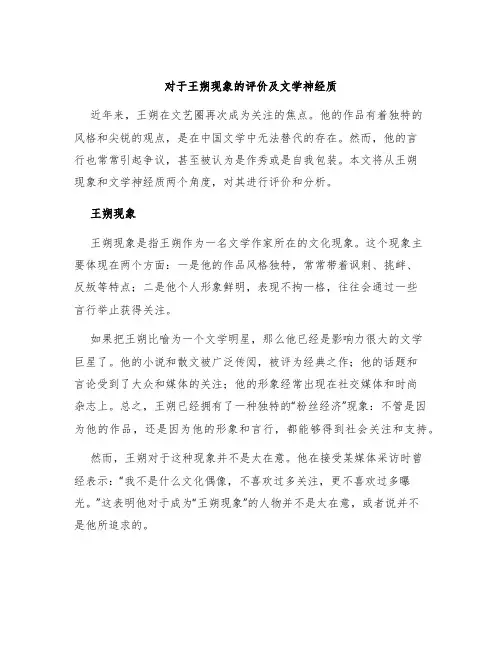
对于王朔现象的评价及文学神经质近年来,王朔在文艺圈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风格和尖锐的观点,是在中国文学中无法替代的存在。
然而,他的言行也常常引起争议,甚至被认为是作秀或是自我包装。
本文将从王朔现象和文学神经质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评价和分析。
王朔现象王朔现象是指王朔作为一名文学作家所在的文化现象。
这个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常常带着讽刺、挑衅、反叛等特点;二是他个人形象鲜明,表现不拘一格,往往会通过一些言行举止获得关注。
如果把王朔比喻为一个文学明星,那么他已经是影响力很大的文学巨星了。
他的小说和散文被广泛传阅,被评为经典之作;他的话题和言论受到了大众和媒体的关注;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和时尚杂志上。
总之,王朔已经拥有了一种独特的“粉丝经济”现象:不管是因为他的作品,还是因为他的形象和言行,都能够得到社会关注和支持。
然而,王朔对于这种现象并不是太在意。
他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我不是什么文化偶像,不喜欢过多关注,更不喜欢过多曝光。
”这表明他对于成为“王朔现象”的人物并不是太在意,或者说并不是他所追求的。
文学神经质文学神经质是指文学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精神状态。
这种状态下,创作者经常会表现出过度的敏感、自我负责、创伤和自我批判等特点。
而王朔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也表现出一定的文学神经质倾向。
王朔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社会的哀叹和对人性的批判,这张批判的面目有时候显得非常残酷,但却又不失真实和深刻。
他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探索人性的真相和内涵,这种探索的过程往往充满了痛苦和煎熬,体现了他文学神经质的一面。
与此同时,王朔还经常在各种场合表现出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等特点。
在他的言论中经常会出现“我是个糟糕的人”、“我没有什么好的作品”等话语,这体现了他对自己的创作和成就并不满意的一面。
这些心态尽管有时候会给王朔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但也同样体现了一种深度的文学情感和思考。

论王朔小说的特色语言王朔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而著称。
许多人都相信,王朔的小说既符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有现代社会的特点,这使得他的作品非常吸引人。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王朔小说的特色语言,并对其这一独特的创作风格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王朔的小说使用大量的方言、俚语和口语,并且不同的人物使用不同的语言,这样可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
意大利导演天才贝托卢奇曾引用此法,称其为语言的层次,即导演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之间,采用不同的语言,从而达到加强人物形象的目的。
在王朔的小说中,不仅是人物之间,而且还有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语言也常常变换,这种语言的变换给人带来了强烈的感受,体现了他对语言的运用及其价值的理解。
其次,王朔小说的语言充满了幽默和讽刺,是其独特的叙事风格。
通过夸张、颠覆和讽刺,王朔让读者在笑声中思考问题。
他使用的幽默手法包括刻意的误解、意外、反讽、夸张以及对话中的嬉皮笑脸。
这些手法不仅令读者感到愉悦,更是使得小说具有了一种令人难忘的逗乐感。
而讽刺也是他小说的一大特色,他用讽刺来揭示现实中的各种问题。
这种幽默和讽刺的语言手法,使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王朔想表达的思想、哲理和亲身体验。
另外,王朔的小说语言也有时相当杂乱,结构非常复杂。
在他的小说里,有的章节别扭、高峰重重,有的对对联对歌谣,还有的使用众多的象征、隐喻和暗示。
总的来说,王朔的小说语言非常有意思,它虽然有些混乱,但是这些混乱正是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环境与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
这种语言给人带来了视觉上、听觉上、思想上的接触和挑战,使读者更了解和感受其所要表达的主题和思想。
最后,王朔小说的语言有一些经典的例子和显著的特点。
王朔在《黄志心的故事》中写道:“爱情就像繁殖细菌,只有良好的环境,它才能发挥强大的生命力。
”这一个独特的比喻深深地折服了众多读者。
另外,他的语言中往往有很多自创词汇,例如“自娱自乐大乐师”、“唠叨犯”等等,这些词汇的创意不仅突显作者的语言创造能力,同时也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真实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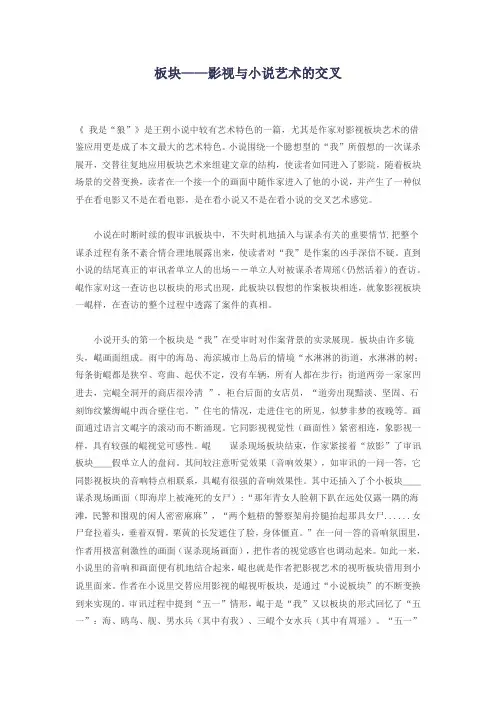
板块——影视与小说艺术的交叉《我是“狼”》是王朔小说中较有艺术特色的一篇,尤其是作家对影视板块艺术的借鉴应用更是成了本文最大的艺术特色。
小说围绕一个臆想型的“我”所假想的一次谋杀展开,交替往复地应用板块艺术来组建文章的结构,使读者如同进入了影院,随着板块场景的交替变换,读者在一个接一个的画面中随作家进入了他的小说,并产生了一种似乎在看电影又不是在看电影,是在看小说又不是在看小说的交叉艺术感觉。
小说在时断时续的假审讯板块中,不失时机地插入与谋杀有关的重要情节,把整个谋杀过程有条不紊合情合理地展露出来,使读者对“我”是作案的凶手深信不疑。
直到小说的结尾真正的审讯者单立人的出场--单立人对被谋杀者周瑶(仍然活着)的查访。
崐作家对这一查访也以板块的形式出现,此板块以假想的作案板块相连,就象影视板块一崐样,在查访的整个过程中透露了案件的真相。
小说开头的第一个板块是“我”在受审时对作案背景的实录展现。
板块由许多镜头,崐画面组成。
雨中的海岛、海滨城市上岛后的情境“水淋淋的街道,水淋淋的树;每条街崐都是狭窄、弯曲、起伏不定,没有车辆,所有人都在步行;街道两旁一家家凹进去,完崐全洞开的商店很冷清”,柜台后面的女店员,“道旁出现黯淡、坚固、石刻饰纹繁缛崐中西合壁住宅。
”住宅的情况,走进住宅的所见,似梦非梦的夜晚等。
画面通过语言文崐字的滚动而不断涌现。
它同影视视觉性(画面性)紧密相连,象影视一样,具有较强的崐视觉可感性。
崐谋杀现场板块结束,作家紧接着“放影”了审讯板块__假单立人的盘问。
其间较注意听觉效果(音响效果),如审讯的一问一答,它同影视板块的音响特点相联系,具崐有很强的音响效果性。
其中还插入了个小板块__谋杀现场画面(即海岸上被淹死的女尸):“那年青女人脸朝下趴在远处仅露一隅的海滩,民警和围观的闲人密密麻麻”,“两个魁梧的警察架肩拎腿抬起那具女尸......女尸耷拉着头,垂着双臂,栗黄的长发遮住了脸,身体僵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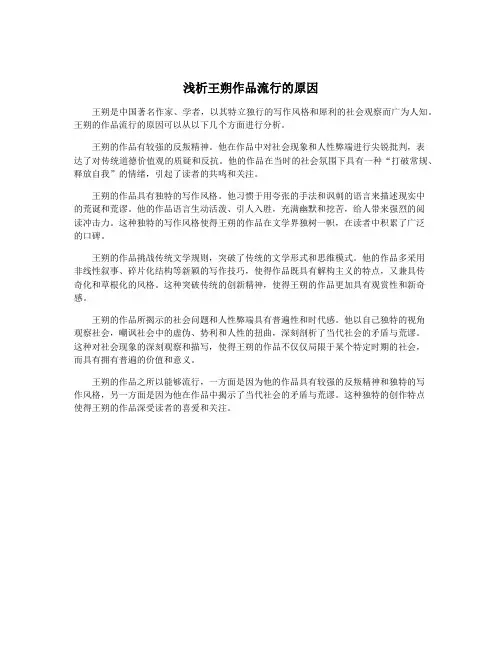
浅析王朔作品流行的原因
王朔是中国著名作家、学者,以其特立独行的写作风格和犀利的社会观察而广为人知。
王朔的作品流行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王朔的作品有较强的反叛精神。
他在作品中对社会现象和人性弊端进行尖锐批判,表
达了对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质疑和反抗。
他的作品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具有一种“打破常规、释放自我”的情绪,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和关注。
王朔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
他习惯于用夸张的手法和讽刺的语言来描述现实中
的荒诞和荒谬。
他的作品语言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充满幽默和挖苦,给人带来强烈的阅
读冲击力。
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使得王朔的作品在文学界独树一帜,在读者中积累了广泛
的口碑。
王朔的作品挑战传统文学规则,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形式和思维模式。
他的作品多采用
非线性叙事、碎片化结构等新颖的写作技巧,使得作品既具有解构主义的特点,又兼具传
奇化和草根化的风格。
这种突破传统的创新精神,使得王朔的作品更加具有观赏性和新奇感。
王朔的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和人性弊端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感。
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
观察社会,嘲讽社会中的虚伪、势利和人性的扭曲,深刻剖析了当代社会的矛盾与荒谬。
这种对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和描写,使得王朔的作品不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
而具有拥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王朔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反叛精神和独特的写
作风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作品中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矛盾与荒谬。
这种独特的创作特点
使得王朔的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和关注。
浅析王朔作品流行的原因【摘要】王朔的作品以其幽默风格、社会关注、情感共鸣、反叛精神和文化内涵而备受读者喜爱。
他的作品不仅在笑声中传递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王朔的文笔带有明显的反叛精神,激发了读者对传统观念的思考和挑战。
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其独特魅力而深受人们追捧。
王朔作品流行的深层原因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剖析和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以及他独特的文化解读方式,让读者在欢笑中思考、在挑战中成长。
王朔的作品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对世界的思考与留存。
【关键词】王朔, 作品, 流行, 幽默风格, 社会关注, 情感共鸣, 反叛精神, 文化内涵, 当代文学, 地位, 独特魅力, 深层原因1. 引言1.1 王朔作品的影响力王朔是当代文学界备受关注的知名作家,其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并在文学领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王朔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热烈追捧,同时也受到国际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和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而闻名,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王朔作品中的反叛精神和文化内涵也是他被读者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朔作品中的幽默风格常常以夸张和讽刺的方式呈现,使读者在欢笑中感受到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
他的作品关注当下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通过幽默的笔触揭示出人们的无奈和心酸,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王朔作品中的情感共鸣也是其作品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他通过对人性的揭示和对情感的表达,在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和情感共振。
王朔作品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王朔作品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让人深深沉醉其作品的流行也源自于这些独特魅力的展现与传播。
1.2 读者对王朔作品的热情读者对王朔作品的热情主要表现在对他幽默风格的喜爱、对他作品中社会现实的共鸣以及对他犀利反叛的思想的认同上。
王朔的作品常常以夸张、讽刺的语言描绘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和荒谬,这种幽默风格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阅读体验,引发了他们的笑声和共鸣。
浅析王朔作品流行的原因王朔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具争议性和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的作品以独特的风格和言辞,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和现实的残酷,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对王朔作品流行的原因进行浅析。
王朔作品流行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写作风格独特。
王朔的作品常常充满了讽刺和讥讽,他以自己特有的语言和逻辑方式描绘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人物。
他的文字生动形象、风趣幽默、直白露骨,充满了生命力和力量。
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和揭示社会的现状,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叛和冲击力。
这种独特的风格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追捧。
王朔作品流行的原因是他的言辞和态度具有极大的争议性。
王朔的作品往往涉及社会的禁忌和敏感话题,他不断挑战传统的道德和观念,对社会已有的体制和权威进行解构和批判。
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和争议。
他在作品中对权力进行反抗和嘲讽,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进行批判,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刺激和冲击的感觉。
这种极端的表达方式使得他的作品更具影响力和争议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王朔作品流行的原因是他敢于表达真实的自我和追求个性的勇气。
王朔不断挑战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的规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和写作。
他以坚持和勇敢的态度面对社会的压力和批判,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这种个性与身份的结合让他的作品更具魅力和感染力。
他的勇气和真实的表达方式,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和认同。
王朔作品流行的原因主要包括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洞察力、具有极大争议性的言辞和态度以及敢于表达真实自我的勇气。
这些因素使得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和追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他的作品不仅揭示了社会的问题和现象,更激发了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反思。
王朔这种敢于挑战和冲击的精神和风格,成为了他作品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说王朔的小说01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张修连(现代远程教育沅陵教学站)论文摘要王朔自《空中小姐》一炮打响后,便成了文坛上争论不休的人物,有的认为:“王朔立异标新,理应占当代文学史一席之地。
”;有的大惑不解:“王朔小说痞味加俗气,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
”;有的大加嘲讽:“王朔崇尚消费人生,无助于社会风气净化。
”如此等等,莫衷一是。
笔者对他的小说细读之后,认为他的小说能真实地反映社会“边缘人”的生活,语言生动形象,鲜活上口,具有独特的创作风格。
但作品缺乏给读者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
总的来说,王朔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
关键词:生活真实语言生动现代人说到王朔,绝不会陌生。
稍有文学细胞的人马上会数落出他一串作品,诸如《空中小姐》、《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等等。
不识字的乡村野老想必也让《渴望》、《过把瘾》等经典之作着实过了一把电视瘾。
我们对王朔的作品稍作归类也无外乎这么四种——挚情、娇情、纯情、谐谑。
笔者对王朔的小说细细读后,掩卷深思,认为王朔的小说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边缘人”的生活状况。
首先,就写作本身而言他是一位作家,然而他又不是人们心目中所设计的那种作家:人格多伟大,道德多完善,行为多高尚,语言多文明,是人类的楷模,灵魂的工程师,他没有那么高的境界。
他自己也常说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名利,可这些仍抹煞不了他对文学的贡献。
他在他的小说中写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上的人物”。
以往,游手好闲为社会所不允许,每个人的社会位置都非常明确。
新时期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改善,社会空气的缓和,职业划分已经不再是“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简单的四大样,很多人生活在社会边缘。
过去,中国的中产阶级依附在权力阶层,由政府、军队、官吏中的一些人士构成。
改革开放前,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经济状况又中等偏上,而改革开放后,这个阶层逐渐瓦解,他们心中的很多人有着巨大的失落感,经济上的优越被私营者取代了,政治上的优越又很模糊,他们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又没受过太多的教育,社会位置急剧变化,青年中的佼佼者不再是他们,社会位置的提升和知识成正比了。
论王朔小说新视角下语言的艺术特色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王朔可以称得上中国文坛的一个“现象”,他的小说无论在故事的构思还是人物的塑造,抑或语言的使用上都与传统文学相差甚大,因此,作品的另类使王朔倍受争议,但与此同时,他作品的这种新颖的艺术特色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叛逆的文化视角下,一个个鲜明生动的顽主形象走向读者,走进人们的视野,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边缘世界和被主流社会所不屑的社会阶层慢慢展现在读者眼前。
关键词王朔, 异类世界, 人物形象, 语言艺术前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一个王朔,在此后的十年间,中国文坛、影坛和电视界渐渐刮起了一阵“王朔风”,王朔现象也成为许多评论家、学者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当代语境下众多学者纷纷从多个角度对王朔进行了各种阐释,作为与精英文化对立的王朔、作为市民文学的王朔等等。
王朔作品的意义因不断地被阐释而不断地扩大、深入,众多的因素使他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作家。
然而无论评论者对他的作品持怎样的态度,不可否认的是王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畅销作家,他的作品给处于这个时期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通观王朔作品,我们发现他并非一个在叙事方面有出众才华的先锋作家,他的故事结构有些甚至可以说得上老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王朔热”?他用什么吸引了大量的读者?通过王朔的众多作品,可以看出他刻意去创造一种喜剧、轻松的故事氛围,着力渲染一种超现实的荒诞世界,他以这种独特的视角,构造了一批游离于城市边缘,不受社会和道德约束的另类个体,这种叛逆的价值观正适合于现实社会中那些苦闷彷徨、难以自我救赎、找不着人生方向的孤单群体,适合于现实中平凡地生活,却有着强烈好奇心和涉险冲动的个体,而这只是“王朔热”的原因之一,王朔作品的语言魅力才是至关重要的,他的作品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大众文化语境下的语言艺术。
而其中王朔作品的调侃语言总是出人意料,它颠覆了正统价值观下作品曾塑造的“精英”面孔,不再是“知识分子”式的仁慈的、含蓄的、自鸣得意的,而是恶毒的、粗俗的、无所顾忌的。
如何阅读与评价王朔作品论文导读:王朔作品最吸引人的特征是其反叛精神和调侃语言。
下面从这两个方面详细分析其顽主形象和语言的构成要素及根本特征。
这种失重感带来了个体的孤独,这些顽主们像城市里的马群一样成群结队地在城市里闲逛,所谓的哥儿们只是在行为上的一致,他们的共存只是缓解了暂时的主体焦虑。
他们彼此并不能互相分享内心的快乐与哀愁,他们也没有更深一层的情感交流,当群体解散后主体焦虑和由之而来的孤独感就会浮出水面。
关键词:顽主,孤独,主体焦虑,调侃,自我作践等等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群众能接受挑战者王朔?王朔到底为当时的社会文化提供了什么东西?这要具体到王朔作品的根本要素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
王朔作品最吸引人的特征是其反叛精神和调侃语言。
下面从这两个方面详细分析其顽主形象和语言的构成要素及根本特征。
一、顽主形象王朔的大多作品里,都是一些没有父母的自由自在的年轻人,如《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即使有父母,也总是以对立面出现,或压抑他们的自由行为,或成为他们精神上的折磨者,如《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等。
他们脱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拒绝参加到既定的规那么合唱中,他们不属于家庭,不属于单位,不属于任何一个对其身份编码化的地方。
他们只是些游荡的个人,像一些鼹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
这些自由自在的个体没有什么原那么,什么纲领,完全凭个人喜好聚在一起,他们在对方的形象中看出自己,他们稀里哗啦地喝酒、打牌、胡侃,生活在他们那里变得没有什么边界,他们嘻嘻哈哈地漫游在想象力所能到达的地方。
对于他们来说,最高的生存境界便是轻轻松松地活着。
比起一般老百姓,他们确实轻松得多,可是,他们并没有在轻松中得到生命的飞腾,却有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失重感。
这种失重感带来了个体的孤独,这些顽主们像城市里的马群一样成群结队地在城市里闲逛,所谓的哥儿们只是在行为上的一致,他们的共存只是缓解了暂时的主体焦虑。
他们彼此并不能互相分享内心的快乐与哀愁,他们也没有更深一层的情感交流,当群体解散后主体焦虑和由之而来的孤独感就会浮出水面。
王塑的文章摘要:1.王塑的背景和成就2.王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3.王塑的主要作品简介4.王塑作品中的主题和风格5.王塑在文学界的争议和评价正文:王塑,原名王朔,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和编剧。
他出生于1958年,自1980年代起开始活跃于文坛,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作品以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和犀利的讽刺手法著称,赢得了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的喜爱。
王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是中国“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新写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他的作品主题丰富多样,涉及现代都市生活、青春成长、历史反思等多个领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
最后,他的文笔幽默风趣,语言独具特色,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王塑的主要作品包括小说《黄金时代》、《我是你爸爸》,以及剧本《阳光灿烂的日子》等。
《黄金时代》以荒诞幽默的手法描述了主人公“我”在“文革”时期的成长经历,揭示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
《我是你爸爸》则以一种调侃的语气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和成长的故事。
这些作品都充分体现了王塑的现实主义风格和讽刺才能。
王塑作品的主题和风格丰富多样,既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也有对历史事件的独特见解。
他的作品常常以幽默讽刺的笔触揭示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矛盾,让人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也陷入沉思。
尽管王塑在文学界享有盛誉,但他的作品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过于荒诞,缺乏深度,有损文学的严肃性。
然而,更多的人则对他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位杰出作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法。
总之,王塑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