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早期小说的悲剧性
- 格式:doc
- 大小:39.50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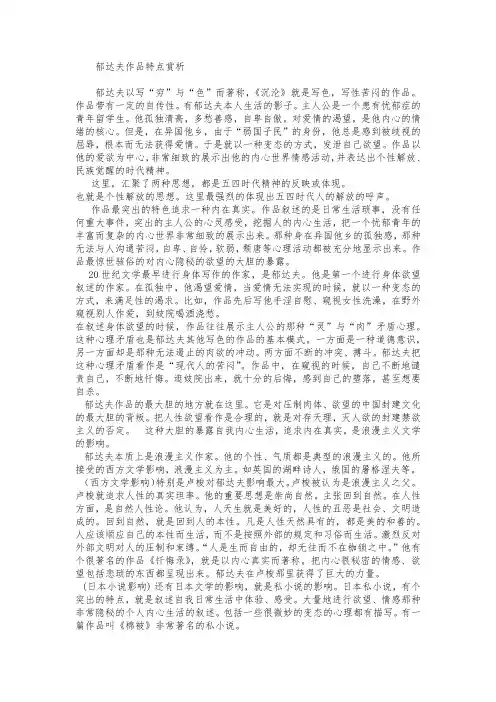
郁达夫作品特点赏析郁达夫以写“穷”与“色”而著称,《沉沦》就是写色,写性苦闷的作品。
作品带有一定的自传性。
有郁达夫本人生活的影子。
主人公是一个患有忧郁症的青年留学生。
他孤独清高,多愁善感,自卑自傲。
对爱情的渴望,是他内心的情绪的核心。
但是,在异国他乡,由于“弱国子民”的身份,他总是感到被歧视的屈辱,根本而无法获得爱情。
于是就以一种变态的方式,发泄自己欲望。
作品以他的爱欲为中心,非常细致的展示出他的内心世界情感活动,并表达出个性解放、民族觉醒的时代精神。
这里,汇聚了两种思想,都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反映或体现。
也就是个性解放的思想。
这里最强烈的体现出五四时代人的解放的呼声。
作品最突出的特色追求一种内在真实。
作品叙述的是日常生活琐事,没有任何重大事件,突出的主人公的心灵感受,挖掘人的内心生活,把一个忧郁青年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非常细致的展示出来。
那种身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那种无法与人沟通苦闷,自卑、自怜,软弱,颓唐等心理活动都被充分地显示出来。
作品最惊世骇俗的对内心隐秘的欲望的大胆的暴露。
20世纪文学最早进行身体写作的作家,是郁达夫。
他是第一个进行身体欲望叙述的作家。
在孤独中,他渴望爱情,当爱情无法实现的时候,就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来满足性的渴求。
比如,作品先后写他手淫自慰、窥视女性洗澡,在野外窥视别人作爱,到妓院喝酒浇愁。
在叙述身体欲望的时候,作品往往展示主人公的那种“灵”与“肉”矛盾心理。
这种心理矛盾也是郁达夫其他写色的作品的基本模式。
一方面是一种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却是那种无法遏止的肉欲的冲动。
两方面不断的冲突、搏斗。
郁达夫把这种心理矛盾看作是“现代人的苦闷”。
作品中,在窥视的时候,自己不断地谴责自己,不断地忏悔。
逛妓院出来,就十分的后悔,感到自己的堕落,甚至想要自杀。
郁达夫作品的最大胆的地方就在这里。
它是对压制肉体、欲望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最大胆的背叛。
把人性欲望看作是合理的,就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禁欲主义的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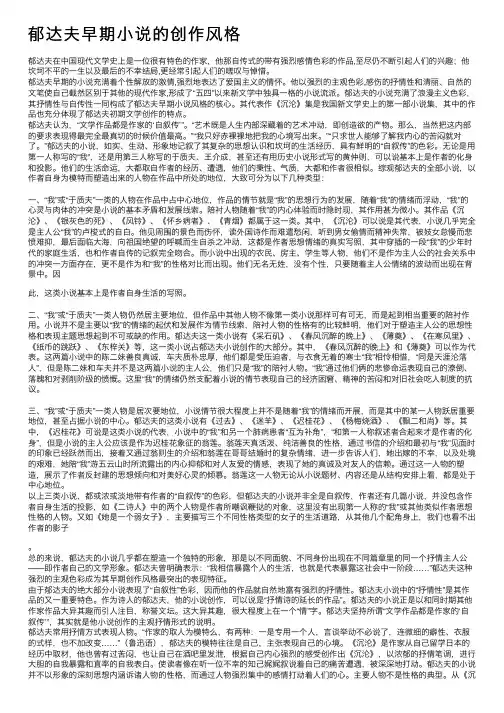
郁达夫早期⼩说的创作风格郁达夫在中国现代⽂学史上是⼀位很有特⾊的作家,他那⾃传式的带有强烈感情⾊彩的作品,⾄尽仍不断引起⼈们的兴趣;他坎坷不平的⼀⽣以及最后的不幸结局,更经常引起⼈们的嗟叹与悼惜。
郁达夫早期的⼩说充满着个性解放的激情,强烈地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情怀。
他以强烈的主观⾊彩,感伤的抒情性和清丽、⾃然的⽂笔使⾃⼰截然区别于其他的现代作家,形成了“五四”以来新⽂学中独具⼀格的⼩说流派。
郁达夫的⼩说充满了浪漫主义⾊彩,其抒情性与⾃传性⼀同构成了郁达夫早期⼩说风格的核⼼。
其代表作《沉沦》集是我国新⽂学史上的第⼀部⼩说集,其中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郁达夫初期⽂学创作的特点。
郁达夫认为,“⽂学作品都是作家的‘⾃叙传’”。
“艺术既是⼈⽣内部深藏着的艺术冲动,即创造欲的产物。
那么,当然把这内部的要求表现得最完全最真切的时候价值最⾼。
”“我只好⾚裸裸地把我的⼼境写出来。
”“只求世⼈能够了解我内⼼的苦闷就对了。
”郁达夫的⼩说,如实、⽣动、形象地记叙了其复杂的思想认识和坎坷的⽣活经历,具有鲜明的“⾃叙传”的⾊彩。
⽆论是⽤第⼀⼈称写的“我”,还是⽤第三⼈称写的于质夫、王介成,甚⾄还有⽤历史⼩说形式写的黄仲则,可以说基本上是作者的化⾝和投影。
他们的⽣活命运,⼤都取⾃作者的经历、遭遇,他们的秉性、⽓质,⼤都和作者很相似。
综观郁达夫的全部⼩说,以作者⾃⾝为模特⽽塑造出来的⼈物在作品中所处的地位,⼤致可分为以下⼏种类型:⼀、“我”或“于质夫”⼀类的⼈物在作品中占中⼼地位,作品的情节就是“我”的思想⾏为的发展,随着“我”的情绪⽽浮动,“我”的⼼灵与⾁体的冲突是⼩说的基本⽭盾和发展线索。
陪衬⼈物随着“我”的内⼼体验⽽时隐时现,其作⽤甚为微⼩。
其作品《沉沦》、《银灰⾊的死》、《风铃》、《怀乡病者》、《青烟》都属于这⼀类。
其中,《沉沦》可以说是其代表,⼩说⼏乎完全是主⼈公“我”的卢梭式的⾃⽩。
他见周围的景⾊⽽伤怀,读外国诗作⽽难遣愁闲,听到男⼥偷情⽽精神失常,被妓⼥怠慢⽽悲愤难抑,最后⾯临⼤海,向祖国绝望的呼喊⽽⽣⾃杀之冲动,这都是作者思想情绪的真实写照,其中穿插的⼀段“我”的少年时代的家庭⽣活,也和作者⾃传的记叙完全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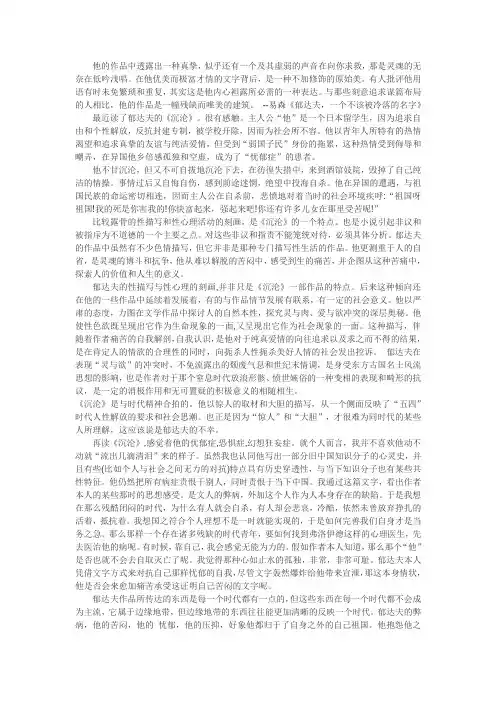
他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种真挚,似乎还有一个及其虚弱的声音在向你求救,那是灵魂的无奈在低吟浅唱。
在他优美而极富才情的文字背后,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原始美。
有人批评他用语有时未免繁琐和重复,其实这是他内心袒露所必需的一种表达。
与那些刻意追求谋篇布局的人相比,他的作品是一幢残缺而唯美的建筑。
--易森《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最近读了郁达夫的《沉沦》。
很有感触。
主人公“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因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被学校开除,因而为社会所不容。
他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渴望和追求真挚的友谊与纯洁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身份的拖累,这种热情受到侮辱和嘲弄,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和空虚,成为了“忧郁症”的患者。
他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在彷徨失措中,来到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
事情过后又自悔自伤,感到前途迷惘,绝望中投海自杀。
他在异国的遭遇,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连,因而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对着当时的社会环境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比较露骨的性描写和性心理活动的刻画,是《沉沦》的一个特点。
也是小说引起非议和被指斥为不道德的一个主要之点。
对这些非议和指责不能笼统对待,必须具体分析。
郁达夫的作品中虽然有不少色情描写,但它并非是那种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他更测重于人的自省,是灵魂的博斗和抗争,他从难以解脱的苦闷中,感受到生的痛苦,并企图从这种苦痛中,探索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郁达夫的性描写与性心理的刻画,并非只是《沉沦》一部作品的特点。
后来这种倾向还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延续着发展着,有的与作品情节发展有联系,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他以严肃的态度,力图在文学作品中探讨人的自然本性,探究灵与肉、爱与欲冲突的深层奥秘。
他使性色欲既呈现出它作为生命现象的一面,又呈现出它作为社会现象的一面。
这种描写,伴随着作者痛苦的自我解剖,自我认识,是他对于纯真爱情的向往追求以及求之而不得的结果,是在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的同时,向扼杀人性扼杀美好人情的社会发出控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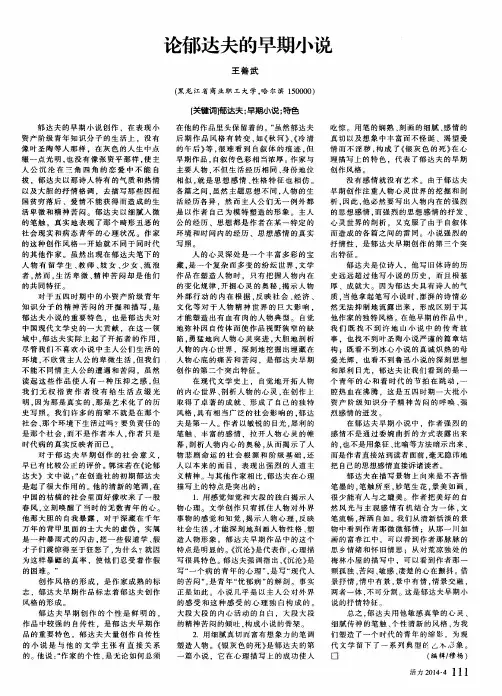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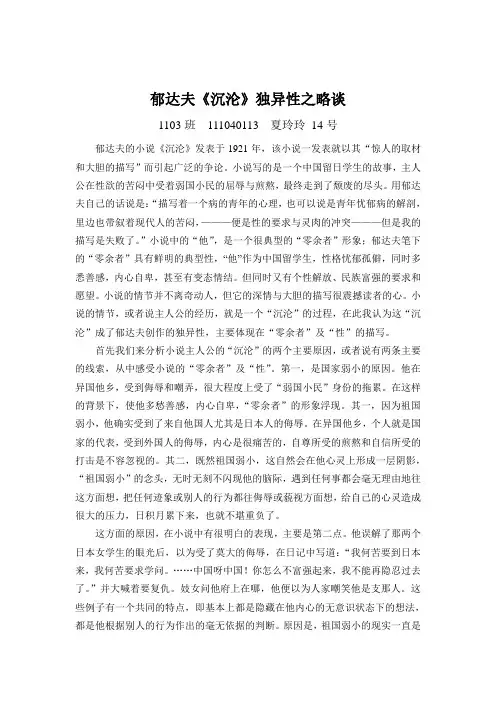
郁达夫《沉沦》独异性之略谈1103班111040113 夏玲玲14号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发表于1921年,该小说一发表就以其“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而引起广泛的争论。
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故事,主人公在性欲的苦闷中受着弱国小民的屈辱与煎熬,最终走到了颓废的尽头。
用郁达夫自己的话说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
”小说中的“他”,是一个很典型的“零余者”形象;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他”作为中国留学生,性格忧郁孤僻,同时多悉善感,内心自卑,甚至有变态情结。
但同时又有个性解放、民族富强的要求和愿望。
小说的情节并不离奇动人,但它的深情与大胆的描写很震撼读者的心。
小说的情节,或者说主人公的经历,就是一个“沉沦”的过程,在此我认为这“沉沦”成了郁达夫创作的独异性,主要体现在“零余者”及“性”的描写。
首先我们来分析小说主人公的“沉沦”的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有两条主要的线索,从中感受小说的“零余者”及“性”。
第一,是国家弱小的原因。
他在异国他乡,受到侮辱和嘲弄,很大程度上受了“弱国小民”身份的拖累。
在这样的背景下,使他多愁善感,内心自卑,“零余者”的形象浮现。
其一,因为祖国弱小,他确实受到了来自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侮辱。
在异国他乡,个人就是国家的代表,受到外国人的侮辱,内心是很痛苦的,自尊所受的煎熬和自信所受的打击是不容忽视的。
其二,既然祖国弱小,这自然会在他心灵上形成一层阴影,“祖国弱小”的念头,无时无刻不闪现他的脑际,遇到任何事都会毫无理由地往这方面想,把任何迹象或别人的行为都往侮辱或藐视方面想,给自己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压力,日积月累下来,也就不堪重负了。
这方面的原因,在小说中有很明白的表现,主要是第二点。
他误解了那两个日本女学生的眼光后,以为受了莫大的侮辱,在日记中写道:“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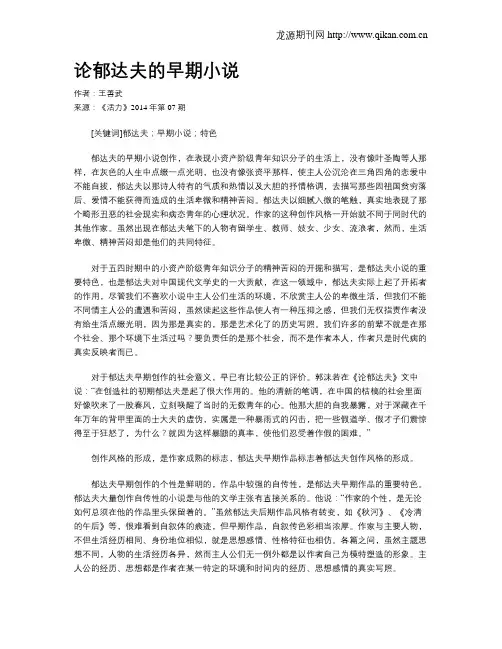
论郁达夫的早期小说作者:王善武来源:《活力》2014年第07期[关键词]郁达夫;早期小说;特色郁达夫的早期小说创作,在表现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上,没有像叶圣陶等人那样,在灰色的人生中点缀一点光明,也没有像张资平那样,使主人公沉沦在三角四角的恋爱中不能自拔,郁达夫以那诗人特有的气质和热情以及大胆的抒情格调,去描写那些因祖国贫穷落后、爱情不能获得而造成的生活卑微和精神苦闷。
郁达夫以细腻入微的笔触,真实地表现了那个畸形丑恶的社会现实和病态青年的心理状况。
作家的这种创作风格一开始就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虽然出现在郁达夫笔下的人物有留学生、教师、妓女、少女、流浪者,然而,生活卑微、精神苦闷却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对于五四时期中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的开掘和描写,是郁达夫小说的重要特色,也是郁达夫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大贡献,在这一领域中,郁达夫实际上起了开拓者的作用,尽管我们不喜欢小说中主人公们生活的环境,不欣赏主人公的卑微生活,但我们不能不同情主人公的遭遇和苦闷,虽然读起这些作品使人有一种压抑之感,但我们无权指责作者没有给生活点缀光明,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艺术化了的历史写照。
我们许多的前辈不就是在那个社会、那个环境下生活过吗?要负责任的是那个社会,而不是作者本人,作者只是时代病的真实反映者而已。
对于郁达夫早期创作的社会意义,早已有比较公正的评价。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文中说:“在创造社的初期郁达夫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唤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实属是一种暴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暴鼯的真率,使他们忍受着作假的困难。
”创作风格的形成,是作家成熟的标志,郁达夫早期作品标志着郁达夫创作风格的形成。
郁达夫早期创作的个性是鲜明的,作品中较强的自传性,是郁达夫早期作品的重要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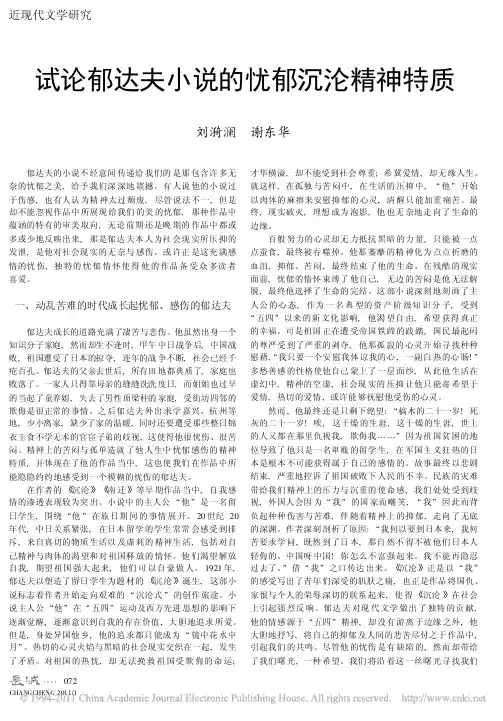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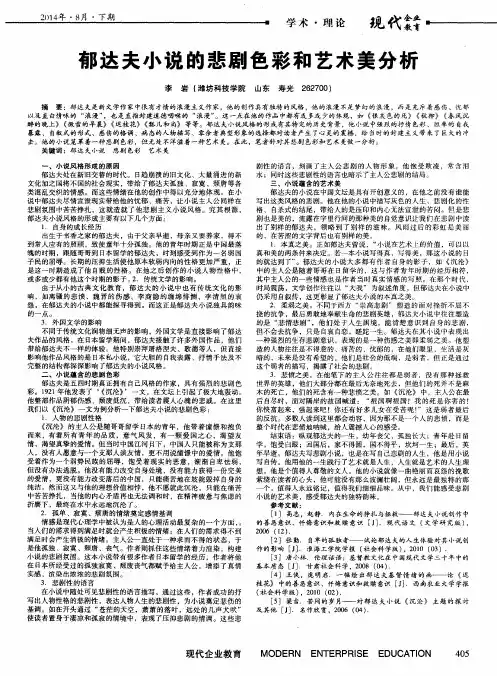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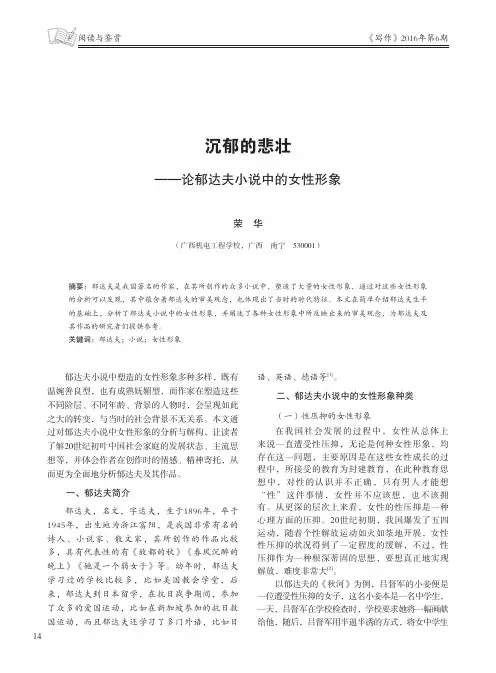
阅读与鉴赏《写作》2016年第6期郁达夫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多种多样,既有温婉善良型,也有成熟妩媚型,而作家在塑造这些不同阶层、不同年龄、背景的人物时,会呈现如此之大的转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
本文通过对郁达夫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与解构,让读者了解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家庭的发展状态、主流思想等,并体会作者在创作时的情感、精神寄托,从而更为全面地分析郁达夫及其作品。
一、郁达夫简介郁达夫,名文,字达夫,生于1896年,卒于1945年,出生地为浙江富阳,是我国非常有名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其所创作的作品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
幼年时,郁达夫学习过的学校比较多,比如美国教会学堂,后来,郁达夫到日本留学,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众多的爱国运动,比如在新加坡参加的抗日救国运动,而且郁达夫还学习了多门外语,比如日语、英语、德语等[1]。
二、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种类(一)性压抑的女性形象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从总体上来说一直遭受性压抑,无论是何种女性形象,均存在这一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这些女性成长的过程中,所接受的教育为封建教育,在此种教育思想中,对性的认识并不正确,只有男人才能想“性”这件事情,女性并不应该想,也不该拥有。
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看,女性的性压抑是一种心理方面的压抑。
20世纪初期,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随着个性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女性性压抑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不过,性压抑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要想真正地实现解放,难度非常大[2]。
以郁达夫的《秋河》为例,吕督军的小妾便是一位遭受性压抑的女子,这名小妾本是一名中学生,一天,吕督军在学校检查时,学校要求她将一幅画献给他,随后,吕督军用半逼半诱的方式,将女中学生沉郁的悲壮——论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荣 华(广西机电工程学校,广西 南宁 530001)摘要:郁达夫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在其所创作的众多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郁达夫的审美观念,也体现出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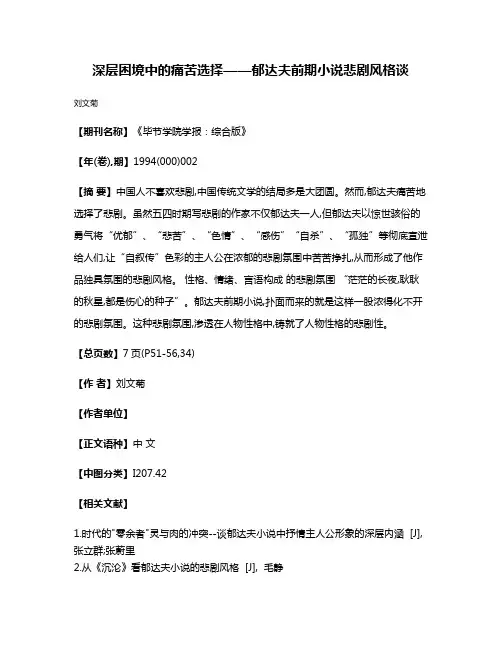
深层困境中的痛苦选择——郁达夫前期小说悲剧风格谈
刘文菊
【期刊名称】《毕节学院学报:综合版》
【年(卷),期】1994(000)002
【摘要】中国人不喜欢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结局多是大团圆。
然而,郁达夫痛苦地选择了悲剧。
虽然五四时期写悲剧的作家不仅郁达夫一人,但郁达夫以惊世骇俗的勇气将“优郁”、“悲苦”、“色情”、“感伤”“自杀”、“孤独”等彻底宣泄给人们,让“自叙传”色彩的主人公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苦苦挣扎,从而形成了他作品独具氛围的悲剧风格。
性格、情绪、言语构成的悲剧氛围“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
郁达夫前期小说,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氛围。
这种悲剧氛围,渗透在人物性格中,铸就了人物性格的悲剧性。
【总页数】7页(P51-56,34)
【作者】刘文菊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相关文献】
1.时代的"零余者"灵与肉的冲突--谈郁达夫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深层内涵 [J], 张立群;张蔚里
2.从《沉沦》看郁达夫小说的悲剧风格 [J], 毛静
3.郁达夫小说忧郁感伤的美学风格--兼谈屠格涅夫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 [J], 王金琼
4.悲剧的命运,悲剧的艺术人格——郁达夫前期小说管窥 [J], 明道煜
5.追求的痛苦超越的代价——谈小说《风景》的历史感和悲剧性 [J], 郑绮梅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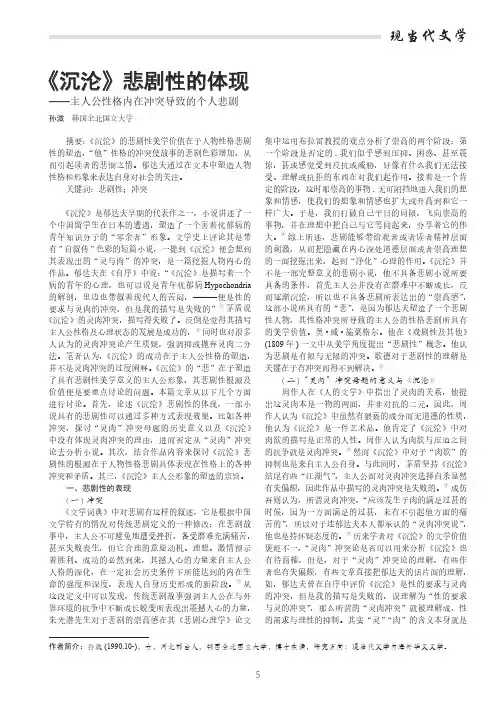
现当代文学《沉沦》悲剧性的体现——主人公性格内在冲突导致的个人悲剧孙溦韩国全北国立大学摘要:《沉沦》的悲剧性美学价值在于人物性格悲剧性的塑造,“他”性格的冲突使故事的悲剧色彩增加,从而引起读者的悲悯之情。
郁达夫通过在文本中塑造人物性格和形象来表达自身对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悲剧性;冲突《沉沦》是郁达夫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塑造了一个害着忧郁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零余者”形象。
文学史上评论其是带有"自叙传"色彩的短篇小说,一提到《沉沦》便会想到其表现出的“灵与肉”的冲突,是一篇挖掘人物内心的作品。
郁达夫在《自序》中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 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的”①茅盾说《沉沦》的灵肉冲突,描写得失败了。
反倒是觉得其描写主人公性格及心理状态的发展是成功的,②同时也对很多人认为的灵肉冲突论产生质疑,强调抑或抛弃灵肉二分法。
笔者认为,《沉沦》的成功在于主人公性格的塑造,并不是灵肉冲突的过度阐释。
《沉沦》的“悲”在于塑造了具有悲剧性美学意义的主人公形象,其悲剧性根源及价值便是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本篇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论述《沉沦》悲剧性的体现,一部小说具有的悲剧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效果。
比如各种冲突,探讨“灵肉”冲突母题的历史意义以及《沉沦》中没有体现灵肉冲突的理由,进而否定从“灵肉”冲突论去分析小说。
其次,结合作品内容来探讨《沉沦》悲剧性的根源在于人物性格悲剧具体表现在性格上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其三,《沉沦》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的宗旨。
一、悲剧性的表现(一)冲突《文学词典》中对悲剧有这样的叙述,它是根据中国文学特有的情况对传统悲剧定义的一种修改:在悲剧故事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备受磨难充满痛苦,甚至失败丧生,但它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激情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必然到来,其撼人心的力量来自主人公人格的深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内在生命的强度和深度,表现人自身历史形成的新阶段。
郁达夫小说的悲剧色彩和艺术美郁达夫小说的悲剧色彩和艺术美正文:郁达夫一生漂泊流浪,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与痛苦,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小说中的零余者漂泊者形象来源于他不行的生活经历,小说源于生活,只有经历了才能写出那种生活的压力和精神的压抑。
一、从零余者形象看郁达夫小说的悲剧色彩郁达夫小说中人物、格调和色彩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忽略掉这些区别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作品中写的都是零余者形象,而郁达夫也曾自己形容过他写的这一形象:“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小说中的主人公给我们就是这种缺乏生气、被生活社会抛弃的可怜人、下层人的形象,我不得不说,郁达夫笔下的人物都是病态的,都是那么穷困潦倒,他们的命运永远都是那么悲哀。
(一)孤独情怀造就的感伤读郁达夫的小说,总觉得有一种伤感笼罩着自己,为个人的孱弱感伤,为国家的软弱感伤他的小说总是让人觉得悲凉、压抑,让人神经紧张,产生无限悲剧色彩。
《沉沦》描写的是青年的挫折和自疚。
郁达夫笔下的是一个在日本留学、远离祖国、穷困潦倒的、在感情上受到挫折的青年人。
小说开始将这个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以诵诗自娱,但是田园景色和诗词却只能给与他精神上短暂的慰藉,他最大的苦恼是性苦闷,这也许与他感情上受挫有关,但读到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另一层原因,那时的中国是软弱的,他因此而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里。
他独自一个人住在旅馆,与其他同来在中国的学生不相交往,夜深却难以克制自己强烈的欲望,于是在一天晚上他偷偷走下楼去看主人的女儿洗澡。
他看后激动不已,匆匆回房,心里不断自责,第二天他便离开了旅馆搬到了山上的梅园去了。
在梅园他曾克制住自己的欲望,然而当他无意间听到一对男女偷情时,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
那天他乘电车进城,在卖酒食的妓院门口看到了卖弄风情、涂脂抹粉的侍女,就鼓起勇气跑了进去,点了酒菜。
但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伺候他的女子并没有对他献殷勤,他想到了自己的堕落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就放大嗓子唱诗,在席上醉倒。
论郁达夫小说的“苦闷”主题【来自: 约翰格利特(死理性派控制狂)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分析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作品与他的人生经历是一脉相承的。
郁达夫的小说始终体现着感伤主义色彩和消沉悲观的情调,体现着它独特的“苦闷”主题。
可郁达夫的“苦闷”小说在作者不同的人生阶段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小说主要体现为“性苦闷”;在回国后的1922---1926年间的小说主要为“经济苦闷”;1927——1935年的小说主要为“社会苦闷”。
郁达夫“苦闷”小说的形成既与郁达夫“卑己自牧”的性格有关,也与时代苦闷有关。
虽然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很难看到前进的道路,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革命战士。
关键词:郁达夫、自叙传、性苦闷,经济苦闷,社会苦闷。
在中国的文坛上,郁达夫无疑是个另类。
它的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在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以自我暴露的笔触,很好印证了“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我们读郁达夫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小说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联系,一脉相承。
翻开他的文集,就好像在阅读他的人生。
仿佛他已跃入文中,向我们讲述他那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
下面我们就从郁达夫的小说入手,深入分析,探索他小说中所蕴含的强烈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是我国“五四"新文学发展史上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他的小说创作影响最大。
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到1935年完成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为时凡十五年,数计四十余篇。
郁达夫曾多次申明和强调过他的艺术主张和对文学的见解。
他“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p203《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选自《郁达夫研究资料》)那么从自叙传的角度出发,郁达夫不同时期的小说带有怎样的自叙传色彩呢?一性苦闷时期(1921——1922)1896年,郁达夫诞生在秀丽的富春江畔的小城——富阳。
论郁达夫小说----《沉沦》中主人公的形象论郁达夫小说----《沉沦》中主人公的形象【摘要】在沉沦中郁达夫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染有“时代病”的青年形象.他酷爱自由,有着多愁善感的性格,耽于幻想;他热爱生活,渴求自由和爱情,却不被人理解;追求而不可得,于是想麻醉自己,但良心又自谴自责;整天过着沙漠般孤寂苦闷的生活,处处受到歧视和欺侮,但又没有与黑暗不合理现实进行搏斗的勇气,感到非常委屈。
郁达夫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他当时那个时代的部分精神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形象.【关键词】沉沦病态知识分子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郭沫若引李初梨的话这样评价郁达夫。
是的,郁达夫在<沉沦>这部小说中大胆直率地进行心理描写,这点经常被时人拿来讨论。
尤其被评论家所诟病的,是小说中毫不掩饰的对病态、畸形的性心理进行了直白的描写,这一点是不能被中国的道学家所接纳的。
第一个站出来为郁达夫的小说进行正面评论的是周作人,他认为“《沉沦》中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无不道德的性质”,因此,他认为《沉沦》是一件艺术品。
一.《沉沦》中“他”的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一出场就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感情,身在异乡独自求学的他无疑孤独的,但他的思想是病态的。
性格也从开始的忧郁到后来的孤愤越来越诡异。
当然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周围的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小说《沉沦》的主人公——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在“他”四处求学中接受的则是较为开放的进步思想。
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下长大的主人公既有中国文人某种气质,同时又有一些自由与叛逆的思想。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他的自由思想被压抑。
当他离开W学校“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他选择了蛰居在小小的书房里,他的内心里也因此而压抑,产生了“忧郁症的根苗”。
因为在异国他乡,饱受“性的苦闷”与“外族冷漠歧视”的“他”渴望真挚的爱情,并愿为此抛弃一切。
然而这种渴望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的内心逐渐失去理智的控制,之后就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心态,以及对性的渴望。
论郁达夫早期小说的悲剧性提要:“逃避沉沦”,率性而为的年轻作家,用生存的真实、用亲生感受创作了一段伤感的往事,一个悲情的时代,一个风雨飘摇的旧中国。
悲剧来自时代,来自悲剧性产生的社会根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失意、苦闷,社会底层民众苦不堪言,造就了郁达夫小说浓郁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郁达夫;早期小说;悲剧性;沉沦郁达夫(1896.12.7--1945.8.29) 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
1914年7月留学日本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广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
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
1922年3月回国,先后编辑《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大众文艺》等刊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到南阳参加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的工作。
后流亡到苏门答腊,坚持抗日斗争,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杀害。
[1]郁达夫的主要小说作品有短篇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中篇小说《出奔》、《她是一个弱女子》、《茫茫夜》等。
作家在这些作品中将自己的苦闷、颓废作为一种反应当代知识分子共性问题的“时代病”提出来,由感伤而转为憎恨,不同程度地控诉了那个时代的罪恶,公然地向封建道德和社会现实大胆宣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作家的颓废,苦闷也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应,下层知识分子无助的悲号、糟糕的生活,更带有一定的悲剧性。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2]十年的异国生活,饱受屈辱和歧视的现实处境,贫困而落魄的生活困境,苦闷而失意的感情生活,既激发了作家的爱国热忱,也形成了他忧伤、愤世、颓废而近于病态的心理,这些心理在他的早期小说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展露。
作家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以自传的形式,抒写下层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情节简单,人物形象少,往往取材于主人公经历的一段往事,利用生活中的一两个片段,毫不掩饰的对病态、畸形的性心理进行了直白的描写,真实而细致地再现生活。
如完成于1921年5月的《沉沦》,1924年8月的《薄奠》和后来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这些作品由写“性的苦闷”转向写“生的苦闷”,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由写知识分子转向写社会底层民众。
但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悲剧性。
这种悲剧性有别于“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这种悲剧是一个时代,准确地说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的反映。
郁达夫作品的悲剧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糟糕黑暗的社会现实赋予作品难以摆脱的悲情色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环境,丑恶的生活现实本身就是铸就悲剧的深渊。
作家郁达夫的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水深火热、黑白颠倒的时代。
在郁达夫的笔下,他所处的这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无趣味,最无价值的时代,也当然就是最可憎恶的时代。
[3]早期的郁达夫如当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苦苦探寻着中国的光明和出路,他们的觉醒是超前的,但他们的奋斗却是艰辛和曲折的,甚至不乏苦闷、彷徨,以至沉沦和毁灭!他们往往以文笔做武器,大胆地向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抗争,他们的奋斗是坚决的,但力量却是微弱的。
在通往光明坦途的漫漫征程上,他们中有的成为坚强的战士,有的成为妥协的逃兵;有的成为壮烈的英雄,有的成为可耻的叛徒!“逃避沉沦”——郁达夫以其坚韧的毅力,将他的所有不着的青年的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
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向一个黑白颠倒的制度发出了哀鸣控诉,虽然也曾颓废彷徨,虽然也曾辗转流离,却最终战胜了狭小的“自我”,成为民族斗争的时代英雄。
由此可见,郁达夫早期的悲剧作品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郁达夫始终在追寻着人性的、人生的自由幸福,始终在挣扎。
然而,黑暗的现实却始终笼罩着他。
他一方面在抗争,一方面又在消耗自己,特别是青年时代十年的异国生活,他的“精神上感到极度的压抑以及爱情上的无比的苦闷的心情,充满了哀怨、忧伤的情绪。
”如《沉沦》中那个忧郁而性格变态的中国留学生,在异邦受尽屈辱,渴望纯真友谊与爱情,但终究没有如愿,这是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强烈控诉,也是对封建礼教大胆的宣战。
作品主人公的苦恼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这种人性的要求索受到的挫折作者归结到是因为自己祖国不强盛,因而表达出热切的希望祖国富强起来的心愿。
正如结尾中深情的哀号:“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也有许多的儿女在那里受苦呢!”[4]这种近乎直白的坦率,完全是自泪的控诉与积郁的愤懑的宣泄。
充分说明了郁达夫的悲剧是时代的、现实的反映。
对祖国的既爱又恨,又无力拯救的矛盾而痛苦的心情,让海外游子悲与愤,让他们的心理承受着无比的伤与痛。
《薄奠》中那个勤劳、善良、纯朴的车夫,一个具有朴素的阶级觉悟和反抗压迫剥削的青年工人形象,他有着倔强意志、善良、正直、真诚。
“我”和他从相识、相知到相关怀直至同情、理解,但最终却没能团结起来。
这是作者从日本归国后,受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深感“生的苦闷”的威胁,在不断地认识和体验现实中,以比较真实、细腻的笔触反映了自己以外的现实和人物。
因而比前期的作品的悲剧色彩更浓厚、更刻骨铭心。
总之,郁达夫早期的作品,主人公有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不管是知识分子、人力车夫还是工人,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都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作者创作的不只是几个悲剧人物,而是呼喊着光明和自由,苦苦追寻着改变现实的真理。
二、作家的个人性格特点导致作品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郁达夫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畸形的社会让他和广大劳动人民走到了一起,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始终不能和广大的劳动人民融合在一起,这注定了没有出路,甚至也看不到希望。
作者在自我式的描写中,把人性的、生活的苦闷一股脑儿地倾斜出来,但始终没能为这些人指明出路,尽管有,也只是概括和模糊的,这多少也就判定了人物的“死刑”,让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在绝望中死去。
如《沉沦》中的“他”,“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之间的那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留日学生,由于忧郁,深受环境的压抑,在按部就班的学习、生活中,没有友谊,更没有同情和理解,整天只能沉湎于现实的抵触和幻想之中,在一些书上去寻找寄托和安慰。
他曾有过许多正常的期望和需求,但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在一个挫折之后,“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5]由于作者自己的阶级局限,“他”不可能找到出路,最后在一个荒凉的小镇上,破灭了自己最后一个梦,而只能归结到因为自己祖国的不强盛而已。
作品坦率,大胆地暴露了病态的心理,展开了病态的人生,一方面表现了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
“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
”使道学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另一方面,主人公的反抗却是采取的慢性自我的方法,爱国心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那浓厚厌世情调,无疑给作品蒙上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与作者个人的阶级局限和个性分不开的,正如郭沫若说:“郁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太纤细了……他感到很骄傲,有时甚是伤心。
”[6]“达夫这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病。
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巨的工作,还有一个或许多也是缺点,是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废,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
”[7]现实性较强的《薄奠》和《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作者在当时可算最早地描写工人阶级了,但在廉价的伤感和同情之外,便没有别的可以肯定的了,“我”送纸车给车夫祭奠,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无力拯救;劳苦大众的痛苦和愤怒,而“我”与“陈二妹”那一片畸形的恋情,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只是一段令人陶醉而又惋惜的悲剧而已。
因此,作品的悲剧性就体现为人物命运、人物性格的悲剧了。
郁达夫早期的作品“清丽婉约”,是受作者人格影响所至,在人生阅历和现实斗争中不断丰富的过程中,郁达夫不断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但作品的悲剧性依然浓厚。
三、独特的浪漫式抒情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中,大量融入心理描写,采用独特的散文式抒情写法把大量的主观抒情的东西写进作品中,下层知识分子失意和颓伤的情感,自然景物的细腻描写,都给作品笼罩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首先,作品情节的安排较为松散,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恢弘的大场面,而是善于选择小事件,用作品主人公的经历作为线索,把一个个片段连接起来,有利于描写自我见闻,擅长通过人物的活动抒发感情。
其次,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
作者许多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的,这有利于抒发内心感情。
例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就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描写我的内心事件,“陈二妹”问主人公:“你天天在这里看的是什么书?”我听了她的话,反而脸红了。
因为我天天呆坐在那里,面前虽则;有几本外国书摊着,其实我的脑筋昏乱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进去。
有时候我只用了想象在书上的上一行与下一行中间的空白时,填些奇异的模型进去。
有时候我只把书里边的插画翻开看看,就有了那些插画演绎不近人情的幻想出来。
我那时候的身体因为失眠与营养不良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成了病的状态了。
况且又因为我的唯一的财产的一件面袍子已经破的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屋全没有光线进来,不论白天晚上,都要点着油灯和蜡烛的缘故。
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缩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的我,听了她这一问,如果能够不红起脸来呢?通过这一段描写,不难看出作品的主人公“我”具有一种独特的“忧郁病”,因而,从这个角度所感受到的自然和社会,都具有一层悲剧色彩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苦闷,抑郁被作者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最后,善于通过环境描写来烘托气氛,抒发感情。
郁达夫早年的作品,几处找不到有亮色的环境描写,例如《沉沦》中“他”寄居的郊外小镇。
通过描写环境来表达主人公忧郁而性格有些变态,主人公非常苦闷,如书中描写的“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日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那里行走。
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
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六寸长的英国大诗人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
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犬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