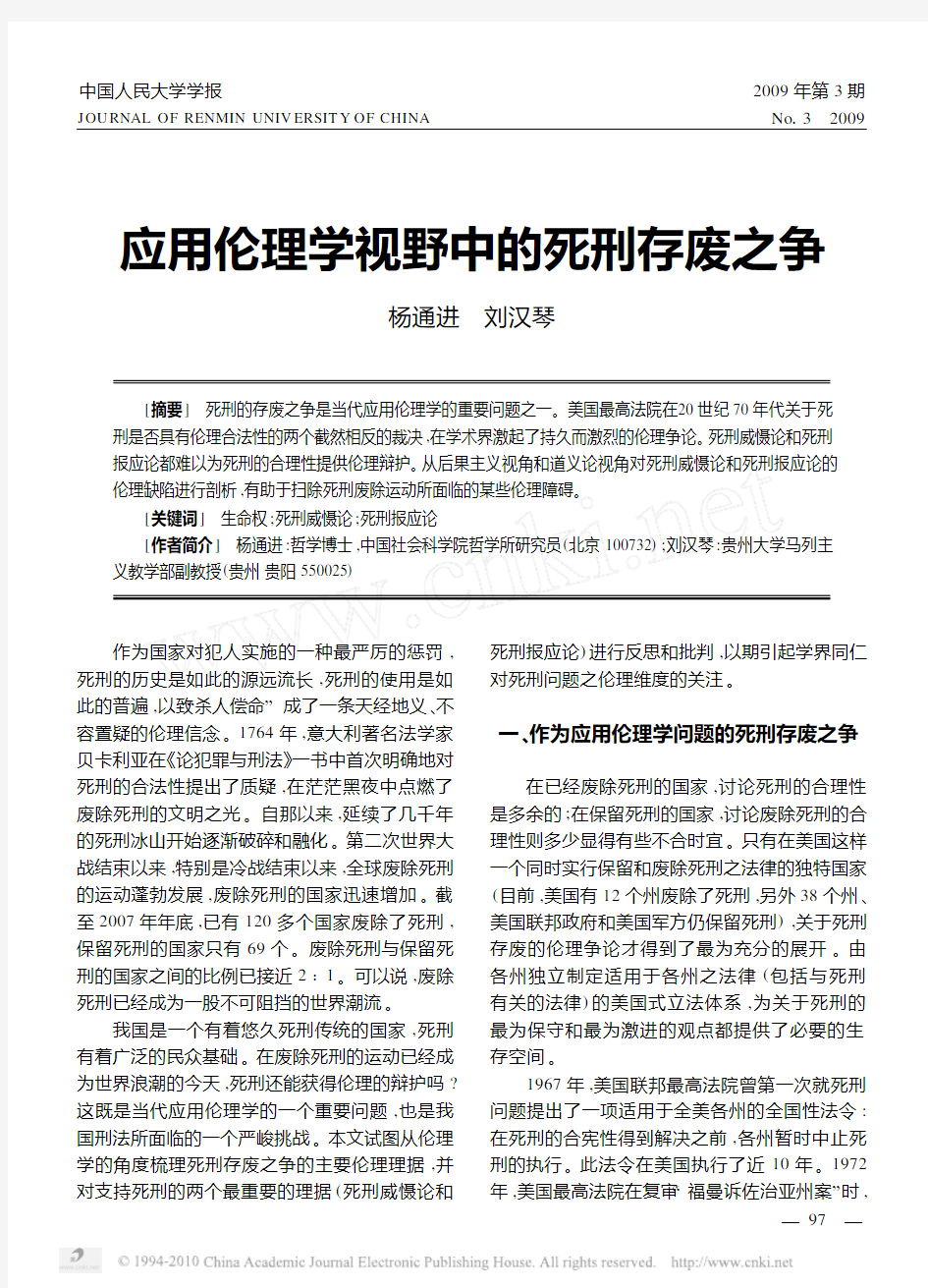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J OU RNAL OF RENMIN UNIV ERSIT Y OF CHINA No13 2009
应用伦理学视野中的死刑存废之争
杨通进 刘汉琴
[摘要] 死刑的存废之争是当代应用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美国最高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死刑是否具有伦理合法性的两个截然相反的裁决,在学术界激起了持久而激烈的伦理争论。死刑威慑论和死刑报应论都难以为死刑的合理性提供伦理辩护。从后果主义视角和道义论视角对死刑威慑论和死刑报应论的伦理缺陷进行剖析,有助于扫除死刑废除运动所面临的某些伦理障碍。
[关键词] 生命权;死刑威慑论;死刑报应论
[作者简介] 杨通进: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北京100732);刘汉琴:贵州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25)
作为国家对犯人实施的一种最严厉的惩罚,死刑的历史是如此的源远流长,死刑的使用是如此的普遍,以致“杀人偿命”成了一条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伦理信念。1764年,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法》一书中首次明确地对死刑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了废除死刑的文明之光。自那以来,延续了几千年的死刑冰山开始逐渐破碎和融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废除死刑的运动蓬勃发展,废除死刑的国家迅速增加。截至2007年年底,已有120多个国家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69个。废除死刑与保留死刑的国家之间的比例已接近2∶1。可以说,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死刑传统的国家,死刑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在废除死刑的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浪潮的今天,死刑还能获得伦理的辩护吗?这既是当代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刑法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角度梳理死刑存废之争的主要伦理理据,并对支持死刑的两个最重要的理据(死刑威慑论和死刑报应论)进行反思和批判,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死刑问题之伦理维度的关注。
一、作为应用伦理学问题的死刑存废之争
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讨论死刑的合理性是多余的;在保留死刑的国家,讨论废除死刑的合理性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只有在美国这样一个同时实行保留和废除死刑之法律的独特国家(目前,美国有12个州废除了死刑,另外38个州、美国联邦政府和美国军方仍保留死刑),关于死刑存废的伦理争论才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开。由各州独立制定适用于各州之法律(包括与死刑有关的法律)的美国式立法体系,为关于死刑的最为保守和最为激进的观点都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
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第一次就死刑问题提出了一项适用于全美各州的全国性法令:在死刑的合宪性得到解决之前,各州暂时中止死刑的执行。此法令在美国执行了近10年。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复审“福曼诉佐治亚州案”时,
—
7
9
—
曾以5∶4的微弱多数裁定,死刑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关于“不得对犯人执行残忍的和不同寻常的惩罚”的规定。但是,4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在复审“格雷诉佐治亚州案”和其他几个案件时又宣布,死刑本身并不违反美国宪法。福曼案和格雷案是美国死刑立法的两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判决所依据的不同伦理理由,从一个方面展现了美国社会在死刑存废问题上的重要道德分歧。
在福曼案的判决书中,布里兰等法官认为死刑不能获得辩护的主要理由是:第一,由国家蓄意毁灭一个人的生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特有的损害。就其痛苦性、终结性和残酷性而言,死刑都是一种异常严厉的、可怕的刑法。生命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死刑摧毁了这个基础,也剥夺了被处决者的所有其他权利。死刑否认了罪犯作为人类大家庭之成员的资格,是对被处决者之人格的否定。死刑还是对罪犯改过自新能力的否认。因此,死刑损害了人的尊严。第二,无论其程序多么复杂,死刑的判决都具有武断、任意和偶然的成分。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死刑判决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判的情形;一旦执行死刑,错判就永远无法得到修正。在被判处死刑的人当中,只有一部分被实际执行(例如,2000年,美国被判处死刑的人超过3500名,但只有85人被执行死刑)。这使得死刑的执行具有“彩票中奖”的性质。陪审团法官的个人判断、罪犯辩护律师的技能、特定的舆论氛围、被害人家属的地位和态度等,都会使得对罪犯的死刑判决因人、因种族、因时、因地而异。死刑本身具有异常的严厉性和终结性,而死刑判决中却存在着难以排除的武断性、任意性和偶然性。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死刑制度的荒谬性昭然若揭。第三,死刑判决的急剧减少、对死刑执行的严格限制、人们围绕死刑展开的激烈争论都表明,在现代社会,死刑的合理性已受到质疑,关于死刑的立法应当反映人们的这一变化了的道德观念。第四,没有理由相信,死刑比长期监禁或其他惩罚能更有效地服务于刑罚的目的。死刑比长期监禁能更有效地遏制犯罪的假设并不能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持。也没有证据表明,不对杀人犯处以死刑就会鼓励个人之间的血腥屠杀和其他纷争。死刑表面上是为了向人们证明生命的不可侵犯性,但它的实际作用却是降低我们对生命的尊重,
并使我们的价值观变得野蛮。第五,如果死刑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来说是不必要的,那么,赞成死刑的唯一理由便是报应。但是,报应是一种过时的道德观念。人们的正义观念是不断演进的。没有任何一种道德秩序要求我们必须处死强奸犯和杀人犯。根据上述几点理由,死刑与人的尊严不符,违背了美国宪法关于“不得对犯人执行残忍的和不同寻常的惩罚”的规定,因而应予以废除。
与福曼案不同,格雷案则作出了死刑符合美国宪法的判决。斯图亚特等法官为该裁决提供的辩护理由主要有:第一,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在制定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时,死刑是被普遍接受的惩罚,因此,不属于“残酷和异常严厉的惩罚”的范畴。第二,判断一种惩罚是否符合“人的尊严”这个“第八修正案背后的基本理念”,关键是看该惩罚是否“过分”。死刑既不包括不必要的和任性的痛苦,也与杀人犯的罪行相等,因此,不是一种过分的惩罚。第三,虽然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关于死刑的威慑理论,但我们仍可以安全地假定,对许多谋杀者来说,死刑肯定是一种重要的威慑。第四,死刑是正义所要求的。报复的冲动是人性的一部分,有序地释放这种冲动,有利于社会的团结。某些罪行对人性的羞辱是如此恶劣,以至于对它们唯一适当的反应就是死刑。第五,19世纪以来的大部分美国人都相信,对杀人犯而言,死刑是一种得体的、必要的和符合正义的法律制裁。根据以上理由,死刑仍然是一种能够获得伦理辩护的惩罚。[1](P189-205)美国最高法院的上述不同裁决,以比较尖锐的形式展现了美国社会在死刑问题上存在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在大多数应用伦理学教材及相关著述中也得到了体现。从应用伦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关于死刑的伦理争论主要围绕两类问题展开:一类是后果主义伦理问题,即死刑能否带来死刑维护者所希望的社会后果;一类是道义伦理问题,即死刑是否符合正义的理念。关于死刑的其他争论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二、死刑能威慑能预防犯罪吗?
在死刑保留论者看来,由于其严厉性和终极性,死刑比长期监禁(包括终身监禁)更可怕,因而它可以对那些不害怕长期监禁的潜在的杀人犯构
—
8
9
—
成威慑。处死杀人犯,不仅可以防止杀人犯再次杀人,而且可以给潜在的杀人犯传递“不可杀人”的信息,防止新的杀人犯产生。因此,死刑是威慑犯罪特别是杀人犯罪的最有效手段。然而,不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关于死刑具有特殊威慑作用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犯罪是一种社会病,它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观念、家庭关系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
其次,死刑也不可能对那些激情杀人犯、情境杀人犯以及所谓的“亡命徒”产生特殊的威慑或遏制作用。
再次,惩罚的威慑效果不仅取决于它的严厉性,还取决于它的快速和确定性。在现代社会,由于限制和慎用死刑是大势所趋,对死刑犯的审判要经过众多繁杂的程序,所以,死刑犯从被指控到最终被执行死刑的时间越来越长。在美国,有的死刑犯往往要在狱中等待一年或数年的时间,才能等到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而且,并非所有的杀人犯都被判处死刑。因此,决定死刑的威慑效果的快速和确定性这两个条件已经大打折扣。
最后,如果越严厉的惩罚越具有威慑效果,那为什么不采用那些更为痛苦的处决方式,如古代的分尸刑、沸油刑、尖刀刑?
对死刑的威慑效果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死刑对遏制杀人犯罪并没有特殊的预防和威慑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对废除死刑与保留死刑的国家之间、美国废除死刑与保留死刑的州之间的凶犯犯罪率(横向比较)以及一个国家(如美国的一些州)在废除死刑之前与之后(纵向比较)的凶犯犯罪率的变化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美国学者嘎特内尔和贝克特查阅了110个国家的“比较犯罪资料档案”,并考察了14个国家废除死刑前后1年、5年和更长时期杀人率的变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跨国比较研究并未发现死刑能够遏制犯罪。[2]与威慑理据相关的另一个维护死刑的理据是,死刑可以彻底剥夺杀人犯继续杀人的能力,从而可以达到阻止杀人犯再次杀人的目的。这一理据的潜在假设是:所有的杀人犯都具有继续杀人的可能性;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我们需要杀死所有的杀人犯。很明显,这种假设是成问题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杀人犯都有继续杀人的动机。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72年被判处死刑但缓期执行的558名死刑犯中,只有1%的人继续杀人。[3]这意味着,为了要剥夺那一个有可能继续杀人的死刑犯的犯罪能力,需要同时处死另外99个不会继续杀人的死刑犯,因为,根据人类现有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我们根本不可能把那一个会继续杀人的死刑犯从另外99个不会继续杀人的死刑犯中挑选出来。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的政策吗?
对死刑在剥夺犯罪能力方面的评估还涉及对死刑和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的比较问题。在彻底剥夺杀人犯的犯罪能力方面,死刑确实比终身监禁有效。但是,死刑的这种边际效果要以处死所有的杀人犯为代价。这一方面加大了死刑的代价,另一方面把“刑罚的改造理念”悬置起来,剥夺了死刑犯改过自新的机会,牺牲了刑罚的改造功能。终身监禁在剥夺死刑犯的犯罪能力方面没有死刑彻底,但它由于没有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代价低于死刑;同时,与死刑相比,它还具有继续改造犯罪的优势。今天的更为先进的监狱管理系统和限制死刑犯假释的制度,已经大大降低了死刑犯再次杀人的风险。因此,死刑的边际效益在总体上未必大于终身监禁。如果终身监禁与死刑的边际效益大致相等(即使不是更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牺牲大量生命的死刑制度呢?
本文无意否认死刑所具有的一般威慑作用。我们这里想强调的是,就对预防犯罪和遏制杀人而言,死刑并不比长期监禁具有更大的功效。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与死刑是否具有比长期监禁(包括终身监禁)更大的威慑力,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后一问题的否定性回答并不意味着对前一问题的否定性回答。既然实际经验已经证明,长期监禁(包括终身监禁)也能起到预防犯罪和遏制杀人的作用,那么,一个人道和理性的社会就不应该选择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法律制度。
死刑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哈格也承认,不被处死的杀人犯可能会继续杀人,也可能不会杀人。尽管如此,哈格仍坚持认为,我们需要为了保护那个不确定的受害人的生命,而牺牲杀人犯的生命,“我们没有权利为了饶恕被定罪的谋杀者而
—
9
9
—
让他们额外的未来受害者冒险;相反,我们的道德义务是拿处决的可能的无效来冒险。”[4]被处死的杀人犯的死是确定的;而谋杀犯的潜在的未来受害者的死是不确定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了某个不确定的东西(被害人的可能的死)而让某个确定的东西(杀人犯的死)来承担风险。
对于哈格的上述论点,我们可以作出如下两点评论。首先,我们并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对杀人犯处以确定的死刑,使得将来的其他杀人犯的受害者有生存下来的可能;要么是让杀人犯确定地活下来,却让新的受害者的死亡仍旧可能发生。”[5](P79)因为,我们还可以选择让杀人犯终身监禁,从而使他不可能再去杀害其他人。通过长期监禁,那些在监狱中步入天命之年的杀人犯,或许已经丧失杀人的激情,磨去了年轻时候的冲动和暴戾;他们或许已经改过自新。通过建立一套更加公平的社会制度(在其中,所有人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都能看到未来和希望),我们也能够预防犯罪,防止新的受害者的死亡的发生。所有这些考虑都使我们有理由不把处决杀人犯当作预防犯罪的最佳选择。
其次,仅仅为了预防犯罪而处死杀人犯,是把杀人犯的生命仅仅当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而根据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理论,我们是不能仅仅把人的生命(包括杀人犯的生命)当作某种工具来对待的。这种极端的工具主义思维方式一旦流行,那么,目的就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较低的目的只是较高的目的的手段。以此类推,世界上就只存在一个终极目的,其他的存在物都只是纯粹的工具。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主宰下,对人权的践踏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
即使从后果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能忽略死刑制度所带来的副产品。死刑是对人的生命的有意识、有预谋、制度化的毁灭。不论在何种年代,对生命的毁灭都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死刑在毁灭杀人犯的生命的同时,可能也会给人们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毁灭人的生命是合理的。这会使人们无视生命的价值,对生命本身麻木不仁。残酷之法常常造就残酷之民。正如贝卡里亚所说:“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因为支配立法者双手的残暴精神,恰恰操纵着杀人者和刺客们
的双手。”[6](P43)国家的行为也具有示范作用;当它公开地杀害犯人时,它就是在培养并鼓励其公民的复仇情感。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人类伙伴做某些事情,哪怕他们应该被这样对待。有意识、有预谋地剥夺一个完全丧失了杀人能力的罪犯的生命,就属于这类不该做的事情之一。“拒绝处决杀人犯(尽管他们应当受处决),这既反映也传承了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对人类物种的驯化。因此……废除死刑是现代国家文明化使命的一部分。”[7]
三、死刑报应论是正义的吗?
在死刑保留论者看来,死刑是杀人犯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杀人犯应得的;这些杀人犯是如此的罪大恶极,只有处以死刑才能平民愤,才能告慰于受害人及其家属。正义要求惩罚有罪者。因此,死刑在道德上是公正的。
死刑报应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同态复仇法或等量报复法。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圣经》也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古训。在近代,这种同态复仇的理念甚至得到了像康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的辩护。在康德看来,等量报复法为死刑提供了支持。对于谋杀犯的惩罚,不能有弹性:“如果……他杀了人,他就必须被处死……没有任何替代方式能够满足法律正义的要求……如果犯罪人不被依法定罪并处死,犯罪与报应之间就无法等同起来。”甚至对那些密谋实施杀人、但尚未得逞的犯人,“最好的等量补偿就是死刑”。[8](P102,104)死刑保留论者哈格也认为,只有死刑施加给杀人犯的伤害,才能与杀人犯施加给其受害者的特殊伤害相等。“如果被害人死了,谋杀犯就不该活着。”[9]
但是,把等量报复法作为报应正义的主要理据,至少会遇到以下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第一,如果等量报复法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应当对伤人肢体者处以肢体刑,对强奸者处以宫刑,对羞辱他人者处以羞辱刑。既然我们认为后面这类处罚是不合理、不公正的,那么,基于逻辑上的同一律,我们也难以证明对杀人者处以死刑是合理的或公正的。
第二,如果严格遵守以命抵命的理念,我们就必须处死所有犯有杀人罪的人。但是,在保留死
—
1
—
刑的国家中,并非所有犯杀人罪的人都会判处死刑,而有的犯人没有杀人却也被处以死刑。
第三,如果用杀人犯的生命能够换回被害人的生命,那么,处死杀人犯或许是公平的。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失而不能复得,死而不能复生。处死杀人犯,并不能使受害人起死回生。杀人犯的死也换不来受害人的生。已经死去的被害人并不能从杀人犯的死中获得任何补偿。因此,处死杀人犯,对被害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
第四,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道德秩序要求惩罚要与犯罪的严重性相适应。杀人确实是一种最严重的犯罪,确实应遭受最严重的惩罚。但是,究竟什么是最严重的惩罚,这却是由一个社会所接受的道德观念来决定的。在古代,以各种酷刑折磨犯人致死的处罚曾经是得到人们的道德观念认可的最严重的惩罚。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和人权运动的发展,酷刑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得不到道德辩护的处罚。在这种形势下,以杀人者的死亡这类具体形态的对等为内容的等害报应观念,已经被以抽象形态的对等报应为内容的等序报应理念所取代。
①
20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史怀泽认为,对生命所做的这种人为的等级划分,会使人陷入“某些生命是毫无价值的”这种危险的思想之中。既然某些生命毫无价值,那么伤害和毁灭它们就没有任何道德障碍。由于对生命缺乏敬畏,“各民族就相互残杀,并使大家陷于恐怖和畏惧之中”。那些自认为更优秀的民族,就会心安理得地去征服、甚至铲除那些劣等的民族。这正是战争的重要伦理根源。因此,把人的生命分为具有不同价值等级的想法是相当危险的。参见史怀泽:《敬畏生命》,131-13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与“以命抵命”式的等害报应不同,等序报应的基本理念是,依据其给他人造成伤害的严重程度为标准,对犯罪进行轻重秩序的排列,同时,依据其严厉程度对惩罚进行轻重秩序的排列。在此基础上,把最严厉的惩罚分配给最严重的犯罪,把较不严厉的惩罚分配给较不严重的犯罪,从而实现犯罪与惩罚的对等。如果我们把杀人行为视为最严重的罪行,把终身监禁视为最严重的惩罚,并把终身监禁分配给杀人罪行,那么,我们就实现了等序报应意义上的公正。因此,对杀人者处以死刑,不再是等序报应意义上的刑罚公正的必然要求。用等序报应取代等害报应,这是报应理念的进步,也是刑法观念的革命性变革。
作为近代天赋权利学说的奠基人之一,洛克曾明确指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独立而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人们遵循着两条基本的自然法:保存自己,
同时尽其所能地保存人类的其他成员。但是,洛克也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有处死一个杀人犯的权利,以杀一儆百来制止他人犯同样的无法补偿的损害行为,同时也是为了保障人们不受
罪犯的侵犯。”[10](P9)
洛克为此提供了两条理由。
第一,杀人犯已经“绝灭理性”(人性),他以“对另
一个人所施加的不义暴力和残杀而向全人类宣战,因而可以当作狮子或老虎加以毁灭,当作人类不能与之共处和不能有安全保障的一种野兽加以
毁灭。”[11](P9)
对于这些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的人,我们享有一种正当而合理的毁灭他们的权利。第二,那些不正当地使用强力威胁或毁灭他人生命
的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生命权”。[12](P112)
杀人犯既然已经把他的生命权放弃给了受害人,受害者就拥有立即剥夺或延缓剥夺杀人犯之生命的权利。
的确,杀人犯在实施犯罪时往往不受伦理法则的约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杀人犯在杀人之前和杀人之后都完全丧失了人性和理性。杀人犯的理性和道德能力不会因为一起蓄意的谋杀或过失杀人而突然消失。没有任何一种可靠的经验论据支持这一看法:被定罪的谋杀犯因其谋杀行为而丧失了他的道德能力。杀人犯仍然是人,他仍然拥有某种道德地位和道德资格,享有人的尊严。
在许多赞成死刑的人看来,杀人犯虽然没有像洛克所说的那样毫无价值,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受害人或潜在受害人的生命比杀人犯的生命更有价值。“无辜者的生命,比杀人犯的生命更加
宝贵”[13](P11)
,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杀人犯的生命以补偿受害人的生命或保护潜在受害人的生命。“保住受害人的生命比保住……谋杀者的生命更
重要。”[14]
这种对人的生命进行分等,认为有些生命更宝贵、更有价值的观点,是与现代人权思想关于人人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的理念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把人的生命分为不同的价值等级,并认为可以为了较高等级的生命而牺牲较低等级的生
命,那么,整个人权理论的大厦就会崩溃。
①
—
101—
洛克的第二条理由(权利丧失原理)被死刑的拥护者广泛接受。根据这一原理,如果一个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那么,他也就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杀人犯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此,杀人犯也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于是,国家就可以代表被害人合理地剥夺杀人犯的生命。然而,这种推理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按照这种“侵犯了别人的什么权利,自己就丧失了什么权利”的逻辑,我们就会推出这样的结论:“强奸犯放弃了其不被强奸的权利,抢劫犯放弃了不被抢劫的权利,以酷刑折磨他人的人放弃了不被酷刑折磨的权利”。这显然是荒谬的。[15]
契约论也是人们支持死刑的一个重要理据。根据契约论的观点,人们在缔结契约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时,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权利(包括保护自己生命、惩罚罪犯的权利)都交给了国家。“社会条约以保全缔约者为目的。”[16](P42)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人们签订了这样一份契约:每一个人都不得毁灭他人的生命;如果有人违背契约,擅自剥夺他人的生命,国家就有权利代表受害人剥夺杀人犯的生命。“正是为了不至于成为凶手的牺牲品,所以人们才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凶手的话,自己也得死。”[17](P42-43)因此,国家对侵犯他人生命的人判处死刑,是完全符合契约正义的。
但是,正如洛克所说,人们是不能把生命权转让给国家的。“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置身于别人的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18](P17)生命权是天赋的,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挣来”的,不是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对象。一个人不拥有剥夺自己生命的权利,他也不可能把自己不拥有的这种权利转让给别人。“谁都不能以协定的方式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即支配自己的生命的权利,交给另一个人。”[19](P17)此外,正如贝卡利亚所说,即使人们拥有剥夺自己生命的权利,他们在签订契约时,也只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了国家,而不可能把剥夺自己生命的权利也交出去。最后,即使以往的人们签订了一份把生杀大权交给国家的契约,现代人也可以不受这份契约的约束。他们可以根据已经进步了的道德观念改变这份契约。因此,从
契约论的角度对死刑所作的辩护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四、生命权:废除死刑的伦理基础
如果说对死刑威慑论和死刑报应论的批判为死刑的废除扫清了理论障碍,那么,生命权的确立则为死刑的废除提供了重要的伦理依据和道义基础。把生命权当作重要的权利来加以确认和维护是所有人权理论和人权公约的共同特征。《世界人权宣言》第3款明确宣布:“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是突出了生命权的特殊地位,把生命权单独列为一款予以强调:“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1983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废除死刑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公约〉第六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死刑应予废除。任何人不应被判处死刑或被处决。”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宣言〉第二任择议定书》。该议定书认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2001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首届反对死刑世界大会”通过的《斯特拉斯堡宣言》也明确指出:“死刑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并确信“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将是对确保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权作出的重大贡献”。
因此,在所有的人权清单中,生命权不仅得到共同的承认,而且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置于各权利之首。事实上,生命权与自由权、财产权等虽同属人权的范畴,但就其性质而言,生命权却具有某种不同于其他权利的特性。生命权的这种特殊属性就是:它是一种基本权利。所谓基本权利,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他人提出的最低限度的合理要求;它们构成了其他合理要求的理性基础。分享基本权利对于分享所有其他权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项权利是真正基本的,那么,任何试图通过牺牲基本权利来分享其他权利的企图都将实实在在地是自拆台角、自挖根基的。因而,如果一项权利是基本的,其他非基本权利可以被牺牲(如果必要)以便确保基本权利。但是,为了确保对非基本权利的分享,却不可以放弃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基本权利或许不能被牺牲,因为它不
—
2
1
—
可能被成功地牺牲掉。如果被牺牲的权利确实是基本的,那么,在缺乏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任何权利(基本权利可能被牺牲给了它)都不可能被实际地分享到。这种牺牲将被证明是自拆台角的。”[20](P19)作为一种基本权利,生命权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享有生命权“是享有一切其他权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21](P175)生命是一切权利的载体。如果人的生命被剥夺了,他就不可能再分享任何权利。人们不可能为了分享其他权利而牺牲生命权,但为了确保生命权,人们却可以暂时牺牲其他权利。不分享生命权,一个人就不可能分享其他权利;而一个人在分享其他权利时,必定同时分享了生命权。
第二,每个人对生命权的分享都只有一次,一旦丧失,就不可能失而复得,而其他权利却可以为了生命权而暂时被牺牲,这些被牺牲的权利可以失而复得,可以丧失多次,也可以分享多次。生命权的一次性导致了它的不可弥补性。生命权的丧失是永久性的,不可弥补的;而其他权利的丧失可以是暂时的,能够得到弥补的。
第三,生命权是某种要么完全享有、要么完全不享有的权利,而对自由权、财产权等非基本权利(相对于生命权而言)的分享则可以有程度的不同,即可以分享得多一点或少一点。对生命权的分享是一次到位的,而对非基本权利的分享则可以是渐进的、逐步到位的。
第四,与其他权利相比,生命权具有某种绝对的性质。这种绝对的性质表现为,享有生命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对于个人来说,生命权须臾不可离,它“是一个人之所以被当做人类伴侣所必须享有的权利”。[22](P158)生命权绝对不容侵犯。即使承认在法定紧急状态下可以牺牲某些人权的亨金也认为,包括“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不能被侵犯或牺牲。[23](P5)
总之,生命权是人作为人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是其他权利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权利中的权利。生命权是人人享有的、内在的、不能让渡也不能剥夺的基本权利。生命权的这种基础性使得以剥夺罪犯生命为目的的死刑难以获得伦理的辩护。
五、余论
死刑问题还涉及对人性和善良生活的理解。死刑的维护者大多对人性持一种比较消极或幽暗的看法,而死刑的反对者更愿意把人性理解得积极或光明一些。他们相信,人们之所以犯罪,乃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家庭、心理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如果条件允许,人们天性都愿意过一种善良的生活,而不会愿意成为杀人犯。不能把罪犯与邪恶等同起来。犯了罪的人仍然是人,是社会的一个成员。死刑废除论者相信:“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使我们不得不接受罪恶,我们仍然有能力作出改变,走向美好。”[24](P32)惩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报应,也是为了改造,实现罪犯与社会的和解,重建社会的团结。我们并不都是锱铢必较的复仇主义者。我们惩罚罪行,但我们应宽恕罪犯。国家也是如此。无论一个人做了什么或变成了什么,他仍然是一个道德主体,应该被当作人来尊重,并享有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在我国,死刑虽然作为一种制度依然存在,但是,死刑的合理性已经日益遭到人们的质疑。在法学领域,我国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死刑应当废除,只是在现阶段的中国不能废除。换言之,从应然性上说,死刑应当废除;从实然性上说,死刑只能暂时保留,逐步予以限制并最终予以废除。的确,要在我国废除死刑,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或许就是民众对死刑的广泛拥护。“以命抵命”的报应观和对生命缺乏敬畏是民众支持和拥护死刑的两个重要伦理理由。我们要改变广泛流行的“以命抵命”的狭隘的罪行报应观,使人们树立尊重和敬畏生命的伦理理念。我们应当用理性、人道的正义理念,引导和提升公民的非理性的、狭隘的报应观念,构建尊重生命、反对死刑的先进伦理文化。
参考文献
[1] Fuman v1Georgia(1972),Greg g v1Georgia(1976)1In Hugo Adam Bedau ed1,T he Death Penalt y in A2 merica:Current Cont roversies.New Y 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
—
3
1
—
[2] 嘎特内尔、贝克特:《杀人与死刑———对一个遏制假设的国际比较》,载邱兴隆主编:《比较刑法》(第一卷,死刑专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3] J1W1Marquart and J1R1Sorensen1“A National Study of the Fuman2commuted Inmates:Assessing the Threat to Society f rom Capital Offenders”.L oy ala of L os A ngeles L aw Review,Vol123,1989。
[4][14] 哈格:《威慑与不确定性》,载斯特巴主编:《实践中的道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13][24] 哈格、康拉德:《死刑论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6]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7] Jeff rey H1Reiman1“J ustice,Civilization and the Death Penalty”.Philosop hy and Public A f f ai rs14,No12 (Spring1985)1
[8] Kant1“The General Theory of J ustice”,in T he Metap hysical Element of J ustice.Indianapolis:Bobbs2Mer2 rill,19651
[9] 哈格:《维护死刑:一个实践的与道德的分析》,载邱兴隆主编:《比较刑法》(第一卷,死刑专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10][11][12][18][19] 洛克:《政府论》,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5] Hugo Adam Bedau1“Capital Punishment”,in Hugh LaFollitte ed1,T he O x f ord H andbook of Practical Ethics1New Y 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
[16][17]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0] Henry Shue1B asic Ri ghts:S ubsistence,A f f l uence,and U1S1Forei gn Policy.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1
[21] 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
[22] 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23] 亨金:《权利的时代》,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Ethical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Death Penalty:
A Perspective from Applied Ethics
YAN G Tong2jin1,L IU Han2qin2
(11Institute of Philosoph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
21Depart ment of Marxism2Leninism,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
Abstract:Et hical debate over deat h penalty is one of t he important issues of contemporary applied et h2 ics.The two oppo site judgment s of t he U1S1Sup reme Court in1970s about t he et hical legitimacy of deat h penalty stimulated t he intense and lasting debate in t he field of applied et hics1The retentionist and deterrent argument s are unable to p rovide et hical justification for capital p unishment1To reveal and expose t he et hical defect s of retentionist and deterrent argument s f rom t he perspectives of conse2 quentialism and deo ntology respectively is helpf ul to eliminate t he et hical obstacles for t he abolition of capital p unishment1
K ey w ords:right s to life;deterrent argument s;retentionist argument s
(责任编辑 李 理)—
—
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