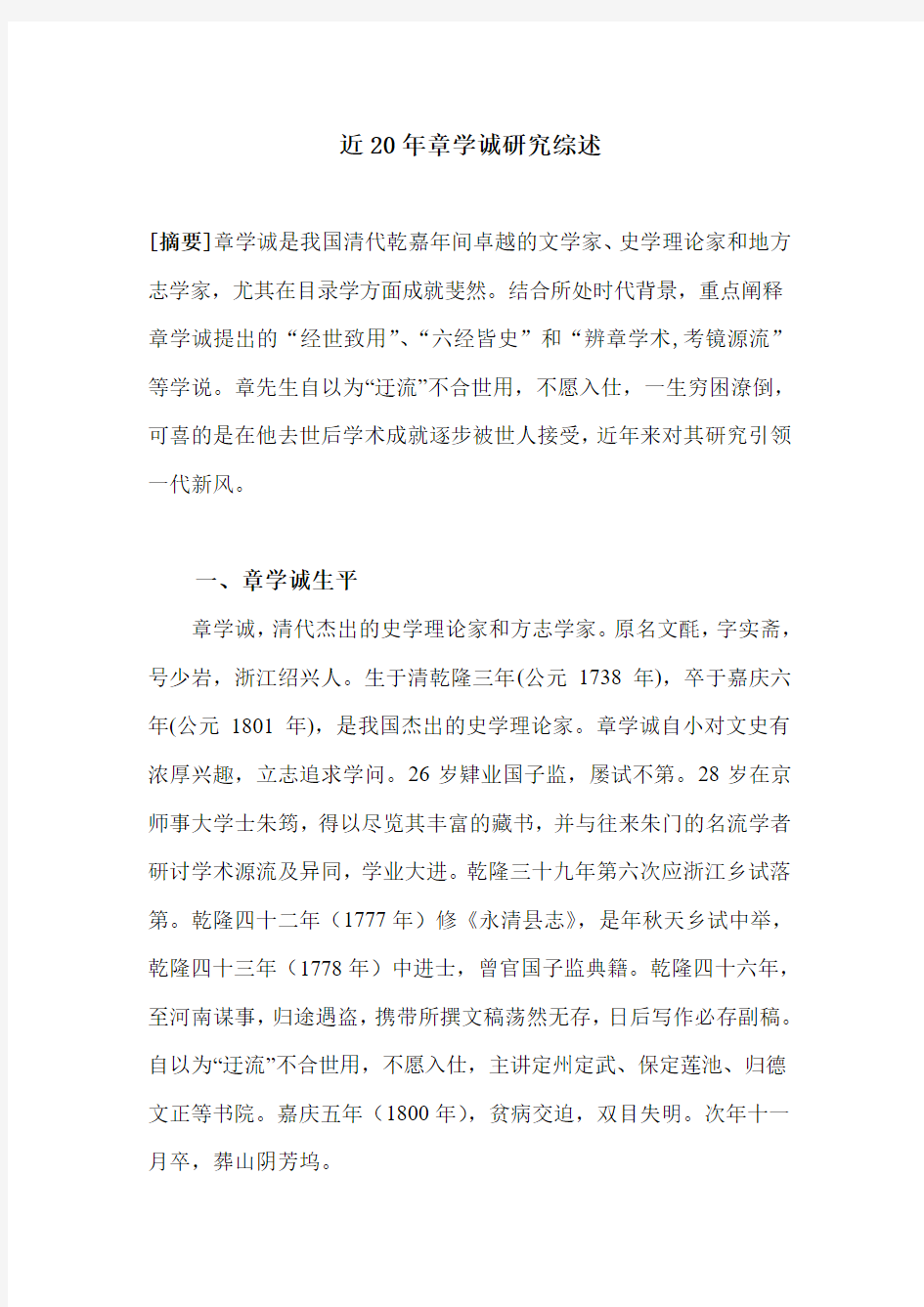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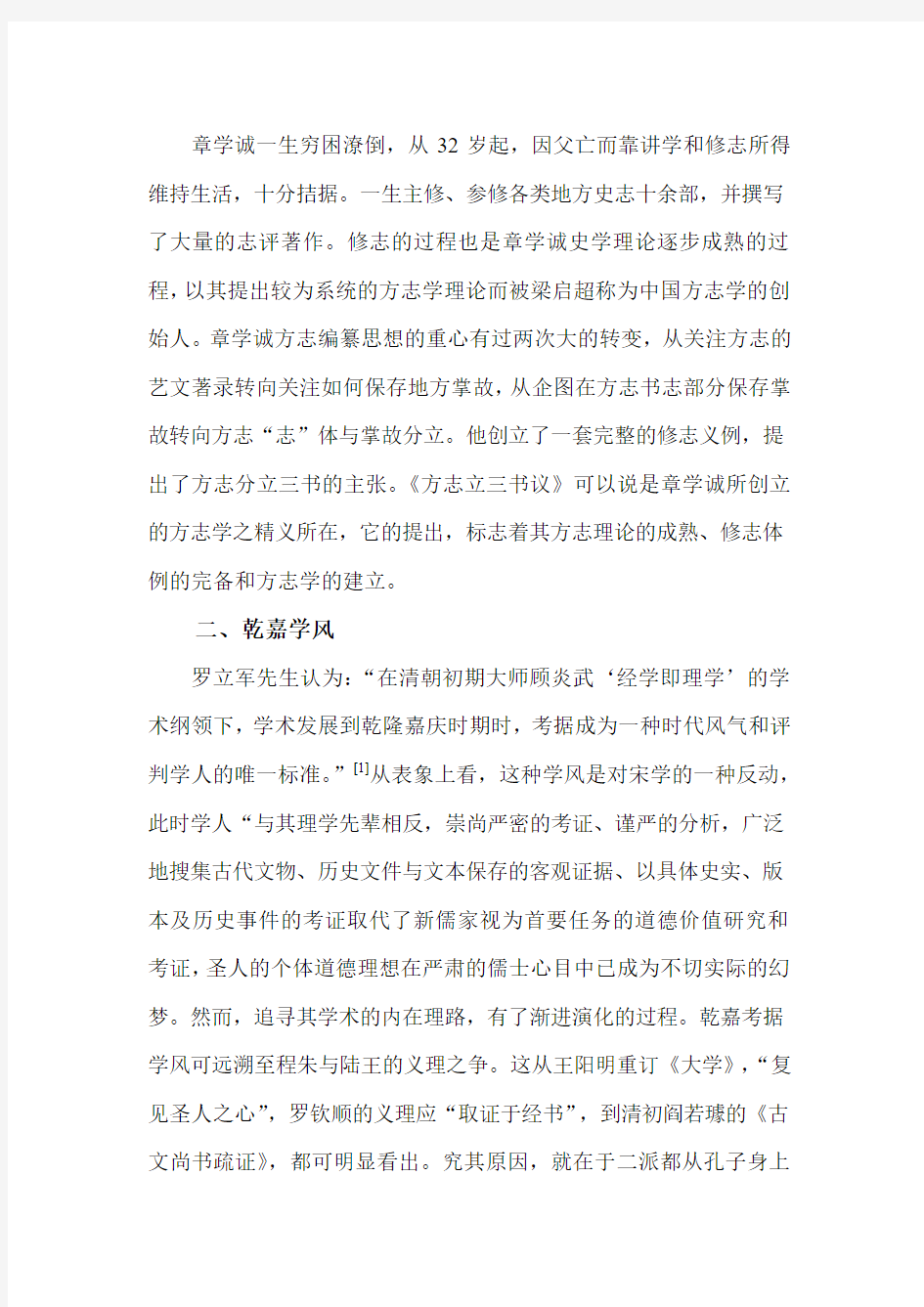
近20年章学诚研究综述
[摘要]章学诚是我国清代乾嘉年间卓越的文学家、史学理论家和地方志学家,尤其在目录学方面成就斐然。结合所处时代背景,重点阐释章学诚提出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等学说。章先生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一生穷困潦倒,可喜的是在他去世后学术成就逐步被世人接受,近年来对其研究引领一代新风。
一、章学诚生平
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字实斋,号少岩,浙江绍兴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是我国杰出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屡试不第。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乾隆三十九年第六次应浙江乡试落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修《永清县志》,是年秋天乡试中举,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曾官国子监典籍。乾隆四十六年,至河南谋事,归途遇盗,携带所撰文稿荡然无存,日后写作必存副稿。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嘉庆五年(1800年),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
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二、乾嘉学风
罗立军先生认为:“在清朝初期大师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下,学术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时,考据成为一种时代风气和评判学人的唯一标准。”[1]从表象上看,这种学风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此时学人“与其理学先辈相反,崇尚严密的考证、谨严的分析,广泛地搜集古代文物、历史文件与文本保存的客观证据、以具体史实、版本及历史事件的考证取代了新儒家视为首要任务的道德价值研究和考证,圣人的个体道德理想在严肃的儒士心目中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梦。然而,追寻其学术的内在理路,有了渐进演化的过程。乾嘉考据学风可远溯至程朱与陆王的义理之争。这从王阳明重订《大学》,“复见圣人之心”,罗钦顺的义理应“取证于经书”,到清初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都可明显看出。究其原因,就在于二派都从孔子身上
做文章,力图证信于经书,从而获得权威,消解争论,这构成了乾嘉考据学风产生的内因;从外缘看,明朝灭亡引发的强烈社会、政治危机,促使清初学者反思,倡导实学,要求研究历史真相,从而达到博古通今,经世致用。但清代的文字狱,阻止士大夫非议朝政,学者欲如清初时期保持强烈的政治色彩,几乎不可能。不过,“清庭对汉族的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他们一方面力图限制知识阶层批评时政,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汉族学者运用经验方法进行研究”[2]。
姜广辉先生认为:“江南处于清朝的经济、文化中心,不仅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丰厚物质条件---图书馆、出版业以及来自官方或商人的经济支持等,而且具有善于学术交流的文化群体。这样的内因与外缘的交汇,使得考据在乾隆嘉庆时期蔚然成风。”[3]从以上分析可知:不管是宋学内部程朱与陆王义理之争诉诸于经书证实的要求,还是明朝灭亡所激起的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情怀,都是宋学自身通过心、性、天、理等的哲学思辩。强调个人道德践履的儒学研究方式是不能满足的,这本身凸显了一个如何开辟新的儒学研究方向的时代课题。清初大师顾炎武、黄宗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斥宋学为空谈,强调“穷经”、“经世”。承继清初大师,尤其是顾炎武新的研究之路,加上学术研究本身发展的深入以及政治的影响,发展到乾嘉时期时,学风已经陷入了“穷首皓经”的考据事业,遗失了清初学者的“经世”大义。因此,如何转换学风、开辟新的学术研究方向的问题又重新“浮到水面上来”。
三、史学
1.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最高成就,他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乾嘉学术时代独树一帜。旧中国的史学体例系统经历章学诚时期发展而完备,“史学”一名也从章学诚而开始。
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人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同时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4]白先生的论断,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民族,历代史家和思想家在考察历史和评论史学的实践中得出了深刻的思想认识,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论。在这些史家中,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具有代表性。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方法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褐集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有助于对其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方法论作出深人研究、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在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上表现出明确的历史进步观念。第一,章学诚客观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演变法则。章学诚论述人类社会的形成,明确指出:“人生有道,人不自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
自然,渐形渐著。”[5]章学诚认为人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圣人偶然设想出来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二,章学诚继承和发展了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和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等人重“势”的历史观念,更加强调“时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因。章学诚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看作是一个自然运动过程,突出强调了“时势”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批评那些盲目颂扬周公制礼作乐的学者,论证人类社会发展乃“时势”相激的自然运动。章学诚指出:“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鉴唐、虞,唐、虞之鉴羲、农、黄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于天也。”[6]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思想。乾嘉时期的史家中不少人有佞古积癖,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矜炫“博古”而昧于“知时”的流弊。
[7]章学诚从理论上总结了“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在关于古今历史相互区别与联系的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第一,章学诚主张认识历史应当明确把握古今关系,反对主观割裂历史的发展进程,强调史家应当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章学诚指出,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史家治史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前后接续,不应在二者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把历史和现实绝对割裂开来,就会陷人崇古论之中。他认为古今社会的发展相因相续,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章学诚指出:“后之视今,犹
今视古也,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8]他讥讽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知时”的人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肩负的时代使命:“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旗帜鲜明地表明治学应当着眼于现实时代,而不是钻进故纸堆中讨生活。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中闪烁着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光辉思想,对古今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了较高的理沦层次。第二,章学诚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前后赓续而来,当代社会乃是这个发展过程的顶峰。他关于“礼时为大”的明确主张,是对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个重要认识。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8]。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古今历史发展面貌是不相同的。居今之世,尤其应当注重现实,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重点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研究历史为现实社会服务。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9]。
中国古代史学中曾经出现过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批评方法,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史学批评的失实。章学诚借鉴了前代史家在史学批评方法上的经验和教训,对史学批评方法论作了深人探讨,形成了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史学批评必须结合特定时代,不能混淆时空概念。章学诚在史学批评中反对以古律今或以今度古的非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突出强调了从实际出发的史学批评原则。史学批评必须继承多
闻网疑的传统,不可凿空立论。罗炳良先生认为:“后人对远古史学源头的认识应当遵循多闻网疑的原则,前代史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后人若无新材料证实只能存疑,不应该凿空立论,形成了重要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历史上某些名物、制度和事件,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搞清楚,遇到这类问题只能存疑。如果争名求胜,一定要超过古人,强作解释,就不免穿凿附会。”[10]中国古代史家大多能够发扬多闻网疑的传统,并以此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然而有些史家却背离了这一传统,治史穿凿附会,以致史学批评中出现许多错误结论。章学诚指出,违背多闻网疑的史学批评原则必然会导致两种错误结局。史学批评必须坚持多闻网疑的原则,否则其结论不是忽视历史事实的存在,就是虚构历史事实的存在,结果都不会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其二,史学批评应当审慎之至,如果没有事实依据而凿空立论,故意标新立异,必然造成貌似创论,实为臆说,曲解古人的恶果。
2.章学诚的“史德”思想
在刘知几之后,章学诚之前,对史家修养问题有重要论述的明代史学家胡应麟不应该被忽视。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提出“二善”说,以补充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呼?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异。史呼?是乎?这里的“公心”与“直笔”即胡应麟所要补充的“二善”,所谓“公心”是指修史者在予、夺、褒、
贬历史时应有的素质,,以“万人之衷为一人之衷”做到客观公正。
[11]胡的“公心”、“直笔”说是对刘知己史家三长中的史识的进一步发展。
章学诚是古典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明确提出“史德”及相关的“心术”等概念,将我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推向了高峰。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集中论述了才、学、识问题。章学诚指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
[12]他采取思辩而不是打比喻的方式来阐述才、学、识之间的关系,学是知识储备的基础,识是判断的能力和水平,而才只是文才,是学与识的表现形式。三者中,他尤重史识。“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章学诚把才、学、识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更加深刻、透彻了。
杨向奎先生认为:“唐以前,史家修养主要是一种史学伦理道德的要求,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论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细化深化,章学诚没有简单地强调道德标准,他意识到,伦理标准和道德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每个人心中都有完善的史学标准,但是要在史学活动中实践它却是个大问题。”[13]因此章氏提出“史德”、“心术”,力图在史学伦理标准和史学实践中架设一座桥梁。
四、六经皆史”与史学的经世致用
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理论是对儒家经典传统统治地位的颠覆,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继承发扬了史学“经世”思想。在宋儒学者看来,“道”既然为“形而上”之本体,则必然是永恒不变的,
因此宋儒要求于“主敬”功夫中见本体。“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一”,万事万物分有“道”,于是有了“多”。离开了“历史化”,“绝对精神”的形上本体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14]如果我们把“六经皆史”的理论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最终还是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
戴震是乾嘉考据学风的代表,其系统发挥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自信“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5]。为了扭转风气,章学诚回归官师政教合一的三代,提出“六经皆史”的论证纲领,对此中心理论提出挑战,力图打破以经载道的神话。“六经皆史”的思想虽非章学诚首倡,但经他奋力阐发,于后世影响深远。在乾嘉时代,“六经皆史”涉及史学是否与经学分庭抗礼之争议,又关乎“汉学”与“宋学”之交攻;到了晚清,则与愈演愈烈之今古文经学争议产生了不解之缘;而民国新史学家胡适先生提出的“六经皆史料”,亦不能与之完全摆脱干系。时至今日,当代学者在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本意为何以及对该命题做出如何评判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
了,甚至表现得更加难解难纷了。其中,在两个关节点上分歧尤为严重。其一,究竟是从“史料”扩展的角度,还是从“经世”或“史意”的角度入手探讨,才更能得章氏之本义?胡适曾说:“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16]这种论断开了从“史料”扩展的角度对之加以诠释的先河。钱穆先生则批评此类看法为“误会”,认为章氏“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而提出的,“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是有着强烈经世精神的大理论[17]。周予同也主张“章学诚所指的‘史’,主要是指具有‘史意’、能够‘经世’的史”。仓修良虽不否认其“经世”之意蕴,而坚执“六经皆史”的“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18]其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是否蕴涵了尊史抑经的意味,是否提出了以史代经或以史抗经之说,从而在清代学术史上是否具有创辟的价值,对后世来说是否具有破除对儒家经典迷信的思想启蒙意义?孙德谦欣赏章氏“六经皆史”说的经世之旨,并对章氏“六经皆史”说与当时“汉”学———“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学相颉颃之意味已略有揭示。钱穆不但系统深入地阐发了章说所针对的语境,指出戴震与章学诚“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并称言“实斋唱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余英时认为章学诚“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他着重于从“心理”角度阐发章氏以文史校雠之学与戴震经学抗争之意。[19]
五、目录学
章学诚在目录学理论上的贡献是把目录学的传统和任务总结为“辫章学术、考镜源流”,主张从学术史的角度开展目录工作,认为类例、序文、叙录、互著和别裁是目录工作的主要方法。章学诚在目录学实践上的贡献是编撰了《史籍考》,树立了史学专科目录的典范,制作了《韵览》、《别录》,引领一代索引新风。王新凤先生《试论章学诚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的贡献》,认为章学诚对古代目录学的贡献:一是明确提出了目录学的主要职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本体论,它包括对文献文本的整理和维护,对文献文本内容的梳理,对文献的超文本内涵之"道"的梳理。[20]二是章学诚对我国古代分类法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分类法应根据学术的变迁及书籍情况而更改”,并把传统的目录学治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目录学的整理和研究,提出了互著别裁、编制索引等目录学治学的具体方法。另外章氏还通过通过对现实流弊的思考、批判和对刘向父子目录学精神的总结弘扬,确立起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目的论;然后以特有的哲学观、历史观来判定目录内涵,使目录服务于著录的目的,由此建立起自己的目录学认识论。
章学诚有关目录学的论述,在他所撰目录学专著《校雠通义》以及《文史通义》、《史籍考》里都有充分反映。首先是有关目录学的目的与任务问题。在他看来,目录学绝非“部次甲乙”的简单分类,而应该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申明大道”,“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21],将文献图籍、目录和学术研究连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最终目的是为学术研究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首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意即分清学术流别,考溯学术渊源,使读者能清楚了解学术之门径,区分学科之范围,有利于治学。对于“申明大道”,章学诚亦作出阐述,认为凡治学者都应该“先明大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22]。因而“明大道”就是指认识学术的发展规律,它显然是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紧密相扣的。可以这样说,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他的目录学理论的核心,它突破了以往人们有关目录学范畴的狭隘概念,赋予目录学以学术史的丰富内容,从而大大地拓宽了目录学领域,提高了目录学的学术地位,更充分地发挥目录学对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章学诚对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大贡献。
在图书著录及分类法上,章学诚亦颇多创见,其要者大致有四:其一是以发展观点看待图书分类法之演进。他自己就经历过这种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如他早年撰《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时,对“四部”分类取代《七略》分类多有批评,认为是“师失其传”;但经其后实践,以发展眼光重新审视,已认识到“《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他甚至具体胪列出“四部”之不能重返《七略》旧法的五大理由:“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名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非总集。”总之,“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
判如霄壤,又安得执。[23]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是所有文献中都论述到的一个问题,是章学诚的重要理论贡献。在谈到他这一思想产生的问题上,梅森认为,章氏的这一理论源于刘向、刘歆,因为他在《校雠通义》一开篇就直言不讳地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24]。但大部分人认为他的这一思想的产生与他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当时,清政府为了巩固它的反动统治,在思想统治方面大大地加强了,屡兴文字狱,提倡脱离政治的考据学,组织学者、专家编纂大丛书,大类书等,在这种反动政策的影响下,学者们都埋头于“故纸堆”中,只知“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章学诚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学术空气,特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编纂图书目录的指导思想。谢伟涛指出认为:目录学的对象是图书,目录学的任务是揭示图书资料的内容,为学术思想研究提供正确的材料,在他看来,学问与图书资料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目录学不能“只为部次甲乙之需,而应当部次条别,申明大道,叙例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凡有涉及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校雠通义》卷一,互著第三)”。[25]
六、地方志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地理、古代世界、历史等,由古代如何演化成现代的因由。最早《周礼》有“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秦
朝以后,方志渐多,《后汉书·西域传》“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南北朝以后方志进入发展时期,有《豫章古今记》、《荆州记》、《华阳国记》,皆初具方志规模。隋唐宋时期方志有进一步发展,体例亦日臻完善。
章学诚一生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所著《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文学理论名著。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后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方志批评是方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学诚的方志批评是章氏方志学思想的内容之一。因此,研究章学诚的方志批评,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章氏的方志学思想,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总观章学诚的一生,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编修史志;二是进行史学和方志学的理论研究。从而实现了他早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的意愿。而且章学诚在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同时代人不能企及的。其中,方志批评则是他史
学和方志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方志批评,章学诚向所重视,他曾说:“哪人少长贫困,笔墨干人,屡膺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其间评鹭古人是非,断酌后志凡例,盖尝详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质,因体立裁,至于立法开先,善规防后,既非职业所及,嫌为出位之谋。峋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通读《文史通义》,就会时时看到他有关方志批评的论述。至于“七志”书后,则更是他关于方志评论的专文,为大家所熟知。
章学诚为什么如此重视方志批评呢?张景孔先生以为:其一,章氏把开展方志批评作为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环节。[26]我们从《文史通义》可以看出,章氏每对方志的批评,多是指其不可,同时明其当行,以期达到求善救弊提高方志编修质量的目的。他指出:“对于“古人已定之评,断不可以私见求异”,然而,对于“不敢轻为称许”者,则予,“专篇讨论”,这是为了救“流弊”,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就是他对方志某一体裁的批评也是旨于此的”。如他批评“今之志人物”,“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骄.尺赎寒温之辞,薄书结勘之语,滥收狠入,无复剪裁”,“其为痛弊久矣”。并且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畸。由此可见,章学诚批评方志人惚志之“病弊”,旨在提高人物志编纂质景姚良苦用心。其二,方志批评是章氏借以阐发方志理论的重要方面。章氏的方志批评,一般是品藻古今方志是非,从而进一步阅述其它方志学理论。“七志”就涉及到有关方志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比如,“志乃史裁”是阐明方志的性质。“史家法度”是评估
方志优劣的绳尺。“文人不可与修志”的提出是强调方志文辞的严谨和史实的确凿。对“纂类之法”和“著作体”的评析,是强调方志采用著述体的重要性。总之,章氏在评论“七志”中所涉及到的有关方志的性质、体例、章法、文辞等方面的问题,都是方志学理论的一些重要内容,为章氏方志学的建立提供了一系列的基础理论依据。其三,方志批评是章氏去“故我”存“真我”的不断进取的过程。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有不少回顾和评析过去之事及往昔之文的论述,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批评“故我”而追求“真我”的不断进取的精神。他说:“出都三年,学间文章,差觉较前有进。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由今观之,悔笔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轻刻板也。然观近所为文,自以为差可矣,由此以往,少或五七年,多或十许年,安知不又视近作为土直乎:念及于此,而日暮途长,勉求进业,以庶几于立言之寡愈,真有汲汲不容稍缓者已。章学诚进行自我批评,以己与往为非,进取追求的精神跃然纸上。这一点,他在不少文章中都有表露,如他还说:“欲存我者,必时时去其故我,而后所存乃真我也。作为一个封建社会时代的史学家、方志学家,能有这徉的以己为非,不断探求的进化演进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罗立军.《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04期.
[2]蒋国保.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新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11月第39卷第6期.
[3]姜广辉.乾嘉考据学成因诸问题再探讨[J]中国哲学.2010年第06期.
[4]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M].台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
[5]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述学驳文[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述学驳文[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罗炳良.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J]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01期.
[11]王嘉川.《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1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礼教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3]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8.
[14]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陈东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J].1998年第01期.
[16]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 1979年.
[17]钱穆.《中国学术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册第239页。
[18]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 2000.
[20]王新凤.《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02期.
[21]章学诚.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966.
[22]章学诚.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937.
[23]章学诚.《校雠通义》[M]北京.古籍出版社.1963.
[24]章学诚,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945.
[25]谢伟涛.章学诚与余嘉锡目录学思想比较研究 [J].图书馆, 2004,(3).
[26]张景孔,《章学诚方志批评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5年9月第37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