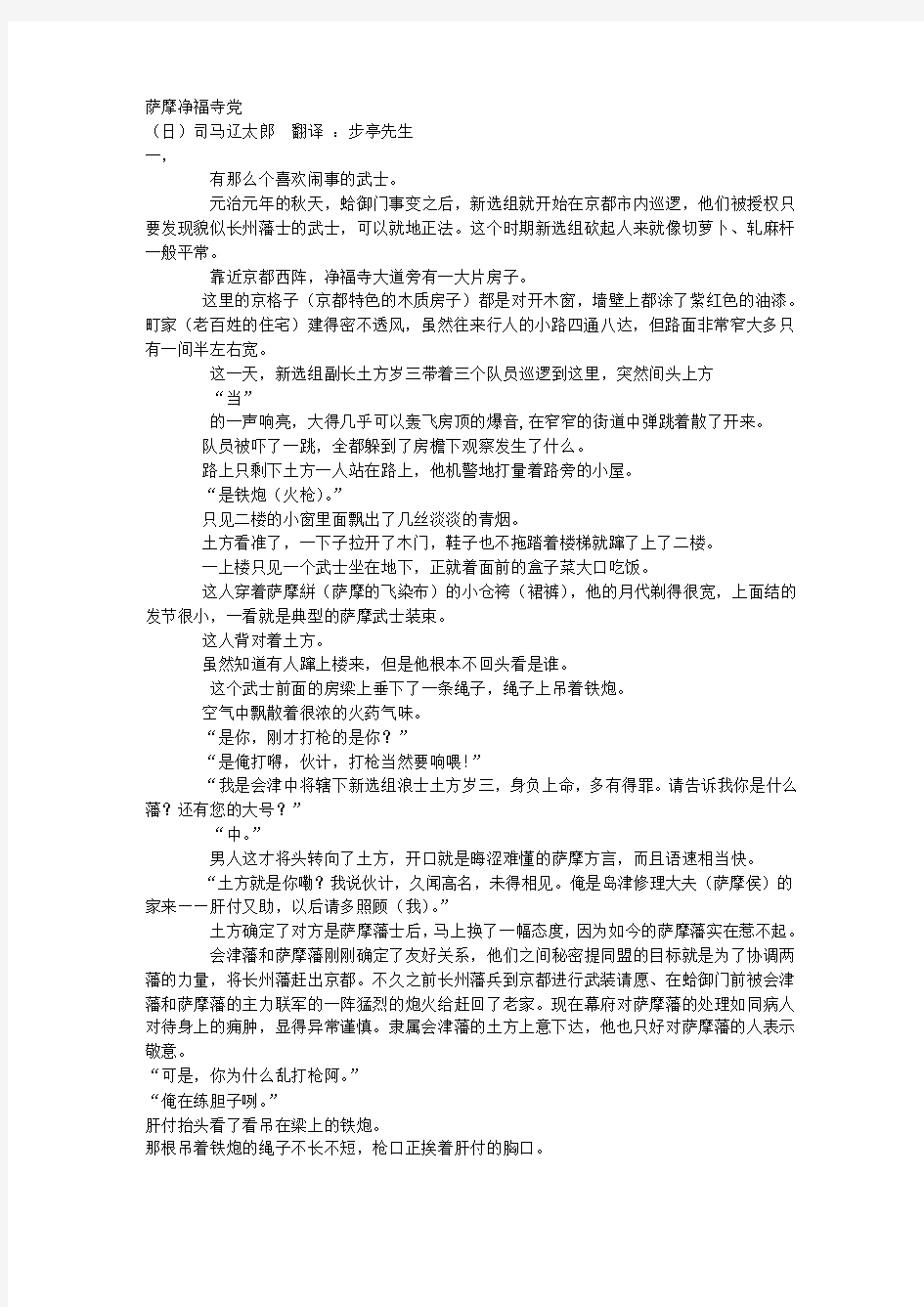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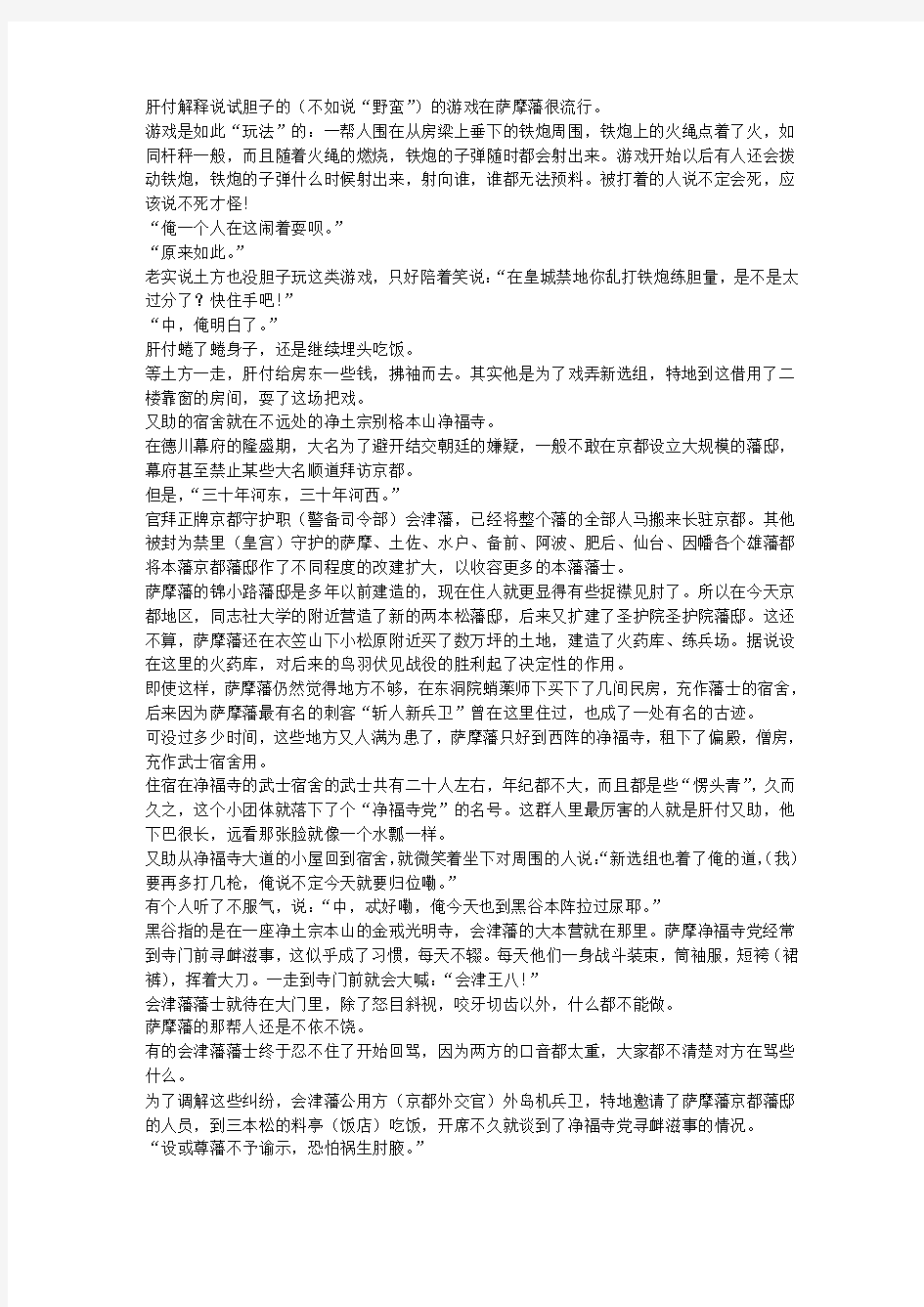
萨摩净福寺党
(日)司马辽太郎翻译:步亭先生
一,
有那么个喜欢闹事的武士。
元治元年的秋天,蛤御门事变之后,新选组就开始在京都市内巡逻,他们被授权只要发现貌似长州藩士的武士,可以就地正法。这个时期新选组砍起人来就像切萝卜、轧麻杆一般平常。
靠近京都西阵,净福寺大道旁有一大片房子。
这里的京格子(京都特色的木质房子)都是对开木窗,墙壁上都涂了紫红色的油漆。町家(老百姓的住宅)建得密不透风,虽然往来行人的小路四通八达,但路面非常窄大多只有一间半左右宽。
这一天,新选组副长土方岁三带着三个队员巡逻到这里,突然间头上方
“当”
的一声响亮,大得几乎可以轰飞房顶的爆音,在窄窄的街道中弹跳着散了开来。
队员被吓了一跳,全都躲到了房檐下观察发生了什么。
路上只剩下土方一人站在路上,他机警地打量着路旁的小屋。
“是铁炮(火枪)。”
只见二楼的小窗里面飘出了几丝淡淡的青烟。
土方看准了,一下子拉开了木门,鞋子也不拖踏着楼梯就蹿了上了二楼。
一上楼只见一个武士坐在地下,正就着面前的盒子菜大口吃饭。
这人穿着萨摩絣(萨摩的飞染布)的小仓袴(裙裤),他的月代剃得很宽,上面结的发节很小,一看就是典型的萨摩武士装束。
这人背对着土方。
虽然知道有人蹿上楼来,但是他根本不回头看是谁。
这个武士前面的房梁上垂下了一条绳子,绳子上吊着铁炮。
空气中飘散着很浓的火药气味。
“是你,刚才打枪的是你?”
“是俺打嘚,伙计,打枪当然要响喂!”
“我是会津中将辖下新选组浪士土方岁三,身负上命,多有得罪。请告诉我你是什么藩?还有您的大号?”
“中。”
男人这才将头转向了土方,开口就是晦涩难懂的萨摩方言,而且语速相当快。
“土方就是你嘞?我说伙计,久闻高名,未得相见。俺是岛津修理大夫(萨摩侯)的家来——肝付又助,以后请多照顾(我)。”
土方确定了对方是萨摩藩士后,马上换了一幅态度,因为如今的萨摩藩实在惹不起。
会津藩和萨摩藩刚刚确定了友好关系,他们之间秘密提同盟的目标就是为了协调两藩的力量,将长州藩赶出京都。不久之前长州藩兵到京都进行武装请愿、在蛤御门前被会津藩和萨摩藩的主力联军的一阵猛烈的炮火给赶回了老家。现在幕府对萨摩藩的处理如同病人对待身上的痈肿,显得异常谨慎。隶属会津藩的土方上意下达,他也只好对萨摩藩的人表示敬意。
“可是,你为什么乱打枪阿。”
“俺在练胆子咧。”
肝付抬头看了看吊在梁上的铁炮。
那根吊着铁炮的绳子不长不短,枪口正挨着肝付的胸口。
肝付解释说试胆子的(不如说“野蛮”)的游戏在萨摩藩很流行。
游戏是如此“玩法”的:一帮人围在从房梁上垂下的铁炮周围,铁炮上的火绳点着了火,如同杆秤一般,而且随着火绳的燃烧,铁炮的子弹随时都会射出来。游戏开始以后有人还会拨动铁炮,铁炮的子弹什么时候射出来,射向谁,谁都无法预料。被打着的人说不定会死,应该说不死才怪!
“俺一个人在这闹着耍呗。”
“原来如此。”
老实说土方也没胆子玩这类游戏,只好陪着笑说:“在皇城禁地你乱打铁炮练胆量,是不是太过分了?快住手吧!”
“中,俺明白了。”
肝付蜷了蜷身子,还是继续埋头吃饭。
等土方一走,肝付给房东一些钱,拂袖而去。其实他是为了戏弄新选组,特地到这借用了二楼靠窗的房间,耍了这场把戏。
又助的宿舍就在不远处的净土宗别格本山净福寺。
在德川幕府的隆盛期,大名为了避开结交朝廷的嫌疑,一般不敢在京都设立大规模的藩邸,幕府甚至禁止某些大名顺道拜访京都。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官拜正牌京都守护职(警备司令部)会津藩,已经将整个藩的全部人马搬来长驻京都。其他被封为禁里(皇宫)守护的萨摩、土佐、水户、备前、阿波、肥后、仙台、因幡各个雄藩都将本藩京都藩邸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建扩大,以收容更多的本藩藩士。
萨摩藩的锦小路藩邸是多年以前建造的,现在住人就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所以在今天京都地区,同志社大学的附近营造了新的两本松藩邸,后来又扩建了圣护院圣护院藩邸。这还不算,萨摩藩还在衣笠山下小松原附近买了数万坪的土地,建造了火药库、练兵场。据说设在这里的火药库,对后来的鸟羽伏见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即使这样,萨摩藩仍然觉得地方不够,在东洞院蛸薬师下买下了几间民房,充作藩士的宿舍,后来因为萨摩藩最有名的刺客“斩人新兵卫”曾在这里住过,也成了一处有名的古迹。
可没过多少时间,这些地方又人满为患了,萨摩藩只好到西阵的净福寺,租下了偏殿,僧房,充作武士宿舍用。
住宿在净福寺的武士宿舍的武士共有二十人左右,年纪都不大,而且都是些“愣头青”,久而久之,这个小团体就落下了个“净福寺党”的名号。这群人里最厉害的人就是肝付又助,他下巴很长,远看那张脸就像一个水瓢一样。
又助从净福寺大道的小屋回到宿舍,就微笑着坐下对周围的人说:“新选组也着了俺的道,(我)要再多打几枪,俺说不定今天就要归位嘞。”
有个人听了不服气,说:“中,忒好嘞,俺今天也到黑谷本阵拉过尿耶。”
黑谷指的是在一座净土宗本山的金戒光明寺,会津藩的大本营就在那里。萨摩净福寺党经常到寺门前寻衅滋事,这似乎成了习惯,每天不辍。每天他们一身战斗装束,筒袖服,短袴(裙裤),挥着大刀。一走到寺门前就会大喊:“会津王八!”
会津藩藩士就待在大门里,除了怒目斜视,咬牙切齿以外,什么都不能做。
萨摩藩的那帮人还是不依不饶。
有的会津藩藩士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回骂,因为两方的口音都太重,大家都不清楚对方在骂些什么。
为了调解这些纠纷,会津藩公用方(京都外交官)外岛机兵卫,特地邀请了萨摩藩京都藩邸的人员,到三本松的料亭(饭店)吃饭,开席不久就谈到了净福寺党寻衅滋事的情况。
“设或尊藩不予谕示,恐怕祸生肘腋。”
话说得很文明,这也是会津藩的无奈之举,他们之间谈话如果不用文言,两个藩就无法交流了。文言不能将话语中的轻重缓急表现出来,萨摩藩照本宣科地敷衍了会津藩的要求。不过萨摩藩官员被其他藩的官员用如此口气训斥,实在是气不打一处来。
萨摩藩答应会津藩说要“善处”,确实也这样做了。他们从京都藩邸派了两个目付(官职)到净福寺对这帮人进行教育,教育当然是表面形势的。不过跟目付一块来的周旋方(外交官)高崎左太郎(后来改名正风,男爵)和萨摩藩的兵学家伊地知正治(后来成为东山道先锋,伯爵)异口同声地说:“今后会津藩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国(萨摩藩)必须要协调(会津藩),不然事情很麻烦。”
就是最后这句话让年轻的肝付又助非常非常不开心,等两个头头一走,就和自己的同志说:“他奶奶的,俺也是为了国家(萨摩藩),罢罢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从此以后他就经常扛着枪,戏弄每天准时巡逻到净福寺大街的新选组队员。
又助本来就是个爱恶作剧的人,除此之外他身上还有一种政治思想在作怪,这其实是个谜。不过,作为一个萨摩人,他对长州过激分子制造的蛤御门事件并不感到厌恶,而且对如今被会津藩、幕府当作朝敌的长州藩非常同情。他对萨摩藩的头头和会津藩联手打倒长州藩的行为非常不感冒。
“那就让我挑拨两个藩开始闹矛盾。”肝付是这么想的,他也就这么做了。不久他就对会津藩和新选组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二,
自从肝付开始自己的行动之后,就没有“小打小闹”,如果将打空枪吓人和他后来干得事相比,打枪吓人只能算是“毛毛雨”。
萨摩藩接受了皇宫九个门之一乾御门的警戒任务。接受任务后不久的一个傍晚,肝付就来到了拱门的岗哨上值班。
没多久,离岗哨不远的路上,来了四个巡逻的新选组队员,只见他们身着队服,趾高气扬地晃过了岗哨。
又助马上跟了上去。
新选组队员一行人朝北走,绕过近卫宅第,朝东一拐,就上了今出川大街。这条路右面是近卫宅第的外沟,左面是藤谷、冷泉、山科诸公卿的宅第,路上异常冷清。
肝付快步绕到队员的前面,和队员正打了个照面。
“俺是长州人勒。”
肝付那口萨摩方言,那像长州人?话音刚落,他就朝今出川大街东面狂奔而去。
四个队员,毫不犹豫的拔刀追了上去。
一追一敢,就来到了寺町,这时又助突然停了下来。
队员被搞得不知所措,只见又助单脚踏住撞木,上身朝右面侧倾,举起手中的太刀直指血红的天空。他又在恶作剧,那幅得意洋洋的样子如同半夜察房的军官一般。
“臭小子。”
新选组队员一哄而上,有人拔刀向他砍去,又助不慌不忙地低下了头,对方的剑正好从他背上轻轻掠过,等到又助再抬头,手中的太刀也挥了出去,一刀正好砍在对方会津藩士的肋骨上,那人连叫都没叫,横翻到了一旁的地上。
又助顺势朝旁一闪,人就没影了。
当又助回到乾御门的岗哨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他的同志。
大家问他到底干吗去了?又助说:“俺替相良报仇去勒。”
所有人一听都沉默不语了。
谈论相良重助和同新八郎兄弟两个人的事在萨摩藩属于最大的禁忌,相良兄弟很早就和长州藩有了联系,他们认同“长州方式”——那种过激勤王理论,在长州藩被赶出京都政界,驱
逐回广岛老家以后,他们还是支持长州藩,不久甚至脱藩来到长州,加入长州部队到京都参加了蛤御门事变。事变失败之后,兄弟俩准备逃往丹波地区,当他们和长州藩士楳本倦之助来到京都西南老之坂附近槛木原时,被新选组和小浜藩藩兵的联合部队发觉了,他们死力奋战,砍死了六个人,砍伤二十个人,最后力竭而死。
敌人将他们的尸体乱砍一气,并在路上拖沓糟蹋了很长一段路程,然后弃尸扬长而去。地方上的老百姓实在看不过去,夜里悄悄地将尸体埋在一个无名的小岗上。第二天有人跑到萨摩藩邸汇报了这件事,萨摩藩邸回答是:“你们大概搞错了吧?我们藩没有叫这样名字的人。”好像死去的人和萨摩藩根本没有关系一般。这是因为如果被人知道“长贼”——长州藩进犯京都的部队中有萨摩人,会让萨摩藩立场异常尴尬。
笔者再说些废话,萨摩人即使在维新以后也没有正式承认过兄弟的存在,维新政府中的长州人实在过意不去,四处奔走了好久,才让政府勉强指定两人的坟墓为“官修坟墓”。
肝付和相良兄弟论起来是堂兄弟,所以只要想起本藩讳莫如深,不予祭祀的堂兄弟,又助原本就狂躁不羁的心就会变得更加波澜激荡。
萨摩净福寺党的过激行动,在新选组里也引起了议论。
“(在这样放任他们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的威信。”
局长近藤勇这样说,可是从幕府和会津藩立场上来说,谁都不敢当面锣,对面鼓挑战萨摩藩。正大光明不行,就有人想阴谋诡计了。
“这个人,蛮有趣的。”
土方岁三边想着肝付那张很有特色的脸边自言自语了起来,这个男人的嗅觉非常灵敏,他很直觉的判断,那天在寺町附近袭击新选组队员就是这个“凹面冲额骨”的萨摩人。
“一定是那个瓢脸的男人。”
土方对敌人也包含着异样的“爱情”。
“找人悄悄砍了那个‘秃瓢’,不过计划一定要周密。把他除掉的话净福寺党说不定就会群龙无首。‘秃瓢’的大号叫肝付又助。”
“干得了吗?这个?”
近藤竖起一个指头,晃了晃。
“我看行,寺町(袭击事件)如果是他干的,我们的组织里对付的了他的队员,两三个人总还是有的。”
土方命令监察部联络町奉行所,找几个“包打听”,全天监视又助的行动。
几个“包打听”很快就将西阵净福寺监视了起来,京都的“包打听”和江户的“包打听”相比,缺少了幕府的庇护,办起事来多是走过场。前年的秋天,绰号“猿文吉”的“包打听”文吉,在三条河原被萨摩藩士田中新兵卫施以“天诛”(过激倒幕分子进行的暗杀活动)——活活勒死以后,京都的“包打听”经过萨摩、长州、土州的藩邸前,都不声不响、低头快快走过了事。
第二天,有个“包打听”被净福寺党给逮住了,还没等他们动手,就招供说是新选组指使他干的。
“甭杀他,后日也好当个凭证。”
又助非常清楚这帮人是针对自己,他认为自己干的事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志士活动”。率性而行,以后再找道理是又助的行事作风。一直以来又助就认为贯彻尊王攘夷的理想,必须彻底破坏萨摩藩和会津藩的同盟关系。以肝付的人生观来说,现在自己的任务就是制造事端,这是一桩完全正义的事业。
京都的萨摩藩邸一直享受着“治外权法”,过去幕府的捕吏从来没踏进过藩邸。
“(新选组的)探子摸了进来。”事情一传开自然让其他净福寺党的党徒气炸了肺,有人还说:“到壬生(新选组的驻地)杀他娘个痛快。”这时又助反而让大家少安毋躁。
“俺要是咯屁了,哪位伙计快到锦小路告诉年寄(萨摩藩的领导),让他们赶快替俺报仇。嘛,你说嘛,五门大炮就能把几百个壬生浪人炸成末,中,这么着会津藩跳脚,幕府跳脚,俺们藩说不定就和长州联手,闹他个天翻地覆嘞!”
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在北野天满宫又发生了一件和又助浑身不搭界的事件,又助一听说事件的原委又出马了。
北野天满宫的庙前,有一对石造的雌雄狮子像,高一丈四。这是前年长州藩势力在京都如日中天之时,藩主毛利大膳大夫捐赠的,自从石狮子被安置好以后,就成了京都新的一道风景。狮子的基石上篆刻着博士高千少纳言修长的文章,落成以来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前来观赏,直到长州藩的势力被赶出京都以后,还是天天人潮不断。有的游客还会高声朗读基石的文章:“肃肃庙前,双狮护卫,帖耳驯服,敢逞勇势。”文章的内容将长州藩比作护卫王城的狮子,他们的军容,精神都是可称可赞。
黑谷本阵的会津藩士非常讨厌这对石狮子,有一次,会津藩士数人提着鞭子来到庙前抽打石狮子。
口中还高声骂道:“长州狮子,汝为何尚未散去。”
他们还恐吓庙里的祢宜(神官):“你们要是不把狮子搬走,那只好我们动手了。”说完就拂袖而去。
天满宫的神官没有去向上级神社汇报这个情况,反而去找一向比较好说话净福寺的萨摩藩士求助,求他们保住那对狮子。
又助听完了神官的诉苦大声说:“中。”马上挑了十个人,连他自己在内,都手拿木刀,头戴天狗的假面。因为他们打扮成天狗的样子,所以后世将接下来发生的事件称为“北野天狗骚动”。
他们每天在天满宫石鸟居(牌坊)后面的忌明塔附近埋伏,等着会津人前来搬狮子。人数按部队操练和警备情况人数不一。
开始埋伏的第三天最惨,躲在忌明塔后面的只剩下又助一个人了。
此时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天狗面具上的红色颜料都被雨水给冲化了,又助还是一动不动的蹲着。
天就要快黑下来了。
七个会津藩士不等天全黑下来,就提着被雨丝打湿的灯笼从参道(神社前的道路)上走来。一行人来到石狮子的前面,七手八脚的用麻绳将石狮子捆了起来,然后架起了撬杠,眼看就要将石狮子搬倒了。
又助身形如同猴子一般敏捷,三蹿两蹿就蹦到了他们面前,挥舞起木刀,迅雷不及掩耳一般砍向手执麻绳的三个会津藩士的脚踝骨。
“有奸细。”
正在拨弄撬杠的其他人迅速从狮子后面绕过来时,又助已经跳进参道旁边的树林里躲了起来。“会贼,竖耳听真,他娘嘚在王城里损毁石像算个逑本事,你们小子就是这么恨长州啊!”“妈个八子,上这疙瘩来耍那!”
“俺是鞍马后院镇守小太郎嘞,怎能放任贼子们侮辱天神!太爷领着手下子子孙孙前来剿灭你们。你们已经被俺们围着水泄不通嘞。”
虽然又助带着面具,但听他满嘴萨摩方言,对手就知道对手是谁了。会津藩士如同吃了炮药一般,就炸开了锅。
黑夜让人数多的一方遭受了更多的损失,又助在人群里上蹿下跳,自由自在的耍着木刀,没一会儿就打伤了好几个会津人。
雨越下越大了,后世天满宫的记载里说“天空一下子变亮了,响亮的雷电从天而降如同要劈开大地一般。”就在离两帮人打斗不远的地方,有棵杉树被雷电劈中,冒出了白烟。
会津藩士和又助都被吓呆了。
“神罚?!”大家都这么认为。
两帮人都听说过天满宫经常发生类似的怪异事件。如今他们一块瞪着眼睛跑到庙门前,如同捣蒜一般磕起头来。
会津藩士大声忏悔了好久,才发现有一头天狗混在他们当中。他们吓破了胆,立刻“撒丫子”了。第二天这件事就传遍了京都,好事者称之为“酉刻的怪异”。
新选组也听到了这件传闻,而且马上猜到那匹天狗就是又助扮演的。
上次跟踪又助的奉行所的“包打听”,翌日就来报告说,现在又助的“吃相”太可怕了,两手、衣服都被颜料染红了,那张脸活脱一把涂了红漆的水飘。
土方马上明白了:“带着天狗的面具,肯定是这个王八蛋。”
又过了十天,土方带着几个手下在祗园下河原的料亭喝酒,突然跑堂的来说,有个人在楼下等他。
一下楼,来人原来是奉行所“包打听”,他悄悄告诉土方,现在又助就在附近祗园南楼门旁边的二轩茶屋。
三,
又助坐在二轩茶屋靠窗的雅座里,一边警惕地望着店外的大道,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着烤豆腐蘸大酱。祗园的烤豆腐好吃,有人还编了一首小调,因为烤前都用两根竹签串着,小调得名《两根串,好软乎》。
“呦,这不是肝付先生吗?幸会,幸会。”
土方如同幽灵一般走进了雅座,只见他身穿黑色仙台平(外套),头上扎着一个大大的发髻,光看这幅打扮谁都会以为他是哪个外藩的高级武士。腰里别着一把两尺八寸的长刀,虽然刀头生锈,刀鞘上的漆都脱了,但是土方用它在京都砍杀了十几个人,中茎浸满了义士的鲜血,后世都知道它的名字——和泉守兼定。
土方不等又助谦让就坐了下来。
“我要麻烦您一件事,这和您的性命大有关联,您好好听着!”
“看您说嘛嘞?”
又助吃完手上的豆腐,将竹签扔在一边。
“肝付先生,您以后不要再耍那套小孩子一般的恶作剧如何?尊藩今后必为你所累。”
“俺不懂嘞。”
“以前您弄伤了我手下那几个不成器的部下,前几天又在北野天满宫打伤了会津藩士,我有确凿的证据是您干的。不,您要是耍嘴皮子说不知道就不像个武士样子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话虽说得咄咄逼人,平常不苟言笑的土方脸上却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
“俺要让萨会两个藩天翻地覆,他娘嘚。”肝付到底没有狂妄到说这样的话。
“俺知不道嘞。”肝付开始装起了糊涂。
“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让贵藩主岛津修理大夫直接给您下命令了啦,如何?”
“要是俺不答应嘞?”
“那我也没办法,只好随你便了。怎么样,给我个痛快话,不急着回答,我在这等您的回答。”土方站了起来,肝付知道土方在想跟在自己背后,捅自己个透心凉。
(王八蛋,闹个逑啊!)
肝付是个点燃的火枪练胆子的不要命的小子,他经过修炼,抛弃自己的生命如同抛弃没吃过几口的馒头一般。维新前期的萨摩人,象又助一样大大小小“妖怪”太多了。净福寺党是这群人中的最最激进的一个小团体,又助又是这个小团体中的最最激进的人。
“要吵架,放马过来。”
肝付的那双小孩一般调皮的眼睛里闪出了道道精光,他慢慢脱下了下駄(木鞋),那付天真烂漫的眼神让杀人不眨眼的土方,也感觉到异常滑稽。
(这小子,把自己的性命视同粪土,他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土方都知道萨摩人视死如归,又助是这群亡命之徒之间的超级另类。
“不过,不过,俺不能这样老掉了,老板,老板。”
又助唤来了二轩茶屋的掌柜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小信封,交给了他。
“麻烦把这个送到萨摩藩邸。”
肝付很早就准备好了这封信,一旁的土方抢过那封信一看,上面写着自己被会津藩壬生浪士用计引诱了出来云云。稳若泰山的土方,一下子慌了手脚。
“不。。。。。后会有期。”
回头就灰溜溜地走了。
虽然像肝付这样娴熟运用政治立场上强势的人还真不多,不过以如今的情势,土方要是激怒了萨摩藩,天下的情势立即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肝付快步跟上土方,两人一前一后翻过斜坡来到了大佛街道,只见几个新选组的队员在路边等着。
呸,肝付朝地上吐了口吐沫。
新选组的队员一下子被激怒了,土方严厉地制住了他们,不过他一回头,朝背对自己的肝付低声说道:“今后你小心着点。”语气带着一股逼人的憎恨。
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土方的评价都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现在他也是这么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要好好筹划一下暗杀又助的计划。
这个小插曲发生之后,肝付在洛中(京都及附近地区)更是横着走路了。其他诸蕃的浪人碰见新选组的巡逻队来了,马上“作鸟兽散了”。别说新选组,幕府的捕役一看又助来了,也躲得远远的。
肝付成了新选组在京洛地区的一块心病,新选组对他是“掉进灰堆的豆腐,动不得,吹不得。”西乡吉之助(西乡隆盛)在庆应元年和肝付谈过一次话。
他对又助说:“伙计,俺从会津藩的秋月剃次郎里扫听到的,新选组碰见又助老弟,好比老鼠见到猫似的。”秋月说这话,着实不易,因为他也是个疯子。
“西乡老爷,您老师怎莫回答嘀?”
“俺说,不只又助,萨摩藩的子弟全是他妈的不要命嘞。”
西乡操纵手下的年轻人很有一套,又助现在成了萨摩藩公认的“拼命三郎”,每天在城市里趾高气扬的阔步前行。有的萨摩藩士问他,有什么诀窍。
又助回答只是一句话:“伙计,要是你挺胸(对着砍来的刀)不动,倒是不会死嘞。”
说实话,又助现在不是找人吵架,是在找死。
新选组的队员如果看见又助从对面走过来,“狂人来了,快闪。”无可奈何的皱皱眉毛,然后找岔道,躲开他。
面对如今又助的盛名,新选组别说动明的,暗杀更是想也别想了。
又助现在很少单独行动,大部分时间他都和“净福寺党”那些人拉帮结队到处惹事生非。洛中地区讨厌新选组的老百姓,自然而然地将“净福寺党”视作新选组的克星。原来谈虎色变的新选组现在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悄悄嘲笑的对象。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土方的耳朵里。
“(将来)一定要作了他”土方是这么想的,但是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对付肝付的办法。庆应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又助到锦小路藩邸领小荷駄,一进院子就觉得情形有些不对。
藩邸里的警备比往常多了好几倍,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蝉一般。又助向要好的朋友打听出了什么事,得到的回答是:“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今天好像有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平常藩邸进进出出的老百姓,今天一律禁止通行。”
又助在等领小荷駄(月薪)的时候,上了趟厕所,正巧碰上一个过去从没看见过的大个子男人提着裤子出来,后来一打听高个子男人就是土州藩坂本龙马。后来又碰见了一个矮个子男人,又助认出他是长州藩的桂小五郎。
小五郎刚冒着重重风险,从长州来到了京度。
又助就此推测,今天大概是萨长密约成立,开始联合倒幕的日子。
又助猜对了,两个藩会谈的地点就在藩邸的内厅,萨摩藩的代表是西乡吉之助、大久保一藏(利通)、小松带刀。长州藩派来的是桂小五郎、品川弥二郎数人。作为两方秘密同盟中间人的是土州藩海援队坂本龙马是乘汽船,刚刚由水路来进入京都的。
长州人非常憎恨萨摩人,萨摩藩不久之前刚刚和会津联手驱逐长州势力赶出了京都政界,并将长州藩树为“朝敌”。长州藩因此饱受了幕府讨伐部队的蹂躏。他们将“萨贼”视作比幕府更可恨的敌人,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世事如棋局”昨天还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经过几重秘密交涉,今天居然结成了讨伐幕府的攻守同盟。
从和约签定那一天开始,萨摩藩就将过去互相提携的同盟者会津藩(佐幕派)给抛弃了。会津藩因为没有得到萨长同盟的谍报,一直蒙在鼓里。
政局的发展从此为之一变。
西乡自从定下同盟以后,思前想后决定找又助谈一次话,这天他在走廊里叫住了又助。
“又助伙计,今后开始别在市面上卖呆了哦。”
谈话异常简短,西乡知道萨长同盟的秘密总有一天会暴露,到了那时候,新选组对又助也就不会再“投鼠忌器”了。
又助哪能理解西乡说话的深意,这是事出有因的。萨长秘密同盟别说萨摩藩的一般藩士,连藩主的生身父亲岛津久光都不知道。
秘密总算瞒住了幕府半年时间,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到了九月份,会津藩和幕府开始疑神疑鬼了起来。这时萨长秘密同盟别说在京都的各个藩的藩士,甚至在浪人之间的都成为了一种常识。
这个秘密同盟甚至影响到了新选组,新选组的参谋伊东甲子太郎带着他周围的志同道合的数名队员投向勤王阵营,为了就是得到新加入萨摩藩的庇护。萨摩藩也堂而皇之的接纳了他们,这些过去的新选组队员成立的新武装团体——御陵卫士团,当然御陵卫士团的运营经费也是由萨摩藩支付的。
京都的情势如今又完全改变了。
土方一看形势的变化就想到:“又助背后的萨摩藩势力已经不可怕了。”
西乡虽然暗示过又助,可是又助显然不知道萨长秘密同盟,也不知道会津藩越来越来咄咄逼人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带着他那帮“净福寺党”时不时到黑谷本阵或是其他地方里,找新选组寻衅滋事。
庆应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的傍晚,又助一个人从净福寺出发到藩邸办事,路上他要走过一条戻桥往东走,一上桥迎面正好遇见新选组巡逻队的大石锹次郎、中村小次郎、崛内勘吾、染田十郎四个人。
“噢,是又助殿(尊称)。”
大石在桥上站住了,殷勤的招呼又助。大石在土方那里听说过又助是个什么人。他往四下打量一番,周围一个行人也没有。心想:“太好了,砍了他,谁都不会怀疑到新选组,只会把这笔帐记在其他杀人狂头上。”
“奇怪。”又助也感觉到今天的新选组队员有些异样。
“完了,今天俺要归位了。”又助一转念就明白了眼前的情况。他毅然决然地脱下了木履,光着脚站在冷冷的地面上。
“来啊,放马过来。”
“着家伙!”
只见刀光一闪,大石出手了,又助勉勉强强才躲过了大石砍来的刀锋。
又助刚站稳脚,如同吓破了胆一般,慌慌张张地掉头就跑,新选组四个人在后面紧追,又助奔回到桥的另一头,朝东一转,三步两步跑到艺州藩邸的大门前,突然停了下了。
只见又助大声喊道:“艺州样御家中,艺州样御家中,伙计们都看见了哦,伙计们都给俺看仔细了哦。”
艺州藩邸里的人被他这一嗓子给吓了一跳,担任警卫的足轻和普通藩士,四、五个人都走出来,看热闹。
这时大石已经追了上来,他一脚将又助踢翻在地,又助的“秃瓢”一着地,鲜血如同泉涌一般喷溅出来。
又助一个鲤鱼打挺,边和大石一帮人周旋,一边朝着看热闹的艺州藩士大叫:“俺是岛津修理大夫的家来肝付又助,周围的这帮王八就是新选组(的队员),这伙直娘贼和俺们萨摩藩有深仇大恨,所以要耍这类下三烂的手段。伙计们看清楚这帮人,俺要是小命不保,麻烦给萨摩藩捎个话勒,告诉他们俺是怎么被闹死的!”
又助说完了该说的话,猛然拔刀开始反击了。
崛内和染田一左一右双刀齐刷刷的砍了过来,又助躲也不躲,只是稍稍弯了弯腰,然后一个“旱地拔葱”,将刀刺进了染田的肚子。可是他没有躲过崛内的攻击,被砍了个正着,鲜血喷溅如飞,但是又助还是站稳了身体,摆出了萨摩藩特有的示现流剑法的特有攻击架式。
又助突然如同发疯的猴子一般,“嘎”的大叫一声,如同野猪一般朝崛内冲了过去,没等崛内反应过来,又助的刀就朝着他脑门砍了下来。只见红光一闪,崛内的头盖骨被砍成了两半,但是脚步并没有慢下来,他大步快跑直到戾桥东面才倒了下来。
艺州藩邸门前看热闹的藩士越来越多,大石和中村也管不得这些,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势成骑虎,退后也来不及了。
大石朝中村使了个眼色“中村,后面去。”
这时又助开始了进攻,中村躲开了他的进攻,顺势转到了又助的背后。大石顺势朝前进了几步,顺势举起了手上的刀,刀身略略偏右。
又助一看来者不善,捏紧了手中的刀,也朝天空中举了起来。
这时背后的中村朝又助背后斜砍将下来,一刀就将他背上砍了大口子,但是又助连躲也不躲,还是直挺挺地朝面前的大石冲了过去。
大石终于害怕了,一退再退,如同眼前的又助不是受伤的武士,而是一头狰狞的猛兽一般。就在他无路可退的时候,背后的中村终于赶了上来。
只听“咔哧”一声,刀刺进了又助的后脑勺,又助还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大石这时才清醒了过来,使出吃奶的劲,用刀砍向又助。
大石的刀口斜斜砍进了又助的头盖骨,只见他踉踉跄跄的走到艺州藩邸门口,身体才软了下来。大石赶上前去,一刀捅了进去,只见刀口背后进前胸出,活活被捅了个“透心凉”。
又助四肢抽搐了好一会,才气绝身亡。
艺州藩立刻将事情的原委通报给了萨摩藩。
“(又助)硌屁了?”
西乡听到消息立刻派中村半次郎(桐野利秋)作为使者,去会津藩和新选组讨个“说法”。新选组甚至懒得搭理萨摩的使者,会津藩算是派了几个重役(高层人士)参加了吊唁,葬礼上萨摩藩对会津藩的使者表现的异常冷淡,会津藩一看局面如此,言不由衷的说了几句节哀顺便的话就溜走了。
又助身前身后就是这般凄凉。
在这个时期和又助一样千千万万的激进青年,都是毫无意义的杀戮之中简单的死去了,又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已。
又助死后不久,萨摩藩就和会津藩断交了,一年以后他们又在鸟羽伏见兵戎相见。和又助一样,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就这样大同小异、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说他们是时代大熔炉下面,助焰的干柴亦不为过。
维新以后,又助被追赠了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