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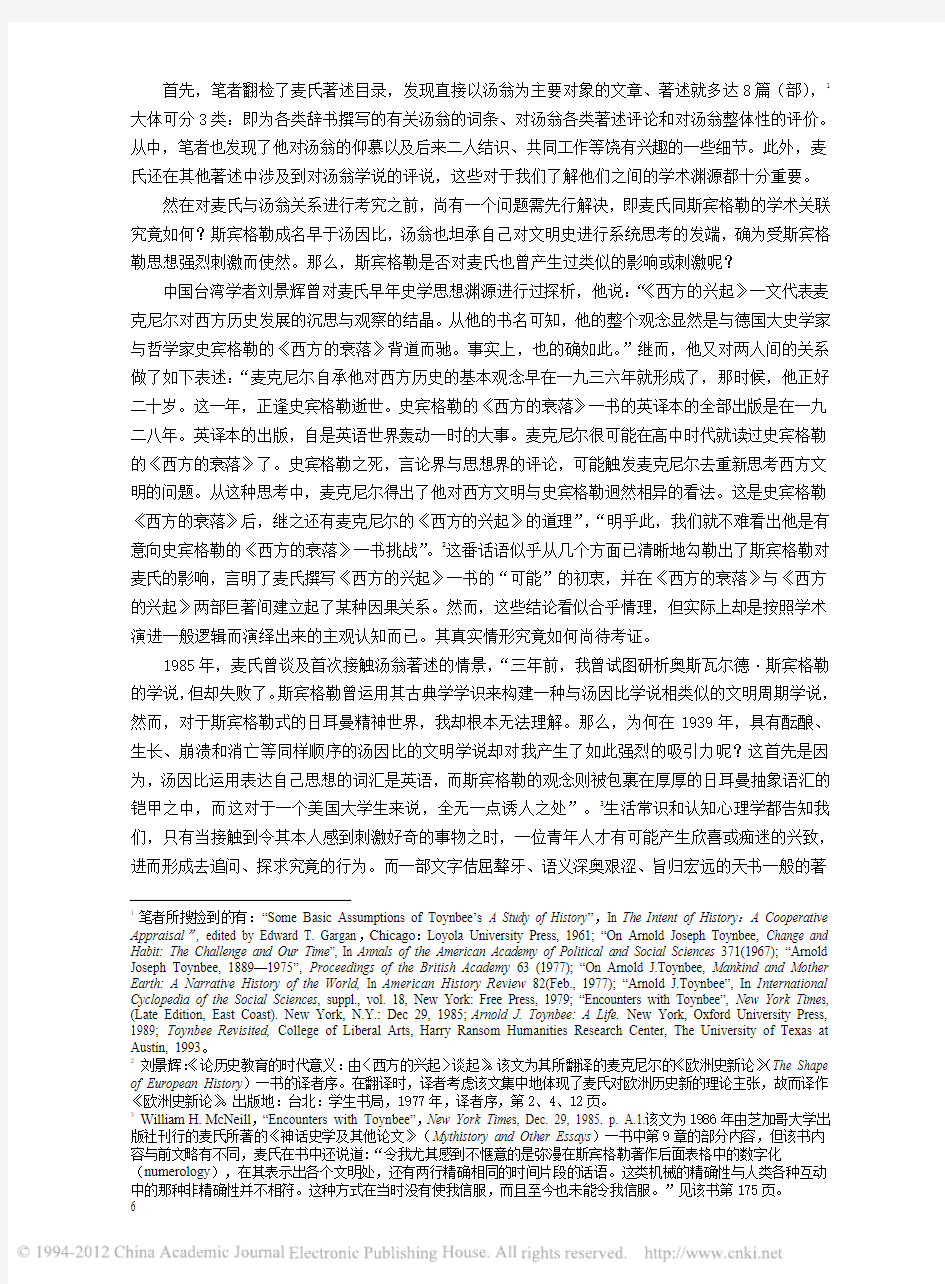
2010年1月 古代文明 January,2010 第4卷 第1期 Th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4 No.1
[理论与思想]
人间与天庭
——麦克尼尔与汤因比之间的学术渊源与分歧
王晋新
提 要:对文明和文明史深刻而独到的认识,是麦克尼尔史学成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学理而言,麦氏与英国著名史学大师汤因比有着密切的关联,故而,就他们之间的学
术关系加以梳理、辨析,不仅对认识麦氏本人史学主张和成就大有助益,亦可从一个特定角
度和层面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有关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传承、变革与发展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与把握。
关键词:麦克尼尔 汤因比 文明史 《历史研究》 《西方的兴起》
威廉·H.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1917—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声名远播,被誉为美国“新世界历史运动的领军人物”1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2麦氏治学严谨勤奋,著述宏富,耄耋之年尚笔耕不辍,对文明史的关注与研究是其史学成就中的重要特征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麦氏史学成就即得益于他对文明和文明史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就学理而言,麦氏学说与文化形态学说,特别是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的学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故而,就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加以梳理、分析,不仅对我们认识麦氏本人史学主张和成就大有助益,亦可从一个特定角度有助于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有关世界史研究和编撰方面的传承、变革与发展达成更为清晰的了解。
一
国内学界对麦氏与汤翁之间的学术联系已有所关注,如邵东方曾撰文专门评析这两位学者学术思想之异同,并特别指出麦氏“正是在汤因比的启迪之下从事研究世界文明史的。他所撰著的《西方的崛起》一书也主要是对各个文明进行研究”。3郭方也认为:麦氏的《西方的兴起》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显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并且麦氏本人曾同汤翁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4这些话语虽然简略,所言不详,但却给笔者以很大启示,也引发了在麦氏心目中,汤翁居于何种地位,麦氏与汤翁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学术交往或联系,尤其是他本人又对汤翁学说作何评价等等一系列的疑惑,深感尚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和研讨的必要。
1 [加]拉尔夫·克劳伊泽尔著,孙岳译:《艺术与世界历史》,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3页。
2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3邵东方:《汤因比与麦耐尔的“文明”概念》,《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总第20期,第87页。
4 郭方:《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第97页。
5
首先,笔者翻检了麦氏著述目录,发现直接以汤翁为主要对象的文章、著述就多达8篇(部),1大体可分3类:即为各类辞书撰写的有关汤翁的词条、对汤翁各类著述评论和对汤翁整体性的评价。从中,笔者也发现了他对汤翁的仰慕以及后来二人结识、共同工作等饶有兴趣的一些细节。此外,麦氏还在其他著述中涉及到对汤翁学说的评说,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都十分重要。
然在对麦氏与汤翁关系进行考究之前,尚有一个问题需先行解决,即麦氏同斯宾格勒的学术关联究竟如何?斯宾格勒成名早于汤因比,汤翁也坦承自己对文明史进行系统思考的发端,确为受斯宾格勒思想强烈刺激而使然。那么,斯宾格勒是否对麦氏也曾产生过类似的影响或刺激呢?
中国台湾学者刘景辉曾对麦氏早年史学思想渊源进行过探析,他说:“《西方的兴起》一文代表麦克尼尔对西方历史发展的沉思与观察的结晶。从他的书名可知,他的整个观念显然是与德国大史学家与哲学家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背道而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继而,他又对两人间的关系做了如下表述:“麦克尼尔自承他对西方历史的基本观念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形成了,那时候,他正好二十岁。这一年,正逢史宾格勒逝世。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的英译本的全部出版是在一九二八年。英译本的出版,自是英语世界轰动一时的大事。麦克尼尔很可能在高中时代就读过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了。史宾格勒之死,言论界与思想界的评论,可能触发麦克尼尔去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问题。从这种思考中,麦克尼尔得出了他对西方文明与史宾格勒迥然相异的看法。这是史宾格勒《西方的衰落》后,继之还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的道理”,“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有意向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挑战”。2这番话语似乎从几个方面已清晰地勾勒出了斯宾格勒对麦氏的影响,言明了麦氏撰写《西方的兴起》一书的“可能”的初衷,并在《西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两部巨著间建立起了某种因果关系。然而,这些结论看似合乎情理,但实际上却是按照学术演进一般逻辑而演绎出来的主观认知而已。其真实情形究竟如何尚待考证。
1985年,麦氏曾谈及首次接触汤翁著述的情景,“三年前,我曾试图研析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学说,但却失败了。斯宾格勒曾运用其古典学学识来构建一种与汤因比学说相类似的文明周期学说,然而,对于斯宾格勒式的日耳曼精神世界,我却根本无法理解。那么,为何在1939年,具有酝酿、生长、崩溃和消亡等同样顺序的汤因比的文明学说却对我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呢?这首先是因为,汤因比运用表达自己思想的词汇是英语,而斯宾格勒的观念则被包裹在厚厚的日耳曼抽象语汇的铠甲之中,而这对于一个美国大学生来说,全无一点诱人之处”。3生活常识和认知心理学都告知我们,只有当接触到令其本人感到刺激好奇的事物之时,一位青年人才有可能产生欣喜或痴迷的兴致,进而形成去追问、探求究竟的行为。而一部文字佶屈聱牙、语义深奥艰涩、旨归宏远的天书一般的著
1笔者所搜捡到的有:“Some Basic Assumptions of Toynbee’s A Study of History”,In The Intent of History:A Cooperative Appraisal”, edited by Edward T. Gargan,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61; “On Arnold Joseph Toynbee, Change and Habit: The Challenge and Our Time”,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371(1967);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63 (1977); “On Arnold J.Toynbee, 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82(Feb., 1977); “Arnold J.Toynbee”, In International 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uppl., vol. 18,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Encounters with Toynbee”, New York Time s, (Late Edition, East Coast). New York, N.Y.: Dec 29, 1985;Arnold J. Toynbee: A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Toynbee Revisited,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3。
2 刘景辉:《论历史教育的时代意义:由〈西方的兴起〉谈起》。该文为其所翻译的麦克尼尔的《欧洲史新论》(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一书的译者序。在翻译时,译者考虑该文集中地体现了麦氏对欧洲历史新的理论主张,故而译作《欧洲史新论》。出版地: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译者序,第2、4、12页。
3 William H. McNeill,“Encounters with Toynbee”,New York Time s, Dec. 29, 1985. p. A.1.该文为1986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刊行的麦氏所著的《神话史学及其他论文》(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一书中第9章的部分内容,但该书内容与前文略有不同,麦氏在书中还说道:“令我尤其感到不惬意的是弥漫在斯宾格勒著作后面表格中的数字化(numerology),在其表示出各个文明处,还有两行精确相同的时间片段的话语。这类机械的精确性与人类各种互动中的那种非精确性并不相符。这种方式在当时没有使我信服,而且至今也未能令我信服。”见该书第175页。
6
作,能否如刘文所描述的那样,具有触发当时年龄尚不足20 岁的麦氏去“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问题”的效应?麦氏本人给出的答案是《西方的衰落》实为一部“根本无法理解”又丝毫“无一点诱人之处”的著作,以至于使他无法对其产生共鸣。“在各个文明都是值得思考的这一点上,斯宾格勒并未能说服我”。1如此看来,刘文所作的描述及结论,恐怕是“想当然耳”。
汤翁在麦氏心目中的地位却全然不同。年值花甲的麦氏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阅读《历史研究》前3卷的情景,他深情地回顾道:“我全身心的扑在了这部《历史研究》之上。此后的两三天里,我天天坐在那里,如饥似渴,全神贯注地阅读汤因比的这3卷大作”。麦氏说,在其一生中只有两次或三次因为读一部富有智慧的著述而如痴如醉,欣喜若狂。而这种情形通常是在阅读那些极富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时才会发生。然而这次,“我的内心此时却是同另一个人以抽象方式表达出来的观念相同一,全然不需那些想象中的人物角色来做中介。并且,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或者与我的思想极为相同”,“一霎那间,我同一位与我有着同样感受的知音前辈相遇了,他以一种令人称奇赞许的技巧,在开掘修昔底德作品中的各种深层含义,并且是站在一种全世界的立场之上,不是将其意义局限在欧洲一隅之中,而是从整个世界历史意义上,把修昔底德的模式运用到地球上所有的文明之中。我完全被震撼了!这位同道的精神已远远地超过了我本人的知识范围和经历。他简直就是一位人间的巨人!一位高擎明灯的真正英雄!” 2这些洋溢着炽热情感的话语,即或在40年后仍能将当年一位青年学子在无涯学海中苦苦寻觅,久无所得,骤然间却同一位可指引自己前行的先哲邂逅相遇时的那种激动得难以自已的情感真实地表达了出来。这同麦氏阅读斯宾格勒著述后的沮丧感受有着天壤之别。
从麦氏的回顾中,我们得知他之所以与汤翁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有诸多缘故。其一:相同语言所带来的思想相通,使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犹如神契般的交流;其二:二人皆对古典史家修昔底德情有独钟。麦氏当时正值撰写硕士论文阶段,选题为“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对其历史结构的思考”(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a consider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ir histories),故而整天埋首于修氏著述之中。而汤翁也曾讲修氏学说于他有启迪之功,二者可谓学术旨趣相投;其三:汤翁那些思考深刻、辩析系统和充满智慧的言说对于一位后学来说简直就是琼浆醍醐。然而,麦氏与汤翁的关系并不只限于此,他们之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二战爆发后,麦氏应征入伍,后前往希腊参战。在希腊,他同后来的夫人相识。他们二人的结识、相爱与成亲,自然对麦氏一生影响甚巨,其中包括给麦氏本人的学术生涯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机遇,即促成了麦氏同自己心目中那位“偶像”的结识。麦克尼尔的岳父,早年曾是汤翁在牛津大学的同窗,并于1911年与汤翁一道穿越整个希腊进行实地文物考察。正是这份友情使得麦氏在1947年4月有缘以后学晚辈的身份拜见了汤翁本人。
1947年前后的汤翁,在整个西方知识界声誉日隆,如日中天。美国大出版商兼报业巨子亨利·鲁斯(Henry Luce)不仅将汤翁作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还邀请他专程赴美向美国公众宣讲《历史研究》的主题思想。一时间,美国各家电视、报刊和杂志纷纷刊登汤翁在美的行踪报道和演讲内容,并将其誉为一位超越了马克思的思想导师,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智者”与“先知”。故而汪荣祖有言:“汤氏俗世大名主要是由美国媒体,诸如《生活》(Life)、《时代》(Time)、《读者文摘》(Readers
1William H. McNeill, “Historians I Have Known: Arnold J. Toynbee”, in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186.在该书中,麦氏还两次讲到,对他内心世界起到了形塑作用的有3位史学家,即卡尔·贝克尔、汤因比和布罗代尔,其中并未提及斯宾格勒之名。见该书第8章第147页、第9章第198页。
2William H. McNeill,“Encounters with Toynbee”,New York Time s, Dec. 29, 1985,p. A.1.
7
Digest)捧出来的”。1就在汤翁旅美讲学“布道”期间,麦氏拜见了汤翁,从而又引发出一段业缘,即汤翁邀请麦氏“于1950—1952年间前往伦敦的查塔姆大厦,承担他本人主编的二战期间国际关系史调查中一卷的撰写工作”。2从时间上推算,1947年4月是麦氏正在康奈尔大学为获得博士学位做最后冲刺的时节,能在此刻得到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师的工作邀请,对一个即将步入史学殿堂的青年学子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其意义自是难以估量。
结束学业后不久,麦氏按照约定于1950年前往英伦。他回忆道:“在横渡大西洋前去汤因比麾下效力的途中,我就希望能够为自己早在大学本科期间所计划的一部大书做好准备。我并不十分明确我究竟将写什么,或许是一部世界史,也或许就是想通过与这位在11年前曾点燃了我的想象力的这个人的私下交谈和日常交往、接触,来对自己所组织起来的各种观念进行一番检验、验证而已”。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此后的两年中,麦氏同汤翁几乎天天都可在查塔姆大厦那充满不列颠绅士情调的下午茶时间相见,彼此交流的内容“既包括我本人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查塔姆大厦中所有工作的情况,也包括他自己为完成《历史研究》最后一卷正在做出的努力。”3此次合作研究,麦氏收获颇丰,如期完成了任务。而依笔者之见,麦氏此番远赴英伦最大收益,在于对汤翁的内心思想和学术主张有了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
偶像、世交、工作指导者,三种身份、三种机缘,集于一身,令汤翁在麦氏心目中的地位极为特殊。可以肯定,他对汤翁内心思想和学术主张了解与认知的深度和细腻程度是他人难以企及的。这正是在跨越数十年的漫长时段中,麦氏为何撰写了那么多有关汤翁的文字,对其学术思想反复进行评说的背景和动因。特别是1986年,汤翁后嗣劳伦斯夫妇恳请麦氏为其父亲撰写一部传记时,他立即予以应允。3年后,麦氏撰著的《汤因比一生》一书,由一直负责汤因比著述出版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并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再次在国际史坛上引发了对汤翁的热评。4
关于汤翁对麦氏的重大影响,如前所述,学界多有论及。然而这些看法或者过于简短、或者只是陈述其结果,很少涉及麦氏本人的感受、体悟。通过对麦氏各类有关著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前后跨越30余载的漫长时光中,麦氏对汤翁史学成就和缺欠进行了反复而周详的辨析与认识,他始终一以贯之地坦承汤翁对自己的启迪之功,明确指出汤翁是他思想的主要塑造者之一,这种影响是多重而深远的,既有史观的启示、视野的拓展,也有方法论层面的影响。
(一)对人类历史整体性与同一性的思考与探求。1961年,正值整个西方学界对汤因比展开大规模“声讨”之际,麦氏发表了“论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几个基本预设”一文。该文代表麦氏对汤翁史学评价的基本理路,这不仅是因为它成文时间较早,而是由于它自身那种客观、全面和深刻性。并且麦氏日后的各种评论文著也都延续着这一理路,其中较重要者为1987年发表的“重新评价汤因比”一文。首先,麦氏认为《历史研究》一书的确存在“事实”或“史实”不太精准、不够确定等诸多弊端,但这并不是对此书予以评价的重心所在,“因为在那些具体专业领域的专家眼中看来的确犯有严重过错的事实和判断,却对这部著作的整体并无大碍,并不必然就导致这部著作在整体上完全站
1 汪荣祖:《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载《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4页。
2William H. McNeill,“Encounters with Toynbee”,New York Time s, Dec. 29, 1985. p. A.1.查塔姆大厦为汤因比所主持的隶属于伦敦大学的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所在地。
3William H. McNeill, “Encounters with Toynbee”, New York Time s, Dec. 29, 1985. p. A.1.
4William H. McNeill, Aronold J. Toynee:A Lif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詹姆斯·焦尔在评价这部传记时指出:“汤因比所撰著的12卷本的《历史研究》无疑是20世纪历史学著述中最具抱负的作品之一,而“麦克尼尔所撰写的这部《汤因比的一生》将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吸引众多的读者,因为这是一部对一位重要作者的富有同情心但又不失批评的著述,这是有关英国知识和社会史的一部珍贵文献,是对一位著名人物的神秘和宗教情感经历,对其在钱财的吝啬态度,对其非同寻常的文化(即其在以古典希腊语撰写诗歌时的精神危机)的研究。”见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 ol. 63, No. 2, Jun., 1991, pp.362-363。
8
不住脚。倘若我们仅仅听信那些专家的一面之词,那么,这部著作的伟大品性(这种品性就深藏在它力求降低减少人类历史的多样性而将其置于一种可予以理解的秩序之上的努力之中)的大部分就会从我们的眼前消失。”128年之后,麦氏依然坚持这一观点:“汤因比同其他史学家一样,不应只是因为史实上的不够精确——无论真实的情形到底怎样,就被置于不予理睬的境况之中。有关事实的不精确是根本无法避免的,因为随着学术不断发展进步,即使是最精确的文本也将成为落伍,显示出它的不精确性。”2麦氏在这一点上为汤翁的辩护,与汤翁当年为威尔斯(H. G. Wells)所做的辩解,在立论和语词上都非常相像。3其次,麦氏认为这部著作与时代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它一方面仰赖于考古学近百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满足了二战以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公众在对未来形势预测方面对知识的需求:“汤因比及其著作之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受到民众最炙热的广泛欢迎……无疑是同他那种文明发展模式所直接得出的一个简单推理有关。假如西方世界正在走向形成一个普世帝国的成熟阶段,那么,按照汤因比在其著作中的说法,美国显然就是承担起具有同罗马帝国当年一样作用的那位竞争者……”4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麦氏认为该书表现出“在历史中寻求一种同一性的冲动……对于我来说,这似乎就是汤因比全部知识世界的基石。这也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基本设想:即在人类多种多样的历史经历背后存在着一种可加以认知的同一性”。5
(二)历史考察视野的拓展。麦氏指出汤翁向现有知识界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具有两重性质:“首先,他勇敢地冲破了史学领域各种特殊的约定俗成的界限。将所有已知的过去人类的历史都作为自己的研究探讨领域,创建了各种自己的韵律节奏和模式,而这些韵律节奏和模式都是任何一种较狭隘的视野所无法探及的”。而“第二个挑战,同样是它构成了一种对于我们学科传统界限的突破,这种突破不是前面所讲的那种平面的,而是垂直的……汤因比获得了一种把自己对历史的研究与终极的哲学和神学问题连为一体的自由……汤因比则以向我们挑战的方式,把历史的真理同社会学、哲学和神学的各种理论以及各种信仰连结起来,同样带来了史学的拓展与丰富”,就如同“人们将经济活动带入到史学研究之中,给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史学所带来的拓展与丰富”一样。6此后,麦氏反复谈及汤翁在史学视野拓宽方面对自己的影响,进一步揭示汤翁“挑战”的涵义。他说,40多年前的《历史研究》一书所以能够如此吸引自己,是因为“他为我敞开了一种全新的景观,它们远远超出了我原有的知识范围。以往所未曾思考过的各种文明,可以说,第一次成为了可以识别的对象。显然,在1939年,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和非洲以及哥伦布以前美洲的存在,并非什么新鲜之物,但是它们的历史并未成为我好奇心的正常和必须关注的对象。在我进入康乃尔大学之前,甚至东欧仍是一片由发不出音的名称和无法理解的细节所覆盖的荒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亚洲、非洲和哥伦布以前的美洲是多么难以认知的呀!然而,汤因比在对它们加以认识理解上却毫无一丝胆怯畏惧。在发现这些地区
1William H. McNeill, “Some Basic Assumptions of Toynbee’s A Study of History”, In The Intent of History:A Cooperative Appraisal, edited by Edward T. Gargan,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26.
2William H. McNeill, Aronold J. Toynee:A Life,p.286.
3 见[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4William H. McNeill, “Some Basic Assumptions of Toynbee’s A Study of History”, In The Intent of History:A Cooperative Appraisal, edited by Edward T. Gargan, p.131.
5William H. McNeill, “Some Basic Assumptions of Toynbee’s A Study of History”, In The Intent of History:A Cooperative Appraisal, edited by Edward T. Gargan, pp.14—145.
6William H. McNeill, “Some Basic Assumptions of Toynbee’s A Study of History”, In The Intent of History:A Cooperative Appraisal, edited by Edward T. Gargan, pp.127,129.
9
存在着比我以往所想象的多出那么多的东西需要去认识时,真是令人既兴奋又清醒”。1“当看到一个个人竟然具备了对整个广袤世界予以思考并赋予其历史意义的能力的时候,我完全惊愕了!这正是我本人曾力图想做的事情,然而我却一直偏狭地将五分之四(甚至更多)人类和有文字的历史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2“从此,我像汤因比一样,也开始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思考,并对那些我所不知道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历史进行探求。”他宣称将过去历史意义赋予全球性视野的智慧,是他在康奈尔大学通过阅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所获得的。3
(三)对世界上所有各个文明予以同样的关注。在相当长时期内,麦氏将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文明作为研究的基本认识和分析单位,作为不同时期世界历史的主要承担者来看待。麦氏曾说:“汤因比的影响和他身后一种悠久的传统,使得我本人选择各个单独的文明作为世界历史大背景下的主要角色。”4而其缘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当时“西方各个学派所研究的和西方各所大学所讲授的历史,仅仅是与欧洲人历史——即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史——以及在海外欧洲人后裔历史有关的内容,而其他各个民族历史仅仅是在被欧洲人发现或被开化、征服之后,才进入到历史场景之中。人们都知道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也都具有悠久历史;但是这些皆被作为西方学术探讨中的特殊领域,完全被西方史学家所忽略,而是将其交由语言学家和宗教比较学的学者来处理”。二是在汤翁之前,只有为数甚少几位来自学术圈之外的勇敢人士,曾试图将欧洲历史同非欧洲历史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知识探险历程中,威尔斯是最为重要的一位人物,然而他所撰著的《历史纲要》(Outline of History)一书,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光(该书于1920年第一次出版),并且其绝大部分信息皆出自于《大英百科全书》。而且,威尔斯的历史是一种进步主义史学,他以这种源自于欧洲的进步,来衡量评价绝大部分的其他地区的历史,故而其他各个民族仅仅扮演着一种边缘的和辅助的角色。斯宾格勒的学识则远比威尔斯要大得多。然而,汤因比的学识“要比斯宾格勒更为精湛,视野也更加广博;他对详情细节的嗜好、饶有兴趣的阐释和常常穿越时空的比较,以及更加符合史学写作传统的文笔都要远远比斯宾格勒的那种宣讲发布神谕式的做法更胜一筹。”“此外,他那种欧洲境内存在着多元文明的观念对于我所关注的俄罗斯历史与西欧历史之间的差异也给予了一定启迪,”“他所说的那种人类过去历史的‘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范畴之内’的景观,就是他为我们传统的知识所做出的最大的和最核心的贡献,这也应该成为他永久地享有盛誉的理由根据。”5而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将欧洲的各个文明同非欧洲的各个文明置于一个同样的平台之上。这是对1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的仅仅将目光聚集在欧洲光荣的过去这种肤浅史观的一种真正的变革,并且,它潜在地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同我们前人的史学加以区别开来”。6
(四)对唯史料方法的批判与对史学研究者主观洞察力的强调与倡导。史学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认知活动,关涉知识、思维、理念和方法等诸多层面。汤翁学说对西方史学的冲击,不仅限于史观与视野的变革和拓展,还表现为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汤翁曾就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本质特性和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弊端进行了反复而详尽的辨析,主张必须破除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思想工业化”诸种
1William H. McNeill, “Historians I Have Known: Arnold J. Toynbee”, in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185.
2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5, p.39.
3William H. McNeill, “Historians I Have Known: Arnold J. Toynbee”, in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185,186.
4William H. McNeill, The Pru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 p.68.
5William H. McNeill, Aronold J. Toynee:A Life, p.285.
6William H. McNei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or, vol.34, 1995, p.12.
10
弊病。1而在这方面,麦氏也有着相近的感受。他虽对兰克史学所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作用予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对美国史学研究和教育中只将这种方法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的极端推崇和过分仰赖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判。麦氏认为其流弊主要为:1,它“无形中为‘科学的’历史研究范畴划出了一道明确界限”,即研究者只能把他所研究的范围,设定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从而造成繁密、琐碎的“小题目研究”达到“汗牛充栋,泛滥成灾的地步”。2,“这类规范更使人们怀疑大格局,大体系历史的可靠性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从而放弃对历史整体大结构的探求。至于“如何将这一类的专题研究融合成一部有意义的历史,则少有人注意。真相就是真相,至于它的大体系,大组织,大架构,不妨留给上帝去处理吧?不然,干脆听其自然”。这种学术缺陷令麦氏深以为憾。3,“考据式的编撰工作只是历史家工作的一部分。历史家除了考证编纂古人所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事迹之外,也要追索古人不自觉的其他各种活动。这一类活动并不是可以从史料的表面型态直接看出,而有赖于史家个人的智慧,从史料的字里行间悟出来……那些不愿对文献的内在含义表示任何意见的历史家,只不过是固步自封罢了,他们不会比过去的人知道更多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4,“这种缺陷更因另一种心理上的因素更为扩大。因为研究者对于愈来愈小的题目知道得愈来愈多,他可以很快地超过所有的人对这一方面的知识,而成为杰出的专家学者,名利双收。只要这一类专家合理地使用史料,其他学者就不会亦步亦趋地做同样的研究,这样,在缺乏强力的竞争,在缺乏有力的反驳下,这位专家的结论就成为权威的结论,为大家所欣然接受了。这种专家也取得了博学的雅号,其学术地位俨然不可动摇。相信这样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更使得这类钻牛角尖的专家加倍的安全了。因为,其他的人不愿浪费时间去查证一些细枝末叶般的琐细之事。在没有竞争者的局面下,他们成为某一方面的‘南面王’。他们的声势也就更加浩大了”。2从这些话语中,我们看到麦氏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缺陷的批判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缺陷,直接指向了沉溺于其中并深以为得意的那些史学研究者。其语词虽然有些刻薄,但却是一段切中肯綮针砭时弊的好文字。
麦氏还对汤翁创建历史解说体系时的大胆和勇敢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就我本人而言,我就深信某些通过大视野而获得的见识,是那些对历史各个分别的具体部分进行近距离密切观察所根本无法获得的……汤因比式的普世历史,我相信,打开了各种短(小)周期统计方式的可能性……各种新的见识或许就是从视野宽度中涌现出来的……历史学中任何一种特殊的或狭隘的领域企图通过使自身更加准确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这种对历史理解的丰富程度都是做不到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各种大的视野、大胆的假说、不精确的直觉同精密而详尽的学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倘若我们仅关注后者,对各种事实进行密切的观察,一味地寻求更加全面完整的细节,那么,我们就会对真实性的其他方面丧失掉观察力。”汤翁的挑战“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对于大多数史学家来说,由于各自对于自己所主要关心的领域已确立起了精确性,从而对普世历史的感觉观察力业已萎缩”。汤翁“对人类过去历史的研究已经将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到了自己面前:即什么才是人类的命运?人类各个社会都须服从的法则是什么?在人类事物中上帝发挥出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许因为力求科学,或者处于暂时迷惘之中,对于这些人类状态的主要迷题,专业的史学家们都倾向绕开或回避;然而汤因比却勇敢地面对这些我们不敢处理的难题,并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解答。撇开这些解答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问题暂且不谈,他的著作毕竟做出了回答”。3这些评说充分地显示出麦氏在史学研究方法和史家应充分地张扬自己的才智与个性等方面对汤翁所持主张的极大认同。
1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版),第3—13页,第423—438页。
2 [美]麦克尼尔著,刘景辉译:《欧洲史新论》,第16—17页。
3William H. McNeill,“Some Basic Assumptions of Toynbee’s A Study of History”, In The Intent of History:A Cooperative Appraisal, edited by Edward T. Gargan, pp.128-129.
11
(五)相似的撰述风格。钱乘旦教授曾在评论麦氏《世界史》一书时提及到一个有趣现象,即该书罕见使用注释,而代之以在各章之末开列一大串“参考书目”的方式。1其实,麦氏所有著述几乎都显现出这种撰写风格。至于麦氏这种风格是否妥当,本文暂不评说,笔者所关心的是麦氏这种文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有何依凭?通过翻检麦氏各种著述,果真找到了答案。
当谈及在汤翁身边工作的收获时,麦氏曾说:我的确发现了汤翁撰写著述的独门秘技。他每天晚上都要阅读几个小时,为《历史研究》收集各种观念和信息。只要发现有意义的东西他都将其记下来。但他的记录方式是采用总结、概括、摘要等方式,主要记录其大意要旨,而不是那种不胜其麻烦的抄录的方式。他对那种誊写劳作极为轻蔑。汤翁的这种写作方式令麦氏获益匪浅,不仅在日后撰写《西方的兴起》等著述时采用了这种方式,而且还向那些意欲撰写综合性历史著述的人们热情地加以推荐,称其为“一种解放的方式”。2
上述这些麦氏与汤翁的交往概况,或许会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过从甚密的私交会使麦氏将汤翁奉若师长,毕恭毕敬,进而衍生出一种奉师言为圭臬,甚至为长者、尊者讳的情感。麦氏本人也坦承汤翁对他的影响尤如父辈。3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麦氏心目中汤翁的地位十分复杂,他既是一位学识渊博、著述煌煌的大师,又是一位极度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人;既是一位对自己学术志业有着导引之功的哲人恩师,又在学术理念上与自己有着巨大的分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麦氏说他与汤翁关系的破裂就与自己得以成名的《西方的兴起》一书有着一定关联。早在1957年,刚刚被任命为剑桥大学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的特鲁弗-罗珀(Hugh R. Trevor-Roper)就曾著文,对汤翁的先知形象和对宗教嗜好讥呵挖苦,猛烈抨击。46年以后,他又以麦氏著作为由向汤翁发起新的攻讦,将其作为一种对于汤因比那种将西方文明视为其他文明的罪恶侵略者观点的有力反驳,并给与麦氏著作以极大的赞誉。5
鉴于初衷,有关麦氏对汤翁的人品、性格等其他方面的评说,本文不做过多的涉及,而是将探求目光推向更深的层次,即对麦氏与汤翁在学术上的不同、差异及其原因进行探析。
三
麦氏在许多演讲和著述中,都曾言及他对汤翁某些观念和观点的不同看法,而他自身的学术理路也确实与汤翁有诸多不同之处。对此,学界已有人评说,其中尤以邵东方的归纳较为系统、明确。他说麦氏曾指出汤翁学说中存在如下弊端:“第一,汤因比未能充分认识到,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的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接触是促使文明演变的主要动力。第二,汤因比在着力描述文明时,总是未能明确其定义;而且他对各文明的取舍也常常失之武断。第三,汤因比过分依赖于古代的希腊、
1 钱乘旦:《评麦克尼尔〈世界史〉》,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该文后来被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96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原版麦克尼尔《世界史》(A World History)的“导读”。
2William H. McNeill, “Historians I Have Known: Arnold J. Toynbee”, in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191,194.
3William H. McNeill, The Pru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 p.69.
4 在1957年,H.R.特鲁弗·罗珀在一篇文章中,将其对汤因比的不满全部宣泄出来,他将汤因比描绘成一位愚蠢的先知,这位先知创造了一个以“A.T.”(汤氏纪年缩写)为标志的崭新的时代,以对抗“A.D.”(西元纪年)。
5 William H. McNeill, The Pru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 p.69.令人深感惊异的是,麦氏这部著作问世之际,封底页上赫然印着的两段推荐性评语就出自这两位史学家之口。汤因比称:“《西方的兴起》一书是本人所知道的各种叙述类型的世界史著作中写得最为清晰透彻之作。我确信任何读过此书的人,都将对铸就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那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获得一种更为深邃的洞察与认知。”罗珀说:“这不仅仅只是一部极有学识和见地的著作,也是已出版的叙述和解释整个人类史的著述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部。阅读此书将是一种令人非常满足的体验。”
12
罗马文明的古典范例,因而难于理解其他文明,尤其是非西方文明。汤因比试图将所有文明纳入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的轨道,因此在分析其他文明时犯了许多明显错误。第四,由于受帕格森理论的熏染,汤因比是凭直觉治史,他习惯于首先确定一个观点,然后再选择适用的史实”。1上述这些将麦氏关于汤翁学说的局限、不足以及其自身与汤翁学说的不同之处基本归纳了出来,但仍有加以补充、完善之处和必要。结合麦氏的各类著述,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文明”范畴不同的界定。长久以来,文明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颇令人费解的现象,即对“文明”这一核心概念一直缺乏明确的界定,故而形成了一种人人竞相言说文明却不知其究竟为何物的奇怪现状。从学理上讲,一个研究领域或者学科,如果对自身基本研究对象的内涵搞不清楚的话,将对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构成直接的甚至是致命的威胁;其次,这也势必导致其研究对象的数量、谱系和研究范围的模糊、不确定和粘黏、纠结等各种弊端。可以说对“文明”这一范畴的界定已成为学界亟须解决的瓶颈问题之一。当下学术界在这一概念认知上的混乱以及社会、理论界对此范畴的滥用也的确堪忧。
那么,作为一生著述达数千万言专门言说人类文明的汤翁,是如何界定“文明”的呢?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汤翁的见解令人极为困惑。正如邵东方所指出的:“尽管汤因比对文明的诠释既富于想象,又慧眼独具,但他从未对文明下明确定义。汤因比著作的前几卷对文明的定义似乎是政治性的,而在最后四卷中却具有了宗教色彩。因此,汤因比笔下的文明究竟是从政治着眼,抑或意在宗教,并无明确答案。学术界对于汤因比在各种文明中的取舍,一向颇多疑问,其中尤以非西方学者为甚。”21972年版的插图版《历史研究》一书,系汤翁晚年所整理的著述,该书不仅篇幅大幅缩减,同时也针对诸多批评意见,在内容上有所修正,其中专门设有一章论及有关文化、社会、文明等术语的定义。在对柴尔德,特别是巴格比所提出的依据城市的出现来规定文明定义的做法表示不满之后,他说“一个摆脱了经济活动的少数人社会的出现,是识别文明的标志,不是文明的定义”。他赞同对以“食物生产的发展或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变化……来解释文明形成的原因”的做法加以拒绝的态度,而对怀特海所说的“世上每一个因具有高级活动而闻名的时代,在其顶峰阶段,以及造成这一顶峰的阶段的代表人物之间,都能发现某种深刻、普遍的特征,它们被不声不响地接受,在人们日常发生的行为上打下自己的印记”的观点极为欣赏,并指出“如果依从怀特海的说法,我就应该在精神的意义上给文明一个定义。它也许可以称之为创造一种社会状态的努力,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整个人类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家庭成员,将在一起和谐地生活。”3这种定义实在令笔者感到十分费解。在文中另一处,汤翁又指出:“一个文明可以确定为‘一个可认识的研究领域’,可以看作是处在一些不同民族的个别活动场所之间的共同场地,也可当作一个特定的‘种’社会的代表”,“其中第一条定义是就主观意义而言的。它对一个文明定义所用的处理方法是认识论的方法。其余两条定义是客观的定义”。并特别指出“它们试图描述询问者心目中所相信的(在我看来这种相信是正确的)那种真实,那种他的思想通过现象所理解的真实”。4这番话语,是笔者所能见到的汤翁著述中对文明范畴所做出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解释,似可作为汤翁的最终定论。至于人们对其涵义做何诠释,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麦氏又是怎样来看待文明的含义呢?邵东方曾指出:“和斯宾格勒、汤因比一样,麦耐尔对文明构成的解释相当含混。他将文明笼统地视为‘生活方式’相同的社会群体”。5而笔者看法则有
1 邵东方:《汤因比和麦耐尔的‘文明概念’》,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第87页。
2 邵东方:《汤因比和麦耐尔的‘文明概念’》,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第86页。
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版),第19页。
4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版),第19—20页。
5 邵东方:《汤因比和麦耐尔的“文明概念”》,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第87页。
13
所不同。1967年,麦氏曾专门为《大美百科全书》撰写了“文明”辞条。开篇伊始,麦氏便指出文明一词被广泛使用,无单一、固定的定义所造成的混乱,并提出任何有关文明的讨论首先即面临文明的定义问题。在对学界一般使用文明的3种含义,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对此所持的基本态度和缺陷,以及历史学对此所关注的重点一一梳理、评点之后,麦氏指出:“可能唯一使人同意的就是‘文明’一词,只能使用在比弱势较强大的族群,或比‘原始’较复杂且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较有控制力量的群体身上”。1从中可见,麦氏以“较强大”、“较复杂”和“较有控制力量”三组词汇来分别对应外部群体、群体自身和自然环境三个维度,基本回答了文明构成的基本内涵。再参照本文以及其他著述,麦氏对柴尔德对文明的定义的看法也可获得进一步的佐证。
在文明构成和定义上,我们可发现麦氏与汤翁之间存在殊多不一之处。一是明晰程度各不相同;二是汤翁倾向于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取文明之内涵,且“一直带有18世纪所规定的含义。文明是一种艺术作品,它防止着人们潜在能量向野蛮行为转化”。2而麦氏则更关注从社会构成与物质层面来认知文明的形成和标准,二者价值取向相差甚远。
(二)对文明运动周期模式截然相反的态度。汤翁继承了斯宾格勒观点,认为每一个文明都要经过四个阶段: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这种循环周期模式构成了文化形态学说的主要特征之一。3麦氏曾说:“年轻的时候,我对这种模式感到是那样的亲切熟悉”,但是后来,“我完全摒弃了这种周期的模式”,并特意强调:“这是我本人同汤因比的最大不同之处”。4在《大美百科全书》的“文明”词条中,他就专门辟有“是否有文明的循环”一节,指出“由于人类可能自我毁灭的倾向,对于古代文明衰落的可能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刺激,人类事物经由自然循环,即由生长而至衰亡,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以柏拉图来说,他就曾讨论到政治组织循环问题……并伴随文艺复兴而在西欧再度显现”,而“中古回教的历史家伊本·赫勒顿(Ibn Khaldun)发展出另一种不同的循环论……在较近的世纪中,维科、赫尔德、黑格尔、蓝普雷茨(Karl Lamprecht)及许多其他欧洲的思想家,试图以多种不同途径将犹太——基督的时间观念与历史直线进步组合起来,建立为历史循环的古典概念”。但是“多数的历史家和社会科学家,并未被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依赖类比的说法所说服,对所有人类而言,可能的局限依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谁能说出在人类事务中的规则和超越人类所能控制过程间的关系是什么?存在人类事务中的规则和周期模式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必须局限于某些无法逃避的循环之中。除此之外,发现了预测的模式在如下的情况也将发生变化,人们既然知道(相信他们知道)他们行动的结果会有不良影响他们就会改变其行为,如是便能改变意料中的历史循环。就目前和可见的未来,由于我们缺少正确及真实的预测,对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知识仍然不足,未来亦是不可知的。若未来真有其形态,我们根本不须知道它是什么,因我们无知的行动正代表完全自由。就像祖先一样,对于人类的未来,必须每日工作使这个未来更加美好”。5这番话语虽在表面层次上覆有一种不可知论的色彩,但却隐匿着麦氏对往昔历史的深邃思考和对开拓未来的坚定立场。
(三)对西方文明当下命运的不同态度。汤翁学说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对西方文明当下命运的担
1 麦克尼尔:“文明”,载《大美百科全书》第6卷,台北,光复书局,1990年版,第437页。
2William H. McNeill, Toynbee Revisited, Aust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3, p.19.
3 将文明或文化视为有机体,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的观点,最早并不出自于斯宾格勒。俄罗斯思想家丹尼列夫斯基在1871年出版的《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据考证,最早提出此类观点的是一位名为Heinrich Ruckert 的德国历史学家,他在1857年出版的Lehrbuch der Weltgeschichte中提出了这一说法。
4William H. McNeill, The Pru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 p.68.
5 麦克尼尔:《文明》,载《大美百科全书》第6卷,第439页。
14
忧。促成这种忧患意识产生的有两大缘由。其一,短短几十年间,两次由西方发起的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剧烈冲击;其二,就是文明历史循环周期法则的内在逻辑。汤翁不仅依据文明循环法则认定西方文明“无可避免地要趋于衰落”,而且衰退之势已在眼前。吴于廑先生曾评价道:作为形态学派史家,汤因比对西方文明之终必死亡,不能有其他论断。但作为一个生长陶冶于其中的个人,又不甘心接受这一冷酷的论断,不得已对此抱一种超然的态度。以一种诗人的忧思,悯然于基督教文明的盛时不在,为天堂的失落,为西方文明的前景的渺茫嗟歌咏叹。1麦氏对此不予赞同,明确指出西方文明尚处在方兴未艾之际,“若是认为,欧洲文明的传统中心的创造进取力已经枯竭,似是言之过早。因为这个缘故,以及因为工业制度与现代经济与政治经营方式的传布,全世界都可以说是欧洲思想与工艺的继承人,所以我们研究,检讨欧洲史的发展似乎仍然是值得做的”。2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ta Kyle Crossley)指出:麦氏认为西方的兴起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此后,西方的统治通过它对海外贸易和美洲及非洲殖民地的控制而得到巩固,然后,它随着美国作为西方及西方统治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的兴起,在19世纪得到完善。到20世纪,工业化、民主、竞争和主要资本主义的经济、高识字率和法治等西方文化的特质(它揭示了西方何以一直保持卓越)稳固地占有了一席之地。3(四)孤立的文明与整体的世界。文化相对主义是斯宾格勒学说的一大特点,即各种社会整体的文化形式都具有严格的独特性,并且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无法像其他的文化进行传播。“汤因比沿循着斯宾格勒的假设模式,即各个现存的文明相互之间的关联十分有限”,而麦氏则申明“我本人绝不相信各个文明完全是彼此隔绝独立的”。4他不像斯宾格勒、汤因比将世界各地的文明视作为一个个孤立的文明来研究,来说明他们自身的兴亡;而是将文明的发展看作是整体的发展,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有他们的相关性。5纵观《西方的兴起》、《世界史》、《竞逐富强》、《人类之网》等麦氏主要著述,我们可得知其主要学术主张之一是更多地侧重关注彼此相邻的各个文明和民族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交往的创新性意义,尤其是对技术变革予以特殊的关注。6麦氏这一理念不仅显现出与汤翁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探索宏观整体性的世界史体系也具有深刻意义。著名学者斯塔夫阿诺诺斯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对《西方的兴起》的评论中指出:“麦克尼尔学说贡献的意义是应当予以重视的。在以往,世界史大多是留给了外行的业余史家和诸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等的历史哲学家。在对人类各个文明的兴起和衰落的模式和一般规律的研究探索中,他们都是把各个文明视作为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的事件来对待。而麦克尼尔在该书中,则对这种对待时间和空间的非历史的贬低做法加以取代,并在这种取代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出世界史是一个可以独自成立且令人充满兴趣的学术研究领域。” 7
1967年,麦氏《世界史》一书问世。麦氏在谈及这部著作的初衷时曾说到:“《西方的兴起》一书所获得的成功,似乎令我有理由相信,一部篇幅稍小一点的著作,可以将我个人对人类全部历史的看法更容易地传达给学生和普通读者们”。8同样,这部著作也大获成功,连续4次再版发行,成为麦
1 吴于廑:《形态学派三家说略》,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4、376页。
2 麦克尼尔著,刘景辉译:《欧洲史新论》,第172页。
3 柯娇燕著,刘文明译:《什么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4William H. McNeill, Toynbee Revisited, pp.19, 21.
5 麦克尼尔著,刘景辉译:《欧洲史新论》,译者序,第12页。
6William H. McNeill, The Pru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 p.68.
7L. S. Stavrianos:“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 ol. 69, No. 3 (Apr., 1964), pp. 713-715.
8William H. McNeill,A World History, (《世界史》), 影印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16页。
15
氏的代表作之一。在北大出版社影印的《世界史》(第4版)封底页上,赫然印有两位著名史学家的评论文字。第一位就是汤翁,他评价道:“麦克尼尔有一种看法,他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一种始终处于潜在状态的整体,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样一个整体也已成为了现实……他把一个复杂的故事讲述得相当流畅”。另外一位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布鲁恩对此书的评价是:“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所展现的那种综合能力,在这本《世界史》中又有天才的发挥。而且,视野更加扩展。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有一种特殊的天赋,他能够将各大文明的发展模式、它们的转嫁移植、冲突斗争以及各自的贡献有机地联系到一起,整合为一部全球的历史”。1
将名家评论刊印在书中醒目位置,是出版商们的惯常方式,意在促销而已,且常常能够达到目的。但学者或有心人却绝不应做如是观,而是要对那些评论文字中的微言大义细加揣摩,进而反观那些评论者自身的主张与立场。笔者以为,杰弗里·布鲁恩对麦氏的才赋、视野、能力的评论皆落在对其史学思想主张的首肯与赞同之上。而汤翁的评价却判然有别,他虽言明了麦氏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人类历史、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然稍加思索,便可见得汤翁对麦氏褒扬的重点并不在此,仅仅只是对其叙事技巧之娴熟比较欣赏而已。由此,我们或许可窥得二人不同的史学理念。
(五)对历史、文明发展动因的不同认知。有人曾将麦克尼尔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并称为三位“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2笔者以为这一说法不仅是强调他们3位各自以煌煌成就独领风骚,开辟一个西方世界史学新时代,而且也暗含着在认知世界、解释历史上,他们有着各自独特的立场和主张。前述种种,只是告知我们麦氏与汤翁在诸多具体事务上的不同见解而已,而他与汤翁最关键的差异则体现为学术理念上的分歧,这就是对推动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前行动力的不同认知。
在回顾与汤翁的交往时,麦氏说道:“同汤因比一道共事的两年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么令人兴奋。实际上,我们二人已经分道扬镳了。那种古典思维方式已经被他抛弃了。沉重的内心压力,在1939年的一次强大而神秘经历之后达到了顶点,从而促使他相信有一种超自然实体的真实存在,他很快感觉到了这一超自然实体具有同上帝相似的特性。历史的确成为了上帝向人类展示自我的记录,并且各个文明也都成为了各种工具,它们反复的破碎崩塌是在警醒人们向这种超自然实体的回归,因而推动着人性朝着一种更为完善的对上帝的认知迈进”。3“无论是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晚期阶段,他始终认为历史就是一出戏剧,而在这场戏剧中,人类的精神一直面对着一个‘他者’,并承受着沮丧的折磨……这位耸立在人类精神面前的‘他者’的性质可能是不同的。它可能是自然环境,可能是其他的人类,也可能是‘上帝’;而在其思想发展的晚期阶段,同其早期阶段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他越来越强调这个‘他者’,是第三种可能性,即上帝”。4并且,汤翁深信在史学研究中“如果不借助一位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即他经常所说的上帝,那么,这个世界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尽管这位‘精神实体’与基督教传统中的那位全能的‘主’之间并无多大的相似性”。5尽管麦氏承认汤翁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为是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但还是实在对汤翁“那种精神实体降临的神秘经历不能予以赞同或产生任何的共鸣”。6
《人类与大地母亲》这部完成于1973年,并于逝世之后的1976年刊行的著作,是汤翁生前的最后一部著述。在导论和最后几章中,汤翁主要是关注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而在其早期思考中,
1William H. McNeill,A World History, (《世界史》), 封底。
2 郭方:《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3William H. McNeill,“Encounters with Toynbee”,New York Time s, Dec. 29, 1985,p. A.1.
4William H. McNeill,“Some Basic Assumptions of Toynbee’s A Study of History”, In The Intent of History:A Cooperative Appraisal, edited by Edward T. Gargan,p.144.
5William H. McNeill, Aronold J. Toynee:A Life,p.288.
6William H. McNeill, Toynbee Revisited, p.21.
16
生物圈这一概念是根本不曾存在的。麦氏曾不无遗憾地对该书加以这样的评述:应当公正地对待汤因比,因为在生命的最后时分,他又重新使自己对人类生活的物质背景产生了兴趣,并且也对以往从文献中所收集的各种证据的感受加以拓宽。然而当转而向下面对尘世的时候,他的生命已接近尽头,并且力量也衰竭了,从而阻止了他去完成自己所拟订的计划。1
那么麦氏本人的历史动因理念又是如何呢?“在撰写《西方的兴起》一书时,”麦氏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我的抱负要远远比众多评论者注意的还要大。这部著作名称的选择,当然,就是试图同斯宾格勒(还有汤因比)进行较量。”2而这种较量的真实意图就是要“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颠倒过来,就如当年马克思曾主张要将黑格尔颠倒过来一样”。3他说:“我本人对人类生活所关注的领域——技术的、物质的和生态的——则同那些曾使汤因比痴迷的领域截然相反。他向上帝靠拢,希望到达天庭。我则向下,在尘世的大地上挖掘,渴望对那些致使人类生活得以维系,并致使我们在生物圈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强大物种的各种物质的和能量的流加以认知和理解”。“人类技术和知识的累积性特征以及为了人类为了满足正常、低俗的需求而对各种设置加以完善改进的持续的侧重关注,对于我来说似乎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们远远超过了各个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相互竞争模式的意义,尽管这些政治模式如同以往一样,仍将继续存在下去,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这种政治模式的统治性作用已经不如20世纪30年代时我所认为它所具有的功用那般重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以及通过经济管理为自由世界人们所提供的更加惬意的生活,使我更加笃信这一观念。”4美国一位学者曾对麦氏史学的基本特征和主张这样总结道:他“所倡导的世界史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相关联的世界史。人类各个社会的进化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物质环境的演化之间密切相关。”5
由此可见,在汤翁与麦氏之间所横亘的是天庭与尘世、神界与人间这道巨大的鸿沟!正是通过对那种上帝意志或超自然实体主宰人类活动和命运的历史理念的颠覆,麦氏才在尘世人间的大地上,完成了对高悬于天庭之上的汤翁学说的真正超越。明乎此,笔者才对一位学者为何以“从汤因比时代到麦克尼尔时代”的提法,作为当时西方“历史学研究所经历的巨大变迁”的表述有了进一步的体悟。6也从另一个角度,对巴勒克拉夫曾给予麦氏的一位秉持“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的史学家的评价的真实含义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7同样,这也使我们从一个更为贴切的角度,对麦氏各种著述中的基本理念和主张加以整体的审视、理解和把握。
汤翁的命运究竟如何?“将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历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史学家们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们是否持续努力地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各种拓展活动转化为一种可为人所理解的整体活动”。8这是在《汤因比一生》的终结之处,麦氏笔下所流淌出的一段话语。兹录自于此,愿与史学同侪一道品味赏析。
[作者王晋新(1957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 130024]
[收稿日期:2009年10月30日]
(责任编辑:赵轶峰)1William H. McNeill, “Historians I Have Known: Arnold J. Toynbee”, in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198.
2William H. McNeill, The Pru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 p.74.
3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s a Long-term Process, in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56.
4William H. McNeill, “Historians I Have Known: Arnold J. Toynbee”, in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196,197.
5 David W. Noble,“The Pur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Review], in History; Fall 2005; 34, 1.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30.
6 [加]拉尔夫·克劳伊泽尔著,孙岳译:《艺术与世界历史》,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第203页。
7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51页。
8William H. McNeill, Aronold J. Toynee: A Life, p.288.
17
2010年1月 古代文明 January,2010 第4卷 第1期 Th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4 No.1
Contents and Abstracts
[Theories and Thoughts]
Title:Professor Lin Zhichun (Ri-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2 Author: Zhan Ziqing,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With a broad perspective of world civilizations, Professor Lin Zhichun conducted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studies in his research and contributed profound rethinking about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iming at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His academic work greatly enlightened and contributed to the Chinese scholarship in the given area.
Key words:polis democracy humanity
Title: On the Earth vs. in the Heaven: The Academic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William H.
McNeill and Arnold J. Toynbee…………………………………………………………………………….../5 Author: Wang Jinxin, Professor, the Center of World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Deep and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s and their histories is a major feature of the historical works of William H. McNeill. In terms of academic connection,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Neill and Arnold J. Toynbee. It i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look into the acade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historians. It is meaningful not only for the study of McNeill’s works and personality, but also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of world history.
Key words: William H. McNeill Arnold J. Toynbe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 Study of History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Ancient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s]
Title: The Adventure of Wen-am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18 Author: Xu Hao, Ph.D. Candidate,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Wu Yuhong,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The adventure of Wen-amon, written in the end of 20th Dynasty, was found at El Khiben in Egypt. It was written in Late Egyptian on two papyruses. It describes an adventure of Wen-amon who was the high-rank priest in temple of Thebes. He was sent to Byblos in order to buy some cedar wood for manufacturing the solar bark. Unfortunately,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his trip, not only his property was stolen by thief in the city of Dor, but also the Byblos prince refused to offer cedar wood because of the debt. And then, he was wanted by city of Phoenicia and fled to Cyprus. However, Wen-amon can always find the way out of difficult every time by his wisdom and eloquence. This text was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resource to study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and maritime trade at that time because it was written in such a period when the nation’s power of Egypt became weaker.
Key words:Ancient Egypt Adventure of Wen-amon Maritime Trade Late New Kingdom
Title: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the Wisdom Literature in Ancient Mesopotamia…………………………./30 Author: Li Hongya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Western As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100871, China
Abstract: No one had ever challenged the validity of the term “wisdom literature” until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amous book Babylonian Wisdom Literature written by W. G. Lambert in the 1960s, in which he wrote:
“‘Wisdom’ is strictly a misnomer as applied to Babylonian literature”. Since then, some scholars began to adopt didactic literature instead of wisdom literature. Others abandoned the use of “Wisdom Literature” and employed “wisdom themes” instead. The present author suggested that neither wisdom literature nor didactic literature is literary genre. The term wisdom literature should be retained, but we should define it differently. Studies on wisdom literature in the West underwent three stages, the first being texts edition, the second classification, and the third pluralistic studies. In China, books and articles on wisdom literature from ancient Mesopotamia are primarily of introductory character.
Key words: Ancient Mesopotamia Wisdom Literature Didactic Literature Gilgamesh Epic
112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
《伤寒论》之六经辨证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张仲景在系统地总结与继承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的同时还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完成了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辨证论治的专书——《伤寒杂病论》。《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理解《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时我们要从多方面综合分析。教材书上对于六经的定义是: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由于六经之每一经又分为手足二经,因而总领十二经及其所属脏腑的生理功能,是生理性概念。笔者认为六经的概念可以更广泛。六经包含六经之气之意,六经脏腑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为本。如阳明胃土属于燥土,土含湿气,当胃显燥气时,临床上就是胃阴受损,脾与胃为表里经脉脏腑,脾显湿气时,临床上就是脾失健运,脾生湿。由此当我们再进行六经辨证时,就可以联系各个脏腑所属经气分析病症,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广义伤寒为一切热病的总称,理解“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对六经概念的明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全面的地掌握六经辩证。在掌握六经辩证之前我们要明确,脏腑,气血津液是其物质基础,经络是其络属联系,气化是功能活动,气化反应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功能活动和病理现象。气化离开了脏腑,气血津液,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脏腑气血津液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映不出其功能活动。所以六经辩证的实质是把脏腑气血津液、经络、气化三者有机结合,再综合病因属性,病势进退,缓急等,从宏观着眼,对外感疾病的发
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症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疾病的方法与体系。在学习六经辩证时除了联系脏腑经络辨证,还要联系八纲辨证。八纲辨证是对一切疾病的病位和证候性质的总概括。六经辨证主要用于外感病的辨证论治的一种辨证方法。因为外感病是在外邪的作用下正邪交争的临床反映,正邪斗争的消长盛衰,决定着疾病的发展变化,关系着疾病的病位与证候性质,所以六经辨证的具体运用,无不贯穿着表里阴阳寒热虚实等八纲辨证的内容,六经辩证的内容包含于八纲辨证之下。 对于六经辨证的更好地理解与剖析有助于我们对《伤寒论》的学习,继承和发扬《伤寒论》的精华,使之为中医药发展再作贡献,为临床疾病的治疗作贡献。
浅谈影响历史演进的因素及文明发展的规律性 关于读汤因比《历史研究》的个人心得 学院:法学院课序号:姓名:张** 学号:2*****031 引言: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罗马、希腊及雅典古文明。他一生著述颇多,但全面反映他总的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就是巨著《历史研究》,此部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在本次政治理论课堂上,经老师推荐,笔者选读此书,并且对书中描述的各个阶段文明发展以及其所运用的历史价值观颇感兴趣,从而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影响因素产生一些个人观点。 关键词:历史发展、规律性、文明演进、社会变动、历史价值观 首先,何为历史?我们从初中开始就在老师的指引下了解世界的起源、各国政治历史文化演变过程,为了应试,我们将每一个阶段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起因过程、历史意义等等烂熟于心,倒背如流,但却没有真正理解过这每一次历史的巨变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其背后的故事,没有深刻领悟到让我们在少年时代观史读哲的意义所在。步入大学,积极主动的了解历史,认识文明起源,塑造自身的历史价值观,更加成为我们当代学生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然而,笔者认为,每一个时刻都包含着历史的踪迹。历史即过去,但其不一定与人类社会发展有关,地理、气象的自然变迁亦属于历史。汤因比在本书中说: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的事情都已是无法改变的了。而我们人类,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在历史阶段所发生的情况以及结合对现如今所造成的影响,更好的充实未来的生活,应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种种,以史为鉴,博古论今。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的背后自然有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在文明演变更替时,不同地域又在汤因比的书中极具相似性与规律性。汤因比以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将人类的历史发展用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各地文明都囊括其中,文明之间的更替叙述都十分详细,好似为读者展现出社会不断演变的动态进程。但本书贯穿其中所存在的历史价值观与当今我们的观念不相符合的问题。在读过本书后,笔者有几点思考,在此简谈心得。 1、不同社会时期有不同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开始时说过: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类交往非常缓慢,变革的步伐更为缓慢。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20世纪七十年代,汤因比以宏观视角对已知的三十一种文明进行了历史情景再现式的分析归纳。而在笔者阅读之时发现,作者汤因比在描述原始社会的发展变革时,总是用大段文字描述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相关农业发展。最使笔者印象深刻的便是亚述文明的兴衰以及作者对查文文明和奥尔梅克文明的简要分析。在后续阅读中,笔者亦发现地理环境位置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明的繁盛衰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特点说明,作者极其重视人与环境的发展关系,并且这对各个文明发展都适用。比如在研究亚述文明时,汤因比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地形地貌以及水源等重要的地理信息罗列出来,来印证其农业发展境况。还将我国与希腊世界的河流通航进行经济发展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谈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原始社会,为人类日益膨胀的私欲而发动的战争提供物质基础的小农经济健康发展,才能更好的推进思想开放以及政治文明的起步。 而在本书中记述文明社会各个地域变革发展时,汤因比又将重点影响文明交替不断前进的因素突出在了一国经济发展及宗教成长之中。宗教文化开始渗透于每一种文明演进中。此部分描述伊斯兰教世界的部分虽篇幅较长、读起来晦涩难懂,但其所叙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所形成的社会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和侵略性。外交政策的改变以及国内政策的调整都与国家社会的经济军事力量以及宗教文化的渗透力量有密切联系。由此可见,人类文明不断
略论梁启超之方志学思想 摘要: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奠基者,梁启超始倡“方志学”这一概念,简明 扼要地概述我国数千年修志的历史,系统阐述了我国方志的编纂理论,并将其分列为单独的史学门类,其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为我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梁启超;方志学;编修方法;章学诚;“三书”之法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有《饮冰室合集》。他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首次提出“方志学”这一概念,并将其分列为单独的史学门类,其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为我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始倡“方志学”一词 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在封建社会里,方志一直被认为是地理书,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从《隋书·经籍志》以来的公私目录,大都把它列入史部地理类。但到了宋代,很多学者提出方志是属于史的范畴的看法,甚至直接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的看法,且这一时期方志编修十分普遍,统治者也格外重视图经的编修,使方志学在这一时期慢慢趋于定型。到了明代,明太祖见过之始,为显示其统一之功,了解各地民情,于洪武三年命儒臣统一编修一统志,“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这一时期方志学得到迅速发展。直至清朝,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编撰《大清一统志》,加之清代学者的推动,方志学进入全盛时期。 但“方志学”一词,从现有材料看,是为梁启超首创。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提出,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
浅谈《伤寒论》的六经辨证 欧阳光明(2021.03.07) 摘要:《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是辨病、辨证、辨症论治相结合的有机体系,辨病论治体现治疗的全局性,辨证论治体现治疗的阶段性,辨症论治体现治疗的即时性。太阳病的本质为邪袭太阳,经气不利,营卫失和,正气分奋起抗邪,正邪交争于表;阳明病病位在中焦的胃肠,性质属实,其有寒、热两大类;少阳病属于热证、实证的范畴,反映了邪犯少阳,枢机不利,胆火上炎,灼伤津液的本质,相对于太阳病而言,其病位再里,热邪初化,但未至阳明病燥热程度;太阴病的性质,尽管其多属脾阳不足证,但亦有脾阴不足证;少阴病的提纲,是寒化、热化的共同提纲,其脉象应为“脉微、细”,从中断句,脉微而见单欲寐,则是寒化证的初期表现,脉细而见但欲寐,则是热化证;厥阴病为两阴交尽,具有阴尽阳生、极而复返的特点。 关键词:《伤寒论》;六经辨证;毕业论文; 实习期间我把《伤寒论》细读了一遍,现将自己读《伤寒论》的体会,简述如下: 1《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是辨病、辨脉、辨证、论治一线贯通的有机体系 关于《伤寒论》的六经实质,历代医家争议较多,提出了许多观点,计有经络说、六经分证说、气化说、经界划域辖病说、阴阳说、六经形层说、阶段说、三焦说、证候群说、正邪消长说、八纲
说、时空说、六病分证说、用控制论模糊识别概念分析六经说等等,可谓见仁见智,尽管观点不一,但都认为其属于一个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对临床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 《伤寒论》中早已建立了相关标准,构筑了祖国医学辨病、辨证、辨症论治相结合的临床体系,直至今日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如《伤寒论》的主要辨治体系,即今日所谓的“六经辨证”,实则即是辨病、辨证、辨症论治相结合的有机体系,此从各篇名称即可昭示。除少数理论论述及具体操作方法论述者采用“辨脉法”、“评脉法”、“伤寒例”等外,凡涉及治疗者,多采用“辨xx病脉证并治”名之,其包括了辨病、辨脉、辨证、论治4个方面内容,其有关诊断的辨病、辨脉、辨证3个方面,辨病、辨证自不待言,而辨脉之“脉”,实即指“症”而言,泛指疾病过程中患者所表现的单个症状或体征,初步建立“病”、“证”、“症”的诊断标准。在具体标准的制定上,首先将疾病分为六大种类,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各立提纲一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21、“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也”199、“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261、“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292、“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303、“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344。其所立六经提纲条文,即是“病”的诊断标准,在辨治过程中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在病的诊断标准下,又细分出诸多“证”的诊断标准,如太阳病中,又分为中风、伤寒和温病之证,分别制订了各
March ,2012 第25卷第2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Vol.25No.22012年3月 Journal of Chongqing Education College 收稿日期:2011-09-14 作者简介:赵献涛(1975-),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晓彩(1981-),女,河北广平人, 文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文艺学。 1914年11月26日,鲁迅得到二弟所寄书籍两束,其中有《文史通义》一部六册,同月的29日,鲁迅 “午后往南通县馆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这是鲁迅日记中对于《文史通义》的记载,从中看不到鲁迅对《文史通义》阅读情况,遑论影响了。但1933年鲁迅所写《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到文坛的斗争、谩骂和诬陷,就谈及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撝叔,如水火之不可调和。[1](P247)由此可知,鲁迅非常熟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因为《文史通义》里就有章学诚对于袁枚的批评文章。章学诚对于鲁迅的影响,陈方竞先生已经做了论述[2],笔者试加以补充。 一、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的影响 鲁迅乡邦文献的辑录与浙东历史学存在着密切关系,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方志,“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的著作。”[3](P256)浙东史学传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特征是“提倡方志学,推广方志这种社会史体”[4](P256)。浙江自古就有撰修方志的传统,《越绝书》不仅是浙江最早的方志,也是方志史上最早的地方志雏形。这个传统在以后的历史中延续,形成了浙江修志最为繁盛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被章实斋从理论上给予阐发,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到章学诚,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章 学诚在自己与前人撰修方志的基础上,在批判继承前人方志理论的基础上,对方志的性质、起源作了明确的探讨。 章学诚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地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5](P124)章学诚也明确了方志的作用。“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当然它的作用也就无异于‘国史’。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就要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能够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贡献。”[3](P263)“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6](P138)在阐释方志的社会功能上,章学诚很明显没有摆脱时代的限制,依然以传统的诗教来解释方志的作用。但只要把章学诚的理论还原到乾嘉学派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他的理论所具有的革新意义。考据学派编修方志的理论观点是“志以考地理”,将作为地方史的方志纳入考据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考证之学。继承浙东经世致用思想的章学诚反对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派,他毅然从经世致用的观念出发,认为方志同国史一样,具有维护纲常、裨益世教的功用。鲁迅辑录丛书,其目的与之遥相呼应。《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告白辑录目的曰:“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逸,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 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赵献涛,李晓彩 (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河北邯郸056038) 摘要:章学诚是鲁迅的乡先贤,对鲁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直接影响了鲁迅早期的辑录工作;章学诚的史学观念影响了鲁迅在读经读史问题上的见解,并对鲁迅杂览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鲁迅;章学诚;史学;影响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2)02-0088-03 88··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一 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
戴震专题研究资料
(一)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戴东原新理学思想探微——兼论其哲学体系诞生之背景 姓名:卓汴丽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哲学 指导教师:张怀承 20050501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引言和文献综述 外篇 内篇 第一章天道系统 第一节元气实体: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第二节对理学超验本体论的否定 第二章(人)性系统 第一节血气心知: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展开 第二节理欲之辨:戴震新理学体系的价值核
心 第三节对程朱派人性论的批判 第三章人道系统 第一节体情遂欲: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终点 第二节对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控诉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摘要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最后的杰出的代表。在中国学术史上,宋儒是“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而乾嘉诸儒又“得其制数,失其义理”。戴震不满二者学术各有偏废,于是将“制数”与“义理”结合起来,创建了一种融二者于一体的“新理学”。一方面,戴震针对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学说,继承并发展了张载“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体情遂欲”的政治哲学主张。同时,戴震也将“由训话而推求义理”的哲学研究方法应用至其哲学体系
当中,从而建构起考据学与义理学相结合的“戴震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值得关注的是,“由训话而推求义理”的哲学研究方法,是戴震创立的一种注重实证,讲究严密逻辑推理的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在戴震建构“新理学”哲学体系的过程当中,他通过对这一方法的灵活运用,重新分析定义了儒家在天道,人性,人道三个领域中的一系列传统哲学范畴,深刻地批判了宋明理学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和在实践上的危害性,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反理学的进步斗争。就戴震创立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本身而言,它又具有了三层代表意义。第一层,它代表了清代学术,尤其是清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即重考据、实证。第二层,它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后的重要代表。第三层,它代表了正统的儒家哲学的回归与创新(即建立了戴震“新理学,’)。 关键词:戴震,训话,义理(道),“新理学” (二)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余英时的明清学术史研究——以《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为例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 09-01-21 13:16:00 ] 作者:裴元凤编辑:studa0714 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 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的脉络,孤引之如下: 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 由此可知清代考证的兴起乃有儒学自身内部的原因。盖因“尊德性”发展到了极端不免流入“反智识主义”,各家各持己说不相上下,于是不得不征诸古本以定是非,走上“道问学”的道路。二者是儒学的两个方面,有其儒学内部的联系,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并不均衡。 书中章学诚是作为与戴震相抗衡的角色出现。余先生首先指出,这乃是出于后人的见解。在戴、章身处的时代里,时人均认为章学诚远远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然在章学诚自己的内心深处,“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 ,并就此一点展开了详细论述。实斋之所以自认自己能与东原并立乃在于他提出了与时人(包括戴东原)迥异的两个观点:一是经、史不应有高下之分,因为二者殊途同归,皆是入道的途径;再则是学问从入之途不限于考据一端,从“观其大意”入手,也能通于道。进而言之,章氏在清初“经学即理学”纲领的笼罩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一理论经过章氏多年的建设已成论证充分的完善系统。因而有了“六经皆史”的有力支撑,章氏遂有信心以“文史校雠”与其时“经学训诂”的领袖——戴东原相抗。然“实斋岁自视甚坚……但并世学人,包括他的桓谭——邵晋涵在内,却未必能同意实斋这种自我评价” 。所以他作《朱陆》篇,指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即指东原;而后撰《浙东学术》,“显然是要为自己在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中找一个适当的位置。这和《朱陆》篇认定东原之学系承朱子数传而后起,意思全相一致” ,由此一来,“南宋有朱、陆,清初有顾、黄,这才能衬托出乾隆时的戴、章并峙”,即从学术史上为自己的学说找寻脉络,以加强其在时人眼中
《伤寒论》之六经辨证 摘要:《伤寒论》一书,以六经为纲,八法为纬,辩证论治为法,贡献给了人类社会。自汉季问世以来,至今一千七百余年,被医者奉为经典,而用之不衰,其使用价值备受医家重视。时至当代,医学科学在飞速前进,而《伤寒论》之辩证论治体系,却仍不失为临床中治疗疾病的最好方法,六经辨证既重视证的变化,又重视人的本质。这正是我中华医学独具一格的治疗方法,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继承和发扬这一学术,正是中医学生所承担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一是《伤寒论》的医学源流,张仲景从哪些著作,哪些医家中获得的医学知识,又收到了当时社会的哪些影响。二是《伤寒论》的三阴三阳理论,张仲景在撰写《伤寒论》以及平时行医过程中都体现了阴阳变化的思想,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三是六经辨证的原理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字:《伤寒论》;六经辨证;三阴三阳;张仲景;辨证论治 一、《伤寒论》的医学源流 1.《伤寒论》的几种重要学术渊源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除此之外,仲景还借鉴了哪些著作呢? (1)《汤液经》 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中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又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而《伊尹汤液》在三国之末齐梁之前已经遗失,据《针灸甲乙经》推测,皇甫谧亲见并阅读《伊尹汤液》,而且还曾亲见“大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他对比二者,得出结论:《伤寒论杂病论》是仲景在《伊尹汤液》一书基础上“论广”而成。张仲景正是在《伊尹汤液》一书进行研究和条理化,并结合自己的治疗经验并补充一些内容,撰成此书。 (2)《黄帝内经》 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一般认为,仲景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郑樵,生活于南北宋交界时期,后世对他的《通志》评价不高,多认为“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①”。而六个多世纪后的章学诚却在其毕生心血之作《文史通义》里单列《申郑》、《释通》、《答客问》等诸篇为郑樵辩护,并大加赞赏,《申郑》篇云: 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② 目前学术界对郑樵、章学诚二者的单独研究众多,而二者的比较研究却鲜见。本文不自量力,欲就此问题稍尽绵薄之力。 一、实学之发展 郑樵生平勤于著述,自述“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③”,但流传下来的书很少④,关于他作 ①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卷五,47页 ②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8年第一版,卷五,46页 ③郑樵:《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3,此书我用的是《四库全书》电子版,列于集部四,别集类三
《通志》的原因,如今我们只能从他仅存的几部书中略窥一二。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纲法纪。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①按郑樵作《通志》,很大一部分原因自然是贯彻其“会通之意大矣哉②”的思想(详后),但郑樵对空言的不满和对实学的推崇也是推动他作《通志》的原因。“实学”思想在郑樵的著作里多有体现: 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③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飨,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④ 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⑤ ①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②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1页 ③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④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4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
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经毕沅同意,仿朱彝尊《经籍考》体例,开始编纂《史籍考》。但不久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史籍考》的编纂中断。乾隆五十五年,章学诚去武昌依毕沅从事编纂工作,继续编纂《史籍考》,还主修《湖北通志》,参与《续资治通鉴》的编撰工
大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 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谈话,《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先后出版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本。以下文字为池田大作为《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出版20周年而作。 “可能我们的对话不惹人注意,但是将永远留存下去。”那时我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已4年。在东西冷战的旋涡中,各种既成势力对我的倡言施加压迫。然而,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中国和日本非缔结友好不可,这就是我的信念。 汤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这种行动。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说:“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浅薄的指责跟本质毫无关系。我们还是谈本质问题吧。”我们谈论的本质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就是探究“何谓人”“何谓社会”以及“何谓生命与宇宙的本质”。这就汇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 博士用他那无以伦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中展开的人类史,遥望未来。博士集毕生学术之大成所说的警世词句须臾不离我耳畔。对于哲学告缺、迷失方向的现代世界,那些珠玑话语今天也深刻提示着根本价值观,即“为了创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么”,“为了可持续的繁荣,人类应该怎样生存” 对谈跨越了两年,总计10天,长达40个小时。我曾问:“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我本人曾10次访问贵国,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优质顺应社会变化、切合时代而改变形态,绵绵搏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性尝试,香港、澳门的历史性回归等,导向成功的动力当中也生动呈现“中华思想的优质”。现在,贵国所切实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有汤因比博士从贵国发现的“罕见的政治、文化性统一的技术与经验”作后盾的21世纪的先驱性行动。 博士一语道破,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正如博士所预见的,贵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对于我前面的提问,汤因比博士还回答:“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 人类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复兴,这也是博士托付给我的文明课题。博士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对话”。 以下为书中〈中国与世界〉一节的内容(节选): 池田博士说过“作为将来的一种可能,中国也许会统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地化”。这有什么根据呢?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郑樵,生活于南北宋交界时期,后世对他的《通志》评价不高,多认为“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①”。而六个多世纪后的章学诚却在其毕生心血之作《文史通义》里单列《申郑》、《释通》、《答客问》等诸篇为郑樵辩护,并大加赞赏,《申郑》篇云: 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②目前学术界对郑樵、章学诚二者的单独研究众多,而二者的比较研究却鲜见。本文不自量力,欲就此问题稍尽绵薄之力。 一、实学之发展 郑樵生平勤于著述,自述“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③”,但流传下来的书很少④,关于他作《通志》的原因,如今我们只能从他仅存的几部书中略窥一二。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纲法纪。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⑤ 按郑樵作《通志》,很大一部分原因自然是贯彻其“会通之意大矣哉⑥”的思想(详后),但郑樵对空言的不满和对实学的推崇也是推动他作《通志》的原因。“实学”思想在郑樵的著作里多有体现: 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⑦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飨,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⑧ 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⑨ 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⑩按郑樵认为有些学问必须要亲身实践方能明白,而且学问亦要付诸实用。 章学诚《文史通义》开篇则曰: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 钱穆先生对章氏的“六经皆史”说有过解释,大意指六经皆三代之史,各守专官之掌故,并非圣人有意要作文章,后人尊崇三代,于是便尊崇所谓“六经”。钱先生引章文: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于空言。 古人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于是宾四先生说道“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捨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 ①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卷五,47页 ②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8年第一版,卷五,46页 ③郑樵:《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3,此书我用的是《四库全书》电子版,列于集部四,别集类三 ④参见顾颉刚:《郑樵著述考》,《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2091页 ⑤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⑥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1页 ⑦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⑧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4页 ⑨郑樵:《昆虫草木略》序,《通志二十略》,1979页 ⑩郑樵:《图谱略?索象》,《通志二十略》,1826页 11
伤寒论六经辩证系统图解 伤寒六经辩证法,无论在辩证方面或治疗方面,都有着极完整的系统性和系列性。所谓系统性,就是数百个伤寒的具体证候,以病位的、病性的同一性组成六个病理阶段,即六经。六经又以同一的病因组成一个伤寒整体,即伤寒病理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伤寒六经病理阶段过程中的若干具体证候之间纵的病理关系,形成了六经辩证的系统性。所谓系列性,即数百个伤寒具体证候,以病理趋势的特殊性相区别,以病因的同一性而组成一个伤寒证候的系列,又以同一的病性而组成阴性证系列与阳性证系列,又以病位病性的同一性形成六经证系列性。六经各证候之间的横的病理关系形成六经辩证法的系列性。从其系列性说,伤寒过程依据器官功能盛衰分化为阴阳两类证候。阴证类与阳证类又依据表、里、气机病位而分化为六经。六经各经中又依据不同的病理趋势分为若干具体的证候。从伤寒一病分六经,六经又各分为若干具体证候,都是以病因、病位、病性相联系,又以病位、病性相区分,形成一个辩证系统。辩证之目的为治疗。由于伤寒病为一种生物病原体所引起的病理过程,因而以“因势利导”为治疗的主导思想。从这一治疗思想出发,对伤寒阳性过程以祛邪为治疗原则,对伤寒阴性过程以扶正为治疗原则。在三阳病中,由于不同的病位有不同的功能特性而有不同的祛邪法;在三阴病中,也因不同病位有不同的功能特性而有不同的扶正法。如太阳为阳性表病而用汗法祛邪;阳明为阳性胃肠病而用吐法、清法、下法祛邪;少阳为阳性气机病而用和法;少阴病为阴性表病因而用助阳温经之扶正法;太阴病为阴性胃肠病而用助阳温里法扶正。祛邪法分汗、吐、清、下、和诸法;扶正分助阳温经、助阳温里、回阳救逆诸法。如此 形成一个伤寒辩证治疗系统。略如下列图表:?????上述是伤寒六经系统与治疗法则。以下为六经辩证治疗系统的各经证治。?(一)太阳经证治系统?在太阳病理阶段,由于是表病位的阳性过程,体表组织在抗御反应中表 现着功能亢进与代谢增高,体表组织因其功能特性而通过排汗的代谢机能以祛除病理物质,所以有发热自汗出与发热汗不出两种向外趋之势态。仲景根据太阳这种外趋之病势而因势利导用汗法祛邪。但汗法据自汗病势用解肌法,以桂枝汤为主方;据无汗病势用发汗法,以麻黄汤为主方。自汗病势之各具体证候因有太阳自汗病势的同一性,又各有其特殊性质,所以皆用桂枝汤加减法治疗。无汗病势之各具体证候也因有着太阳无汗病势的同一性及各自的特殊性质,也皆以麻黄汤加减方治疗。桂枝汤加减方共十五个都以桂枝为主体,都以脉浮、发热恶寒、自汗为病理依据。麻黄汤加减方包括葛根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等四个,都以麻黄为主体,都以脉浮、发热恶寒、无汗为病理依据。这样组成一个伤寒太阳辩证治疗系统。但在太阳病理过程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造成这样那样的并发或继发证。这些并发或继发证因为不是伤寒病因引起的,所以属杂病的范畴。如蓄血、水逆、热喘、水饮、虚烦、悸气、结胸、心下痞、胀满、停饮、滑脱等证。太阳阶段的辩证治疗系统略如下表:??(二)阳明经证治系统 ?在阳明病理阶段,由于肠胃的生理特性(如胃的呕吐和肠的排便亦为保护和防御反应),在抗御过程中,表现为上越、里热、下夺三种趋势。仲景据上越趋势而用吐法,以涌吐而祛除病理物质;据里热之势而用清法,以通肠来祛除里热;据下夺之势而用下法,以排便来祛除病理物质。上越、里热、下夺以胃家实为共性,上越以愠愠欲吐,里热以汗出而渴,下夺以不大便为各自病理特性。吐清下三法皆祛邪法,以邪之所在不同,因其所趋之势而祛除之。在阳明阶段中亦有并发或继发证,例如黄疸、热入血室、